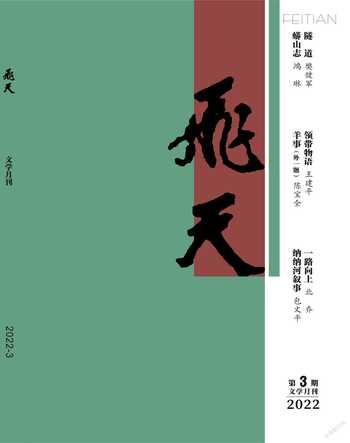沉疴中年的修行與自渡胡笑梅
中年,是一個沉重的詞語。
工作上“十年媳婦熬成婆”,早無新鮮感和斗志,因尚未退居二線不能懈怠,只為養家糊口無奈堅持。上有老人要贍養,下有孩子要撫養,經濟上壓力山大。伴侶如室友,數十年的煙火日常磨滅了所有的激情,彼此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情感上無所寄托,精神上無法溝通,身體器官也出現各種程度不同的病痛和罷工。
如果,更年期綜合癥是生理性的,尚有藥物可以治愈;那么,中年綜合癥是心理性的,只能靠修行和自渡。也許,中年畫家會揮毫潑墨,音樂家會引吭高歌,舞蹈家會水袖清影,旅行者會寄情山水,中年詩人自然會用生花妙筆,在語言文字的騰云駕霧、神游八荒里完成修行與自渡,這也是最簡單、最生態、最易行的方式。
詩人李滿強很聰明,很睿智,就像當年他用最擅長的詩意文字《畫夢錄》一樣,博得同齡人的喝彩無數。如今,他在經歷了家庭和個人的種種變故之后,痛定思痛,對人生的上半場進行沉淀、反省、總結。以“一個在生活的夾縫里側身匍匐的人”的視角,客觀描摹現實,反映社會,觀照人生,在自我治愈中年沉疴的同時,也鼓勵幫助同樣“在生活的泥潭里掙扎的中年群體”(體育場里暴走的中年男人,半夜在QQ上糾結的女鄰居,《就診記》中的抑郁癥患者“現在已是中年,我的口袋里/有著足夠的金幣,掌聲和玫瑰/我的父母健在,兒女成雙,可我/還是覺得空空蕩蕩,半夜會突然驚醒/在未知的道路上狂奔,無法停下來!”)砥礪前行。這,是李滿強寫作的初衷,亦是《螢火與閃電》的象征寓意。
人生天地間,皆如滄海一粟,山間草芥,螻蟻蚍蜉。在浩瀚的夜空中,螢火半點,極其微弱而渺小。但,萬千螢火,就亮如燈火,億萬螢火,就燦如閃電。甚至,有時候,身處迷茫逼仄的人生困境之中,一丁點微不足道的螢火給予人前程的照亮,內心的震撼,精神的啟迪,也許就是一場驚天動地的電閃雷鳴(例如,《暴雨中的事物》“迎著閃電的方向……這道德和法律無法限制的時刻/總有一些事物,需要懺悔,大聲哭泣/總有一些事物,會因為沖刷和擊打/而獲得救贖與重生。”相比一帆風順的人生,千錘百煉,烈火重生,鳳凰涅槃,破繭成蝶的人生更值得經歷與回味,更值得期待與贊美,因為它更富有價值和意義)。
相比《畫夢錄》的年輕氣盛,意氣風發,激情澎湃,張狂浮躁,個別的大詞假腔,《螢火與閃電》則顯得低調內斂,沉穩從容,舒緩平和,韜光養晦,用詞精微更接地氣(例如,《夢中三日》“余生陡峭”,將未知的余生比作高聳入云、連綿起伏、“一山放過一山攔”的峰巒,溝壑縱橫,險峰叢生。四兩撥千斤,給予讀者無限廣闊的想象空間)。此種詩歌風格的變化,并非李滿強刻意為之,而是年齡與心境使然。辛棄疾的《丑奴兒 書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是此處最恰切的腳注。不惑之年的李滿強,去掉了浮夸綺麗,去除了媚俗迎合,其人其文愈發返璞歸真,感情更加率性,表達更加質樸,而意蘊則如靜水流深,更加醇厚雋永。大道至簡的文字,初讀,雖語不驚人,有點兒像白開水,再讀,卻富有哲理(例如,《線索》中:“此時,地球的某一個地方/一顆炸彈,正在落下/無數水滴一樣的人/就要永遠陷入沉默——在偶然和必然之間/在活著和死亡之間/水龍頭和它的滴答聲,只是/被我虛構的一條線索”,觸景生情,推己及人。提醒很多身處和平年代、富裕國度的人們,不要忘記在地球的另一個地方,仍有許多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且不說解決溫飽問題,就連生命安全也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每天命懸一線,朝不保夕,他們根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先來”),耐人尋味,發人深省,比各色花里胡哨的飲料更能解渴。
畢竟,真情實感才是詩詞文賦的第一要義。正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所寫:“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意。”誠哉斯言!中年的李滿強,已經過了“炫技”的年齡,也不再狹隘地沉浸在個人的小情小愛、小怨小恨、小格小調之中,他開始追尋活著的意義與答案,為內心的憂傷與熱愛尋覓一處精神的落點,他開始主動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蒼耳》“時隔三十年/我才消除了對一株植物根深蒂固的敵意”,這是人與自然的和解,是人類自身的成長),關注人的命運和未來(《答案》中“活著,就是不斷跨過每一個坎/就是和自己,打一場又一場的戰爭/但沒有勝利可言”,在重大疾病和災難面前,人類手足無措,除了接受和共處,無計可施)。如此,便水到渠成地開闊了寫作的視野,厚重了寫作的內涵,提升了寫作的格局,這也是一個詩人走向成熟的標志之一。
回顧中國新詩的百年征程,在經歷了二十世紀20-30年代的啟蒙,80-90年代的狂歡與井噴之后,近10年,日漸歸于沉寂與蕭條,所以,能夠自始至終堅持寫作至今的詩人,都是叱咤詩壇的英雄和勇士,其精神可嘉、可歌、可泣、可嘆。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對李滿強而言,“詩歌如同一條隱秘的河流,數十年來,一直在我身體里穿行,它讓我開心、愉悅、興奮,但不癲狂;它讓我憂傷、冥思、流淚,但不絕望。我選擇了這種方式,也迷戀這種方式。在閱讀和寫作中,我完成了自我的救贖,也獲得了內心的安寧。”(《自序》)無疑,自創作伊始,詩歌就成為李滿強與自己、與他人、與世界對話的路徑,現如今,歷經生活風雨捶打之后,深諳“藏鋒不露勢,口訥不激辯”的中年李滿強,更把詩歌當作修行、自渡、渡人的方式。無論從生到死,從陽到陰,還是從弱到強,從小到大,從此岸到彼岸,其目的都是為了直面現實,遇到更完美的自己,一起抵達更幸福的歸宿。
誠然,“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網絡作為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其全方位的普及,給詩歌生態帶來了諸多根本性、全局性的變化。挑戰亦是機遇,為詩歌提供了多元、開放、自由、豐富、活力的創作沃土。“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那么,詩歌寫作如何與時代同頻共振,如何呼應民情人心,如何與生活摩擦互動,就不僅是李滿強,更是“李滿強們”,應該大膽深入思考、試驗、探索并積極加以實踐的研究課題。
記得,亞馬遜河流域的一只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以引起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誰敢說幾只螢火的光亮,不會集結成一道炫目的閃電,融匯為無垠的星辰大海呢?
3558500338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