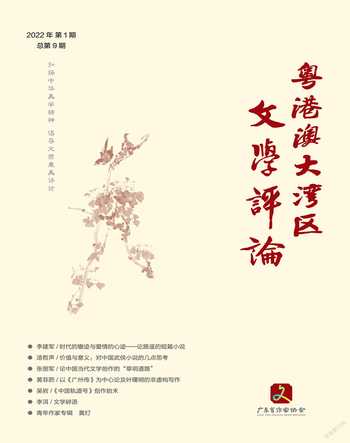歷史文化維度中的城市傳記與近現代史書寫
黃菲菂
摘要:《廣州傳》是一部重要的非虛構“城市傳記”。葉曙明從城市形態、商業形態、文化發展以及市民社會變遷等四條脈絡梳理了廣州兩千多年的城市發展歷程。作品在豐富史料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有價值的歷史判斷,是廣州城市傳記的標高之作。在近現代史的書寫上,葉曙明致力于尋找重要歷史事件與廣東地域和人物之間的關聯,確認廣東在國家與民族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與價值。葉曙明的非虛構寫作有超越文學視角走向文化文本的自覺,為非虛構文體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與可能。
關鍵詞:城市傳;廣州傳;近代史;非虛構寫作
一、城市傳:廣博的史料與問題意識的自覺
有著千年歷史演進的城市,其身上承載的人類文明興衰,早已使之成為歷史的標本與文化的符號,永遠刻進了人類文明史進程。歷史學者孜孜不倦地為后人記載和描摹著這些城市文明的狀貌,以地方志和歷史文獻的方式長久留存。后人也總是聚合起這些記錄的片段,以形成更完整的城市記憶。近年來,一些非虛構寫作者悄然開始了“城市傳記”的主題書寫,但與歷史學著作不同的是,這些文本一方面建立在歷史史料之上,一方面又多了一層文學的視野。這樣的城市傳就在歷史真實與個體審視之間有了豐富多重的文化意蘊。從整個非虛構創作來看,走入我們視野的主要有英國彼得·阿克羅伊德的《倫敦傳》,國內邱華棟的《北京傳》,葉兆言的《南京傳》,以及葉曙明的《廣州傳》。
為城市立傳頗為不易。在歷史上舉重若輕的古老城郭都一定有著自身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只有尋找到這些文明的密碼,才能把握住這座城市的靈魂。與北京、南京作為歷代都城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不同,廣州偏安嶺南,遠離中原,形成了具有自身獨異性的經濟和文化形態。以《廣東新語》《番禺縣志》《廣州市志》《廣東通志》等為代表的諸多歷史文獻從地理、文化、宗教、貿易等角度記載了廣州城市發展脈絡。但真正能夠涵蓋廣州兩千年建城史物質形態與精神形態演變歷程,又能被普通大眾所接受,兼具學術性和可讀性的廣州傳記,當屬葉曙明的這部《廣州傳》。《廣州傳》全書上下兩卷,皇皇60萬言,共十一章,52小節,將從蒼茫南海間的一片礁石到新中國成立曙光初現這兩千年廣州的興衰囊括其中。作者從城市形態、商業形態、文化發展、市民生活變遷這四條線索架構起全書脈絡,一座有古老時光印記,又可觸摸日常生活紋理的南方城市在宏闊的史料與微茫的歷史細節融匯下開始生動起來。
《廣州傳》是歷史文化維度下的全局性寫作。葉曙明研究廣東歷史文化多年,被稱為“廣東文化的代言人”,此前就已出版過《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三卷)、《廣州辛亥年》《廣州舊事》《廣州河涌史話》等多本廣州歷史紀實之作。作者對廣東歷史文化的了解全面且深入,這使得他能多維度構筑起廣州社會全貌。
能夠調動的文史知識越多,內容就越豐厚充實。作品開篇第一小節“山與海之間”就是一個知識完備的例證。作者從“昔者五嶺以南皆為大海,漸為洲島……”的記錄中確認新石器時代南海上的這一葉島礁;又從“自白云蜿蜒而來,……至城北聳起為粵秀,落為禺,又落為番”的記載中考證番禺地名的由來;登臨番、禺二山,越秀山,白云山,以考察重要山脈的地理形態;提出“越族”不是一個民族,而是指向更寬泛的族群這一新觀點;對越人房屋、穿戴、器皿、出行工具都做詳細描述;更對“五羊神話”這一流傳千年的故事做出多個版本的考證,尋找神話與廣州被稱為羊城的歷史由來。
在更微觀的細節上,作者又興致勃勃地對一個個地理名詞做出詳細考證。廣州人一直把穿城而過的珠江稱為“海”,大家認為這是方言的說法,并非指真的大海。葉曙明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古詩文上尋找佐證:東漢班固在《漢書》中說番禺(廣州)是“近處海”;三國東吳中書丞華覈在上表文書中稱廣州“州治臨海,海流秋咸”;唐代詩人高適吟誦廣州“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宋代詩人楊萬里詩云“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這些詩詞文章是這樣的真實可信,又是那般的浪漫可愛。“海”這個字既具有了地理意義,又多了一份遼遠的人文想象。文本中這樣的段落還有很多,盡顯作者史家誠懇和文人情懷。
就全書而言,作者提供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浩繁史料又在作品章節設置和文本內在結構的考究之上得到了有效整合。作者雖按照朝代順序展開敘述,但并不簡單依從朝代更迭劃分城市演進階段,而以廣州經濟文化自身演變的重要節點作為章節劃分依據,歷史階段劃分的邏輯自成體系。諸如:從上古時期到東晉是廣州城市形態初步形成的階段,因此為第一章“城的誕生”;“海上絲路”一章集中展示隋唐時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盛景;南漢在歷史朝代中并非鼎盛時期,但卻是廣州城市發展的快速階段,因此作者用“奢華年代”做專章講述。作者對每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都做論述,形成完整的歷史橫斷面,但又有的放矢,對一個時期最重要的發展成就做深度書寫,以此突出廣州在各個歷史事情的典型面貌。比如,宋代以降,是廣州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宋代以降,廣東文風大開,不僅出現了學問大家,民間書院也日漸興盛,作品以“厓山之后”“鳶飛魚躍”兩章講述了嶺南文化之繁茂。看似簡單的時間分段,內在顯示的其實是作者的獨立學術判斷和問題意識。浩如煙海的看似毫無關聯的史料就在這縱橫交錯的布局之間形成清晰可見的歷史脈絡。而廣州城也就沿著這歷史的脈絡不急不緩地從千年前走到了今天。
在對城市形態、商業發展、文化演變、生活變遷這四條線索的并行書寫上,作者對商業發展著墨較多。這是因為,廣州在農耕與海潮的共同培育下,很早就發展起濃郁的商業文明,滋養著煙火可親的市民生活,至今依舊是我國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城市之一。
在“海上絲路”一節,作者將廣州重商的傳統上溯至秦代南征,《資治通鑒》中記載秦始皇“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南下商人成為廣州人中最早的經商者。但因南嶺阻隔,南北的旱路交通并不通暢,廣州在先秦時期就“向海看”,漢代已開創海上貿易通道,商船已可抵埃及和羅馬。絲綢精致華麗,價格昂貴,羅馬人視如珍寶。驚濤駭浪之中的往來貿易,逐漸形成海上絲綢之路。至南朝,廣州的海貿已成為南梁的重要財政支柱;至唐朝則達到空前規模,在“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這樣的詩文中,可以想象彼時絲路之盛況;到宋代,“全國每年有三千多艘新造的海船、江河舟船下水”,其盛狀令人驚嘆。我們再看“鎮海樓下”一章中的繁華廣州。明代政治和學術上的鉗制反過來激發了民間文化藝術的繁榮,此時廣州城的繁華勝過秦淮數倍。瓷器、絲綢、繡品、珍珠等奢侈物品由海上絲綢之路運抵歐洲;花農月下采花,曉色波光之間,碼頭上泊滿花船,香滿珠江;嚴謹考究的衣服剪裁、打破禁令的婦女穿戴,各色零食甜品、酒香茶濃,酒樓林立,處處笙歌。
但作者并不抽離出來簡單寫商業的繁榮,這背后總有個歷史的厚重面影。在明代城市繁榮的背后,作者隱隱感受到了隱憂:“這種繁華景象,還能維持多久?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去想。在遙遠的北方,后金胡馬長驅,連陷沈陽、遼陽,明軍在廣寧之戰中大敗。北方難民,杖履相從,開始向南逃亡。這一場景,讓天性敏感的讀書人,驀然想起殘唐五代、南宋末年那些兵荒馬亂的歲月,內心充滿不祥之感。”就在這歌舞升平的同時,北方的金戈鐵馬傳來了皇朝的亡音,城市也就在這戰爭與和平的轉換之間走過滄桑千年。
商業的繁華必然造就市民生活的富足,生活的滋味,吃就是第一條。今天我們依舊說“吃在廣州”,原是這一方人養成的生活方式。明代,廣州人就把魚生吃得高級,“草魚、鯇魚或是鱸魚切成薄片,以呈現雪白質感為佳,不能有一絲血跡,拌以腌姜絲、蔥絲、酸蘿卜絲、香芝麻、檸檬葉絲、椒絲、蒜絲等調料,食之爽口美味。”廣州的味道就全在這魚生的咂摸里了。也正是這舒坦的生活讓廣州人養成了淡然舒緩的市民性格,“‘講古寮里的講古佬,每天下午在那里說書,聽眾也還是那些販夫走卒、屠兒咕哩,為口奔馳了一天,精疲力盡,就等著講古佬把茶壺往桌上一放,把香點燃,再把驚堂木一拍,說一句‘閑文少敘,書接上回……,一天的疲勞就忘記了。”商貿往來的傳統,生活方式的安逸,使廣州養成了包容、開放、務實、平和的城市性格。這里接納幾乎所有的到來者,不論是戰敗后茍安嶺南的北方朝廷,還是躲避戰亂的中原百姓;有貶謫此地的朝廷官員,也有波斯、大食前來經商的異域蕃客。到來,即為廣州人。大家相安無事,彼此接納,各地文化就隨著主人一起流淌在民間,接續共存。
在傳統的歷史視野中,嶺南從來都是中原文明的被動接受者,似乎嶺南的每一次進步都得益于中原文明的南遷,嶺南文明史,如同一部接受中原教化的歷史。葉曙明對此不能認同,中原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心,有著天然強勢的話語權,文化傳播確實給嶺南帶來了重要的文明氣息,但并不是沒有中原文明,嶺南就處在蒙昧落后的蠻荒狀態,這種長期的固化認知與因權力而產生的文化優越感有重要關系。其實,早在新石器時代,嶺南就結合地理、氣候、耕種等方面的特點,產生了適合自身特點的各種生產生活的工具。對此,作者通過大量的考古遺存證明了嶺南人有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智慧,比如,先秦遺址出土的陶器,不僅實用,而且美觀。每件器皿上都配上復雜精美的紋飾,既有質樸醇厚的味道,又顯示出典雅的審美眼光。不僅如此,廣州還在農耕文明之外,面向海洋開創了獨具優勢的一面,“廣州與南洋的貿易航線,早在先秦時期已經建立”,發展海外貿易,這是中原城市無法企及的。
因此,作者對文明與地域的關系做出這樣的論述:“帝王都的聲教,并不是文明的唯一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以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創造出來的。這才是恒久的、最基本的文化之源。”提出了自己對嶺南與文明關系的價值判斷:“天地間自有人類以來,廣州人便生于斯,長于斯,耕耘樹藝,漁海樵山,從石器時代走向青銅時代,文化一天天茁壯成長。”寫盡一座城市兩千年的歷史,葉曙明慨嘆道:“那些駕著扁舟,擂著銅鼓,出沒于江滸河汊的羽人,與眼前滿街衣著光鮮,拎著大包小包,帶著歡聲笑語走過的廣州人,重合得起來嗎?他們是同一片土地養育的兒女嗎?是他們前赴后繼地創造了這座城市的嗎?是的,就是這片土地,就是這些人們。”作者將以廣州為中心的嶺南放在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之中考察其歷史定位與文化價值,文本也就超越了史料的鋪陳,獲得了更為廣博闊大的思想和文化意義。
至此,作者融匯考古、地理、文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方法,沉潛于浩繁的史料,建構起一個真實可信的廣州;同時,又堅守自己強大的學術意志,將自身新的思考和認知投射到歷史敘事之中,提供給大眾一個可思考、可想象的廣州。從這樣的書寫中,我們看到了非虛構寫作從個體性走向公共性的自覺與可能。但令人遺憾的是,新中國成立至今70余年的城市歷史,《廣州傳》沒有涉及。這是廣州城市發展格外重要的70年。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給廣州帶來了和平與安定,給百姓帶來了獨立與尊嚴;珠江潮起,廣州更是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幾十年間取得的發展成就令世人矚目。如果把這一歷史階段納入寫作,《廣州傳》才是更完整的廣州傳,我們對此抱有期待。
二、近現代民族歷史的地域化書寫
除了城市傳記,葉曙明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非虛構書寫也成績斐然,有《山河國運:近代中國的地方博弈》《1911,一個帝國的光榮革命》《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圖說香港抗戰》等代表性著作。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屈辱史,也是贏得民族獨立與解放的抗爭史。從鴉片戰爭、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再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些近現代的重大歷史事件都被記錄在無數歷史與文學著述之中。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對它們進行再書寫都是有難度的,選擇何種視角觀照并以主體性介入歷史敘事,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作品的區分度和價值感。葉曙明選擇以廣東為地域中心,觀照這片地域與中國近現代歷史之間的關系,以確認廣東在國家與民族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與價值。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繞不開“五四”。“自從發生五四運動以來,它就不斷被述說。”但“五四”仍需要“被述說”,葉曙明的《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一書就試圖把五四運動與廣東的重要歷史人物關聯起來考察,以闡釋一方地域與“五四”的深刻關聯。
歷史的魅力在于真實,非虛構寫作恰是基于歷史和現實真實的寫作,這就要求寫作者尊重并選擇那些真實的歷史細節。為了獲得最大程度的歷史真實,葉曙明考究諸多史料,援引重要人物回憶和報刊記載,為大歷史脈絡填補鮮活生動的肌理。五四運動中的政客、軍閥、教授、學子、警察各色人等均出現在作品中,他們以自身姿態參與了這個重大歷史事件。這部分真實呈現,為我們對“五四”現場的感知增添了豐富的細節。在非虛構文體求真求實的規范下,作者以“故事化”的方式為大眾講述著“五四”風云,易讀易懂。這就區別于一般歷史著述的深奧和學理性,更符合普通大眾的閱讀期待。近年來,伴隨著讀者閱讀和接受知識方式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一種叫“公共史學”的歷史研究類型,主要是指“讓學院外的人們對歷史學家的職業和史學方法產生興趣”[1]。從這一角度而言,葉曙明的這一著作可看成是“公共史學”在有關“五四”歷史敘事中的一個成功文本。
非虛構寫作需要基于真實,但僅描摹或呈現出客觀真實則遠遠不夠。寫作者對這些材料進行審視和判斷,以個人思考介入客觀真實,并表達出自己的歷史觀和社會理想的過程,則是非虛構寫作中作家主體性表達的重要環節,葉曙明的寫作表現了這種非虛構寫作的態度和能力。在《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中,他將五四運動置于晚清、民國這一更廣闊的歷史語境中,對這一時期歷史人物與時代輿論做細致剖析,重新思考其發生的原因。他認為公車上書與戊戌變法第一次把知識分子的訴求引向國家政治制度改革方向,涉及“體”的問題,而之前的變革皆未跳出“用”的范疇。因此,他將晚清的公車上書視為“五四”時代的起點,往后延伸到“五四”核心人物的終結。同時將廣東作為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歷史地域來敘事,把廣東人梁啟超和陳炯明看成五四運動的起點和終結。他認為戊戌變法是五四運動爆發的深層基因。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化運動主將接受西方現代思想,懷抱著制度和國民性改造的理想,積極推動社會啟蒙。盡管他們在后來思想分歧下分道揚鑣,但他們啟蒙和救亡的社會理想是一致的。此外,作者對陳炯明這一歷史人物有著自己的認知。陳炯明在廣東禁煙、辦大學、辦平民教育、推行自治運動,是一個熱切實踐新文化運動理念的人。“他的成功,是新文化運動的成功;他的失敗,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失敗。”葉曙明從人物初心和實際作為的角度對這一人物給予了較多的同情和理解。
歷史是復雜的,當我們置身于龐雜的歷史現場時,通過對歷史事實的分辨,得出自己的歷史感受和判斷不僅是重要的,而且也以其生動的歷史細節和新的歷史認知構成對宏大歷史敘事的精彩補充。這種貫穿著探尋真實和主體性介入的非虛構寫作態度,給歷史敘事提供了諸多新的思考生長點。
在某種程度上,葉曙明的非虛構歷史書寫與新歷史主義有相似之處,他們在史實上構建起自己的歷史觀和歷史書寫維度,形成一個融合史學、文學、社會學龐大內涵的跨界文本,從而呈現出多維度的意義,它既是客觀上的近現代史,是葉曙明個人視野中的近現代史,也是廣東地理上的近現代史。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戰史的書寫上,葉曙明把香港抗戰史納入關注視野。香港抗戰史是全民族抗戰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圖說香港抗戰》一書真實呈現了香港抗戰的悲壯與慘烈,茫茫波濤之上,神州北望,游子歸家的心情從未改變。也恰恰是這份游子的屈辱和孤獨,才更讓他們懂得祖國母親的意義,有一份更深切的赤子之心。經濟上,香港是戰時中國進出口軍用物資的重要口岸;文化上,香港是宣傳愛國思想的陣地,著名電影人蔡楚生推動進步電影,《最后關頭》一經播出,“一定要把侵略者驅逐出去”的口號聲震寰宇;軍事上,香港軍民頑強抵抗,決不投降。香港和香港同胞以自己的方式為全民族抗戰付出了巨大犧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完成香港抗戰書寫,才能從更廣范圍內形成全民族抗戰書寫的格局。由此,《圖說香港抗戰》有極其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歷史意義。
歷史遠去,但對歷史書寫者而言,這是歷史,也是現實。作者在客觀敘事上所張揚的主體人格和歷史判斷,無不寄寓著現實的出發點和當代性。我們從歷史人物和事件身上找到人類進步的經驗,最終是為了回答當代的問題,正所謂“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2]。朱光潛先生在《克羅齊的歷史學》一文中做了恰當的解讀:“一切歷史都必是現時史……著重歷史的現時性,其實就是著重歷史與生活的連貫。”[3]換言之,只有在現實眼光的審視下,在尋求現實意義的指歸下,歷史才獲得歷史性和當代價值。
三、走向“寬闊的寫作”:非虛構寫作的方向與可能
在對葉曙明系列非虛構寫作的探討上,除了思想內容上的論述,似乎還可以做一點非虛構文體上的思考。2010年,《人民文學》發起的非虛構寫作計劃,意在“探索比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更為寬闊的寫作,不是虛構的,但從個人到社會,從現實到歷史,從微小到宏大,我們各種各樣的關切和經驗能在文學的書寫中得到呈現”。[4]報告文學對現實的直接和深度參與決定了其從集體的、時代的宏觀視角去考察現實與歷史的寫作立場,并采用與此對應的宏大敘事手法,某些個體的、細微的、民間的生活因此有所遺漏。這就給非虛構留下了寫作空間,這也恰恰是以上主編這段話的重要意旨,即試圖建構起區別于報告文學在社會性和公共性文體屬性框架下形成的宏大敘事,形成從個人經驗、個體視角出發考察社會人生的寫作范式。同時,“‘非虛構寫作是在虛構寫作面臨困難的現實語境下興起的,其核心內容是讓更多作家走向民間,走向這個時代豐富多彩的內部”[5],這表明,非虛構寫作正是在“真實”顯示力量、“虛構”遇到危機的語境下被倡導的。虛構文學對龐大現實的呈現和闡釋能力日漸削弱,與大眾的聯系更為淡漠疏遠,因此希望通過非虛構的方式介入部分現實,重新建立起與時代和人生的聯系。
以《梁莊》為代表的系列非虛構作品推出后獲得了讀者青睞,作品中的底層敘事,讓作品迅速凝聚了人心,并一度成為非虛構寫作的范本,被后來者模仿。但作品卻存在寫作倫理上的危機與困境。作品中包括“梁莊”在內的地名及人名都是虛構的,故事在原型基礎上經過了虛構的加工,作者在敘事上也刻意營造較為傷感的氛圍,這樣的所謂非虛構,最終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給讀者一個真正的中國鄉村社會實景呢?我們知道,大眾認為在非虛構寫作中找到心靈的共鳴,是他們以為看到了“真實”。作品以真實的名義吸引了讀者,卻又違背了真實的原則;貼上了非虛構的標簽,又不承擔真名實姓書寫的風險。在非虛構作品中,這已是普遍存在的問題。還有,個人化應該把握到什么程度才合適,過度個人化會違背非虛構走向“更為寬闊的寫作”的初衷嗎?非虛構寫作,應恪守真實,遵循“誠實寫作”(馮驥才語)的原則。筆者認為,除了事件、材料、細節的真實,作家還應當誠懇并有勇氣寫出這些真實,以及敘寫問題的動機要誠實,不給讀者虛假的真實。此外,非虛構寫作應關注如何把握自身的文學性等問題。
在葉曙明的非虛構作品中,我們看到了突破這種困境的努力和可能。首先是做到真正意義上的“非虛構”。以《廣州傳》為例,寫作參考書目近90本,涵蓋古今中外各類典籍,遍尋與廣州相關的資料記載。比如,上古時代城市名稱的由來、地理位置的確立、早期越人生活起居的方式等,這些信息久遠難考,但作者并不只做簡單交代,而是窮盡史料,從古書記載中辨析出更多真實狀貌,同時還考察了諸如“五羊傳說”這一流傳千年神話故事的多個版本,給出大量新的歷史信息。《圖說香港抗戰》一書,作者用了幾百幅珍貴歷史照片,以展示更直觀的歷史現場,讀者如有身臨其境之感。
其次,包括報告文學在內的非虛構寫作一直面臨作品文學性的質疑。長期以來,大家總是囿于“文學就應當是虛構的”這樣的傳統文學認知,認為完全建立在真實性上的寫作只能算新聞或者文獻。現代以來的文學理論話語與以小說為書寫中心的文學創作相伴相生,文本與批評和理論之間構成了言說與闡釋的統一體,形成虛構中心論的理論體系。但溯源傳統,《漢書·藝文志》有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清代章學誠也在《章氏遺書·上朱大司馬論文》中說:“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這說明中國的敘事作品“雖然在后來的小說中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它的形式技巧和敘事謀略,但始終以歷史敘事作為它的骨干”[6]。換言之,中國文學自發生以來就包含歷史敘事和小說敘事,且以歷史敘事為正宗。而《史記》就是中國歷史敘事的范本,本質上是一個非虛構的文本。因此,從本源上看,作品的文學性并不取決于虛構與否,而在于作者如何取材和書寫。對非虛構而言,“從生活存在中選擇具有故事性的內容,以適合的結構方式和具有個人性的語言方式呈現真實。文學性就存在于被選擇和結構的真實之中。這是非虛構文學中文學性的一種獨特性”[7]。
《廣州傳》中有一個寫清末現代商業企業真光公司的段落,展現了真光公司的現代商業光景,但更有意味的是,作者著重描述了這里上演的古老的“師娘”表演。女藝人雙目失明,一張小桌,一把木椅,抱著琵琶,自彈自唱:“花易落,花又易開。咁好花顏問你看得幾回。好花慌久開唔耐,想到花殘,我都愿倨莫開。”情凄意切,觸動多少人心往事……底層的悲涼在璀璨的繁華里嗚咽沉沒,幽怨的唱詞里似乎還隱喻著動蕩時局的到來。在這真實上演的場景中,構成了一個多么意味深長的人生和時代語境。這段出色的真實描寫給出了不虛構也能創造文學意境的回答。其實,真實往往比虛構更精彩,作家真正腳踏實地走進現實和歷史,發現真實中那些有深刻人生意味或歷史意蘊的細節,是非虛構文學性獲得的一個根本原因。
作者在章節標題的設置上也是精致考究的,給不同歷史時期廣州城市的特點做了相對文學化的概括,諸如寫在“山與海之間”這座“城的誕生”,寫唐朝盛世繁華的“奢華年代”,展現南宋之后文化興盛的“鳶飛魚躍”和“先生的背影”,還有清朝年間由盛而衰的“一場春夢”等。歷史類書寫中往往有繁復龐雜的史料鋪陳,給人以枯燥乏味之感,作者的文學表述很好地介入了敘事節奏的處理,讓讀者接受理性的歷史知識時獲得感性的情感體驗,讓歷史成為可讀、可感、可思、可評的生動鮮活的人文存在。
更重要的,非虛構寫作應當十分注重寫作空間的開闊。“使文學創作走向更為開放性的文化語境之中,其中的不少作品已延伸到社會學、歷史學或人類學等其他人文領域,成為它們的某種文本參照。”[8]這是對非虛構文本意義的一個重要提示,非虛構文本不應只是一個單純的文學文本,而應追求具有歷史學、社會學等多重學科價值的復合文本。葉曙明的系列寫作就有著這種復合文本生成的自覺意識。葉曙明在非虛構寫作之前,是成功的小說家、近代史專家和出版人,有著豐富的社會經歷、寫作積累和文史知識儲備。這是他非虛構寫作明顯具有跨學科視野的重要原因。比較而言,以上提到的《北京傳》《南京傳》更傾向于一位文學家眼中的北京和南京。《廣州傳》則一方面是面向大眾的文學讀物,提供給讀者一個文學家眼中的廣州;一方面,關注社會宏大題旨,深入歷史細節,對磅礴的史料做出甄別、選擇、提煉、整合、判斷,深度探究嶺南文化、廣府文化的內涵,并嘗試做出新的闡釋,寫出歷史的深度與現實的重量,并最終在一個問題意識的框架內形成兼具真實性、歷史性和當代性的文本,是真正努力走向“寬闊的寫作”。
[注釋]
[1] [俄]H.M.薩維利耶娃:《“公共史學”芻議》,張廣翔譯,《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10期。
[2][法]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頁。
[3]? 朱光潛:《克羅齊的歷史學》,蔣大椿主編:《史學探淵——中國近代史學理論文編》,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9頁。
[4] 《人民文學》,2010 年第2期主編留言。
[5] 李敬澤:《“虛構寫作”面臨困境》,《錢江晚報》,2011年10月30日。
[6] 楊義:《中國敘事學》,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頁。
[7] 丁曉原:《非虛構文學的邏輯與倫理》,《當代文壇》,2019年第5期。
[8] 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
本論文為2021年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優秀青年項目“新時代文藝思想與‘湖南報告文學現象研究”(項目編號:21B075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長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