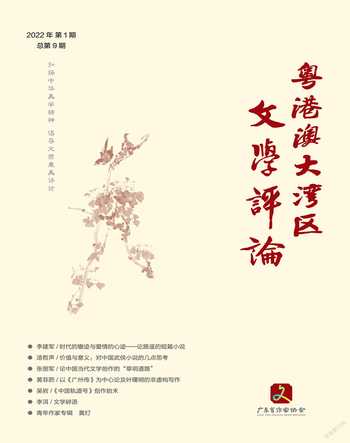亂世蒼涼,蒼涼亂世
劉川鄂
摘要:張愛玲涉及戰爭題材的作品不多,且不直面戰爭本身,而是以戰爭為背景,寫凡人的凡人性,“正常的人性和人性的弱點”。她最關注戰爭這種極端環境中的人性的扭曲,情感的浪費,生命的無辜。文明脆弱,人性蒼白,道德蛻變,說不盡的蒼涼故事。可以說,張愛玲的相關作品是戰爭心理學、災難心理學的形象范本和人性微病歷,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精細刻畫戰爭中的人性和人性的戰爭的精彩篇章。
關鍵詞:張愛玲;戰爭題材;人性;人性的弱點
1987年秋,正在上海、南京、杭州查閱有關張愛玲碩士論文資料的我,抽空在西湖畔看了一場電影《最后一班地鐵》。二戰德軍占領巴黎期間,戲劇照演如常,劇場比平時更熱鬧。戰爭為什么加劇了劇院的火爆?因為待在家里有未知的恐怖,只有在人群中尋求安全感才能忘卻恐懼感,抱團取暖,驅逐心魔。戰爭災難,淡化了家庭的重要性。
猶太籍的劇場主人兼編劇呂卡斯為了躲避納粹的種族迫害,一直住在劇院的地下室,繼續領導和排練他所編的劇目。這一切全都是通過他的妻子、著名女演員瑪麗翁來完成的。每次他都是靠地下室內的偽裝通風系統來傾聽舞臺上的排練,同時他也感覺到瑪麗翁和男主角的扮演者格朗惹之間產生了微妙的愛情。考慮到自己的處境,他決定成全他們。但格朗惹見到呂卡斯之后,決定到抵抗運動中去。巴黎解放了,瑪麗翁站在舞臺上,一手拉著丈夫,一手拉著情人,向觀眾頻頻謝幕。丈夫和情人在平常狀態中是仇人關系,而在這種非常態的環境中卻變成了同志關系,全拜戰爭所賜。大敵當前,死活難顧,愛情,天生具有排他性的愛情,關于兩性關系的道德,退居其次。戰爭災難,淡化了道德的重要性。
我們可以說,在漫長的人類歷史文明中,和平是常態,戰爭是非常態。所有戰爭都是人類的敵人,都是人類的災難,尤其是平民的災難。
災難可分為自然災難和人為災難。前者如地震、瘟疫,此為天災。后者如戰爭和政治浩劫,此為人禍。當然也有二者混合的災難,此為天災人禍。前者觸發人類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后者多讓人思考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系。應該說后者的社會含量、人性含量更豐富,對人自身的反思對文明的反思更深刻,這是不言而喻的。災難具有不確定性、破壞性和長期性,大災害、大災難對人們心理的傷害遠超想象,所以需要心理援助,從個體層面、群體層面、組織層面、社會層面去預防災難、救援災難、重建災區和心理疏導,應對和醫治創傷。[1]作為社會生活的極致表現,災難往往是人性最活躍的、最徹底的、極端的表現舞臺,因此也是深邃敏感的文學家觀察和描寫的重點領域。反常態的環境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某些變化、人性的極致表現,都是作家樂于觀察和表達的。很多偉大的文學家都是災難的見證者、審視者和反思者。“人道災難對人造成的最深遠、最持久的傷害就是對共同人性的扭曲和敗壞。 人道災難因此也成為人性災難。人道災難發生以后, 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人性和道德秩序再難修復的世界之中,不管他是受害者、加害者,還是袖手旁觀者。”[2]
現在中國作家中有幾個跟死亡隔得特別近的人,他們往往是人性洞察最深邃的人,作品的人性含量最豐富的人,如魯迅的絕望抗爭(父親的病與死加速了他對中國文化的厭惡與反抗)、沈從文的邊民生趣(少年時代見過太多的殺人場面,所以他看淡了生死、看輕了文化)、穆旦(參加遠征軍的自殺式滇緬大撤退,成天看著戰友倒下,自己也差點病死、餓死、被敵人打死)的文明反思、張愛玲(香港戰爭中的看護經歷)的亂世蒼涼。
一、去掉一切浮文,只剩下飲食男女
香港戰爭的爆發,毀滅了張愛玲的留學夢。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氣勢洶洶,香港慘遭血與火的洗刷。相持了二十多天,英軍彈盡糧絕,投降日軍,戰事遂告一段落。
因為戰爭,香港大學受到炮火的重創,學校的文件記錄統統被燒掉了,張愛玲的一個個優異成績化為灰燼。而且她連一張畢業文憑也沒拿到便不得不結束學業,重返上海。仿佛命運之神故意要捉弄她,使她永遠不能走科班出身的循規蹈矩的讀書求學之路。愛玲回憶說:“我在港大的獎學金戰后還在。進港大本來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戰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國慘勝,也在困境中。畢業后到牛津進修也不過是當初的一句話。結果我放棄了沒去,這使我的母親非常失望。”[3]從這話的表達口吻來揣摩,在香港擺脫了日本人的魔爪之后,愛玲本來是可以繼續她的學業的,但她沒有去。她雖然仍有掛懷,但沒有后悔,失望的是母親而不是她。那時的張愛玲已是著名作家,大紅大紫,還在熱戀中,她此時沒有了當學生的心境。但戰爭畢竟使她中斷了“超級學霸”本來可以延續的童年的留學夢,使她部分地失去了常態生活的可能性,聯系到一系列的言論和作品,她對戰爭可沒有好感。
《流言·燼余錄》,可以說是戰時單身女郎的百態圖,情態各異,千姿百態。一位女華僑,平時不同場合有不同的衣裝,但她沒有打仗時應該穿的衣服,這是她在戰爭中的最大憂愁。說來是個笑話,但這也是一種真實的女性心理,女人愛美愛裝飾天性的病態發揮,令人無限感慨。
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小美人,入學時天真得可恥,問解剖尸體時死人穿不穿衣服。飛機一響,她就拼命喊叫,歇斯底里,嚇得大家面無人色;戰時糧食供應不夠,也正因為不夠,便有人努力地吃,張愛玲稱之為健康的悲觀。
港戰打響后,學校停了課。愛玲和同學們參加了守城救護之類的工作,這不僅可以解決膳食問題,而且可以填補因無所事事帶來的空虛,于是她們紛紛當上了防空隊員和救護員。當防空員時駐扎在馮平山圖書館,她看見了一本《醒世姻緣》,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圖書館的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日軍轟炸的目標。一顆顆炸彈落下來,越落越近。張愛玲心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炎櫻,在戰爭中欣然自樂,冒死上街看電影,在被流彈打碎玻璃的浴室里邊洗澡邊大聲唱歌,像是在嘲諷眾人的恐怖。——絕望中的放縱,無奈的任性。
人們都想到過死的可能性,而一旦真的有人受傷,眾目睽睽之下的傷者反而因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而頗為自得。傷口怎樣發膿,怎樣因長新肉而欣喜自憐,怎樣以捉米蟲而打發時光。——人總是求存在感,求被關注,但是這種方式也太特別。自得的背后是更大的孤獨和恐懼。有的病愈而走,有的死亡而終。一個又一個凍白的早晨過去了,人們若無其事地活下去了。
她的一個英籍教授戰時投筆從戎,沒能死在戰場上,卻因未及時回答己方哨兵所問口令而被打死了。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
人們不敢外出,紛紛搶購糧食,以防挨餓。但仍餓了不少人,愛玲和她的一班愛吃零食的女友們自然也跟著吃苦挨餓。停戰后人們又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是記錄戰時香港居民心態的傳神之筆。——劫后余生,常態生活升格為超級享受,人的物質性。
更有不少女孩子為驅散戰爭恐怖要抓住一點兒真實的人生而匆忙結婚了。戰后香港報紙上的征婚廣告密密麻麻,缺少工作與消遣的人們都提早結婚了,仿佛兩個人在一起比獨身一人更容易驅散戰爭的恐怖的陰影,但這似乎也降低了對精神的需求。
食與性成為最基本、最真實的人生內容。男女同學之間的道德感也松弛了。學生們似無所事事,成天在一起燒飯、打牌、調情——帶著絕望傷感的調情,有一次算一次的調情。
男生躺在女生床上玩紙牌,大清早就闖入女生宿舍廝混。清晨的靜寂中,不時傳來嬌滴滴的“拒絕”聲:“不行!不嘛!不,我不!”其他人習以為常,決沒有大驚小怪,也無人岔岔不平。死里逃生的人的貪歡,人人都能理解,人人都會同情。透過這些故事,愛玲驚訝地發現: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
“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這是一個敏銳獨到的人生見解。它不同于平面地從時代、環境等外部因素觀察社會的歷史學家的眼光,而是文學家們特有的人性的視角。
港戰使她眼界大開,她不停地思考著生活的價值,先前對人的認識也得到了實證和矯正。她覺得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似乎僅是飲食男女這兩項。人類的文明就是要跳出單純的獸性的生活圈子,但卻這樣難,幾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嗎?
空襲和警報、逃亡與堅守、傷兵和死尸、正義與自私、求生和求愛、人性與獸性……港戰前后極大地豐富了張愛玲的人生經驗。她回憶這段生活的長篇散文《燼余錄》是現代文學中精細刻畫戰爭中的人性和人性的戰爭的精彩篇章。它的結尾也是一段名言: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 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里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4]
她最寒心的是人性的扭曲,情感的浪費,生命的無辜。亂世蒼涼、蒼涼亂世。反常態的時空里,凸顯著人性和正常的人性弱點。
二、“亂世的人,沒有真的家”
香港,是成長期的張愛玲體悟人性的“圣地”。港戰,給了她觀察人性的良機。她的人生觀開始在形成,在成熟。她對個人的志向偏于寫作方面亦有了信心。“張愛玲的香港故事,呈現了奢華與衰頹、浪漫迷魅和精神墮落并置的復雜圖景。這個島嶼,為張愛玲眼中深受傳統制約的上海中國人,提供了一面扭曲的鏡子;相對于所扎根的上海,香港成了她的自我‘他者。多年之后的1952年,當她被迫離開上海時,她別無選擇再次前往香港,并以之為試圖開啟新文學生涯的臨時基地,爾后再移居美國。可以說,是香港,才令她后來的文學寫作成為可能”。[5]
不論張愛玲怎樣三頭六臂,不管她的題材如何變化萬千,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點,是她半個世紀筆耕生涯的專注重心。《傾城之戀》中范柳原的花花公子性格似乎定了型,不可改變,白流蘇的婚姻算計似乎很難實現。兩個人的談戀愛無休無止,花樣無窮無盡,但永遠停留在高等調情階段。然而,似乎等不了那么久,香港戰爭爆發了,無論什么人都共同面臨著生死、饑餓。他們齊整整地站在人的底線上了,這一對男女結婚了。有人不能理解一場戰爭使二人結為夫妻,以為這是作者的突兀之筆。作者的用意是明顯的:一場戰爭毀滅了高等調情的場所,洋場氣氛淡化了,洋場文明如何不收斂些?質樸的生活逼迫了他們,一對自私的人才能結合。飄在云端的愛情落在了現實的婚床上。假若沒有戰爭,盡管柳原對流蘇有情,但流蘇永遠只是他的情婦,而柳原永遠只是一個愛匠而不是愛人。從《傾城之戀》可以看到,人在戰亂的殘酷現實面前是多么無奈、多么脆弱,不堪一擊。
“亂世的人,沒有真的家”(《封鎖》)。城市因戰爭而驚慌失措,生活節奏被打亂,人們失去安全感。一聲警笛,電車原地停頓,造就了一個封閉的時空。封鎖內外是兩個迥然有別的世界。呂宗楨有家庭,有事業,但他連為什么每天要上班、下班后要回家都不明白。吳翠遠是一嚴肅得過分、平淡而無生氣的女性。“思想,是件痛苦的事情。”但他倆在一個與世相對隔絕的環境中相愛了。封鎖期間的他倆與在塵世中生活的他們判若兩人,墜入愛河、煥發了活力。但一旦封鎖開放,他們又不得不繼續扮演著原來在塵世中的形象。純潔的情如美麗的曇花,剛開即逝。作者通過封鎖期間與開放以后的時空變化,表現出塵世與純情的對立。封鎖期間,正是一個純情的世界。解除封鎖,又回到凡俗的人間。
如果說讀者們普遍欣賞張氏描繪的常態下的人性及弱點的話(如《傳奇》集中的中短篇小說),對《色,戒》這篇因題材的尖銳而顯得格外“打眼”的小說,還是應該從這一角度。《色,戒》在特異的狀態下探尋人性和正常的人性的弱點,到了相當深入的程度。除了作者關注人性的自覺意識及長期的琢磨之外,與她在這篇作品中調動多樣藝術手法為之服務相關。不露痕跡的細節鋪墊、精微的心理刻畫、高潮中的“反高潮”寫法,都相當成功。尤為出色的是“反高潮”手法。美人計歷時兩年,幾經周折,女主人公也費盡心機、嘗遍酸苦與甘辛,總算熬到了除掉易先生實現暗殺計劃的那一刻,眼見得高潮就要出現,萬事俱備,沒有任何細節差錯,卻被王佳芝臨時“變卦”把易先生輕而易舉地放走了。完備計劃付諸東流,常態結果沒有出現。這就是“反高潮”——走向高潮的反面。它不過是將人性置于反常態的狀態之下拷問、探尋。唯如此,我們才能找到《色,戒》與張愛玲其他作品的相通之處。
如果說政府和社會學家關注的是災難中和災難后群體的行為反應,抑郁癥、焦慮癥等明顯具有醫學特征的身心障礙,文學家更關注災后個體身心反應,一些可能當事人不以為然的、沒有明顯病理特征的潛在疾患。張愛玲涉及戰爭題材的作品并不是很多,除了這里提到的幾部之外,《赤地之戀》部分內容與之相關。而且基本上都不是直面戰爭本身,而是以戰爭為背景,寫凡人的凡人性。可以說,張愛玲的相關作品是戰爭心理學、災難心理學的形象范本和人性微病歷。“受害幸存者既是災難的‘道德見證人,也是后災難的‘世界修補人。他既反叛災難的邪惡,也反叛后災難對邪惡的忘卻。他的見證體現的是一種人為自己生命做主的決心。災難見證是一種寶貴的社會道德力量,它能幫助所有的人在共同人性的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6]沒有英雄敘事,不是大悲大喜,而是凡人的悲哀,“幾乎無事的悲劇”,小人物的常態性格和性格變異。張愛玲刻畫了否定性的樣本,或者說精細地繪出了病例,做出了診斷,但是她沒有開藥方。悲哀的人無藥可救,悲涼的心沒有未來,這的確不是她的強項。
三、說不盡的蒼涼故事
“自從文明的社會一經出現,戰爭和奴隸制就是文明的一對毒瘤。”[7]為政治權力爭斗、為經濟利益爭奪、為宗教文化沖突,戰爭作為人類生活的一種特殊存在,造就了社會發展的災禍與人類生存的動蕩,帶來人口、疆域、政治、經濟、科技等社會人文環境的急劇變化,甚至成為決定人類生存命運的重大轉折。功不可沒,罪不可赦。
戰爭題材文學作品在世界文學格局占有重要位置。“戰爭是人類存在景況的最鮮明、最全面、最精細也是最權威的百科全書。戰爭是一個無比巨大的顯影器皿,人類的優點與弱點,人類的智慧與愚昧,人類的理性與瘋狂,人類的正義與邪惡,人類的高級品性與低級欲望……都可能在這個顯影器皿中獲得前所未有的甚至是終極性的暴露……所以,戰爭之于小說創造的誘惑,往往處于一種永恒的狀態。”[8]古今中外有不少關于戰爭文學的經典著作。歷史的進程、人性的糾葛、正義與邪惡、和平與暴力、人性與獸性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戰爭文學是國民性格的充盈展示,人類精神在特殊時期的極端發展。
“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國家主義使時代變得瘋狂而混亂,使得她的人生變得無法控制,使她的寫作和私生活都備受詬病。正因為親歷了戰爭,對戰爭的殘酷和絕望有了更為直觀和感性的認識,國家主義對于她才更像是洪水猛獸。她不明白為什么人們要拿生命去信奉國家主義,這樣的狂熱造就的不過是無謂的戰爭。整個世界在二十世紀都沉迷在這個宗教中,喃喃地癡迷在國家民族的想象里,爭相為自己賦予神圣的使命。[9]
災難一直伴隨著人類的進步,危機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創傷,還有與創傷抗爭之后的成長。“戰爭的結局不是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了下來,也不是世界經過勝利者的分配擁有了全新的格局,它最大的結局是人性的改變。人性的改變決定了未來的人類是什么樣的人類,它比戰爭本身更加危險。”[10]如同海明威那樣,戰爭中士兵們遭受的令人難忘的身體和精神的創傷。在《太陽照常升起》和《永別了,武器》等作品中,在他塑造的尼克·亞當、杰克·巴恩斯和弗里德里克·亨利這樣一些反戰經典形象中,在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福克納和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等世界經典名作中,從英雄主義、國家主義、浪漫主義三位一體的戰爭小說,到懷疑主義的人性探尋、深層拷問弱者本位,是世界經典軍事題材文學的重要發展趨勢。不管戰爭有多少正義性、合理性、必要性,但之于平民就是災難,之于凡人,就是生命的掙扎和人性的煎熬、撕咬、扭曲。
因為安全沒有保障,生計沒有保障,生命沒有保障,所以家庭也沒有保障,有時候只能顧自己一個人。一個人的生活是更加隨意的生活,更加沒有責任感、沒有家庭義務的生活。既然是死是活都不可知,顏面和規矩也就放松下來了。亂世的生活更加個人化。
死生契約,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實在是最悲哀的一首詩,死與生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力量,我們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們偏要說:“我要永遠和你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分開。”好像我們做得了主似的。(《傾城之戀》)
生逢亂世,小人物是做不了主的,誰都做不了主。男人女人做不了主,洋人華人做不了主,華僑土著做不了主,已婚未婚做不了主,窮人富人也做不了主。唯有蒼涼。文明如此脆弱,人性的底色如此蒼白,道德似乎可有可無,說不盡的蒼涼故事,不問也罷。
[注釋]
[1] 時勘等著:《災難心理學》第一篇“理論方法”,科學出版社版2010年版。
[2][6] 徐賁:《見證文學的道德意義:反叛和“后災難”共同人性》,《文藝理論研究》,2008年第2期。
[3] 張愛玲:《對照記》,臺北皇冠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頁。
[4] 張愛玲:《流言·燼余錄》,中國科學公司1944年版,第56頁。
[5] 李歐梵:《張愛玲在香港》,《南方文壇》,2019年第5期。
[7] [英]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下)》,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2頁。
[8] 周政保:《戰爭小說的審美與寓意構造》,《文學評論》,1992年第3期。
[9] [美]維克門(Yohn? Wakemen)主編:《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紐約沃爾遜公司1975年版。該書介紹了959位作家。入選者必須為英語世界所熟悉的文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新聞記者。參見高權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張愛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版。
[10] 鄧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4頁。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