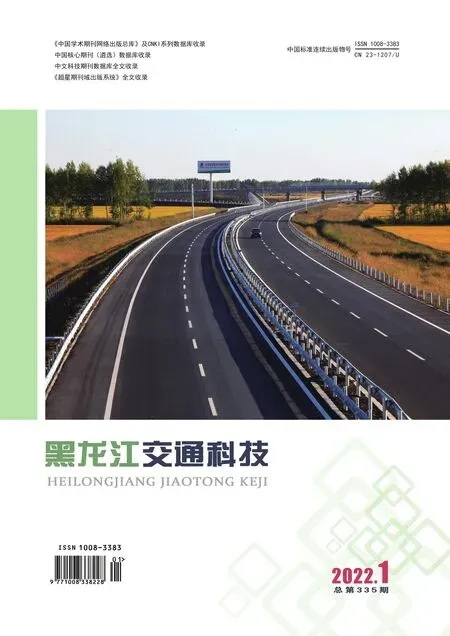基于超邊際分析的居民出行方式選擇模型
張 馳
(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廣西壯族自治區(qū) 桂林 541004)
0 引 言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嚴重的交通擁堵問題仍是制約我國城市發(fā)展的重大問題。其主要是由于交通工具分配不合理,因此有必要對城市居民出行結(jié)構(gòu)進行優(yōu)化。
Koppelman[1]通過引入“廣義效用”的概念,提出了一種包括交差分層Logit模型和雙層Logit模型在內(nèi)的廣義模型。Chandra[2]在分析個人不可觀測和可觀測的偏好與特征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描述個體對交通工具的偏好的多項Logit模型。Paeto等[3]研究發(fā)現(xiàn)人們的生活方式對出行選擇有影響,不同的人對出行成本和出行時間的偏好不同,出行方式的選擇也不同。馬俊來等[4]在研究客運交通工具選擇的舒適度時認為,后續(xù)研究中更應考慮擁堵程度、設施等微觀因素。Marshall[5]認為無論是宏觀經(jīng)濟學還是微觀經(jīng)濟學,研究的重點依然是在一個固定稀缺水平的社會中如何優(yōu)化資源配置。楊小凱[6]認為通過使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能夠?qū)⒐诺浣?jīng)濟理論中關于分工和專業(yè)化的思想轉(zhuǎn)化為決策均衡模型。周梅妮[7]運用新興古典經(jīng)濟學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研究社會如何在制度改進的條件下由低分工水平向高分工水平的發(fā)展過程。
目前國內(nèi)外對于居民出行方式的研究僅考慮到出行者自身,沒有考慮到基于分工的動態(tài)演化過程。將新興古典經(jīng)濟學引入居民出行交通工具選擇研究中,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構(gòu)造居民出行交通工具選擇決策模型,并分析靜態(tài)比較均衡隨著交易效率的增加分工結(jié)構(gòu)的變化。
1 基于超邊際分析的模型的建立
1.1 基本假設
新興古典經(jīng)濟學的假設前提是“人天生相同”。通過構(gòu)建交通工具選擇決策效用函數(shù),假設如下。
假設1:假設一個人數(shù)為M的生產(chǎn)者—消費者系統(tǒng)。系統(tǒng)中個體作為消費者時,在支出不超過收入的情況下,選擇多樣化的消費,使效用達到最大化。作為生產(chǎn)者在其工作范圍中有專業(yè)化經(jīng)濟,出行會產(chǎn)生需求信息,同時將相關信息反饋至使用者,推進整體出行過程中各類主要乘坐交通工具的生產(chǎn);
假設2:在一個城市區(qū)域內(nèi),居民出行均需要選擇出行方式為x、y和z、x為汽車,y為電車或自行車,z為公交車;
假設3:使用αi為影響因素,共設置3類因素,即(個人屬性、交通供給、出行特性)。
1.2 居民出行模型建立
根據(jù)假設,首先建立居民出行和影響因素之間的效用函數(shù),根據(jù)楊小凱老師在新興古典經(jīng)濟學理論中提出的“科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shù)”形式,構(gòu)建居民出行決策效用函數(shù),效用函數(shù)用ηi表示

(1)
式中:ηi為出行決策效用;b為模型的殘差向量,即偏差部分;αi為影響因素的權(quán)重比重。
對于城市發(fā)展和環(huán)境的問題,利用收益率建立決策權(quán)重模型,居民選擇某種出行方式后所計算的城市收益權(quán)重,公式為
(2)
式中:w+和w-分別為出行決策所帶來的城市收益和城市損失;p為出現(xiàn)的決策選擇概率;γ為風險收益系數(shù);σ為風險損失系數(shù)。
通過上述迭代運算,可以得出居民出行決策與城市收益和損失的關系,進而得出對城市發(fā)展和環(huán)境的量化影響。
對于城市中的一戶居民來講,賦予其一個單位的勞動,即勞動稟賦約束為
lix+liy+liz=1
(3)
式中:lij為對于住戶i其進行上班工作效益j的勞動投人,即住戶i對工作效益j的專業(yè)化水平。
住戶i的出行生活預算為
(4)

因此該決策問題可以表述為
效用函數(shù)
(5)

根據(jù)超邊際分析方法,首先利用文氏定理(Wen Theory)剔除一些變量組合,并通過后續(xù)的成本約束和效用函數(shù)為正的條件,最終將整體最優(yōu)的決策減少到8種。將決策變量關于零與正值的一個組合,稱為一種決策模式。所以對于每戶居民來講,共包含10類決策模式,每一個模式均存在一個角點解,每一個角點解均給出其城市影響程度和在該模式情況下的最優(yōu)資源分配。每戶居民在不同的模式之間進行成本—收益的分析,以選擇最優(yōu)的角點解。
自給自足結(jié)構(gòu):即居民不采取任何交通措施。
半專業(yè)化分工結(jié)構(gòu):即使用單一的出行方式,或兩種結(jié)合的出行方式,模式為(xi),(yi),(xi/yi),(xi/zi),(yi/zi)。
完全專業(yè)化分工結(jié)構(gòu):即使用三種出行方式:(xiyizi)。
2 基于超邊際分析的分工結(jié)構(gòu)與角點均衡分析
上述的決策分析模型中共得出8種模式,將其進行組合可以得到如下出行決策模型的市場結(jié)構(gòu),即社會中不同的決策模式的組合可以產(chǎn)生不同的分工結(jié)構(gòu)。每個結(jié)構(gòu)都存在一個角點均衡,假設生產(chǎn)、消費和交易數(shù)量的自由是建立角點均衡的驅(qū)動力。
采用兩步求解法則計算各結(jié)構(gòu)的角點均衡,首先求出每種模式的的最優(yōu)解,再根據(jù)效用均等和供需均等的均衡條件求解每個結(jié)構(gòu)的角點均衡。
2.1 自給自足結(jié)構(gòu),寫為A
模式A即三類交通方式均不選擇,而是自行步行出行,因此得到:
根據(jù)公式(5),決策問題可表述為
(6)
lix+liy+liz=0
根據(jù)公式(6),得到最終效用函數(shù)為
(7)


該結(jié)構(gòu)中,自給自足的出行決策模式不需要借助外界的交通工具,僅依靠自給,因此模式A的角點解就是結(jié)構(gòu)A的角點均衡。
2.2 局部分工結(jié)構(gòu),寫為PA
該結(jié)構(gòu)下共有6種模式,將單一選擇的模式歸為一類進行求解,剩下三類分開求解。

此時決策問題可以寫為
(8)
liy+liz=0
根據(jù)公式(8),得到最終效用函數(shù)為
根據(jù)拉格朗日函數(shù)進行求解,并構(gòu)造拉格朗日函數(shù)得到
對上述式子以x1求偏導,最優(yōu)決策解為



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兩類的最優(yōu)決策解。
(9)
l2x+l2z=1
根據(jù)公式(9),將約束條件代入到效用函數(shù)中得出
(10)
構(gòu)建拉格朗日函數(shù),得到最優(yōu)決策解為



間接效用:
通過實際分析及上述求解得到的模式的最優(yōu)決策解,根據(jù)該條件以及效用相等條件,求解結(jié)構(gòu)PA的角點均衡。
以出行xi為例,根據(jù)需求與供給均衡,可知
2.3 完全分工結(jié)構(gòu),寫為D
該結(jié)構(gòu)將三種出行方式全部組合。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作為主要出行工具,以公共出行zi作為主要出行為例,得到
則決策模型寫為
(11)
l3z=1
將上述的約束條件再次代入后得到
構(gòu)建拉格朗日函數(shù),得到最優(yōu)決策解為:
專業(yè)化水平:l3z=1



間接效用:
得到上述模式的最優(yōu)決策后根據(jù)擁堵條件,得出上述模式D的角點均衡解,即其效用可以表示為
將上述的分析結(jié)果本文進行了歸納總結(jié),得出角點均衡結(jié)果如表1所示。

表1 三類分工結(jié)構(gòu)中的角點均衡結(jié)果
3 靜態(tài)均衡比較結(jié)果
角點均衡分析僅是在既定的結(jié)構(gòu)下完成了交通工具的資源配置。但若要內(nèi)生得到分工水平結(jié)構(gòu),則必須進行完全均衡及超邊際分析中的一個解。
如果一個分工結(jié)構(gòu)是完全均衡的,則就說明在該結(jié)構(gòu)的角點均衡所確定的相對價格下,其選擇各類交通工具的均衡效用比其他結(jié)構(gòu)要高。
(1)如果自給自足分工結(jié)構(gòu)A為完全均衡,因此該結(jié)構(gòu)匯總的城市效用不低于其他結(jié)構(gòu)
(12)
根據(jù)公式(12),求出交易效率系數(shù)的取值區(qū)間為
(2)如果局部分工結(jié)構(gòu)PA為完全均衡,則該結(jié)構(gòu)中的交通工具效用則不應小于其他結(jié)構(gòu)
(13)
交易效率系數(shù)的取值區(qū)間為
(3)如果完全分工結(jié)構(gòu)D是完全均衡,則該結(jié)構(gòu)中的交通工具效用則不小于其他結(jié)構(gòu)
(14)
交易效率系數(shù)的取值區(qū)間為
k>k2
超邊際的比較靜態(tài)分析的結(jié)果如表2所示。

表2 交通工具分工模型的完全均衡及超邊際分析比較靜態(tài)分析
4 結(jié) 論
(1)當三類交通工具的城市交易效率k很低的時候,特別是在區(qū)間0 (2)三類交通工具的城市交易效率k有所提高,處在區(qū)間k1 (3)三類交通工具的城市交易效率k達到較高水平,處在區(qū)間k2 (4)隨著分工的不斷深化,居民的出行選擇特征和出行需求會不斷促使社會專業(yè)化提供高效出行交通工具的發(fā)生和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