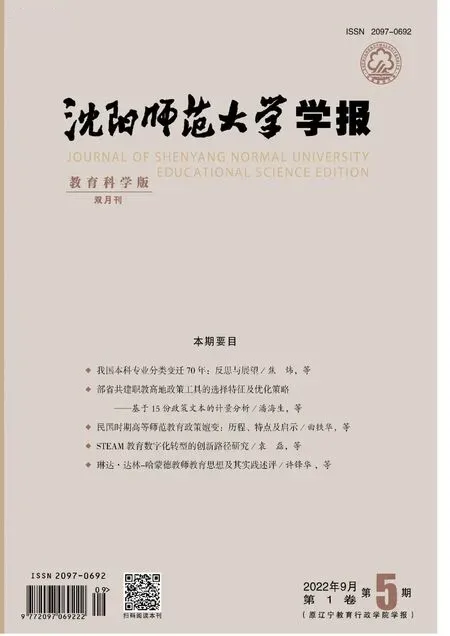教育如何以人為本:一種人學視角的追問
李梟鷹,郭新偉
(大連理工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院,遼寧 大連 116024)
教育“從人而來,向人而去,與人同轉”[1],無論時空如何更替,這一點永存不變。因此,教育不能“人空場”。這不僅意味著“教育為何要以人為本”[1]并非一個毋庸贅述的問題,也意味著從人學視角來追問“教育如何以人為本”是一種務本的追問、必需的追問、終極的追問。教育當以人為出發點、軸心和歸宿,以自我塑造、謀求幸福、豐實靈魂、升華境界、延拓生命為責任、使命、目標、承諾和擔當。
一、指引學生自我塑造
教育根本上是人的一種社會實踐,為了培養人、發展人、塑造人,以及釋放人自我塑造的潛質和能力。從張楚廷先生關于“人本教育思想”[2]的主張來看,“為了人”的教育過程可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教育“讓人像人”,即幫助人實現從“自然人”到“社會人”的轉變,使人從一個“自然實體”成長為一個“社會實體”,使人具備基本的認知能力和必要的賴以支撐認知、形成和發展素質的非認知能力,這是人之所以為人而非動物的重要“分水嶺”;二是教育“讓人更像人”,即讓一個個活生生的“社會人”或“社會實體”變得更有知識、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更有思想、更有格局、更有高度、更有視野、更有境界,完成一系列“更”的升華和超越,從一種粗糙的、單調的、低水平的生命狀態,躍遷和進化至一種更精致、更豐實、更高層次的生命狀態。在“為了人”的教育過程中,外在力量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否則受教育者會四處碰壁卻不得要領。然而亦要看到,培養人、發展人、塑造人表現為手段與目的的統一,在短時間內是目的,而長久來說,皆是人自我塑造的手段。無論是教育“讓人像人”還是教育“讓人更像人”,二者的實現及其帶來的教育之世代延續和生生不息,都扎根于教育的過程,這個可看作人通過“自反”來實現“自增”的過程,亦即受教育者自我塑造的過程。
人的自反性和自增性肯定個體天賦潛能的存在,同時指明通過教育途徑開發天賦潛能和實現自我塑造的基本理路。具言之,人都是在外力的助推下自我生長、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別人去完成這些活動。在教育中,學生并不是教育影響的被動接收者或消極承受者,之所以時常稱之“受教育者”,乃是出于同“教育者”的指稱對應的考慮。相反,他們必須自己去“解構”、自己去“建構”,在解構與建構的超循環中實現螺旋式發展,完成從“像人”到“更像人”的飛躍,在“成人”的基礎上追尋“成完人”“成大才”等更高層次的目標。在真善美的價值規約下,每個學生都可以且應當遵從自身的天賦潛能,成長為其所希望的樣子,形成和發展獨立的自我、真實的自我,成為“本人”而非“他人”,成為真人而非“假面之人”,盡顯個性化的迷人光彩。當然,這一切必須在“成事”中完成,因為人只能在成事中獲得成長;在成事中,成己、成人和成才方有所憑、有所依、有所靠。
學生好比一粒蘊含無限潛能的種子,而教師乃至教育要做的是為之提供陽光、水分、溫度、土壤等適宜生長的條件,使之長成參天大樹并結出累累碩果。這意味著教師與學生的雙重解放;意味著教育要將自主探索的選擇權重新交付給學生;意味著教師只是“領進門”,而學生“修行在個人”;意味著師生之間要建立起一種平等的對話與溝通關系,教師不能異化為工匠,學生也不能異化為被雕刻的原材料。在實現受教育者自我塑造的教育中,學校也要擺正定位。一方面,學校為學生的成長和自我塑造創建平臺,為他們自主選擇、自由思考、自覺探求、自我決斷及獨立地反思、質疑和批判創造環境,而非千方百計地提供現成的知識、完整的知識,或者將大部分的教育時間單一地困守課堂之上、囿于教師的學術領地之中,讓學生按照預設好的軌道一路前行。這種預設性的教育面向的是學生整體而非個體,容易帶來整齊劃一、千人一面的消極結果,將教育異化為一種模式化、技術化、程序化、量產式的流水作業,使本應該與眾不同、豐富多彩的人生簡化和扭曲為“軌道式人生”。另一方面,學校亦非血淋淋或冷冰冰的“規訓場”,必須使學生遠離權力的控制和監視。為此,學校要禁止權力以“偽善面孔”隱藏在任何一個角落,杜絕權力以形形色色的樣態被教師操持和把玩而攻向任何一名學生。工業化的教育、冰冷的制度安排,只會泯滅學生的個性、扼殺學生的自由、戕害學生的天賦,導致教育失去育人之真、公正之善、和諧之美。
二、成就學生謀求幸福
教育以獲得幸福為主要目的。19世紀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就曾說過:“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學生獲得幸福,不能為任何不相干的利益而犧牲這種幸福,這一點當然是毋庸置疑的。”[3]213在今天,一方面,為了幸福的教育依舊是理論界歷經歲月蕩滌而傳之不朽的聲音,正如有學者所言,“從最美好和最深刻的意義上說,所有的教育都應當是幸福教育”[4]。教育理當指向人的幸福,也必須為人謀幸福。一切以犧牲人的幸福為代價的教育都是徹頭徹尾失敗的教育,無論它給予人多少知識或技能。另一方面,現實中的教育卻被不同程度地演變為一份“苦差”。很多時候,這樣的教育非但對提高學生的幸福感鮮有裨益,甚至還生出許多“副作用”,有損學生的健康,殘害學生的心靈。這之下隱藏著價值觀念的偏頗和背離。正如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所指出的那樣,當今“價值序列最為深刻的轉化是生命價值隸屬于有用價值”[5]141。這并非一種健康的、合理的、正義的轉化,教育不可“同流合污”,而須糾正這一謬見。站在生命價值的高度,教育絕不能“幸福空場”,幸福空場的教育一定不是好的教育;站在生命價值的高度,教育要全面服務于人的幸福、著力于拓寬人的幸福道路、提升人的幸福品位、延長人的幸福生命。
人的幸福有理性幸福和感性幸福之分,二者既有區別又存在聯系、相互對立又辯證統一,這源自人本身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理性幸福和感性幸福的來源渠道不盡相同,各自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也存在差異。相比之下,前者要比后者艱辛和復雜得多。細言之,人的理性幸福主要孕生于人的完美性與達到它的可能性之間距離的縮短,孕生于人之生命的整體、人之精神世界的豐實及人之理性價值的實現,孕生于自我的覺醒、依賴性的減退、審美能力的遞增、本質力量的釋放。“大多數人的所作所為,以及對逆境的忍受,背后秘而不宣的動機其實都是為了獲取幸福、保有幸福、找回幸福”[6]66,這里所體現的即為理性幸福。某學生為了“拿下”即將到來的考試,“忍痛割愛”,揮別費時而無用的娛樂,最終斬獲傲人成績,由此帶來的滿足和欣喜同樣是理性幸福的例證。感性幸福則主要孕生于可見的、可感的直接刺激及生理和心理的快感,而非靈魂的豐實、價值的實現、信仰的尊重。如饑腸轆轆之人突獲一塊面包,櫛風沐雨之人來到一處屋檐,闊別故鄉的游子歸來時的喜悅,久經陰霾的天空乍晴時的明朗,以及物質或言語的獎勵帶給人的直接慰藉等。理性幸福不否定感性幸福,二者并不矛盾、沖突,反而內在統一、相得益彰。無數的人生體驗告訴我們:象征感性的激情一旦衰減或退去,理性的動力將隨之弱化或萎靡;理性一旦缺失,感性也會信馬由韁而迷失方向。為此,教育在鼓勵和引導學生追尋理性幸福的同時,切不可無睹甚至打壓感性幸福的激發與催化作用,而要使學生從理性和感性兩個維度都能體會幸福。一方面,學生自當發展扎實的學術能力,產出豐碩的學術成果,但背后不能是巨大的“生命陰影”或“快樂缺失”,應是燦爛的陽光和漫溢的幸福。幸福源自真實的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絕不是純粹理性主義的,因為純粹的理性主義違背人性的完整性,是桎梏人的巨大“囚籠”,由其支配的教育必是一種異己力量,只能造就畸形的個體。另一方面,幸福不等于輕松或休閑,教育也絕非越感性越幸福,簡單的輕松愉快帶來的幸福是膚淺的幸福、消磨意志的幸福,以及可能讓人丟掉大好前程或發展空間的幸福。教育要讓學生學會拒斥當下之安逸或快樂的誘惑,教會學生通過付出勞動和智慧抵達幸福的彼岸。
幸福既是教育的永恒主題,也是教育理論研究的永恒主題。我們需要在教育系統之中,遵循教育的一般規律并吸收一切有價值的教育理論或教育思想的營養,譬如生命教育、生活教育、情感教育、快樂教育、閑暇教育、通識教育、賞識教育、超越教育等。它們立足于不同的角度或視域,從不同的維度洞見人的自然性、社會性、生成性、存在性、實踐性和整全性等特征,隱藏著通往幸福的教育路徑。教育可以從中探尋幸福生發的理論依據,探索“幸福空場”的規避策略。
三、喚醒學生豐實靈魂
人有思想、有靈魂,而人的思想和靈魂源自教育。教育是一項靈魂工程,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言,“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和認識的堆集”[7]4。這是教育的本質和真諦。人不能沒有靈魂,教育不能缺少靈魂,學校也不能追求那種“失去靈魂的卓越”。從某種程度上說,“學生”只是一個稱呼或名字——那些接受正式教育的人所共享的一個稱呼或名字,它本身是符號的、抽象的和空洞的,若不填充名副其實的靈魂,則無異于“空空的皮囊”。靈魂的核心是內涵,亦即內在涵養。從此意義上看,豐富和充實靈魂亦即發展個體的內在涵養。
長期以來,教育界存在一種“唯智主義”,亦即唯知識、唯理性至上,似乎除了這二者,教育別無其他。固然,人類在歷史長河中創造了許多不可磨滅的美好事物,熟知、洞悉乃至記憶這些事物是每個人最重要、最基本的內涵,但這并非內涵的全部。人的內涵是一種綜合性、系統性的內在涵養,這意味著教育必須塑造“完人”或“整全之人”。由此,單純的知識教育或專業教育是不完整的,只會造就擅長考試的“偽人才”和某一領域的專才或某類人才。錢穆先生曾經有言,僅僅注重“智識之傳授”的教育只能培養出“不通之愚人”[8]。懷特海也指出:“我們的目標是,要塑造既有廣泛的文化修養又在某個特殊方面有專業知識的人才,他們的專業知識可以給他們進步、騰飛的基礎,而他們所具有的廣泛的文化,使他們有哲學般深邃,又如藝術般高雅。”[9]1愛因斯坦于1952年應《紐約時報》教育編輯請求而寫的一份聲明亦曾告誡我們:“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學生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社會倫理、準則)有所理解并產生熱烈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10]310
反觀當前教育,中小學階段“唯分數”“唯排名”“唯升學率”的“三唯”勢頭仍在不同地區不同程度地上演。雖然素質教育的呼聲已經響徹多時,但是流于形式、只做“表面文章”的現象屢見不鮮,這更為應試教育提供了可乘之機,致使素質教育名亡實存。大學中,專業教育“特立獨行”的慣性也相當程度地被保持著,專業化、技術化、模式化、功利化的傾向尚未得到修正,專業知識的灌輸和專業能力的培養始終占據不可撼動的至尊地位。相比之下,通識教育及其課程的開設僅是輔助或補充。事實表明,這種“生產流水線式”的教育或經由裁剪的教育,一方面造就了大批高層次專業人才,以及在考試中“游刃有余”、善于“披荊斬棘”的“學霸”;另一方面也“產出”了不少“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或者靈魂貧瘠的“機器人”。人是一種整全性存在,是一種集合自然性與社會性、肉體與靈魂、感性與理性、情欲與理智等多重矛盾關系的統一體。教育理當尊重、呵護、捍衛人的整體性、統一性和辯證性,否則人就不能被稱為完全意義上的人。尤其是靈魂的貧瘠或缺失,關系到人的失落、瓦解,以及整全性、統一性的破壞。沒有靈魂的軀體無異于行尸走肉。
學生靈魂的填充和豐實是多入口和多途徑的,而有些入口或途徑尤為重要和關鍵。目前來看,最需要重視的是師生之間的平等對話與溝通,即師生需要從單向的“獨白式說教”步入雙向的“對話式交流”,邀請對方走進自己的內心世界和靈魂深處。誠如此,將意味著“學生的教師”或“教師的學生”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學生式教師”或“教師式學生”,即“通過對話,學生的老師和老師的學生之類的概念不復存在,一個新名詞產生了,即作為老師的學生或作為學生的老師。在對話過程中,教師的身份持續發生變化,時而作為一個教師,時而成為一個與學生一樣聆聽教誨的求知者,學生也是如此。他們共同對求知過程負責”[11]80。教育從“單向度理性塑造人”轉向“雙向互動實踐生成人”,讓學生在師生平等對話與溝通中生成自我,在自主行動與探索中創造自我。
總而言之,教育并不只是單純的知識或專業教育,靈魂的塑造也絕非僵硬的說教和聽從能夠實現的。教育必須以豐富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存本真為根,在師生的雙向奔赴中走出外在化和空心化的窠臼。強行“灌注”的專業教育或知識技能教育只能給學生體內裝上一堆沒有溫度的“知識石塊”,而且彼此之間常缺乏關聯,不僅于靈魂和涵養無益,還會導致學生無法學以致用。
四、照亮學生升華境界
境界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無事不在。大境界惠澤整個人生,不僅關乎個人的快樂和幸福,也關系到周遭人的快樂和幸福。大境界是一種覺悟和修為,也是一種正能量和積極力。自古以來,有思想、有能力、有作為者不乏其人,然而有大境界者寥若晨星。
人要有境界,每個人當為有境界之人。人生之路漫漫且瞬息萬變,絕非一條行云流水的坦途。在人生這條路上,每個人難免會遇到林林總總的拐點和岔路,踏上形形色色的征程和路途。這些路有時直,有時彎;有時寬,有時窄;有時順暢,有時受阻。人有時走在林蔭大道上,有時步入田間小徑,有時踏上崎嶇山路,有時又會誤入那泥濘不堪、步履艱難的窮途和險途……而且,何時啟程又何時結束,往往非人力所能完全掌控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就無可作為,只要有“長風破浪、直掛云帆”的勇氣和魄力、“一路風景一路歌”的安之若素和處變不驚,林蔭大道和田間小徑自有它的春陽如沐、微風習習,而崎嶇山路甚至所謂的“窮途末路”也可能“峰回路轉”,在“山重水復”中邂逅“柳暗花明”。如果我們理解生命的意義、悟得生命的真諦,歧路也有別樣的收獲與光景。無論走在什么樣的路上,學會體驗、品嘗、欣賞和享受才是“真理”:在直時體悟直,在彎時欣賞彎;在寬時感受寬,在窄時體驗窄;在受阻時經受逆境的洗禮,在順暢時享受遂愿的幸福。正如赫拉克利特在論證辯證法時所言:“結合物是既完整又不完整,既協調又不協調,既和諧又不和諧,從一切產生出一,從一產生出一切。”[12]23-24面對生活世界,我們應當把完整與不完整、協調與不協調、和諧與不和諧等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使不同的音調合奏出最美、最和諧的旋律。這就是境界,教育理當為之開道、鋪路和奠基。
蒙培元曾言:“中國傳統哲學都是人生境界之學。”[13]23在此背景下,我們需要借鑒其中的優秀思想,返本開新,為新時代的“境界教育”提供養料。尤需指出的是馮友蘭的“四境界說”(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分別從生物本能、物質利己、社會利他、宇宙覺解的范疇理解和探求人生的意義與價值。雖然有學者認為該理論存在“根本性迷失”,即“由于主觀覺解支撐起的境界實質上只是一種虛無的心靈體驗,從而造成了主體內在精神境界與客觀人生實踐的脫節;由于對理、道體及宇宙等范疇中人性道德內涵的徹底抽空,又導致了其本體與境界的完全斷裂”[14],但不能否認,該理論對于形塑當代人的心靈境界仍有不容小覷的指導價值。置于當代語境下,胸懷、責任感和使命感當屬境界的要義,也是孕生境界的土壤,甚至與境界具有“同質性”和“同構性”。其中,胸懷與具有宇宙人生覺解、自詡“宇宙一分子”的天地境界相通,責任感和使命感則內含社會性和利他性的道德意味。三者都有層次之分,大胸懷、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大境界。對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指出:“教育必須教導人們學會如何在承受壓力的地球上生活;教育必須重視文化素養,立足于尊重和尊嚴平等,有助于將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結為一體”“促進正義、社會公平和全球團結”[15]3。這無疑是對“何為大胸懷、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的詮釋,暗含服務“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大境界。
五、點燃學生延拓生命
人是自然的存在,也是超自然的存在,還是生命長度與厚度相統一的整體性存在。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并非只有一種。有人將生命劃分為自在生命和自為生命[16];有人則將生命劃分為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價值生命和智慧生命[17]71;還有人將生命劃分為肉體生命、精神生命和社會生命[18]。
延拓生命是每個人的夙愿。生命之長并非長壽,延拓生命也并非延拓壽命,意義才是生命的底蘊。人的一生是一種成人的過程、一種生命綻放的過程、一種實現人生價值的過程。人的生命意義正是源自這種“成人、生命綻放和人生價值”的實現,這也是生命延拓的要義。學生是一個發展中的人,一個完整的、具有獨立意義且尚未完全長成的人,更需要通過教育使其向著未來延長與拓展生命,敞開解構與建構自我,不斷實現自身的意義與價值。
生命的延拓要求每個人都要遵從自己的內心,活出個性、底色和精彩,否則全人類的解放、自由和幸福就是一句空話。世界萬物都是個性化的,世界也因為萬物的個性化而多姿多彩,因為萬物的多姿多彩而魅力無窮。自然世界是多樣化的,人類社會也需要多樣化,人類社會的多樣化又根源于人的個性化。為了實現人的個性化,教育不能是產品加工,不能按照固定的模具進行批量生產,而要遵從每個人的天賦塑造不一樣的人才。學校或教師一廂情愿設計的“軌道式教育”,在根本上無視了學生的天賦,這無異于“讓魚高飛、讓鷹鳧水”。教育要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生也要允許自己成為自己。人只有成為自己,而非任何“第二個誰”,才能活出風格、活出優雅、活出美麗、活出價值。我們反對學生的同質化和去個性化,而主張尊重每一位學生的興趣和愛好,發現和釋放每一位學生的天賦和潛能,創造最佳的教育環境讓學生在自己最感興趣和最有天賦的領域或方面充分發展。
生命的延拓意味著“生命之花”的現實綻放。存在主義認為“存在先于本質”,生命在體驗中綻放,人生意義在體驗中彰顯。換言之,生命質量的滋養、生活意義的獲得,只有回歸“現實生活世界”才能實現,只有建構“可能的生活世界”才能達成。每個人的生命意義與價值、生命靈動與創造,都是在“認識你自己”中孕育和生成、在社會實踐中彰顯和釋放的。每個人都在現實社會中定型,在現實社會中實現社會化。整個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每個人都是在社會關系中實現生命的綻放的。對此,西班牙大提琴家、指揮家帕布羅·卡薩爾斯(Pablo Casals)有言:“我們應將全人類視為一棵樹,而我們自己就是一片樹葉。離開這棵樹,離開他人,我們無法生存。”[15]12從該意義上看,沒有“我們的意義與價值”就沒有“我的意義與價值”,“我的意義與價值”存在于“我們的意義與價值”之中。“認識我自己”必須先認識“我們”,而“認識你自己”也要先了解“你們”。當然,“我”與“我們”是相互消解的,一個個“我”的離去消解了“我們”,而“我們”的存在又消解著一個個的“我”;“你”與“你們”也是相互消解的,一個個“你”的離去消解了“你們”,“你們”的存在又消解著一個個的“你”。可見,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是綜合性、整體性、系統性和整生性的,人與人相互聯結在一起,成就各自的意義與價值。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體驗,體驗即教育。教育不只是求知,也不只是“為求知而求知”。教育不只是在知識的海洋里暢游、在知識的森林中漫步、在知識的太空中翱翔,還求真、求善、求美、求益和求宜。教育是可見、可感、可悟的真實生活,是尚個性和尊自由的自主生活,是注視當下和觀照未來的此刻生活,是意義與價值齊頭并進的整體生活。學生是活的存在,只有在生活世界才能感知自己,也才能活出意義與價值。教育不能犧牲當下的生活來換取未來的生活,不能犧牲今天的幸福來換取明天的幸福。受教育不只是為了獲取一張“學歷文憑”,也不只是為了謀求一張特殊的“營業執照”,而是出于增長自身的知識、發展自身能力和提升自身的素養的需要,為了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為了自由地生活在真實世界里。總之,教育理當是一種真實生活,一切學子都理當回到真實的生活世界中去珍惜、呵護、尊重、享受、升華自己的生活,在真實生活中從經驗世界走向理性世界,從現象世界走向本質世界,從有形世界走向無形世界,從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在真實生活中品嘗教育的全過程,體驗人生的每一次“再出發”。
六、結語
“教育如何以人為本”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即便是同一個人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也會給出不一樣的答案。這個問題源于“人到底該如何發展”和“社會究竟需要怎樣的人”。其中,“人到底該如何發展”是根本的,但要受到“社會究竟需要怎樣的人”的影響;“社會究竟需要怎樣的人”是重要的,卻要受到“人到底該如何發展”的規約。與此對應,教育既要適應人的全面發展需要,也要適應社會發展需要。這是追問“教育如何以人為本”的基調。
一切教育皆是特定時空下的教育,我們需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地對“教育如何以人為本”作出認識與行動上的抉擇。從人學視角來看,我們需要自我塑造的教育、謀求幸福的教育、豐實靈魂的教育、升華境界的教育、延拓生命的教育。毫無疑問,這只是基于當前的某些教育缺失且從人學視角對理想教育的“一種追問”,并未囊括教育的所有“應然態”,也并不意味著全盤否定當前教育的所有“實然態”。譬如,在肯定和強調自我塑造的同時,來自教師、學校、家長等外力的塑造同樣不可或缺;在強化通識教育、情感教育、快樂教育、幸福教育等教育理論或思想的同時,也并不否定知識、技能的授受和練習。無論在任何階段,知識、技能等的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語境下,我們所批判和摒棄的絕不是知識或技能,而是“唯知識”“唯技能”的極端化。另外,正如自我塑造、謀求幸福、豐實靈魂、升華境界和延拓生命的教育并不代表人本教育的全部要義一樣,從人學的視角來理解教育可能是最務本的視角、最必需的視角、最終極的視角,但也絕非唯一的視角或唯一切口。教育的內外部關系規律提醒我們,教育不僅關乎人的發展,而且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歸根結底,教育所培養的人都必須是“社會人”,社會是影響教育如何作為的重要標尺。鑒于此,從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視角來理解教育,同樣不失為應有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