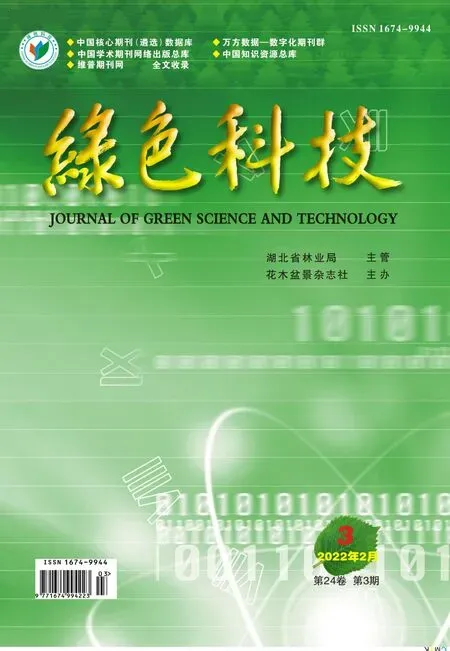大熊貓國家公園社區為主導的自然教育發展模式研究
——以平武縣關壩村為例
何海燕,李芯銳,馮 杰
(1.北京市海淀區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北京 100000;2.綿陽市平武縣白熊谷鄉村旅游開發專業合作社,四川 綿陽 622550)
1 引言
大熊貓國家公園是由國家批準設立并主導管理,邊界清晰,以保護大熊貓為主要目的,實現自然資源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陸地區域,具有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完整性,同時兼具科研、教育、體驗等綜合功能。在《大熊貓國家公園總體規劃》(試行)中明確提出通過“合理設置崗位,安置原住居民從事自然教育、生態體驗以及輔助保護和監測等工作”[1],實現自然保護與社區建設的共贏發展。自然教育作為一種新型的教育發展模式,有助于培養社會公眾的自然環境保護意識和責任感,是踐行生態文明思想,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進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2]。開展以社區為主導的自然教育是順應大熊貓國家公園建設,促進社區生計轉型,實現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將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路徑之一。
近年來,不少學者和基層實踐者對國家公園自然教育發展進行相關研究,李杰對大熊貓國家公園佛坪分局自然教育進行了分析,提出以科研轉化促進自然教育發展[3];馮科根據SWOT分析,梳理了長青保護區自然教育的對策建議[4];張會文梳理了大熊貓國家公園白水江分局自然教育的方法、成效和思考[5],劉俊分析了臥龍保護區開展自然教育的模式[6],黃驍從規劃設計的角度闡述了自然教育和生態體驗的發展思路[7],余孟韓提出自然教育對鄉村建設具有積極作用[8],唐藝挈從運營管理、場地設施、產品服務以及課程教材等方面構建了大熊貓國家公園自然教育體系[9],趙敏燕提出五位一體的自然教育功能的環境解說系統[10],崔慶江通過實證分析提出目前大熊貓國家公園公眾體驗普遍缺乏“教育、游憩、社區參與功能”等功能[11]。這些研究從保護區發展、設計規劃、鄉村治理、體系構建等視角探討了大熊貓國家公園自然教育的發展路徑,但是缺乏社區視角,尤其是缺乏社區參與大熊貓國家公園自然教育發展的案例分析。為此,本文將基于社區視角,從關壩村以社區為主導的自然教育發展案例入手,分析模式、成效和總結建議,以期對大熊貓國家公園社區發展提供參考。
2 大熊貓國家公園社區發展現狀
2.1 原住民數量龐大,社區參與問題突出
大熊貓國家公園總面積27134 km2,涉及152個鄉鎮12.08萬人,有藏族、羌族、彝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侗族、瑤族等19個少數民族。原住居民數量龐大,歷史遺留問題較多,社區是大熊貓國家公園建設難點和問題。大熊貓國家公園以原有大熊貓保護區為基礎,同時將國有林、集體林以及社區擴展進來,形成保護地和社區空間接壤重疊、資源相互交錯、利益共享自然生態與社會經濟相互影響的保護格局,對大熊貓國家公園管理而言,社區是繞不開和離不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長期以來,社區居民和自然資源被統一視為管理對象,忽視了社區作為資源管理與利用的主體地位,導致社區參與動力不足、參與層次較低、參與態度消極、參與機制薄弱,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貓國家公園“社區協調發展”的原則和體制試點建設要求。
2.2 傳統資源利用方式突出,生計水平較低
大熊貓國家公園內整體經濟收入水平總體較低,地方經濟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其中包括平武縣在內的15個縣(區)是我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縣和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主要依靠財政轉移支付,相對貧困特征突出。長期以來,大熊貓國家公園范圍內普遍形成了自然資源依賴的初級產業結構,傳統種養殖收入是當地社區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原始粗放型的資源利用方式突出,長期陷于區域性經濟落后,收入水平較低的發展狀態[12],形成了一定的生態貧困困境。
2.3 生態價值實現程度較低,負外部性突出
在大熊貓國家公園中社區往往處于自然生態資源豐富和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的重疊區域,當地自然資源豐富,但卻長期處于貧困狀態,相關的保護政策雖然對國家生態安全、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環境等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性,但是當地社區承擔了保護的成本,影響了社區發展經濟、利用自然資源的公平權利[13]。大熊貓國家公園內較高的生態價值沒有得到有效轉化,尤其是當地社區沒有獲得與之投入相匹配的生態產品收益[14]。整體而言,大熊貓國家公園社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程度較低,僅停留在第一產業,規模較小,實現機制單一,獲益人群有限。
3 區域概況
3.1 社區概況
關壩村位于綿陽市平武縣木皮藏族鄉,全村總面積98 hm2,其中林業用地3880.9 hm2,占總面積的96.3%。該村原屬于貧困村(已脫貧),轄4個村民小組共121戶,分布有藏族、苗族、羌族等少數民族。中蜂養殖和核桃、藥材種植是當地傳統生計方式。在地理區位上,關壩村位于大熊貓國家公園范圍內,處于大熊貓分布范圍較廣的岷山山系大熊貓A種群,是國家發布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中35個生物多樣性優先區域。根據全國大熊貓第四次調查分析,在關壩村的生產生活區域內,大熊貓種群密度為0.06~0.2只/km2,屬于中密度分布,預估溝內熊貓數量在4~7只左右,是重要的大熊貓棲息地以及走廊帶。
3.2 資源條件
關壩村自然生態環境較好、野生動植物資源種類豐富,分布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大熊貓、羚牛、川金絲猴、金貓,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水獺、斑羚、黑熊等,國家一級保護植物有紅豆杉和珙桐等。當地民族文化濃厚,具有白馬藏族、白熊部落以及土司歷史文化資源,同時長期的人與自然互動過程中形成了以中蜂養殖和庭院經濟為主的傳統農耕文化資源。2009年關壩村成立森林巡護隊,開始了社區自發性的生態保護工作;2018年關壩村上線螞蟻森林公益保護地,形成了一定的社會資源和公眾吸引力。自然、文化、社會和社區等資源為關壩村自然教育活動的開展提供了多元化的素材和天然的場所,是關壩自然教育發展的基礎。
4 模式與做法
為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將關壩村良好的資源優勢和長期的社區保護行動轉為高質量、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在大熊貓國家公園建設的背景下,2018年關壩村開始探索以社區為主導的自然教育,探索保護與發展共生模式。
4.1 模式
目前,關壩村形成了“一核多元”的自然教育發展模式(圖1)。具體內容是:社區以合作社為自然教育管理運行的主體,基于合作社的經濟功能與自然教育行業機構以及社區農戶開展合作,形成上下游產業鏈。合作社通過利益反哺和自然教育活動推動社區保護工作,保護中心結合巡護監測工作為自然教育提供活動內容、場地以及人員,在村內形成保護組織和發展組織之間相互支撐與內循環的關系。政府部門通過政策支持,為社區自然教育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合作社通過二次分配實現全村收益,促進社區發展。最終形成多個利益相關者充分參與且充分受益的格局,通過以社區為主導的自然教育發展模式,構建經濟社會和生態保護的統一。

圖1 關壩村以社區為主導的自然教育發展模式
4.2 主要做法
4.2.1 調查規劃
關壩村先后從產業發展需求、自然教育資源稟賦、社區接待能力、保護發展協調關系等多個方面出發,規劃了《關壩保護小區生態產業及生態旅游概念方案》《四川平武縣關壩村保護與發展指導原則與要求》,同時開展關壩村自然教育調查等,為關壩村自然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4.2.2 組織構建
在關壩村“兩委”的領導下,成立“平武縣白熊谷鄉村旅游開發專業合作社”,以合作社作為集體經濟的組織載體。通過多次社區會議,由利益相關方共同制定旅游合作社的管理模式和利益分配制度。由村民大會選舉成立旅游合作社管理團隊,在對外合作、后勤管理、能力培訓等方面進行分工。合作社作為社區自組織之一,通過社區參與實現社區管理的主體性,這是社區發展自然教育的核心。
4.2.3 能力建設
在社會組織和當地政府的支持下,針對社區不同利益相關者參與,開展不同類型的能力建設。關壩村旅游合作社管理團隊、接待戶等多次外出考察學習管理經營、接待服務;關壩村巡護隊員參與自然導賞培訓,學習自然解說、課程設計和野外救助;關壩村村委考察學習社區參與和集體經濟等內容。能力建設在開拓眼界、提高專業知識能力水平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4.2.4 課程設計
開發具有本土特色的自然教育課程是以社區為主導的自然教育模式的核心競爭力。關壩村自然教育課程開發最大化的利用了當地環境、資源、人力和現有場地等要素,整合了生態保護理念與當地文化、社會、產業等資源關系,尤其是圍繞著生態保護主題的課程成為當地自然教育活動的主要內容。這是在自然教育中體現并回應大熊貓國家公園保護目標的重要環節。
4.2.5 利益分配
通過合作社,自然教育收入在社區內部的分配包括基本收益、激勵收益以及二次分配3個方面。直接參與自然教育活動的村民將獲得相應的基本收入,同時根據參與者的反饋評估情況獲得一定的經濟激勵。自然教育純利潤的20%用于全村普惠,50%用于合作社管理團隊勞務,15%反哺給關壩保護中心用于保護工作,15%形成旅游合作社發展風險基金。社區利益分配體現大熊貓國家公園促進原住民參與和收益的重要目標,也是平衡社區保護與發展內生關系的重要手段。
5 成效分析
5.1 經濟效益
自然教育在社區發展中作為一種產業類型,能夠形成集餐飲、住宿、導賞、體驗為一體的第三產業鏈,由于第三產業往往具有較大的乘數效益,能夠產生較大的經濟效益。2018~2021年底,關壩村共開展自然教育活動約18次,累計到關壩村參與自然教育活動的人數達500余人次,收入約24萬元,全村約50余名村民直接或間接參與到自然教育活動中,間接帶動當地5萬元的蜂蜜、核桃、山野菜等農產品收益。社區開展自然教育活動,涉及層面廣泛、參與性強,能夠帶動更多社區多層次、多環節收益,有效促進了生計轉型發展。
5.2 生態效益
關壩村基于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自然教育是大熊貓國家公園社區參與自然資源有效保護與合理利用的有益探索。自然教育本身帶有生態保護的使命,是一種保護的手段。通過自然教育引導可以使參與者形成尊重自然且對社區負責任的行為[15]。通過自然教育讓85%的本地村民意識到優質的生態環境與較高的經濟收入掛鉤,增強社區的生態保護意識,2018~2021年關壩旅游合作社向保護中心反哺生態資金8350元,通過二次利益分配實現經濟對保護的反哺,一定程度上激勵了社區保護行為,森林巡護監測達450人次,極大的促進了社區保護工作。同時不少自然教育體驗者也通過保護地文創設計、生態宣傳、巡護監測以及人獸沖突圓桌會議等方式共同參與到關壩保護地自然保護問題的解決之中。
5.3 社會效益
自然教育要素眾多、內涵豐富,是社區產業、文化、自然、人才、組織等各方面的集合,是助推鄉村振興的重要載體。通過自然教育,關壩村獲得當地政府和社會關注,將“三月三蜂王節”“白熊部落文化”等傳統活動以民俗節慶的方式進行傳承;全村共多名返鄉青年進行合作社、保護中心等社區自組織建設;促進約30名社區婦女自發性成立關壩舞蹈隊,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服務于社區自然教育活動;對外進行不低于200人次的活動宣傳等等。通過自然教育構建起社會組織、社會企業、志愿者、自然教育參與者等多利益相關群體共同支持的社會網絡系統,促進社區社會長遠發展。
6 總結與建議
社區是大熊貓國家公園建設中不可忽視的主體之一,自然教育是尊重社區自然資源使用權的重要體現。以社區為主導的自然教育具有多重目標和效益,既可以實現社區的協調發展,也能服務于生態保護目標,它能夠通過市場化的形式促進大熊貓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的有效轉化,在協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實現從自然資源到社會服務價值和經濟價值有機轉化上具有獨特優勢。但同時,以社區為主導的自然教育發展依然面臨著社區導賞能力不足、組織能力有限、市場參與不足、保障機制薄弱等問題,導致社區自然教育發展緩慢,受益機會較少。因此,基于今后社區自然教育發展提出以下策略。
6.1 提高社區自然教育的組織管理能力
社區自然教育需要長期的能力建設和開放合作,提高社區開展自然教育的組織管理能力和業務水平。建立可持續的社區自然教育管理模式和利益分配模式,放權給村級自然教育發展組織,讓自組織擁有更多的自主性和主體性,參與市場競爭增強活力;動員社區的廣泛參與,識別社區內的巡護隊員、手工藝人、耕作勞動者等,培育不同活動類型和組織管理的社區人才,實現社區賦能。積極加強與政府、學校、自然教育商業機構、社會組織等橫向合作,構建多樣化的自然教育發展模式,增強市場抗風險能力。
6.2 強化以資產為本的自然教育發展路徑
以社區為主體的自然教育發展需要深度挖掘社區的資產和資本,以當地生態自然資源、歷史遺跡、社區人力資源、人文風情為基礎,不斷形成具有社區特色的課程內容。針對不同的目標人群和市場需求提供差異化和定制化的自然教育產品,增加自然教育的體驗環節和內容。在持續增加吸引力的同時延長社區環節參與的時間,實現收入的多樣性,擴大社區受益人群。
6.3 促進社區自然教育與大熊貓國家公園政策相結合
自然教育是大熊貓國家公園建設的重要內容,尤其是以社區為主體的自然教育發展需要與社區協調發展、特許經營、大熊貓國家公園入口社區建設以及生態公益崗位等內容相結合,發揮國家公園、地方政府、社會組織、社區治理、企業參與等多主體的功能和作用,真正將自然教育內化為地方和國家公園的發展內容之一,構建良好的外部環境和保障機制,從而促進可持續發展。這對大熊貓國家公園社區的發展意義深遠,這些也將在今后進一步地影響自然教育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