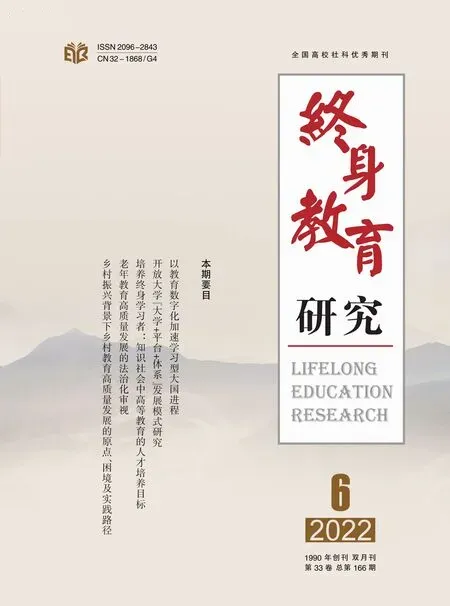培養(yǎng)終身學(xué)習(xí)者:知識(shí)社會(huì)中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biāo)
□戴子涵
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和普及化,推動(dòng)“雙一流”建設(shè)成為我國(guó)現(xiàn)階段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戰(zhàn)略選擇,而人才培養(yǎng)則是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根本目標(biāo)與改革的重中之重。黨的十九大要求“加快一流大學(xué)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實(shí)現(xiàn)高等教育內(nèi)涵式發(fā)展”,其中“人才培養(yǎng)始終是改革發(fā)展的著力點(diǎn)”;2018年印發(fā)的《關(guān)于高等學(xué)校加快“雙一流”建設(shè)的指導(dǎo)意見(jiàn)》明確了“雙一流”建設(shè)要“引導(dǎo)學(xué)生成長(zhǎng)成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養(yǎng)體系、培養(yǎng)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要求充分發(fā)揮高等學(xué)校的育人功能,落實(shí)立德樹(shù)人的根本任務(wù)。黨的二十大報(bào)告強(qiáng)調(diào)了要加快建設(shè)高質(zhì)量教育體系。“我們要建設(shè)的高質(zhì)量高等教育體系是培養(yǎng)高水平人才的體系,也是服務(wù)全民終身學(xué)習(xí)的體系”,這要求高等教育加快實(shí)現(xiàn)人才培養(yǎng)的格局性變化。但事實(shí)上,無(wú)論是國(guó)際組織中的“代表性缺失”,還是在高校審核評(píng)估中學(xué)生培養(yǎng)效果的被質(zhì)疑,都反映出“高校的人才培養(yǎng)是我國(guó)高等教育改革與發(fā)展中的短板”這一重大問(wèn)題。[1]可以說(shuō),過(guò)去高等教育對(duì)“高級(jí)專(zhuān)門(mén)人才”的培養(yǎng)指向已經(jīng)不足以應(yīng)對(duì)不斷變革的社會(huì)需求,因此,推進(jìn)以一流人才培養(yǎng)為根本的雙一流建設(shè)需要從當(dāng)下知識(shí)社會(huì)的時(shí)代特征出發(fā),澄清終身學(xué)習(xí)趨勢(shì)下高等教育所能發(fā)揮的獨(dú)特價(jià)值,探究能夠回應(yīng)新的時(shí)代和社會(huì)需求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biāo)及其實(shí)踐路徑,從而助力高等教育的縱深發(fā)展與人才培養(yǎng)的提質(zhì)增效。
一、知識(shí)社會(huì)中重新審視大學(xué)①的人才培養(yǎng)使命
管理學(xué)家德魯克(Peter F.Drucker)是最早窺見(jiàn)工業(yè)時(shí)代向知識(shí)時(shí)代變革趨勢(shì)的人之一,他指出:在過(guò)去的一百多年里,隨著從“道”轉(zhuǎn)變?yōu)椤捌鳌钡闹R(shí)相繼催生了工業(yè)革命、生產(chǎn)力革命和管理革命,基于資本、土地和勞動(dòng)力的社會(huì)正在逐步轉(zhuǎn)向以知識(shí)作為主要資源、以組織作為核心結(jié)構(gòu)的社會(huì),即知識(shí)社會(huì)(knowledge-based society)。[2]近幾十年來(lái),他對(duì)知識(shí)社會(huì)的大膽預(yù)測(cè)已經(jīng)在知識(shí)經(jīng)濟(jì)的推進(jìn)下成為現(xiàn)實(shí):“今天的工業(yè)生產(chǎn)由以物質(zhì)生產(chǎn)和勞動(dòng)力為主的產(chǎn)品平穩(wěn)地向以知識(shí)為主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轉(zhuǎn)移,新知識(shí)的創(chuàng)造與應(yīng)用成為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cái)富的最新形式,在這個(gè)時(shí)代,智力資本與人力資源成為力量、繁榮與富裕的源泉,社會(huì)更加關(guān)注知識(shí)、更加依賴(lài)于創(chuàng)造知識(shí)的社會(huì)機(jī)構(gòu)。”[3]盡管尚未形成一個(gè)非常完備的知識(shí)社會(huì)的概念,但當(dāng)今時(shí)代進(jìn)入以知識(shí)為主要驅(qū)動(dòng)力的全球型知識(shí)社會(huì)已經(jīng)成為一種共識(shí)。而步入知識(shí)社會(huì)對(duì)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yǎng)而言有更深層次的意義。一方面,大學(xué)自誕生起就與知識(shí)有著天然而緊密的關(guān)系,其人才培養(yǎng)職能的發(fā)揮始終圍繞著知識(shí)及知識(shí)功能展開(kāi),知識(shí)社會(huì)中知識(shí)生產(chǎn)和傳播的變革必然引起大學(xué)人才培養(yǎng)的根本轉(zhuǎn)型;另一方面,隨著現(xiàn)代以來(lái)與社會(huì)聯(lián)結(jié)愈發(fā)緊密,大學(xué)普遍被認(rèn)為是“在人力資源上社會(huì)投資的最佳途徑”,在培養(yǎng)社會(huì)所需要的人才方面被賦予了越來(lái)越多的責(zé)任。因此,深入探查知識(shí)社會(huì)對(duì)大學(xué)功能的影響,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時(shí)代大學(xué)的人才培養(yǎng)使命。
從歷史來(lái)看,不同時(shí)期和國(guó)家的大學(xué)在以知識(shí)為核心的人才培養(yǎng)中所發(fā)揮的具體職能并不一致。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指出,作為知識(shí)大復(fù)興時(shí)期的產(chǎn)物,中世紀(jì)的大學(xué)是一種制度:它首先是“教師和學(xué)生組成的社團(tuán),他們過(guò)著共同的知識(shí)生活”,其次是“學(xué)習(xí)課程概念,明確制定學(xué)習(xí)的時(shí)間和科目,借助考試測(cè)驗(yàn)成績(jī),方可獲得一個(gè)學(xué)位”,最后是系科和學(xué)院。[4]可以說(shuō),大學(xué)最初的主要職責(zé)是通過(guò)知識(shí)培養(yǎng)學(xué)者、通過(guò)知識(shí)傳承學(xué)習(xí)和研究的傳統(tǒng)。此后,紐曼(John Henny Newman)宣揚(yáng)了著名的“知識(shí)本身就是目的”的大學(xué)理念:“它是教授全面知識(shí)的地方。這說(shuō)明了它的宗旨,一方面,是心智性的而非精神性的;另一方面,是對(duì)知識(shí)的普及和擴(kuò)展而非提高。”[5]這種理念很好地反映了當(dāng)時(shí)以牛津大學(xué)為典型的英國(guó)傳統(tǒng)大學(xué)以教學(xué)為核心要?jiǎng)?wù)的狀況,此時(shí)大學(xué)的核心要旨在于通過(guò)教授和傳播普遍知識(shí)以培養(yǎng)心智完善之人,也因此逐漸承擔(dān)起知識(shí)的集聚和保存職責(zé),而以研究為主要途徑的知識(shí)生產(chǎn)則被排除在主要職能之外。
然而,幾乎與紐曼同時(shí),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帶領(lǐng)柏林大學(xué)開(kāi)創(chuàng)了“研究型大學(xué)”的先河,提出大學(xué)是“帶有研究性質(zhì)的高等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的理念。洪堡對(duì)19世紀(jì)以前大學(xué)的單一教學(xué)職能提出了異議,認(rèn)為大學(xué)具有科學(xué)探索(即研究和發(fā)展純科學(xué))和個(gè)性與道德養(yǎng)成(即培養(yǎng)青年人)的雙重職能,其統(tǒng)合原則是“由科學(xué)而達(dá)至修養(yǎng)”,也就是說(shuō),人才培養(yǎng)是在發(fā)展科學(xué)的過(guò)程中實(shí)現(xiàn)的。[6]這種強(qiáng)調(diào)原創(chuàng)性研究、專(zhuān)注于知識(shí)生產(chǎn)的理念使得德國(guó)大學(xué)成了典型的“從事高深學(xué)問(wèn)的機(jī)構(gòu)”。然而,隨著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越來(lái)越密切,大學(xué)的知識(shí)職能所涉的范圍很快就超出了紐曼和洪堡的論述所及。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抱怨1930年時(shí)作為有機(jī)整體的大學(xué)已經(jīng)解體:“它們是中學(xué),是職業(yè)學(xué)校,是師范學(xué)校,是研究中心,是‘社會(huì)事業(yè)’機(jī)構(gòu),是企業(yè)——同時(shí)是這些事物和其他事物。”[7]20世紀(jì)初,范·海斯(Charles Richard Van Hise)領(lǐng)導(dǎo)下的威斯康星大學(xué)通過(guò)向社會(huì)推廣技術(shù)和知識(shí),為政府部門(mén)提供專(zhuān)家咨詢(xún)服務(wù)等使大學(xué)與政府部門(mén)、社會(huì)間建立了雙向的合作與服務(wù)關(guān)系。[8]隨著世俗化與普及化程度迅速提升,克爾(Clark Kerr)提出的以美國(guó)大學(xué)為典型的“巨型大學(xué)”概念成為當(dāng)今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學(xué)形象。大學(xué)開(kāi)始成為“一個(gè)不 一 致 的 機(jī) 構(gòu)”[9]10“一 個(gè) 變 化 無(wú) 窮 的 城市”[9]23,“多元性”成為其本質(zhì)特征:它有若干群體、若干目標(biāo)、若干權(quán)力中心,沒(méi)有明顯固定的客戶(hù),不再是一個(gè)有機(jī)體。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現(xiàn)代大學(xué)不僅繼承了關(guān)于知識(shí)的四個(gè)核心職能,即“通過(guò)研究推進(jìn)知識(shí)、通過(guò)教學(xué)傳授知識(shí)、以學(xué)者著作保存知識(shí)、通過(guò)出版?zhèn)鞑ブR(shí)”,[10]還逐漸拓展出其他知識(shí)職能,如知識(shí)的轉(zhuǎn)化與應(yīng)用功能,即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為國(guó)家安全和社會(huì)富強(qiáng)提供智力與人力資源等。但無(wú)論如何變遷,大學(xué)始終通過(guò)知識(shí)來(lái)培養(yǎng)人,知識(shí)始終是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核心所在。
然而,隨著知識(shí)社會(huì)的到來(lái),知識(shí)生產(chǎn)、傳播乃至應(yīng)用的新模式和新特征對(duì)大學(xué)傳統(tǒng)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造成了重大沖擊。第一,在知識(shí)數(shù)量不斷激增、內(nèi)涵不斷復(fù)雜化、更新?lián)Q代速度越來(lái)越快的背景下,大學(xué)在確定知識(shí)的傳授方面發(fā)揮的作用愈發(fā)受到質(zhì)疑,甚至其本身不再是知識(shí)生產(chǎn)的唯一陣地。對(duì)此不少學(xué)者給出了質(zhì)疑的理由:“很難說(shuō)大學(xué)有能力生產(chǎn)和駕馭新的、社會(huì)分散化的知識(shí)……在新的大眾化階段,大學(xué)不能保證學(xué)生獲得‘特權(quán)’知識(shí),因?yàn)檫@樣的知識(shí)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11];“以自反性、跨學(xué)科性和多樣性為特征的新的知識(shí)生產(chǎn)模式使得現(xiàn)代大學(xué)就不再是知識(shí)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支配者,并且其地位不斷下降”[12]144。因此,知識(shí)社會(huì)中的大學(xué)不能也不應(yīng)僅僅依賴(lài)作為工具的知識(shí)進(jìn)行人才培養(yǎng),因?yàn)椤肮ぞ摺北旧硪呀?jīng)逐漸失去其完備性和確定性。第二,在信息技術(shù)和消費(fèi)邏輯的加持下,知識(shí)已經(jīng)變成了大眾共享、唾手可得的資源,越來(lái)越多專(zhuān)門(mén)化或私有化的新型知識(shí)機(jī)構(gòu)也因此不斷興起,這使得高等教育失去了對(duì)知識(shí)資源的集體壟斷權(quán),喪失了曾經(jīng)對(duì)專(zhuān)業(yè)技能與能力標(biāo)準(zhǔn)的決定權(quán)。正因如此,高等教育被要求以適當(dāng)?shù)姆绞阶C明在這樣一個(gè)“知識(shí)碎片化、永恒價(jià)值受到挑戰(zhàn)、多元主義相對(duì)主義盛行”的時(shí)代中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尤其是在人才培養(yǎng)方面的獨(dú)特價(jià)值。第三,知識(shí)成為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主要驅(qū)動(dòng)力和新的生產(chǎn)力,由此而來(lái)的“知識(shí)價(jià)值革命”撼動(dòng)了大學(xué)中傳統(tǒng)的知識(shí)等級(jí)及基于此的人才培養(yǎng)取向。當(dāng)今高等教育領(lǐng)域在產(chǎn)學(xué)研合作以及大學(xué)、政府與企業(yè)的三重螺旋互動(dòng)關(guān)系過(guò)程中開(kāi)始高度重視知識(shí)的應(yīng)用,學(xué)術(shù)資本主義開(kāi)始成為許多研究型大學(xué)發(fā)展的新理念。[13]但這也帶來(lái)了學(xué)界對(duì)高等教育使命的深入追問(wèn),如米特爾曼(James H.Mittelman)對(duì)21世紀(jì)取代了高等教育“三位一體的教育使命”(即培養(yǎng)公民意識(shí)、培養(yǎng)批判性思維和保障學(xué)術(shù)自由)的新功利主義進(jìn)行了反思,指責(zé)它“優(yōu)先考慮有用的知識(shí)和解決問(wèn)題的技能,而非基礎(chǔ)性的探索;將市場(chǎng)價(jià)值置于教育價(jià)值之上;強(qiáng)調(diào)理性思維,不推崇藝術(shù)、古典語(yǔ)言、歷史和哲學(xué)等其他思辨模式”[14]。
雖然知識(shí)變革帶來(lái)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但這并不意味著大學(xué)不再重要或者應(yīng)當(dāng)被取代。布魯貝克(John Seiler Brubacher)曾指出,20世紀(jì)的大學(xué)依托于兩種哲學(xué)確立其合法性,一種主要以認(rèn)識(shí)論為基礎(chǔ),另一種則以政治論為基礎(chǔ)。前者強(qiáng)調(diào)以“閑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識(shí)作為目的,后者關(guān)注知識(shí)對(duì)國(guó)家的深遠(yuǎn)影響,在很長(zhǎng)的時(shí)間里二者相互沖突引發(fā)了諸多爭(zhēng)議。[15]在他看來(lái),統(tǒng)合兩種高等教育哲學(xué)的最有效方式是以實(shí)用主義的補(bǔ)充為基礎(chǔ)。一方面,知識(shí)經(jīng)濟(jì)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創(chuàng)新的引領(lǐng)作用,無(wú)論是專(zhuān)業(yè)方面還是研究方面對(duì)高深學(xué)問(wèn)的需求都在迅速增長(zhǎng),即使不再是唯一的知識(shí)中心,大學(xué)依然在實(shí)現(xiàn)二者的各自繁榮與相互促進(jìn)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知識(shí)社會(huì)中的工作任務(wù)對(duì)勞動(dòng)者的要求越來(lái)越高,接受高等教育成為普遍需求,而大學(xué)的教育功能發(fā)揮從來(lái)不是僅僅依托于知識(shí)的傳授。正如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說(shuō):大學(xué)的任務(wù)不在于傳授給學(xué)生知識(shí)或提供給教師研究機(jī)會(huì),而在于把青年人和老年人聯(lián)合在對(duì)知識(shí)的富有想象力的思考當(dāng)中,在于使之構(gòu)建新世界的理智見(jiàn)識(shí),并把知識(shí)與經(jīng)驗(yàn)融為整體。[12]20事實(shí)上,當(dāng)其他機(jī)構(gòu)從大學(xué)手中分散了知識(shí)傳播這一功能時(shí),大學(xué)尤其需要重視開(kāi)發(fā)在提供良好教育方面的獨(dú)特之處。當(dāng)今大學(xué)文憑的合法性也說(shuō)明了公眾仍然信任與認(rèn)可大學(xué)在某些非功利性原則的指導(dǎo)下進(jìn)行的教育活動(dòng)。這也使得越來(lái)越多的人認(rèn)識(shí)到,在由知識(shí)驅(qū)動(dòng)、重視智力資源與人力資本的知識(shí)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中,大學(xué)以知識(shí)為核心的各項(xiàng)活動(dòng)正在變得比以往更有價(jià)值,其在培養(yǎng)人與服務(wù)社會(huì)方面的使命變得比以往更為引人注目。
二、培養(yǎng)終身學(xué)習(xí)者:高等教育的時(shí)代回應(yīng)
1.知識(shí)社會(huì)要求培養(yǎng)終身學(xué)習(xí)者
人才培養(yǎng)依然是當(dāng)今大學(xué)的重要使命,其重要性甚至隨著知識(shí)社會(huì)的深入發(fā)展而更加凸顯,這要求我們?cè)诎盐罩R(shí)社會(huì)特征的基礎(chǔ)上重新思考高等教育應(yīng)當(dāng)“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這一根本問(wèn)題,從而為人才培養(yǎng)變革奠定與知識(shí)社會(huì)相匹配的邏輯起點(diǎn)。
知識(shí)社會(huì)帶來(lái)了多樣化的變革,而教育和學(xué)習(xí)正處于核心位置。具體到人才需求方面,知識(shí)社會(huì)在以下三個(gè)方面的變革是尤其需要關(guān)注的。第一,知識(shí)增長(zhǎng)速度和獲取方式的變革要求個(gè)體保持終身學(xué)習(xí)的習(xí)慣以提升知識(shí)辨別力。知識(shí)社會(huì)中,呈現(xiàn)爆炸式增長(zhǎng)而又唾手可得的知識(shí)既給人類(lèi)生活帶來(lái)了更多便捷,也經(jīng)常使得缺乏甄別力的個(gè)體遭遇迷茫。正如格喬伊(Herbert Gerjuoy)所說(shuō),“未來(lái)的文盲將不再是白丁,而是那些從未學(xué)習(xí)‘如何學(xué)習(xí)’的人”,因此當(dāng)前教育“必須教導(dǎo)每個(gè)人精細(xì)地區(qū)別知識(shí),判斷其真實(shí)性,必要時(shí)改變范疇,由具體轉(zhuǎn)為抽象,由抽象還原為具體,以一種新觀點(diǎn)觀察問(wèn)題。”[16]第二,知識(shí)發(fā)生的情境、流動(dòng)狀況以及知識(shí)特性正在變革,知識(shí)社會(huì)中信息更迭速度加快、知識(shí)多領(lǐng)域全景連通、結(jié)構(gòu)化的硬知識(shí)開(kāi)始“變軟”等特征要求個(gè)體具有更高水平的知識(shí)遷移應(yīng)用技能。西蒙斯(George Siemens)指出,知識(shí)變革的特性對(duì)新時(shí)代的學(xué)習(xí)者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如“知識(shí)過(guò)濾”技能,即管理知識(shí)流和提取重要要素的能力;“彼此連通”技能,即建立網(wǎng)絡(luò)以保持知識(shí)的時(shí)代性和熟知性的能力;“知識(shí)定位”技能,即在達(dá)成有意圖的目的時(shí)在知識(shí)庫(kù)、人、技術(shù)和思想之間進(jìn)行知識(shí)定位,等等。[17]毫無(wú)疑問(wèn),無(wú)論是這些技能本身的學(xué)習(xí)還是通過(guò)這些技能展開(kāi)的高質(zhì)量知識(shí)學(xué)習(xí),都是與時(shí)俱進(jìn)而持續(xù)終生的學(xué)習(xí)過(guò)程。第三,知識(shí)生產(chǎn)的模式和重心的變革要求新時(shí)代人才具備與之匹配的新技能以提高知識(shí)生產(chǎn)水平。20世紀(jì)末,吉本斯(M.Gibbons)等人率先指出知識(shí)生產(chǎn)已從模式Ⅰ向模式Ⅱ轉(zhuǎn)型,即從具有高度專(zhuān)門(mén)性、獨(dú)立性、同質(zhì)性的學(xué)院研究的知識(shí)生產(chǎn)模式轉(zhuǎn)向具有一定跨學(xué)科性、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用語(yǔ)境、異質(zhì)性的知識(shí)生產(chǎn)模式。[18]而隨著知識(shí)社會(huì)進(jìn)入深化發(fā)展階段,卡拉雅尼斯(Elias G.Carayannis)等人進(jìn)一步提出了更符合當(dāng)前特征的知識(shí)生產(chǎn)模式Ⅲ,其以“知識(shí)集群、創(chuàng)新網(wǎng)絡(luò)”為核心要素,以“分形研究、教育與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為主體系統(tǒng),以“四重螺旋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為動(dòng)力機(jī)制,對(duì)人才培養(yǎng)的創(chuàng)新性和創(chuàng)造力提出了更高要求。[19]對(duì)于從事知識(shí)生產(chǎn)者而言,這意味著他們需要具備“靈活的和多元的技能,保持開(kāi)放的學(xué)習(xí)態(tài)度……這些技能被稱(chēng)為‘軟技能’,并且是知識(shí)密集型的技能。”[20]因此可以說(shuō),知識(shí)變革深刻影響著當(dāng)前人才培養(yǎng)定位,要求各級(jí)各類(lèi)教育能夠培養(yǎng)可以終身學(xué)習(xí)的新時(shí)代人才。
誠(chéng)然,知識(shí)社會(huì)對(duì)終身學(xué)習(xí)的要求經(jīng)歷了不斷深化發(fā)展的過(guò)程。一般認(rèn)為,“終身學(xué)習(xí)”正式作為一種系統(tǒng)的教育理念得到廣泛關(guān)注始于20世紀(jì)60年代朗格讓?zhuān)≒aul Lengrand)在國(guó)際會(huì)議上所做的題為終身教育的報(bào)告,②他指出:現(xiàn)代社會(huì)不斷加速的變革、人口增長(zhǎng)帶來(lái)的教育需求增長(zhǎng)、科學(xué)知識(shí)和技術(shù)的不斷進(jìn)步、勞動(dòng)力被部分解放而帶來(lái)了更多閑暇、生活模式和相互關(guān)系的危機(jī)等帶來(lái)了諸多挑戰(zhàn),這要求教育幫助人在一生中保持其學(xué)習(xí)和訓(xùn)練的連續(xù)性。[21]此后,伴隨著知識(shí)社會(huì)的深入發(fā)展,終身學(xué)習(xí)“從一種教育思想逐漸發(fā)展到關(guān)注人的生存與發(fā)展,進(jìn)而演化為人們的一種權(quán)利與生活方式,歷經(jīng)理論—實(shí)踐—反思的嬗變過(guò)程,其張力從人類(lèi)自身求得生存擴(kuò)展到人與社會(huì)、自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為引領(lǐng)世界各國(guó)終身學(xué)習(xí)實(shí)踐提供了明確的指導(dǎo)思想”。[22]從內(nèi)涵來(lái)看,“終身學(xué)習(xí)”背后最為簡(jiǎn)潔的理念可以概括為“有目的的學(xué)習(xí)能夠而且應(yīng)該貫穿人的一生”。[23]對(duì)個(gè)體而言,終身學(xué)習(xí)是通過(guò)有目的的、持續(xù)一生的學(xué)習(xí)活動(dòng)實(shí)現(xiàn)全面發(fā)展的過(guò)程;對(duì)于社會(huì)而言,終身學(xué)習(xí)越來(lái)越被視為推動(dòng)社會(huì)可持續(xù)發(fā)展、構(gòu)建人類(lèi)命運(yùn)共同體的重要推動(dòng)力。在深入貫徹終身學(xué)習(xí)理念的過(guò)程中,克羅普利(Arthur J.Cropley)等人指出了高等教育所發(fā)揮的獨(dú)特價(jià)值:“高等教育在幫助發(fā)展和實(shí)施一種終身學(xué)習(xí)體系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為終身學(xué)習(xí)提供了必要的組織框架。這種重要性源于高等院校在多數(shù)國(guó)家教育系統(tǒng)中享有崇高威望和重要影響,源于它們?cè)趧?chuàng)建理論和開(kāi)展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學(xué)的教學(xué)內(nèi)容、研究課題和學(xué)術(shù)主張對(duì)許多社會(huì)領(lǐng)域的知識(shí)、態(tài)度、價(jià)值觀和實(shí)踐都產(chǎn)生影響,高等院校在教師培訓(xùn)方面也起重要作用,它們不僅傳授知識(shí)也傳授理論原理(如對(duì)終身學(xué)習(xí)重要性的信念)和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24]3-4可以說(shuō),高等教育在服務(wù)知識(shí)社會(huì)上具有重要的創(chuàng)建和示范價(jià)值,承擔(dān)著培養(yǎng)能夠有效建立并不斷更新知識(shí)網(wǎng)絡(luò)、能夠創(chuàng)造性地將知識(shí)轉(zhuǎn)化為應(yīng)用資源,以及能夠進(jìn)行突破性的知識(shí)生產(chǎn)的終身學(xué)習(xí)者的重要使命。
2.培養(yǎng)什么樣的“終身學(xué)習(xí)者”?
從時(shí)代特征及需求來(lái)看,高等教育應(yīng)該以“終身學(xué)習(xí)者”為人才培養(yǎng)方向顯得越來(lái)越清晰合理。那么“終身學(xué)習(xí)者”的意蘊(yùn)內(nèi)涵是什么?什么樣的人才是合格的終身學(xué)習(xí)者?結(jié)合目前最具共識(shí)性的宏觀教育綱領(lǐng)和學(xué)習(xí)科學(xué)等相關(guān)研究成果,本文從以下三個(gè)維度對(duì)“終身學(xué)習(xí)者”的培養(yǎng)目標(biāo)進(jìn)行更具體的闡釋。
首先,知識(shí)社會(huì)中的終身學(xué)習(xí)者具有良好的、充分的知識(shí)基礎(chǔ),以及靈活的、不斷豐富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學(xué)習(xí)革命發(fā)生以前,最狹義的“學(xué)習(xí)”的核心要義就是獲取知識(shí),但知識(shí)社會(huì)中知識(shí)的增長(zhǎng)和更新迭代速度越來(lái)越快,對(duì)能力的推崇逐漸勝過(guò)對(duì)知識(shí)的關(guān)注,以至于出現(xiàn)了“學(xué)習(xí)知識(shí)并不重要”的認(rèn)識(shí)。細(xì)究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的兩個(gè)重要誤區(qū):其一,概念誤區(qū)。國(guó)內(nèi)對(duì)于知識(shí)學(xué)習(xí)的理解往往將之局限于狹義的“陳述性知識(shí)”層面,即主要是用來(lái)說(shuō)明事物的性質(zhì)特征和狀態(tài)、用于區(qū)別和辨別事物的描述性的知識(shí)。但事實(shí)上,“知識(shí)包括認(rèn)知領(lǐng)域的全部學(xué)習(xí)結(jié)果,既包括信息加工心理學(xué)家區(qū)分的陳述性知識(shí)和程序性知識(shí),哲學(xué)家區(qū)分的顯性知識(shí)和默會(huì)知識(shí),還包括奧蘇伯爾(David Pawl Ausubel)區(qū)分的機(jī)械知識(shí)和有意義知識(shí)。”[25]其中,程序性知識(shí)恰恰是從人的智慧技能與動(dòng)作技能中推測(cè)而來(lái)的知識(shí),因而以此籠統(tǒng)地否認(rèn)知識(shí)在教與學(xué)中的地位是不妥當(dāng)?shù)摹F涠壿嬚`區(qū)。高等教育培養(yǎng)從知識(shí)話語(yǔ)向能力話語(yǔ)的轉(zhuǎn)變背后的理念是“突破傳統(tǒng)教育追求知識(shí)和智性能力的局限性,為學(xué)生提供持續(xù)增進(jìn)個(gè)人和職業(yè)發(fā)展的信心和能力”[26],根本上是對(duì)傳統(tǒng)大學(xué)知識(shí)教育邏輯的反思,而不是為了否認(rèn)知識(shí)的教育價(jià)值。事實(shí)上,知識(shí)與能力的關(guān)系絕非二元對(duì)立,能力是對(duì)知識(shí)、技能、個(gè)人素質(zhì)和理解等多方面的有效結(jié)合。對(duì)于高等教育人才培養(yǎng)而言,“有能力的人不僅知道自己的專(zhuān)業(yè)知識(shí);他們也有信心在不同的和不斷變化的情況下應(yīng)用他們的知識(shí)和技能,并在離開(kāi)正規(guī)教育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后繼續(xù)發(fā)展他們的專(zhuān)業(yè)知識(shí)和技能。”[27]在這個(gè)意義上,高等教育對(duì)知識(shí)的祛魅并非剝奪了其在培養(yǎng)終身學(xué)習(xí)者中的重要性,反而在自主、自覺(jué)學(xué)習(xí)層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當(dāng)然,知識(shí)爆炸的背景下掌握所有知識(shí)是不現(xiàn)實(shí)的,因而更關(guān)鍵的知識(shí)學(xué)習(xí)目標(biāo)在于結(jié)合先有知識(shí)為新知識(shí)的獲取與吸收搭建起有效的聯(lián)結(jié)橋梁,從而構(gòu)建結(jié)構(gòu)靈活、內(nèi)容豐富、便于提取所需信息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
其次,終身學(xué)習(xí)者需要修煉能夠保障和促進(jìn)有效學(xué)習(xí)、長(zhǎng)期學(xué)習(xí)、終身學(xué)習(xí)的相應(yīng)能力,逐漸實(shí)現(xiàn)創(chuàng)造性學(xué)習(xí)。關(guān)于學(xué)習(xí)的本質(zhì)一直存在著諸多爭(zhēng)議,但在最終指向上有一種觀點(diǎn)得到了廣泛的認(rèn)可:“教育與學(xué)習(xí)的終極目標(biāo)是發(fā)展‘適應(yīng)性能力’,即將有意義條件下習(xí)得的知識(shí)與技能巧妙并創(chuàng)造性地應(yīng)用到不同情境的能力。”[28]32-33以此為出發(fā)點(diǎn),泰利(Terry Doyle)的團(tuán)隊(duì)在關(guān)于學(xué)習(xí)的研究實(shí)踐中采取的概念能夠提供有力的參照:“學(xué)習(xí)是一種能力,能重拾相當(dāng)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已經(jīng)停用的信息,能運(yùn)用有關(guān)信息在與原來(lái)學(xué)習(xí)這些信息時(shí)的不同的環(huán)境中解決問(wèn)題。”[29]5根據(jù)這一定義,終身學(xué)習(xí)者需要具備的能力在內(nèi)容上可以涵蓋如何找到信息、如何鑒定信息源、如何與他人合作共創(chuàng)有意義的學(xué)習(xí)、如何在不熟悉的環(huán)境中解決問(wèn)題等。與此相關(guān)的具體能力可以列出來(lái)很多,有學(xué)者將其總結(jié)為彼此相互聯(lián)系而又具有一定層次的能力框架:基礎(chǔ)學(xué)習(xí)能力—適應(yīng)和利用學(xué)習(xí)環(huán)境的能力—元學(xué)習(xí)能力—知識(shí)管理能力。[30]這里尤其需要關(guān)注的是元認(rèn)知/元學(xué)習(xí)能力,即“人們預(yù)測(cè)他們?cè)诟鞣N任務(wù)中表現(xiàn)的能力以及對(duì)目前的理解和掌握程度進(jìn)行監(jiān)控的能力”[31],大量研究證明了監(jiān)控解決問(wèn)題方式的能力是學(xué)習(xí)者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重要表現(xiàn),能否使用元認(rèn)知彈性地處理新情境、挑戰(zhàn)現(xiàn)有知識(shí)水平并實(shí)現(xiàn)超越,是適應(yīng)性專(zhuān)家與新手的根本差異。因此高等教育所要培養(yǎng)的學(xué)習(xí)者應(yīng)當(dāng)具備通過(guò)積極監(jiān)控自身學(xué)習(xí)策略與資源、評(píng)估學(xué)習(xí)表現(xiàn)的能力。此外,作為知識(shí)生產(chǎn)與創(chuàng)新的重要陣地,大學(xué)中的主要教育對(duì)象是已經(jīng)具備相應(yīng)學(xué)習(xí)基礎(chǔ)與高度自主性的成人學(xué)習(xí)者,他們被賦予了成為“創(chuàng)造性研究者”的更高期待。這意味著,高等教育對(duì)學(xué)習(xí)者的培養(yǎng)中既要特別重視其自主學(xué)習(xí)能力,如結(jié)合正式學(xué)習(xí)與非正式學(xué)習(xí),協(xié)調(diào)自主學(xué)習(xí)與交互學(xué)習(xí),從而實(shí)現(xiàn)“深度學(xué)習(xí)”;又要更聚焦于學(xué)習(xí)的創(chuàng)造性維度,注重鍛煉學(xué)習(xí)者的問(wèn)題意識(shí)與探究能力,鼓勵(lì)其拓寬思維,努力成為時(shí)代所需要的創(chuàng)新型人才。
最后,高等教育所致力于培養(yǎng)的應(yīng)該是“選擇成為學(xué)習(xí)者”的人,也即主動(dòng)、自主、自律的終身學(xué)習(xí)者。雖然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教育實(shí)踐中,包括情感與動(dòng)機(jī)等在內(nèi)的學(xué)習(xí)的非認(rèn)知因素是經(jīng)常不被重視甚至被忽視,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情感與動(dòng)機(jī)等因素在維持終身學(xué)習(xí)狀態(tài)中發(fā)揮的作用開(kāi)始得到廣泛的關(guān)注。有學(xué)者總結(jié)概括了情緒與動(dòng)機(jī)在學(xué)習(xí)中所起到的關(guān)鍵作用:“學(xué)生通過(guò)與學(xué)習(xí)目標(biāo)相關(guān)的情緒的不斷變化判斷自身與目標(biāo)之間的距離,并選擇和完善達(dá)到目標(biāo)的策略”,“學(xué)生使用他們的動(dòng)機(jī)信念為學(xué)習(xí)任務(wù)和環(huán)境以及他們的社會(huì)和教育環(huán)境賦予意義”,“動(dòng)機(jī)信念包括自我效能感、結(jié)果期望、目標(biāo)取向、價(jià)值判斷和歸因,它們決定了學(xué)生所做的選擇、所付出的努力以及面對(duì)困難時(shí)所堅(jiān)持的時(shí)間”。[28]74-75越來(lái)越多的研究證明,積極的動(dòng)機(jī)信念與情感(如熱情、好奇心、快樂(lè)等)能夠促進(jìn)學(xué)習(xí)活動(dòng)的發(fā)生以及學(xué)習(xí)效果的改善。培養(yǎng)終身學(xué)習(xí)者意味著要為他們脫離了以學(xué)校為主要環(huán)境的正式學(xué)習(xí)體系后持續(xù)學(xué)習(xí)打下良好的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他們自身如何看待學(xué)習(xí)境脈以及發(fā)生在學(xué)習(xí)過(guò)程中的經(jīng)歷是其學(xué)習(xí)目標(biāo)的根本依據(jù)所在。因此,這里的“選擇”是存在主義意義上的,正如薩特(Jean-Paul Sartre)所言,“自由就是人對(duì)他的存在方式的選擇,這種選擇是個(gè)人意志支配的主觀選擇而不是服從別人意志的盲目選擇,所以不能給選擇施加任何規(guī)律、規(guī)則和規(guī)范”[32]。而“選擇成為學(xué)習(xí)者”則意味著“對(duì)永遠(yuǎn)無(wú)法完全了解的世界表現(xiàn)出開(kāi)放的姿態(tài),愿意在‘現(xiàn)實(shí)面前’生活”,[33]意味著在豐盈的世界面前主動(dòng)保持學(xué)習(xí)的熱情與開(kāi)放,并承擔(dān)起隨之而來(lái)的責(zé)任。
三、培養(yǎng)終身學(xué)習(xí)者的已有探索與改進(jìn)可能
1.“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現(xiàn)有探索
雖然,作為人類(lèi)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人類(lèi)經(jīng)驗(yàn)的核心,學(xué)習(xí)始終為教育所關(guān)注,但它從未像今天這樣占據(jù)如此重要與核心的地位。隨著終身學(xué)習(xí)的理念在全球范圍內(nèi)得到越來(lái)越多的認(rèn)可與推動(dòng),高等教育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轉(zhuǎn)向。約書(shū)亞·金(Joshua Kim)帶領(lǐng)團(tuán)隊(duì)考察了在學(xué)習(xí)科學(xué)傳播、泛在學(xué)習(xí)管理系統(tǒng)興盛、網(wǎng)絡(luò)教育持續(xù)發(fā)展、慕課泡沫影響以及新的學(xué)習(xí)型組織陸續(xù)產(chǎn)生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所發(fā)生的重大學(xué)習(xí)轉(zhuǎn)向,并指出:“學(xué)習(xí)轉(zhuǎn)向是一種趨勢(shì),它推動(dòng)了許多高校在學(xué)習(xí)方面的巨大進(jìn)步,相當(dāng)多的學(xué)校現(xiàn)在有潛力為學(xué)生提供高質(zhì)量的學(xué)習(xí)方式。”[34]37我國(guó)教育部也多次發(fā)文指出,“現(xiàn)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就是要面向?qū)W習(xí)者個(gè)性化、多樣化的學(xué)習(xí)和發(fā)展需求,因材施教,促進(jìn)學(xué)習(xí)者釋放潛能”,在此背景下,各階段教育都應(yīng)“加快建立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35],“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越來(lái)越成為對(duì)培養(yǎng)終身學(xué)習(xí)者的重要使命的積極回應(yīng)。但事實(shí)上,目前我國(guó)的這種探索在理念、教學(xué)以及評(píng)價(jià)等維度的變革中還有不少可以改進(jìn)的空間。
在理念層面,“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可以視為對(duì)“以教師、學(xué)科知識(shí)、課堂教學(xué)為中心”與“以學(xué)生、直接經(jīng)驗(yàn)、活動(dòng)為中心”之爭(zhēng)的超越。[36]事實(shí)上,在新舊中心的爭(zhēng)議中孕育出的“學(xué)生主體,教師主導(dǎo)”的理念已經(jīng)在試圖調(diào)和這種對(duì)立,2010年《國(guó)家中長(zhǎng)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就明確提出了“以學(xué)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dǎo),充分發(fā)揮學(xué)生的主動(dòng)性”的教育發(fā)展原則,也在教育實(shí)踐中取得了不錯(cuò)的效果。隨著終身學(xué)習(xí)思想在教育中的深入,“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理念在超越傳統(tǒng)教育與進(jìn)步教育的二元對(duì)立的基礎(chǔ)上,更有針對(duì)性地從學(xué)習(xí)的視角回應(yīng)了時(shí)代的人才培養(yǎng)需求。但在具體的人才培養(yǎng)實(shí)踐中,高等教育工作者還有一些理解上的誤區(qū),即將“學(xué)習(xí)者中心”直接等同于“學(xué)生中心”。這種理解是有問(wèn)題的:一方面,“學(xué)生”身份向“學(xué)習(xí)者”身份的話語(yǔ)轉(zhuǎn)向“凸顯了以學(xué)習(xí)者為本的個(gè)性化學(xué)習(xí)取向、以‘做中學(xué)’為核心的進(jìn)步教育取向,也意味著讓學(xué)習(xí)者‘發(fā)聲’的解放教育價(jià)值取向”。[37]“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理念試圖將學(xué)習(xí)的主體從單一學(xué)習(xí)場(chǎng)域(學(xué)校)、師生關(guān)系秩序中解放出來(lái),擴(kuò)大了學(xué)習(xí)的開(kāi)放性與自覺(jué)性,彰顯了主體價(jià)值與自由。另一方面,雖然高等教育領(lǐng)域中的“以學(xué)習(xí)者中心”的“學(xué)習(xí)者”依然主要指學(xué)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把這種變革理解為“以學(xué)生為中心”的實(shí)踐,如歐洲學(xué)生聯(lián)合會(huì)的定義中,“以學(xué)生為中心的學(xué)習(xí)”既指高等教育的一種觀念與文化,也是為建構(gòu)主義學(xué)習(xí)理論所支持的一種學(xué)習(xí)方法,表現(xiàn)為以創(chuàng)新性的教學(xué)方法促進(jìn)學(xué)生學(xué)習(xí),將學(xué)生視為學(xué)習(xí)過(guò)程的積極參與者,著重培養(yǎng)問(wèn)題解決能力、批判性思維、反思能力等可遷移能力。[38]但其涵蓋范圍顯然已經(jīng)擴(kuò)大,有學(xué)者傾向于將教師也歸入“學(xué)習(xí)者”行列,認(rèn)為在此過(guò)程中師生構(gòu)成了學(xué)習(xí)共同體。[39]理念理解上的窄化導(dǎo)致了人才培養(yǎng)中的種種問(wèn)題,如忽視學(xué)習(xí)者的主動(dòng)性與個(gè)性、忽視教師的學(xué)習(xí)狀況與師生學(xué)習(xí)共同體的構(gòu)建等。
人才培養(yǎng)的核心途徑是教學(xué),培養(yǎng)理念的升級(jí)最直接落實(shí)在以課堂為主要場(chǎng)域的教學(xué)改革中。體現(xiàn)在高等教育中,“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理念加劇了教學(xué)中的“學(xué)習(xí)轉(zhuǎn)向”,也即進(jìn)行由“教學(xué)范式”向“學(xué)習(xí)范式”的轉(zhuǎn)向。本質(zhì)上,這種轉(zhuǎn)向是對(duì)傳統(tǒng)教育過(guò)程中存在的單向灌輸、填鴨式教學(xué)等問(wèn)題的反思,已經(jīng)初步取得了良好效果,如美國(guó)自20世紀(jì)80年代開(kāi)展的以學(xué)生為中心的本科生教育改革經(jīng)過(guò)了學(xué)術(shù)進(jìn)步、社會(huì)推動(dòng)、高校投入三個(gè)階段,取得了不錯(cuò)成效[40];我國(guó)也在2017年的全國(guó)教育工作會(huì)議明確了“加快建立‘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推動(dòng)了以關(guān)切學(xué)生學(xué)習(xí)獲得感、倡導(dǎo)學(xué)習(xí)中心的學(xué)習(xí)范式、強(qiáng)調(diào)辦學(xué)資源為學(xué)生學(xué)習(xí)服務(wù)為特征的“學(xué)習(xí)質(zhì)量取向”的本科教學(xué)改革[41]。然而這種轉(zhuǎn)型中也出現(xiàn)了由于對(duì)“教學(xué)”與“學(xué)習(xí)”辯證關(guān)系的把握失當(dāng)而造成的“矯枉過(guò)正”,即用“學(xué)習(xí)”代替“教學(xué)”的問(wèn)題。長(zhǎng)期以來(lái),中國(guó)高等教育中教學(xué)模式遭到的最猛烈批判在于重知識(shí)傳授而輕自主探究,如約翰·比格斯(John B·Biggs)所提出的“中國(guó)學(xué)習(xí)者悖論”,認(rèn)為中國(guó)學(xué)生在學(xué)習(xí)過(guò)程中重視知識(shí)的接收和死記硬背、依賴(lài)教師的知識(shí)傳授、追求學(xué)習(xí)可能帶來(lái)的外部收益,卻能產(chǎn)生優(yōu)異甚至大幅領(lǐng)先于西方國(guó)家學(xué)生學(xué)習(xí)成果。[42]因而在新的人才培養(yǎng)理念引導(dǎo)下,對(duì)學(xué)習(xí)的強(qiáng)調(diào)成為教學(xué)改革的重要指向。但問(wèn)題在于,高等教育中“學(xué)習(xí)”的地位與價(jià)值是否應(yīng)該,又是否真的能夠超過(guò)“教學(xué)”,甚至取代“教學(xué)”?比斯塔(Gert Biesta)對(duì)此的回應(yīng)是:“從概念來(lái)看,我們既不應(yīng)該把教學(xué)當(dāng)做學(xué)習(xí)的導(dǎo)因,也不應(yīng)該認(rèn)為教學(xué)必然旨在讓學(xué)習(xí)發(fā)生……教學(xué)的意圖應(yīng)該從更廣義的教育意圖,即關(guān)于資格化、社會(huì)化以及主體化的領(lǐng)域來(lái)發(fā)揮影響。”[43]在他看來(lái),真正的“教學(xué)”是一種“異識(shí)”,其價(jià)值恰恰在于為主體打開(kāi)了一種可能性,為他們創(chuàng)造另一種空間從而使之在其中是自由的。也就是說(shuō),一方面,教學(xué)乃至教育所承擔(dān)的任務(wù)并不能隨著“學(xué)習(xí)的語(yǔ)言轉(zhuǎn)向”而被化約,以學(xué)習(xí)代替教學(xué)將會(huì)剝奪這些功能與責(zé)任;另一方面,學(xué)習(xí)并不是教學(xué)能夠開(kāi)展以及教育能夠發(fā)生的唯一有意義方式,比斯塔在進(jìn)行的“無(wú)須學(xué)習(xí)的教學(xué)”就是一種“遭遇”真實(shí)世界之存在的嘗試。因此,“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并不意味著“教學(xué)”的退場(chǎng),也不意味著教師作為個(gè)體或集體所承擔(dān)的關(guān)于學(xué)習(xí)的責(zé)任有絲毫的減輕,也許恰恰相反,人才培養(yǎng)模式變革要求的正是教學(xué)與學(xué)習(xí)的有機(jī)配合,以及教師在促進(jìn)學(xué)習(xí)者發(fā)展方面的職能“升級(jí)”。
最終,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yǎng)成效要顯現(xiàn)在學(xué)習(xí)的效果評(píng)估以及更長(zhǎng)遠(yuǎn)的個(gè)體發(fā)展中,然而無(wú)論從大學(xué)生對(duì)于學(xué)習(xí)的主動(dòng)性與學(xué)習(xí)效果來(lái)看,還是從他們步入社會(huì)后的學(xué)習(xí)與發(fā)展?fàn)顟B(tài)來(lái)看,教育成效都并不理想。很多研究顯示,在推行“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培養(yǎng)模式變革過(guò)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往往來(lái)自學(xué)生本身,即“學(xué)生們常常對(duì)主動(dòng)學(xué)習(xí)的要求畏縮不前,被動(dòng)聽(tīng)講比主動(dòng)建構(gòu)學(xué)習(xí)更容易”[34]195,“在推行過(guò)程中很多學(xué)生感到憤怒、沮喪,對(duì)于實(shí)行的改變抱怨紛紛……敵意的根源在于學(xué)生們心中根深蒂固的以教師為中心的學(xué)習(xí)觀念”[29]13。學(xué)習(xí)并不經(jīng)常是令人愉快的,對(duì)于長(zhǎng)期接受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模式的大學(xué)生而言,“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意味著他們要承擔(dān)更多的責(zé)任、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改變舊有的學(xué)習(xí)習(xí)慣與思維模式是需要時(shí)間和努力的,也需要包括教師在內(nèi)的整個(gè)教育環(huán)境提供更有力的支持。這種培養(yǎng)成效的欠佳在高等教育結(jié)束后則表現(xiàn)為兩個(gè)層面的問(wèn)題:其一,人才市場(chǎng)的供需不匹配。1997年歐盟在建設(shè)知識(shí)社會(huì)的戰(zhàn)略規(guī)劃中提出了“可雇傭性”的概念,反映在當(dāng)下指的是“能夠滿(mǎn)足并適應(yī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動(dòng)態(tài)發(fā)展需要的人才,不僅是具有某一學(xué)科專(zhuān)業(yè)知識(shí)、專(zhuān)業(yè)能力的人才,而且是能夠根據(jù)不同崗位需求對(duì)知識(shí)和能力進(jìn)行遷移的‘通用型人才’”。[44]但從近年來(lái)的實(shí)際就業(yè)情況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所培養(yǎng)的人與人才市場(chǎng)的契合度并不充分。其二,脫離正式教育后學(xué)習(xí)與發(fā)展意愿的停滯。理想狀態(tài)下,終身學(xué)習(xí)的觀念包含效用價(jià)值模式,“在該模式中,學(xué)習(xí)和工作可以同時(shí)進(jìn)行,工作的經(jīng)驗(yàn)?zāi)軌虼龠M(jìn)后來(lái)的在校學(xué)習(xí),反過(guò)來(lái)在校的學(xué)習(xí)能夠促進(jìn)后來(lái)工作中的學(xué)習(xí)”。[24]34但近年來(lái)出現(xiàn)的“躺平”“擺爛”等青年亞文化反映出了社會(huì)壓力下的個(gè)體精神危機(jī)以及發(fā)展?fàn)顟B(tài)的停滯,這與知識(shí)社會(huì)對(duì)終身學(xué)習(xí)者的期待無(wú)疑背道而馳。
2.如何更好地培養(yǎng)終身學(xué)習(xí)者?
高等教育領(lǐng)域面向“培養(yǎng)主動(dòng)的終身學(xué)習(xí)者”的人才培養(yǎng)變革近年來(lái)取得了不少良好成果,這可謂是一個(gè)非常好的起步,但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其在轉(zhuǎn)型上升期的過(guò)程中依然存在著不少問(wèn)題和進(jìn)步空間。圍繞這一核心培養(yǎng)目標(biāo),高等教育人才培養(yǎng)改革還可以從以下三個(gè)方面進(jìn)行更深入的思考與探索。
第一,充分利用學(xué)習(xí)科學(xué)、學(xué)習(xí)哲學(xué)等領(lǐng)域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以更科學(xué)、更智慧的學(xué)習(xí)理論引導(dǎo)“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改革實(shí)踐。近年來(lái)關(guān)于學(xué)習(xí)的研究呈現(xiàn)出蓬勃發(fā)展態(tài)勢(shì),日益豐富的研究成果為人才培養(yǎng)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和實(shí)證依據(jù)。有學(xué)者將20世紀(jì)初由心理學(xué)家轉(zhuǎn)向教育而誕生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概括為“整合心理學(xué)、認(rèn)知科學(xué)、教育學(xué)、計(jì)算機(jī)科學(xué)等領(lǐng)域的研究成果,從不同學(xué)科視角對(duì)人類(lèi)學(xué)習(xí)進(jìn)行全方位研究而形成的一個(gè)全新的跨學(xué)科的研究領(lǐng)域”[45]。這些理論為建構(gòu)遵循個(gè)體認(rèn)知發(fā)展規(guī)律的課程體系、循序漸進(jìn)地優(yōu)化個(gè)體的終身學(xué)習(xí)技能提供了科學(xué)依據(jù),如符茨堡學(xué)派的思維心理學(xué)提示教育教學(xué)要重視頓悟與理解,建構(gòu)主義學(xué)習(xí)理論強(qiáng)調(diào)了個(gè)體和環(huán)境的交互作用和創(chuàng)設(shè)情境的學(xué)習(xí)價(jià)值。21世紀(jì)以后,有學(xué)者在對(duì)學(xué)習(xí)科學(xué)進(jìn)行了學(xué)術(shù)史考察后提出,學(xué)習(xí)科學(xué)即將迎來(lái)“工程轉(zhuǎn)向”,即基于“基于設(shè)計(jì)的研究”的工程隱喻,實(shí)現(xiàn)科學(xué)思維向工程思維的轉(zhuǎn)換,促進(jìn)學(xué)習(xí)研究中科學(xué)、技術(shù)與工程的一體化發(fā)展,同時(shí)利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彌合學(xué)習(xí)研究從基礎(chǔ)科學(xué)向應(yīng)用實(shí)踐轉(zhuǎn)化面臨的挑戰(zhàn)與倫理問(wèn)題。[46]但事實(shí)上,令很多學(xué)習(xí)科學(xué)家感到遺憾的是,“基于學(xué)習(xí)的研究在迅速發(fā)展,卻并沒(méi)有引領(lǐng)變革。”[28]9這些豐富的研究成果沒(méi)有被應(yīng)用在高等教育的教育實(shí)踐與政策制定中。學(xué)習(xí)科學(xué)研究和教育實(shí)踐變革即將邁入互為需求的“雙向道”階段,[47]只有充分利用相關(guān)研究成果,如遵循學(xué)習(xí)科學(xué)所揭示的個(gè)體認(rèn)知、技能等方面的發(fā)展規(guī)律,通過(guò)學(xué)習(xí)哲學(xué)理念的傳播與推廣激活學(xué)生的終身學(xué)習(xí)意愿等,才能更順利地推進(jìn)人才培養(yǎng)改革進(jìn)程、切實(shí)培養(yǎng)知識(shí)社會(huì)所需要的終身學(xué)習(xí)型人才。
第二,在厘清“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是以學(xué)習(xí)者為本、重視主體性發(fā)揮與學(xué)習(xí)共同體建構(gòu)的學(xué)習(xí)變革的基礎(chǔ)上,深刻把握“教學(xué)”與“學(xué)習(xí)”的辯證關(guān)系,深化教學(xué)改革,提升高校教師的教學(xué)與育人能力,使高等教育超越功利主義的桎梏回歸人本主義立場(chǎng)。前文已經(jīng)提到認(rèn)識(shí)層面的誤區(qū),在澄清了這些誤區(qū)之后,如何升級(jí)教學(xué)、提升教育質(zhì)量便成了關(guān)鍵問(wèn)題。事實(shí)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不少促進(jìn)教學(xué)的努力:為了使教學(xué)更好地回應(yīng)對(duì)學(xué)習(xí)的關(guān)切,舒爾曼(Lee S.Shulman)等人創(chuàng)立了卡耐基教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研究院并嘗試在高等教育領(lǐng)域推行“教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其涉及的所有問(wèn)題都圍繞著學(xué)習(xí)的議題,研究既包括教師的實(shí)踐,也涵蓋由這種實(shí)踐所帶來(lái)的學(xué)生學(xué)習(xí)表現(xiàn)特征與深度,[48]其引領(lǐng)下的教師專(zhuān)業(yè)學(xué)習(xí)社群在發(fā)展杰出教學(xué)和促進(jìn)學(xué)生學(xué)習(xí)發(fā)展方面有顯著提升。[49]我國(guó)也在2020年首次舉辦了以“教與學(xué)學(xué)術(shù):國(guó)際視野與本土實(shí)踐”為主題的國(guó)際學(xué)術(shù)會(huì)議,呼吁下一階段深入推進(jìn)大學(xué)教學(xué)和學(xué)習(xí)的學(xué)術(shù)研究與實(shí)踐創(chuàng)新,以專(zhuān)業(yè)的態(tài)度和方式從事教學(xué),以改善學(xué)生學(xué)習(xí)、促進(jìn)學(xué)生發(fā)展為目標(biāo),全面提高教育教學(xué)質(zhì)量。[50]可以說(shuō),高等教育中對(duì)大學(xué)生學(xué)習(xí)質(zhì)量的關(guān)注與人才培養(yǎng)的學(xué)習(xí)取向落實(shí),與充分發(fā)揮教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研究的先鋒作用以推動(dòng)整個(gè)教育領(lǐng)域的學(xué)習(xí)發(fā)展,是玉汝于成的關(guān)系。在根本立場(chǎng)上,雖然大學(xué)隨著與社會(huì)聯(lián)系的日益緊密確實(shí)出現(xiàn)了一種功利主義教育取向,但越來(lái)越多的人開(kāi)始認(rèn)識(shí)到并致力于更正這種偏向,如2021年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發(fā)布了《一起重新構(gòu)想我們的未來(lái)》報(bào)告,肯定了教育目的的公共性、正義性和超越性的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了其新內(nèi)涵:促進(jìn)人與人之間的彼此聯(lián)結(jié)、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tài)聯(lián)結(jié)、人與技術(shù)之間的創(chuàng)新聯(lián)結(jié)。[51]這種理念的糾正反映在高等教育中便是新時(shí)代的育人要求清晰地指向了促進(jìn)人的全面發(fā)展的人本主義立場(chǎng)的復(fù)歸。
第三,繼續(xù)完善包括高等教育在內(nèi)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shè),為學(xué)習(xí)者提供更有支持力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鼓勵(lì)學(xué)習(xí)者實(shí)現(xiàn)更自主的、更自覺(jué)的、更自律的終身學(xué)習(xí)。本質(zhì)上,終身教育是“一組有系統(tǒng)地提供學(xué)習(xí)機(jī)會(huì)的組織原則”,該原則在時(shí)間維度展現(xiàn)為“必須為縱軸低端至頂端(即人的整個(gè)一生)的學(xué)習(xí)提供便利”,在空間維度則意味著正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的橫向整合。[24]32-37而高等教育是個(gè)體從正規(guī)學(xué)校學(xué)業(yè)邁向更廣博教育過(guò)程中的最后一道正式發(fā)展支架,為非學(xué)校情境中的學(xué)習(xí)打下基礎(chǔ)的關(guān)鍵階段,因此,發(fā)展高等教育是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shè)的重中之重。21世紀(jì)以來(lái),蓬勃興起的泛在學(xué)習(xí)系統(tǒng)、網(wǎng)絡(luò)教育和新的學(xué)習(xí)型組織共同構(gòu)成了突破時(shí)空界限的學(xué)習(xí)網(wǎng)絡(luò),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高等教育的補(bǔ)充與配合,尤其是新冠疫情以來(lái),在線教育教學(xué)逐漸顯現(xiàn)出其獨(dú)特的價(jià)值,也使得高等教育必須思考如何統(tǒng)合不同學(xué)習(xí)方式以實(shí)現(xiàn)最好的教育教學(xué)效果。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發(fā)現(xiàn)指出,包括學(xué)習(xí)者、教師和其他學(xué)習(xí)專(zhuān)家、內(nèi)容、教學(xué)設(shè)施和技術(shù)四個(gè)關(guān)鍵要素在內(nèi)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的支持力對(duì)學(xué)習(xí)者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28]17因此,高等教育應(yīng)從不同層面打造良好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如提供充分的學(xué)習(xí)資源,溝通正式學(xué)習(xí)與非正式學(xué)習(xí)的渠道,推動(dòng)師生學(xué)習(xí)共同體建設(shè),配備有利于學(xué)習(xí)者自主學(xué)習(xí)的設(shè)施與技術(shù)等。當(dāng)然,外在條件的改善不足以實(shí)現(xiàn)最核心的培養(yǎng)期待,高等教育最終應(yīng)該幫助學(xué)生主動(dòng)、自覺(jué)、自愿、自律地學(xué)習(xí),而這要求充分關(guān)照學(xué)習(xí)中認(rèn)知因素與非認(rèn)知因素的有機(jī)結(jié)合,如加強(qiáng)對(duì)元學(xué)習(xí)能力的培養(yǎng)、教授關(guān)于終身學(xué)習(xí)的核心技能,以及創(chuàng)建有情感支持與無(wú)威脅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幫助學(xué)習(xí)者發(fā)現(xiàn)學(xué)習(xí)興趣、改善歸因方式、保持積極的動(dòng)機(jī)信念,從而將學(xué)習(xí)的習(xí)慣與意愿持續(xù)一生。
毋庸置疑,在知識(shí)大變革的當(dāng)今社會(huì),關(guān)注終身學(xué)習(xí)、培養(yǎng)有意愿且有能力的終身學(xué)習(xí)者已然成為推動(dòng)社會(huì)發(fā)展和關(guān)切個(gè)體幸福的必然要求。作為終身教育體系的一部分、服務(wù)于終身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的重要組織,高等教育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起其時(shí)代使命,在澄清以“培養(yǎng)終身學(xué)習(xí)者”為人才培養(yǎng)目標(biāo)的基礎(chǔ)上,通過(guò)完善相關(guān)培養(yǎng)體制機(jī)制、革新教育教學(xué)方式、激發(fā)學(xué)習(xí)者終身學(xué)習(xí)的意愿與活力等途徑予以落實(shí),協(xié)同各方探索更有支持力的終身學(xué)習(xí)體系,從而為推動(dòng)知識(shí)社會(huì)的深化發(fā)展提供堅(jiān)實(shí)可靠的人才保障。
注 釋?zhuān)?/p>
①雖然在中世紀(jì)大學(xué)產(chǎn)生以前也存在著高等教育(如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教育成就),但由于其并未發(fā)展成永久性知識(shí)機(jī)構(gòu)的組織形態(tài),這里暫不予討論。此處對(duì)人才培養(yǎng)的理念及實(shí)踐的相關(guān)歷史梳理并未嚴(yán)格區(qū)分“大學(xué)”與“高等教育”,主要沿用了一般情況下二者可以視為同義語(yǔ)的使用方式。
②但也有學(xué)者(如周作宇)指出雖然對(duì)終身教育思想有重要貢獻(xiàn),卻并非第一人,如英國(guó)人伊克斯利在更早的時(shí)候就提出并出版了以《終身教育論》為題的專(zhuān)著。在這個(gè)意義上將朗格讓看作“終身教育之父”的觀點(diǎn)仍然有待商榷。
- 終身教育研究的其它文章
- 基于文獻(xiàn)計(jì)量的國(guó)內(nèi)完全學(xué)分制研究現(xiàn)狀及趨勢(shì)
- “三區(qū)聯(lián)動(dòng)”:應(yīng)用型本科高校“雙師型”教師隊(duì)伍建設(shè)策略探析
- 繼續(xù)教育助力高素質(zhì)農(nóng)民生態(tài)素養(yǎng)培育的價(jià)值邏輯與實(shí)踐方略
——基于文化資本理論的分析 - 基于數(shù)字環(huán)境的中老年人非正式學(xué)習(xí)特點(diǎn)探析
- 新西蘭老年人數(shù)字素養(yǎng)評(píng)估框架研究與啟示
- 開(kāi)放大學(xué)自主在線學(xué)習(xí):挑戰(zhàn)、實(shí)施路徑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