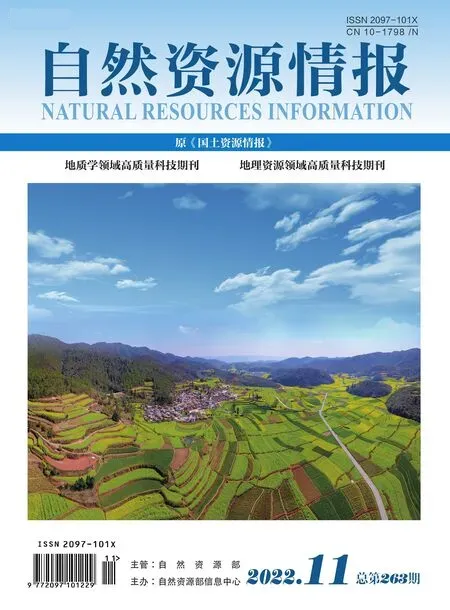資源民族主義與典型國家行為分析
劉天科,張 鐸,王伊杰
(中國自然資源經濟研究院,北京 101149)
礦產品作為重要的初級產品,在國際形勢多變的環境下,關注供給保障尤為關鍵。受資源稟賦條件的約束,我國部分礦產品長期依賴海外進口。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是我國的基本礦業戰略。因此,我們要深化對于世界主要能源和資源生產國礦業政策和形勢的認識,提高海外資源保障的應對能力。
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世界各國均面臨著地緣政治、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等問題,使得越來越多的資源生產國受到資源民族主義崛起的影響,并對礦產資源采取不同程度的國有化政策。資源民族主義對全球礦業市場,乃至國際政治格局影響深遠,迫使各國為此調整外交政策、資源安全和開發戰略。因此,研究國際礦業政策演變,特別是資源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國的演進過程,有助于增強我國在國際礦業市場的運營能力,進而提升我國能源資源供給安全。
通過文獻研究發現,對資源民族主義的研究多局限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研究相對較少,而就目前國際形勢來看,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對我國的影響可能更大。從研究方法上來看,目前的研究集中在某個國家的歷史或現狀,并側重于資源政策法規方面,通常忽視該國面對的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條件和權力結構變化,而這些因素往往是資源民族主義思潮形成過程中的主因。因此,本文選取不同地區的國家,分析資源民族主義的演變和對資源政策產生的影響。
1 資源民族主義的內涵
資源民族主義是指[1]“基于國家對自然資源的合法管轄,通過控制和支配資源,以及市場干預行為,實現為政治服務和國家特定發展等目標”。資源民族主義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并非是一種新興的思潮[2]。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時期開始,一些發展中國家就喪失了對本國礦產資源的主權。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殖民體系結束之后,發達國家還是通過其占據主導地位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通過掌控資源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進行變相掠奪,而資源民族主義便隨著第三世界國家獨立浪潮應運而生。因此,從政治角度看,資源民族主義浪潮有爭取本國經濟和資源主權的意義,其發展是合理的。但是,資源民族主義,或者說資源領域的保護主義傾向,又對經濟全球化浪潮形成遏制,加劇國際社會的地緣沖突風險,威脅各國的能源資源安全與經濟發展。
資源民族主義思潮的表現形式具有多樣性特點,在形式上包含提高資源的國家占有率,對本國員工比例的要求等,涉及的國家不限于發展中國家,也涉及發達國家。但是,總體上拉丁美洲和非洲為主要資源民族主義多發地區,并且主要通過提高資源的國家占有率實現[3]。
由于資源民族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往往受到地緣政治形勢和國內政治傾向變化影響,而這些因素是多變的,所以進行相關分析時,不應僅從靜態的政策視角入手,而是應將之視為一個綜合體,特別關注政治經濟變化對其資源政策的影響。例如,智利自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化改革以來,在礦業領域被認為是對私有投資和國外投資相對友好的國家。但是,自2019年智利抗議和左翼新總統博里奇當選后,政治上的轉向就影響到礦產資源經濟政策上,智利制憲議會初步通過了一項提案,旨在促進銅礦、鋰礦和其他戰略資源的國有化;提案計劃沒收私人經營的礦產業務,并終止特許權,理由是戰略資源應納入“國家完全的、專屬的領域”,并服務于全體國民利益。因此,分析不同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傾向,需要以動態的眼光,結合其實際的政治動向作出判斷。
2 礦業政策演變與資源民族主義
從歷史角度上看,國際礦業政策與立法可以分為4個階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早期礦業立法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獨立引起的國有化階段,20世紀80—90年代的非國有化改造階段,以及21世紀礦業政策的理性發展階段[4]。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實體經濟陷入低迷狀態,大量資源生產國的政府財政陷入不平衡狀態,直接導致全球資源民族主義浪潮重新興起[5]。
各個階段的礦業政策和立法都是伴隨著歷史進程而逐漸演進的。早期的礦業法受到歐洲礦業法傳統的影響,并伴隨著殖民征服的過程,各殖民地國家礦業由宗主國的礦業公司經營,受外國企業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伴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獨立運動和世界范圍的工業化進程,如玻利維亞、印度等國推行礦業國有化政策,幾內亞、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由國家以股本方式參與礦業項目,總體上強調國家控制。自20世紀80年代起,由于發展中國家因經濟危機陷入債務問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張對這些國家的國有礦業公司進行私有化改造。21世紀以來,由于私有化改造導致的礦業收益不公問題使一些國家轉向資源民族主義,而一些對外開放程度較低的國家則選擇吸引外商投資[4]。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許多資源出口國陷入實體經濟低迷的狀態,出于維護本國經濟利益、保障國家資源安全、實現社會穩定和可持續性發展的動因,出臺了一系列資源民族主義的政策和法律,強化資源行業的國有化程度,并且將資源作為國家對外影響地緣政治的實力杠桿[2]。
3 典型資源民族主義國家
3.1 俄羅斯
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能源和礦產資源,是世界上少有的資源能夠自給的國家之一,許多礦產資源儲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石油和天然氣構成了俄羅斯的經濟核心和政治基石。因此,俄羅斯的資源民族主義主要集中在這兩個領域,并且對國際地緣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6]。
自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以來,葉利欽政府主要實行全球化和私有化政策,并形成了一系列能源領域的寡頭。而進入21世紀,普京政府認為過去給予外國公司的利益過多,推行了一系列資源民族主義政策[7]。這些資源民族主義政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加強能源領域的國家控制,包括限制能源企業私有化,調整外國企業的產品分成合同。例如,2003年解散尤科斯公司,2006年在薩哈林二號項目中要求國外企業轉交項目控股等。另一類是在地緣政治和外交領域,利用本國的能源優勢和國際市場的賣方優勢地位,通過能源出口擴大其經濟影響力[6]。例如,屢次對烏克蘭、摩爾多瓦等能源嚴重依賴俄羅斯的國家,通過停止供應、漲價等手段實現地緣政治上的目的,并且在2022年俄烏沖突中,也將石油、天然氣資源作為對抗歐盟制裁的手段。
3.2 玻利維亞
礦業是玻利維亞最重要的經濟產業,2020年礦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22%,約15億美元。玻利維亞的礦產資源種類和儲量都十分豐富[8],錫儲量115×104t,鐵儲量約450×108t,在拉美僅次于巴西。因此,玻利維亞有“礦業共和國”之稱,該國從殖民時代起,便有500年連續不斷的礦業歷史。
1952年,民族主義革命運動取得勝利,執政之初就受資源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但伴隨著國內和冷戰局勢的變化,特別是美國政府的影響,玻利維亞逐漸放棄資源民族主義,轉向資源的新自由主義化道路。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其礦業用地一直由玻利維亞礦業公司(COMIBOL)控制,1983年恢復民主政體后,采礦業也向私人投資者開放,由私人投資者與COMIBOL簽訂租賃合同或合資協議開采。在20世紀末,能源領域得到了進一步的資本化,并獲得了大量海外投資。
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策轉向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為莫拉萊斯總統任上的資源民族主義轉型政策埋下了伏筆。莫拉萊斯于2005年當選總統,并一直連任到2019年,推行了一系列資源民族主義政策,重塑了玻利維亞的資源管理結構和理念。例如,在2014年玻利維亞頒布了《礦權回收法》,限制了本土和海外私營企業的礦業特許經營權,規定采礦活動必須通過與COMIBOL簽訂協議進行。對于海外投資,雖然玻利維亞允許外國企業在玻利維亞進行投資,但是在采礦、油氣領域的重大投資項目需要與玻利維亞合作,且玻利維亞必須持有超過半數以上股份[9]。
3.3 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也是中國企業投資的首選[10]。該國的煤、錫、鎳、金、銀等礦產產量居世界前列,是國際煤炭,及鎳、鐵、錫、金等金屬礦產品市場供應的重要來源[11]。礦業作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支柱產業,資源民族主義思潮對于其資源政策有著深刻的影響。
印度尼西亞的資源民族主義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印度尼西亞經歷了荷蘭長期的殖民統治,在殖民統治時期,荷蘭政府和私人公司通過占據原住民的土地開采礦產獲得了巨大收益,而原住民始終被排除在外。印度尼西亞自獨立起,資源民族主義和對待海外投資的懷疑態度便成為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參與者的共識。因此,印度尼西亞獨立初期對礦產資源主要實施國有化政策。印度尼西亞在1965年政變后到1998年的“新秩序”時期,其經濟政策比較搖擺,在早期或是大宗商品低價時期推行自由化政策,試圖盡量吸引海外投資,并在后期或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后推行資源民族主義政策。在這些資源民族主義政策中,本土的礦業開采和相關下游企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話語權也得到進一步增強。因此,在后蘇哈托時代制定全新的礦業法律過程中,更多的礦產資源本土化和國有化目標得到了實現,并且在2009年制定的礦業法、2014年對原礦出口的禁令中得到更加明確的體現。總體而言,印度尼西亞政府的資源民族主義觀念在后蘇哈托時代形成了一種常態,區別于蘇哈托時代政策的“鐘擺化”,即使在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情況下,這種資源民族主義政策傾向依然明顯。
3.4 坦桑尼亞
坦桑尼亞礦產資源和能源都十分豐富,礦業是坦桑尼亞的主導行業,也是發展速度最快的行業之一。由于礦業在坦桑尼亞的重要地位,自坦桑尼亞獨立以來資源民族主義就深刻地影響著其礦業管理方式,乃至政治結構。總體而言,坦桑尼亞經歷了三次資源民族主義浪潮[12]。
坦桑尼亞第一次資源民族主義浪潮是獨立不久后的1967年,左翼發展思想認為自然資源是生產資料的一部分,應該歸屬全民所有,由國有企業代表國家直接進行開采利用,而非交給外國。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受到外部政治環境,以及經濟危機的影響,坦桑尼亞的公共部門受到沖擊,導致私人非法采礦泛濫,坦桑尼亞不得不接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新自由主義化要求,實施吸引外資和保護外國私人投資者權益的政策。第二次資源民族主義浪潮發生在2005—2015年,具體表現為要求對外國投資公司簽訂的合同和條款進行重新談判,對外國投資者參與的采礦項目進行調查,對相關法律進行修改,強調在礦業中增加本土成分等。第三次資源民族主義是2015年馬古富力就任總統后,采取了更加嚴格的資源民族主義措施,頒布一系列法律法規,強調對含有外資的采礦公司的審查權力,要求采礦公司滿足本土持股比例的要求,以及優先選擇本地的雇員和服務等。
3.5 發達國家
對資源民族主義的研究通常聚焦于發展中國家,然而資源民族主義思潮和政策卻不僅局限于此,資源生產型的發達國家同樣在礦業政策上受到資源民族主義影響[13]。這種資源民族主義通常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典型的重商主義政策,包括國家對于資源合同的干預介入和以國家安全為由,對能源資源領域中的外資進行限制[7]。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繁榮期,日本對澳大利亞的鐵礦石有大量的需求,澳大利亞就借此機會推行資源民族主義政策。1973年,澳大利亞政府聲稱日本鋼鐵和外國采礦公司掠奪了澳大利亞資源,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減少日本控制份額的措施,如對境外投資進行審查,增收礦產品出口稅,推動礦產品價格上漲,以此增強澳大利亞從礦產品出口中獲利的能力[14]。另一方面是在資源戰略方面,傾向于保留本國的資源。美國的能源政策同樣受到政治影響十分嚴重,自20世紀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以來,特別是21世紀民主黨執政期間,作為石油儲量十分豐富的國家,以環境保護為由限制開發本國部分地區(如東部墨西哥灣等)的石油,而是從其他產油國大量進口石油[7]。而在共和黨執政期間,則傾向于強調能源自給,如布什政府解除了對阿拉斯加灣的油氣禁令,特朗普政府則進一步強化這種“能源新現實主義”,大力推進頁巖油氣的生產,擴大美國油氣資源的出口[15]。
因此,資源民族主義并非是某些地域或是發展中國家的特質,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個資源出口國。但是,從空間地域上看,不同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舉措和訴求是有差異的;從時間演變上看,同一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表現也會受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影響。就本文討論的國家而言,俄羅斯作為地區性強國,資源民族主義政策對內是對其20世紀90年代過度自由化的糾正,對外作為杠桿,起到實現地緣政治目標的作用;玻利維亞的資源民族主義則與其政治方向變化關系密切;印度尼西亞的資源民族主義與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有著深厚的淵源;而在澳大利亞、美國等發達國家,資源民族主義政策是保證本國利益和資源安全的重要手段。
4 結論和建議
資源民族主義廣泛存在于世界各國,其目的是服務于本國的資源利益,但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國內國際環境中表現形式不同。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作為資源輸入國,我國企業有“走出去”的需求,在國際市場投資和競爭中資源民族主義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必須持續跟進和深化對該問題的研究,加強對資源供需體系變化趨勢和資源生產國政策取向的把控能力,避免投資損失,提升我國能源資源的供給保障能力。
我國要深入實施“一國一策”戰略,針對各個國家特點,深入了解當地的資源開發格局和投資環境,熟悉鉆研當地法律條款和政治變化趨勢,未雨綢繆,避免在利益分配或者政權變化時產生糾紛。與資源合作國建立穩定的外交關系,創新資源外交模式,營造有利于我國企業投資的競爭環境。研究資源民族主義背后的真實訴求,提前準備應對方案,并長期關注其動向和發展趨勢。以實現共贏為目標,可以適當放棄短期利益,構建與當地政府的友好關系,以獲取長遠收益。遇到糾紛時,要堅持立場,充分利用外交、法律、利益協調等多種方式予以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