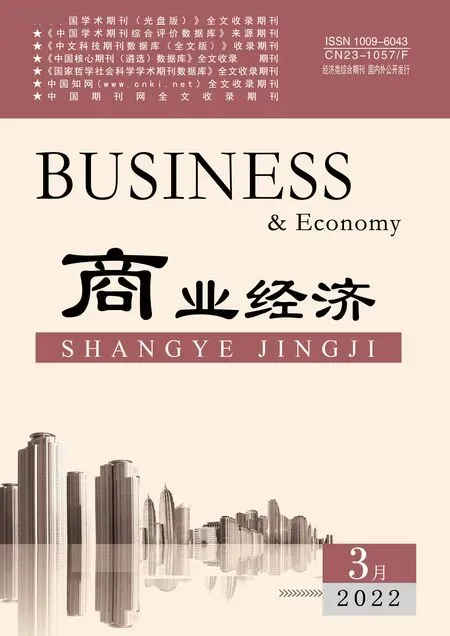全球價值鏈視角下我國中藥產業國際化問題及策略分析
吳玲霞,高 山,翟 菲
(南京中醫藥大學翰林學院, 江蘇 泰州 225300)
一、引言
中醫藥作為中華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國各族人民在幾千年生活實踐和與疾病做斗爭中逐步形成并不斷豐富發展的醫學科學,是我國醫藥衛生事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我國對中醫藥事業發展的重視不斷加強,相繼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劃(2016-2020)》《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中藥材保護和發展規劃(2015-2020)》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使中醫藥事業得到長足發展。
隨著中藥國際化進程的加快,我國中藥已出口到193個國家和地區,已同國外政府、地區主管機構和國際組織簽署了86 個中藥合作協議。2019 年我國中藥類產品出口額40.19 億美元,同比上升2.82%,然而,隨著世界各國對天然藥物潛力市場的重視,國際中藥產品市場競爭激烈,但是國際市場占有額較低,且出口產品結構以中藥材為主,保健品出口占比較低,附加值較高的產品出口占比較低。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醫藥抗疫方案更是為全球疫情防控貢獻了中國智慧,為中醫藥國際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因此,基于價值鏈角度分析我國中醫藥產業貿易,為更好地推動我國中醫藥國際化、推動產業邁向價值鏈中高端具有重要意義。
二、全球價值鏈理論
邁克爾·波特于1985 年在《競爭策略》中首次提出全球價值鏈概念。波特認為,每個企業的產品設計、生產、銷售和售后,包括商品采購、技術支持等輔助器產品的過程都可以用價值鏈來表示。“微笑曲線”理論是臺灣宏碁創始人施振榮先生于1992 年提出的,其也稱“附加值曲線”將產業鏈明確地劃分為上游、中游、下游三個階段。即整個產業鏈條價值實現過程中,生產活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的利潤分配。該理論的提出為全球價值鏈的研究提供了一種視角。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國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參與國際分工體系,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如我國通過改革開放,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引進資本和先進技術,以代工方式切入全球價值鏈。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分工向發達國家學習先進技術和現代企業管理方法,但是只能通過廉價勞動力或自然資源參與,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階段,總體獲益較低。
中醫藥產業體系由中藥材出發,經過中藥商業、工業部分,對原材料進行加工,得到中成藥、中藥飲片、中藥保健品等中藥產品,最后流向醫院藥房等使用場所,包括種植、加工、流通等環節,涉及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傳統的中藥產品包括中藥材、中藥飲片和中成藥三大類,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中藥資源得以開發與綜合利用,中藥產品的形式逐漸多樣化,其用途不斷擴大,現已形成了中藥提取物、中藥保健食品、中藥化妝品及中藥日用品等范圍較廣的系列產品。
三、我國中藥產業國際化現狀
(一)中藥類商品貿易額穩步增長
近年來由于全球經濟下滑,加之中美貿易的摩擦,我國中藥類商品貿易受到一定影響,但在政府出臺一系列政策的支持與引導下,我國中藥類商品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保持穩定增長態勢。如圖1 所示,2014-2019 年我國中藥類商品貿易額穩步增長,從35.92 億美元增至40.19億美元,出口平均增速為7.11%(如圖1)。

圖1 2014-2019 年我國中藥產品對外貿易額(單位:億美元)
2020 年中醫藥在抗疫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藥貿易取得了一定成績。中藥材出口量達11.77 萬噸,同比增長8.8%,出口額達8.4 億美元,同比增長1.8%;進口量達5.86 萬噸,進口額達1.76 億美元;中式成藥出口量達1.11 萬噸,出口額達2.39 億美元,同比增長2.5%。
(二)出口的商品附加值低
我國出口中藥產品的種類豐富,不僅包括附加值較低的中藥材及飲片、植物提取物,而且包括附加值較高的中成藥、保健品等。因中藥產品出口沒有獨立編碼,出口的中藥產品中附加值較低的植物提取物占比最高(如圖2),在中藥總出口中占比約60%,其中蟲膠、樹脂及其他植物液、汁在植物提取物出口占比72.5%,雖然我國中藥產品出口總額在不斷增長,但處于價值鏈高端的保健品在中藥出口總金額中占比僅6%左右,且2014-2019 年出口總額反而下降。

圖2 2014-2019 年四種中藥類產品出口額(單位:億美元)
附加值不同的產品其出口方式也有差異。中藥材及飲片和植物提取物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無需太多的技術性加工,屬于價值鏈的低端,以直接出口為主。中成藥和保健品對技術要求較高,則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投產,并運用國外的科技優勢以推動產品升級。
(三)新興出口市場增速強勁
目前,我國中藥類產品已經出口至193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是最主要的中藥產品出口市場。2019 年,我國對越南、印度、馬來西亞、中國臺灣與韓國出口金額均呈現了雙位數增長,其中對排名前三的國家出口中藥商品的總金額增幅為69.26%、34.05%與24.55%,向亞洲市場出口的中藥產品占中藥品出口總金額的54.26%。
就細分市場而言,美、日、中國香港分別為中國中藥產品出口前三的市場。美國作為穩定需求國,進口額從2015 年的5.4 億美元持續攀升到2018 年的6.66 億美元,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2019 年我國出口美國的中藥產品總金額有所下降,但仍居我國中藥產品第一大出口市場。隨著中日關系的緩和,日本為我國中藥材出口的最大市場,中藥產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場,且出口量較為穩定。香港為我國中藥品出口的第三市場,由于近些年失去了中藥品轉口貿易的優勢,越來越多的買家選擇從原產國直接采購,因此近年來對香港出口中藥產品的規模呈下降趨勢(如圖3)。

圖3 2015-2019 年中藥產品出口各國貿易金額(單位:億美元)
(四)中藥企業以出口為主,國際化經營較少
目前,我國中醫藥企業國際化多以直接出口為主,由于國際上嚴格的認證標準,對中藥藥品質量控制要求和臨床試驗要求非常嚴格,中藥生產企業在國外市場注冊難度較大。同時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國外消費者對中藥文化的認同度較低,使得中藥企業國際化經營難度加大。另一方面,中藥企業內部高級管理人員對國際市場缺乏相應的認識,且缺少海外學習和工作的經驗,對開拓海外市場,國際化經營比較保守。目前我國部分中藥企業國際化通過海外建廠,如北京同仁堂通過境外投資建立跨國公司、三九集團通過收購日本東亞制廠、天津天士力通過海外建立銷售渠道,進行國際經營。
四、我國中藥國際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中藥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弱
近年來,雖然中藥產品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認可和使用,出口總金額也在增加,但是我國生產的中藥產品在國際市場中所占比例較低。國際市場中中藥及植物藥的銷售額每年可達300 億美元以上,我國中藥出口額不足國際中草藥市場的10%,出口的中藥產品中有超過70%的產品為處于產業鏈上游且附加值低的原料藥材。其中日本和韓國憑借漢方藥、韓藥享譽海外,其中日本的漢方藥占比70%以上,韓國漢方藥占比約10%。美國目前擁有TwinLabs、GNC 等雄厚的大型植物藥公司,英、德等國家的擁有先進的技術與雄厚研發資金,生物植物藥在國際市場中占據競爭優勢。日、韓、美等國以低價從我國進口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原料藥,然后運用先進的生產與制藥工藝,精煉提取后生產附加值高的植物藥產品,從而賺取高額利潤。
(二)中藥企業創新能力較弱
我國中藥企業缺乏大型的制藥跨國企業,研發投入嚴重不足,創新能力薄弱。國際上一般認為,研發經費占營業收入的1%或以下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難以生存,占5%以上才具有國際競爭力,2019 年我國67 家上市中藥企業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比的中位數僅為3.28%,只有33家中藥企業達到或超過這個水平,僅有龍津藥業和康緣藥業兩家企業的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比超10%。其中,白云山、大理藥業、太安堂、云南白藥、信邦制藥、國發股份的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低于1%,遠低于發達國家10%的平均水平。同時,許多企業將資金分布在廠房、設備的更新換代方面,或者將精力放在研發成本低、周期短的仿制藥領域,企業缺乏自主知識產權,致使產業發展缺乏持續動力,我國的中藥產品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處于低端的生產原料等領域,而價值鏈的高端領域被日、韓、歐美等國所占據。
與此同時,中藥企業在拓展海外市場的過程中,注重中藥產品的商品功能,而忽視創新的營銷方式。加之,市場的特點與文化的差異使得中藥與出口國融合度不高,從而使得中藥產品附加值低,市場黏性不足。
(三)缺少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標準體系
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是國際化的重要保障,清晰的國際標準建設定位將賦能中藥產業。發達國家對藥品有效成分、砷化物和重金屬等藥品質量方面有高規格標準,因此我國出口的中藥產品質量標準與國際植物藥有一定的差距。對于中醫藥ISO 標準的制定,世界中醫藥標準化技術委員會(ISO/TC249)于2019 年底公布了47 項,雖然我國參與制定的數量以34 項在數量方面占有絕對優勢,但我國在制定中藥國際標準時對中醫編碼規則、相關術語等方面比較重視,而忽視了中藥制劑生產、劑型質量等關于產品導向方面的國際標準。一方面我國中藥產品質量標準與國際通行標準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制定中藥國際標準的產品與產業導向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中藥國際化。
(四)缺乏國際化經營的意識與經驗
我國中藥企業缺乏國際化戰略規劃,對海外經營風險的擔憂,缺乏“走出去”的勇氣。目前,我國中藥企業有數千余家,但是多以中小微企業為主,且90%以上的企業年營業收入在千萬元以下,真正走向國際市場經營的中藥企業屈指可數。同時,大多數中小型中藥企業缺乏國際化經營應具備的先進管理體系、且經營模式較為陳舊,對國際化經營缺乏系統的、適合自身發展的國際化戰略規劃,所以中藥企業難以適應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化,與日、韓、歐美等國家的同類企業相比缺乏競爭力。此外,我國中藥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產業集群效應明顯不足,即使有部分企業已經“走出去”,但由于其缺乏國際化戰略規劃,在海外孤軍奮戰,不利于形成產業集群。
五、提升我國中藥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策略
(一)制定我國中藥產業國際化戰略
中醫藥國際化不僅是產品國際化,而是集政、產、學、研等為一體的系統工程,因此,國家應從宏觀層面制定中藥產業國際化戰略以推動中醫藥朝著國際化發展,應建立多部門協調機制,完善中藥產業發展平臺。由政府主導部門牽頭,地方政府、中醫藥教育機構、社會服務組織機構、中草藥材種植和加工生產企業、金融機構等聯動匯聚,組織研究中醫藥國際化相關扶持政策。醫藥并舉,推動中草藥種植,中醫藥品生產加工、中藥材現貨期貨交易服務為代表的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重點扶持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推動中藥事業和產業相融合。
(二)技術創新引領我國中藥產業全球價值鏈分工
我國有數千年的中藥文化與理論系統,根據藥材的產地不同又有北藥、云藥、廣藥等,產自不同區域的中藥其在全球價值鏈建設中,需要根據出口國家和地區的地理位置,因地制宜從而選擇合適的對外貿易的產品。政府應增加專項經費投入鼓勵科研單位進行藥材育種技術創新,支持跨國藥材的發展,將先進成熟的藥材種植技術傳遞給出口國家。同時,中藥企業應持續加強研發投入,做好醫藥科技研發,用科技手段實現傳統藥物價值,打發提供其資源附加值,通過國外投資策略與出口國家的相關醫藥企業合作建設中藥資源產業供應鏈及參與價值鏈分工。
(三)加快與國際標準接軌,全面參與規則制定
目前,標準與知識產權已成為提高中藥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世界已進入由標準與知識產權規范制約市場的時代,ISO(國際標準化組織)成立的中醫藥技術委員會對中醫藥國際標準出臺了20 余項,因此,應重視我國中藥標準化建設,加快與國際關于中醫藥的標準接軌,以提高我國中藥企業提高中藥產品質量,促進中藥國際化。
宏觀層面,政府應對不同的機構進行標準制定的合理分工,做好傳統醫學標準建設的統籌工作,重視產品標準的質量建設,與相關國家的科研機構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建立國際合作,抓住中藥原料的國際認證標準,建立國際認可的傳統藥物標準規范體系,提高良好生產規范管理水平,完善中藥方劑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微觀層面,我國中藥企業與相關監管部門應熟悉中醫藥國際通行標準與新立標準,重視標準申報,同時通過與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標準化組織等提供的平臺積極參與國際化標準修訂,做好與國際化標準接軌。
(四)強化中藥企業國際化經營意識,提升跨國經營能力
中藥企業應深入研究海外市場的醫藥法律與政策,熟悉海外市場的投資環境,根據海外市場特點,制定合理的營銷策略。一方面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建立完備的中藥產品研發中心,研發難以仿制與替代的產品,以提高國際競爭力。同時,充分借鑒日本漢方、韓國韓藥的國際化經營的經驗,規范管理體系,提高國際化經營意識。
中藥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可通過“一帶一路”戰略與沿線國家的開展互補性合作,通過海外直接投資、合作經營等方式探索新型的國際化經營模式。結合中醫藥文化的特點,拉動行業內的優勢資源走出去,挖掘中藥產品的文化內涵與人文關懷,提升中藥產品的附加值。同時,中藥企業應在數字貿易的大環境中,運用云計算等現代技術手段,依托“互聯網”發展跨境電商,探索中藥新零售模式,積極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