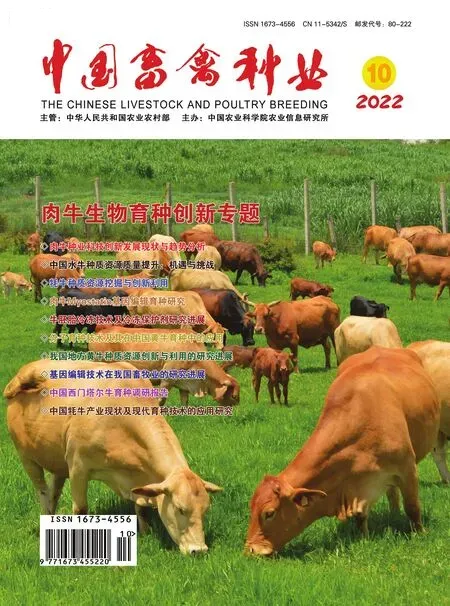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提升:機遇與挑戰
張博 肖鵬 周金陳 尚江華,3*
(1.廣西水牛遺傳繁育重點實驗室,廣西南寧 530001;2.農業農村部水牛遺傳繁育技術重點實驗室,廣西南寧 530001;3.中國農業科學院廣西水牛研究所,廣西南寧 530001)
中國畜禽遺傳資源約占世界總量的1/6,是世界上畜禽遺傳資源最豐富的國家。種業是國家重要戰略產業,畜禽種質資源是現代畜牧產業發展的基礎。中國水牛,作為一種在中國古代便被馴化并在農業領域發揮作用的家畜,是我國重要牛種資源,也是我國畜禽遺傳資源的重要部分。中國是世界水牛養殖大國,水牛存欄量多年保持在2000 萬頭以上,水牛存欄量位居世界第三[1]。隨著我國畜牧業的快速發展,人們消費水平、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對營養價值更高的水牛奶、水牛肉的需求也在日益提升。水牛種質資源提升是我國發展水牛產業的前提和根本,是振興我國水牛業的關鍵環節。
中國水牛開發利用前景廣闊,在農耕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能順應人們對水牛奶和水牛肉的需求,因此水牛業逐漸成為我國養殖行業的發展重點。特別是在潮濕氣候的南方,奶水牛產業逐漸成為畜牧業發展重點之一。在過去幾十年內,中國水牛業在國家政策的指引下,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水牛種質資源也有所提升,但是由于我國水牛業起步較晚,水牛業在國內畜牧業中所占份額較小等因素,使得我國水牛由役用轉向乳用、肉用的時間跨度較長,水牛產業整體水平偏低。與水牛業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水牛業在種源數量、產業化程度、種質資源保護等方面還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我國水牛種質資源保護相關工作不盡人意,發展速度緩慢,有些本地品種如上海水牛已經滅絕,這與中國水牛養殖大國的地位嚴重不符。另一方面,我國現有水牛存欄量、水牛肉及水牛奶等各種水牛產品的市場存有量逐漸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因此,對于我國水牛業來說,解決當下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難題、提升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并開發新品種水牛的工作具有長遠意義。該文概括了中國水牛繁育及水牛種質資源發展歷程和現狀,介紹了國內外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提升先進方法,為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改進和提升提供了建議。
1 中國水牛品種類型、分布特征及歷史起源
水牛(Bubalus bubulbs)是偶蹄目(Artiodactyla)、牛科(Bovidae)、水牛屬(Bubalus)的馴養家畜,屬于大型動物,因其皮膚較厚、汗腺不發達、天氣炎熱時需要在水中浸泡散熱而被稱為“水牛”。水牛在全球各大洲都有存在,物種資源豐富,其品種可分為沼澤型和河流型。中國水牛系由亞洲野水牛馴化而來,具有耐熱、適應力強、肌肉豐滿;生長發育快、飼養成本低;性情溫順、易調教管理;挽力大且役力強等品種特點,故長期以來水牛在我國主要為役用。中國水牛分為沼澤型,包含濱海湖水牛、福安水牛、德昌水牛等共計14 個地方類型。另外,中國本土水牛在來源、體貌特征、生物學特性等方面都相近,因此目前尚難對中國本土水牛做出品種劃分,故我國水牛只有中國水牛這一個品種[2]。
中國具有廣袤的土地面積,東西、南北跨度大,中國水牛廣泛分布于中國中部和南部的18 個省份,如廣西、廣東、湖北以及云南等,集中分布在中國西南和東南部的長江流域周圍,而在中國西北部的陜西和山東兩省也有少數水牛存在。就我國水田分布和各地區地勢情況來看,中國水牛分布又存在南多北少、西多東少及湖區、平原多,丘陵、山區少的特征[3]。
中國馴化、飼養水牛的歷史悠久,在農耕文明時期水牛就作為役用家畜在農耕領域中發揮重要作用,當前在我國一些欠發達地區及農業機械化普及程度較低的水稻種植區,水牛仍然被視為主要的農耕工具。我國考古學家已經證實,中國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馴化出家養水牛。另外,我國曾發掘出距今300萬年前新生代第四紀更新世紀的水牛化石,在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水牛骨骼,有關沼澤水牛在中國被馴化的時間,最早可追溯至七千年前中國長江流域開始發展水稻種植之后的時期[3]。這些考古學領域的發現都證實了中國具有悠久的水牛馴化、飼養歷史。
2 中國水牛種質資源開發與應用歷程
中國有大面積的水稻種植區,農業機械化發展、普及程度比西方農業發達國家晚,所以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中國水牛因中國農業發展現狀及其腕力大、役力強等品種特性在中國的許多地區主要被視作農耕役用工具,水牛乳用、肉用性能的開發利用工作也是在近幾十年來才有所發展。相比豬、雞等家畜,水牛作為大家畜,世代間隔長,育種周期也長,這對我國水牛繁育及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提升工作來講是很大的挑戰。此外,相比我國黃牛、奶牛的養殖量及黃牛、奶牛產品的市場需求量而言,水牛養殖量與水牛產品市場需求量還存在很大的差距,水牛養殖業規模化、標準化整體水平也偏低。隨著我國農業的發展,機械化逐漸在農業領域普及,加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水牛肉和水牛奶的營養價值逐漸被發掘,中國水牛逐漸開始了由役用向肉用和乳用的轉型。但是長時間以來,我國水牛繁育方法較為傳統,沒有形成系統的水牛選育方法,因此也出現了一定規模的遺傳漂變,使得我國本土水牛的優良性狀逐漸減少,水牛種質資源質量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和發展。現有水牛品種、數量所帶來的水牛產品已經逐漸無法滿足市場更高的需求,且有些地方品種水牛已經滅絕或是瀕臨滅絕。因此,建立科學高效的中國水牛繁育方法,吸收國內外水牛先進育種技術,提升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應是中國水牛產業當前的工作重點。
2.1 中國水牛傳統育種方法
中國水牛傳統育種方法依據較為簡略,如通過測量水牛乳房性狀指數、泌乳天數、產乳量等數據來判定水牛的乳用性能;根據水牛的體貌特征、體尺和體重、群體遺傳基礎等數據作為判定水牛種質特征的依據;通過統計水牛發情周期、犢牛初生重、生命周期及利用年限等數據來判定水牛繁殖性能等,并且結合以上數據對水牛品種質量做出評估。中國水牛傳統繁育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中國水牛的種質資源的質量,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保證了中國水牛作為農耕役用工具的數量。
從整體水平看,水牛傳統繁育方法較為粗放,選種及水牛種質資源質量的依據多停留在生長性能等表型數據,并沒有考慮到影響水牛性狀的分子、基因等更深層次的因素,使得中國水牛許多優良性狀逐漸減少,水牛種質資源質量逐漸降低,水牛種質資源保護和提升工作在很長一段時間止步不前,甚至還出現了水牛數量下滑和中國水牛地方品種滅絕的情況。因基因型的缺乏,傳統的繁育方法不能高質量、高效率的完成中國水牛由役用向肉用及乳用轉型工作,很難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因此,提升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完成中國水牛功能性轉化工作迫在眉睫。
2.2 中國水牛雜交改良之路
隨著家畜繁殖育種技術的發展,傳統選種選育方法逐漸不能滿足提升我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任務的要求,這使得我國逐漸開始引進國外優良品種水牛進行水牛雜交改良工作,通過雜交改良、橫交固定等育種方法,逐漸培育出了乳肉兼用型雜交水牛群體。在1957 年和1974 年我國分別引進了印度摩拉水牛和巴基斯坦尼里-拉菲水牛,并與中國本地水牛進行二品種和三品種雜交改良實驗。通過數十年的選育、鞏固遺傳性等一系列雜交改良工作,我國水牛品種改良工作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加快了中國水牛向乳用、肉用的轉化速度,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提升明顯。例如摩雜一代、摩雜二代、尼雜一代、尼雜二代、三品雜(摩拉×尼里·拉菲×中國本地水牛)和三品雜互交子一代泌乳期產乳量要明顯高于中國本地水牛,并且多個雜交水牛品種乳汁中蛋白質、干物質等成分含量均有所提升。由于雜交牛體格和體重更大,產肉性能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乳用性能方面,雜交改良獲得三品雜和尼雜二代兩類水牛群體的產乳量已經達到了引進水牛品種的水平,成為了中國水牛乳用雜交改良的主要方案。水牛雜交改良工作取得斐然成績的同時,也為我國許多水牛養殖區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我國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自1997 年開始,以“中國—歐盟水牛開發項目” 為契機,開展中國水牛雜交改良工作,在十年的時間內累計改良水牛近五萬頭,其中優質雜交水牛近兩萬頭,由此產生的水牛奶等水牛產品的經濟效益為德宏畜牧業產值做出了巨大貢獻。
引進國外水牛優良品種的雜交改良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國水牛種質資源,提升了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但通過引進國外水牛來改善中國水牛品質,以實現向乳用、肉用轉化的雜交改良工作也面臨很大挑戰。引進國外優良品種水牛進行雜交改良工作所需時間周期長,且會使我國水牛培育優良品種工作對國外核心種源依賴性強,不利于我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我國水牛業整體養殖水平不高,養殖環境較差,水牛缺乏適宜的養殖環境和科學的養殖方法,水牛動物疫病防控體系還未到達養豬業、養雞業等養殖行業水平。在我國,水牛雖然抗病力較強,但也存在子宮內膜炎、腐蹄病等疫病。水牛疫病是影響我國水牛生產性能的一大難題,也是提升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工作必須解決的困難,長期從國外引進水牛進行雜交改良工作,國外各種水牛動物疫病傳播至國內的風險也會隨之上升。
2.3 家畜繁殖技術在中國水牛育種中的應用
在我國水牛雜交改良工作取得優異成績的同時,國內水牛產業開始探索更高效的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改良方法,即采用各種家畜輔助生殖技術。家畜輔助生殖技術是一種協助家畜高效率、高質量繁育的手段,包括人工授精、精液和胚胎冷凍保存、超數排卵、胚胎移植等方法[4]。家畜輔助生殖技術的推廣應用使得我們能夠利用具有遺傳優勢的公母畜獲得更多優秀品種后代,進而提升優秀公母畜的利用效率和后代種質資源數量和質量。目前,我國水牛業已經基本普及了人工授精,并逐漸推廣使用同情發情、活體采卵、胚胎移植等輔助繁殖技術,提高了水牛繁育的效率和質量,但是我國早期人工授精和同期發情技術所使用的受體大多是雜交水牛或是本地水牛,很難有效提升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近年來,我國利用引入的國外優秀品種水牛凍精及培育的純種后代,結合人工授精、同情發情、活體采卵、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等技術來改良中國水牛品種質量,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如我國廣西地區曾引用水牛凍精與原引進的本品種母水牛建立新的水牛品系,研究表明,培育的后代在成年體重、體斜長、胸圍等數據指標與地方標準相比達標率高達93%,并且有些生長指標已經超過了地方標準[5]。2018 年以來,利用整合的水牛活體采卵—胚胎體外生產技術開展了較大規模的胚胎移植技術產業化應用,也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水牛凍精、胚胎的引進和我國傳統的引進國外優秀品種水牛進行中國水牛雜交改良工作本質是相同的,都是為了最終固定優良基因型,形成專門化水牛品系,區別在于胚胎和精液屬于細胞水平遺傳資源引入,可以減少個體引入疾病傳播風險,降低運輸成本。引入細胞水平優良水牛基因型,可以快速增加符合我們育種目標的基因資源,加快我國水牛種質資源快速質量提升。通過水牛胚胎的引入無疑是更直接而高效的,胚胎屬于全基因組基因資源引入,就猶如攜帶全能性的種子一般,通過在國內進行胚胎移植后,快速擴繁不同家系、建立不同種群,快速增加我國水牛育種素材,大幅度縮短育種年限。同時根據我們的需要還可以進行胚胎性別控制,根據養殖場的需求進行不同性別水牛的擴繁,以滿足我們的生產需要。在胚胎資源引入方面,廣西壯族自治區做了許多工作積累,首先在水牛胚胎生物技術研發方面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胚胎生產技術、胚胎移植技術能夠實現產業化運作,為引入國外優良胚胎資源提供核心技術支持。隨著“一帶一路” 的發展及中巴全方位、多領域合作的深入推進,中巴經濟走廊項目的實施促進了巴基斯坦優良奶水牛資源引入我國的進程,目前,中巴兩國政府就水牛胚胎輸華的檢驗檢疫協定已經達成一致。中國皇氏集團子公司皇氏賽爾生物技術(廣西)有限公司已經在巴基斯坦建立了水牛胚胎體外生產中心并投入使用,并將在巴基斯坦建立中巴雙方認證的水牛無疫小區,為巴基斯坦良種奶水牛胚胎出口到中國做好前期工作基礎。一旦巴基斯坦水牛胚胎可以批量出口到中國,將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中國奶水牛產業發展的良種需求,為我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提升提供良好的契機。
3 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提升的曙光—分子育種技術
3.1 分子育種技術的應用
家畜分子育種是一種利用分子數量遺傳學理論及相關技術來改良家畜品種的技術,是家畜傳統育種理論的創新發展,包括轉基因育種和基因組育種兩種技術手段。其中,轉基因育種通過轉基因技術等手段將外源基因導入到家畜基因組上,并在后代進行選種選育,直至育成轉基因品系,從而達到改良家畜性狀的目。與轉基因育種不同,基因組育種通過基因標記技術對動物數量性狀座位進行選擇,或通過標記輔助來導入或清除基因,以此來高效率的改良家畜品種。隨著分子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及現代生物技術在家畜育種領域的逐漸普及,動物育種技術已經逐漸從群體水平進入分子水平,向著改變基因型的方向發展,涉及DNA 層面的分子家畜育種技術也逐漸開始嶄露頭角。并且隨著分子育種技術在豬、雞、牛等家畜領域應用的加深,其展現出了家畜傳統育種方式所不具有的高效率性、高精準性及創新性。豬的育種技術經歷了由表型選擇至育種值選擇再過渡到基因型選擇的過程,并在分子育種技術的加持下取得了可觀的進展。例如,有學者利用CRISPR/Cas9 介導的基因編輯技術對中國巴馬香豬的肌肉生長抑制素基因(MSTN)進行了雙等位敲出,在進行體細胞核移植之后獲得了MSTN 雙等位基因敲除的中國巴馬香豬,為中國巴馬香豬性狀的快速改良及遺傳資源保護奠定了基礎[6]。優良品種個體的選擇基于準確的育種值預測,而育種值預測又依賴于精確表示關系的譜系。有學者評估了使用單核苷酸多態性(SNP)標記校正譜系關系對肉牛對蜱抗性遺傳評估準確性的影響,結果證明,使用SNP 評估雙親和后代之間的沖突增加了關系的確定性,能夠提高候選肉牛育種值預測的準確性,進而能夠更高效率的選擇優良品種后代[7]。除了家畜領域之外,分子育種技術在許多農作物如白菜、水稻、玉米等行業也取得了矚目的成績,利用分子育種技術培育出的作物新品系在品質、抗逆性、產量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
3.2 水牛業的分子育種技術
分子育種技術在水牛上應用主要是為了開發水牛產奶性狀的遺傳力,為水牛優秀品種后代的選擇提供依據,隨著研究的深入,迄今為止已經鑒定出五百多個與水牛產奶性狀相關的候選基因。盡管我們對水牛的生產特性及水牛產奶特性的分子機制尚未完全了解,但不可否認這些產奶性狀候選基因對水牛產奶性狀都存在一定影響。如有研究人員對384 頭水牛SCAP 基因的分子特征、表達分析以及單核苷酸多態性與產奶性狀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在水牛SCAP基因鑒定出了11 個SNP,其中有6 個與水牛305d 的產奶量顯著相關[8],這為穩定水牛優良產奶性狀奠定了基礎。性別控制在家畜生產中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對繁育周期和時代間隔較長的水牛等大家畜而言。有學者利用CRISPR/Cas9 介導的基因編輯技術和體細胞核移植技術成功獲得了Y-Chr-eGFP 轉基因胎牛成纖維細胞和克隆水牛胚胎,優化了轉基因BFF 細胞的制備方法,并成功地利用這些細胞作為供體產生了Y-Chr-eGFP 轉基因胚胎,為水牛性別控制工作提供了便利性[9]。另一方面,隨著家畜領域分子育種技術應用的不斷深入,相比較傳統雜交技術而言,能夠更快、更簡易、更廉價的對大量基因序列檢測和分析的基因芯片技術也逐漸在家畜育種領域興起[10],基因芯片技術可以作為分子育種的有效工具使得研究人員和育種者能夠將基因組序列信息付諸實踐。分子育種技術的興起為水牛遺產潛力的開發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使水牛優良性狀利用效率最大化速度加快,同時也為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提升工作創造了光明的前景。
3.3 中國水牛分子育種仍然處于起步階段
毋庸置疑,家畜分子育種技術為水牛帶來了更高的育種效率,縮短了育種年限,真正做到了精確育種。中國水牛分子育種研究經過多年發展,獲得了許多中國水牛分子遺傳特征信息,發現了一些生產性狀相關的功能基因,但是由于我國水牛群體穩定性差、缺乏水牛基因組數據、對水牛產生特性尚未完全了解且對水牛產奶特性的分子機制仍不明確等原因存在,加上我國目前對水牛遺傳特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血液蛋白質多態性上,對遺傳物質DNA 的研究很少,中國水牛分子育種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奶水牛基因組數據庫建設及中國水牛保種場建設工作,以為分子育種技術更好地開發中國水牛遺傳潛力、提升中國水牛育種值、改善水牛生產性能等做準備。分子育種技術的興起給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提升工作指引了一條高效率的道路,中國水牛育種應從傳統的育種方式逐漸向以傳統育種為基礎的結合家畜輔助生殖技術發展,并逐漸引入分子育種技術的育種模式。即利用傳統育種方式并結合家畜輔助生殖技術固定中國水牛優良性狀,采用基因芯片等分子育種技術檢測、分析、挑選水牛優良候選基因并付諸到水牛上,不斷提升中國水牛遺傳力,拉近中國水牛從優良基因到優良表型的距離,從而提高中國水牛育種值,擴大中國水牛遺傳優勢,進而逐步建立起中國奶水牛專門化品系,實現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提升的目標。
4 總結與展望
水牛乳含有更高的乳脂、不飽和脂肪酸、乳蛋白以及更低的磷脂和膽固醇,具有更高的營養價值。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對水牛奶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水牛作為世界第二大奶源,據FAO 最新數據(2022 年2 月17 日更新)統計表明,2020 年世界水牛奶產量(13442.52 萬t)占奶類總產量(88686.18萬t)的15.16%,而我國水牛奶產量(292.00 萬t)僅占奶類總產量(3921.95 萬t)的7.45%,遠遠不能滿足國內需求。因此,提升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完成中國水牛由役用向乳用、乳肉兼用的轉化工作,應是當下中國水牛遺傳改良的主要方向。我國傳統育種方式,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中國水牛的數量,穩定了中國水牛部分優良性狀。但各地水牛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遺傳漂變,使得中國水牛丟失了部分優良基因型,部分優良表型也出現了退化的現象。目前,我國主流的水牛育種方法為傳統育種方式結合家畜繁殖技術,其中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在該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績,胚胎引進、生產、移植等技術上走在世界前列,加快了中國水牛轉型速度,為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提升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能夠預見,在不遠的將來分子育種技術將成為中國水牛育種的大趨勢,結合傳統育種方法,融入先進繁殖技術,做好個體、細胞、分子水平水牛遺傳資源利用與保存,使中國水牛種質資源質量呈現出新的高度,是我們當下應該抓住的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