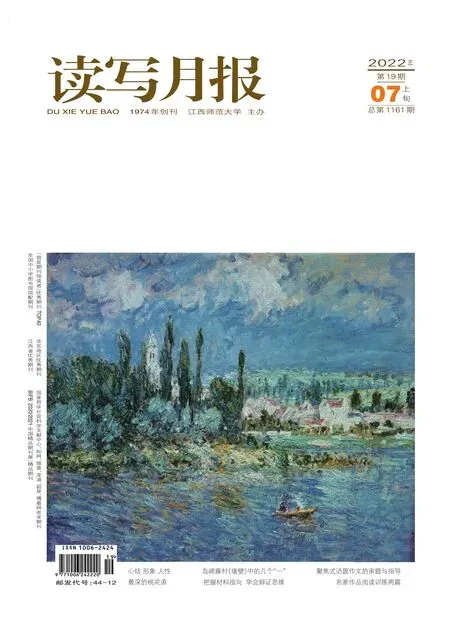【附文】什么是旅行的意義?
[法]保羅·莫朗
旅行在過去首先是集體性質的:遷徙、打仗、朝圣、逃難、轉移,諸如此類。
今天又回到了它的本義:群體遷徙。現在,假期被社會學家冠以別名——“季節性移居”,同時也被看作“消遣活動”。藍色海岸的一處社交圣地的廣告語則委婉表示:旅行是群體的孤獨!
大家都是旅客;留守的人反而變得特立獨行。所有的人都在路上。旅行不再是心血來潮,而是受神秘的遷移規則左右。人情巨變:世人不再難離故土,反而欣然踏上旅程。
當重讀人文地理學大師們的著作時,人們驚訝于游記在白呂納[1]或維達爾·白蘭士[2]的作品中所占的比重之小。他們似乎遺漏了人際關系中變化無常、捉摸不定、變幻莫測的一面。在他們眼中,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間的簡單劃分、歷史上的先例及丹納的環境影響論都各有其長。可能這是因為“地理學家是從土地而非社會出發的吧”(呂西安·費弗爾)。
這是一顆“棲息地”無人棲息的星球;生活的人造環境勝過自然環境,因而導致經濟地理學新篇章的開啟(這些經濟學家在看到外匯大量涌入、無形進口增加后,馬上認識到這關系到一種新興事物)。
地圖冊沉默無言;現代水文模糊了古老的邊疆概念,在圖冊里面尋找它們只是一種徒勞。“自然框架”已死,領土疆界的虛線到此為止;尤其是自發明飛機以來,公路再也不是必然選擇。低匯率打造的“天然通道”比河流、山坳還要多。此外,山坳也不再讓人望而卻步;意大利籌劃在國界處開鑿一百三十七條隧道。
每次參觀野營區、車子組成的移動城市都讓我們收獲頗豐。它們的街道、商店、供水點,一切在幾個小時內都會消失,只消折好帳篷,卷起床褥,發動車子,像馬戲團一樣下次又出現在其他地方,難以想象這會對當地經濟造成何種程度的改變。這就是前原子時代具有“彈性空間密度”的城市。
兩年前,在我們游覽巴利阿里島時,一個馬略爾卡人的話讓我們十分震驚:“這個夏天我們都不能出島;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外地人預訂了;一天內二十架飛機從倫敦起飛,在帕爾馬降落;八月份,島上的外地游客比居民還多。”這在島上是種奇觀。這一單向通道應該具有一種道德含義,即作為一種新文明——度假車文明的征兆。公共汽車取代了被人種學家視為珍貴細胞的村莊,從此葉落歸“輪”。
人的出行同這些外匯交易一樣不可見。相關數據即使不算無用,至少也是滯后的。當數以萬計、難以核實的旅客在星空下露營時,我們如何相信瑞士旅館業每月評估的整夜住宿量的最高數據?
旅行成為新的遷徙動機。人種學家們認為除了饑餓、季節性活動、尋找勞動力外,遷徙還有其他動機:出于圖騰崇拜而遷徙。我們難道沒有參與新偶像——旅行俱樂部、旅游廣告、被所有小說家贊揚過的海灘盛典、海底捕魚、音樂節——的誕生?從前有思想之路;從前有信仰之路,德爾斐[3]、麥加[4]、德?孔波斯特拉之路[5];我們今天還存在尋味之旅,或更甚,迷戀之路,這些路跨越了政治意義上的國界線。
可悲的是,理想的邊境線突然分崩離析。荷蘭人匆匆出國去滿足他們的山脈情結,騰出位置給渴望大海的瑞士人。在不考慮熱火朝天的罷工,辦理簽證,酷熱或蚊蟲叮咬,接種狂犬病、破傷風、天花、百日咳、黃熱病或百白破疫苗的情況下,只消在夏日一個美好的周末注視駛向加拉萬區或瓦洛爾布鎮的鳴著笛、長達三千米的車隊,我們就能發現邊境線存在的日子屈指可數。今天的海關就像1920年前后設置在城市入口的關卡,那時老爺車上哪怕有只諾曼底的小雞沒有申報,也會被攔在馬約門外。
昨天,旅客在靜止的世界坐立不安。在那最好的日子,在經濟危機中的三十年代,人們無須預訂座位,就能跳進總是空蕩蕩的火車里,以低價買到火車最好的車廂的座位!今天,人人都在旅行;公路成了逃離路線;英國人修建了三十分鐘就能組裝完成的房屋;保守主義的象征羅馬教皇也在路上;洋流疲倦于永恒的軌跡,偏離位置,改變了氣候;工程師在中亞山脈引爆原子彈,抽空海水,人工造湖(這種“滲流式遷移”無視國界線,和平條約的起草人及戰略家劃定爭議領地、切割短命國土的心思都白費了);柏林墻同抵御蘇格蘭皮克特人的羅馬長城一樣,都是一種逆行倒退。
我們認為在這些持續的轉移、滲透式的遷徙中存在一種深刻的原因:現代的旅行是個人防御的一種反應,是一種反社會的舉動。旅客則是不屈服的人。這是遠離國家、家庭、婚姻,逃離稅務、多元功能、民族禁忌,避開毆打、違法的一種方式。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類似胡格諾派[6]的反對的抗議,因為胡格諾派的反對口號就是避難;避難、逃離、旅行、自由、解放,凡此種種互為依賴。這些皆關系到“遠離”……
英國人渴望遠離霧霾;美國人渴望遠離中西部的無聊;也有人渴望從專橫的母親、暴躁的妻子、嫉妒的情人身邊逃開。而一旦越過邊境線,你便成了一個異鄉人,不管帶沒帶外幣,你都是一個不可侵犯的人物、一個外國富豪;用利涅親王的話來講:“我喜歡自己無處不是異鄉人的樣子。”有人為了存在旅行,有人為了生存旅行,有人為了擺脫束縛旅行。而為了向自己解釋清楚,我們需要沉到潛意識中去。不由想起亨利·莫尼埃《通俗場景》中的那出幕間短劇。一對巴黎戀人在驛站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年輕女子:要分開了,不吻我嗎?
年輕男子:當然……來……
(女子把面孔埋進手帕里。)
(男子抽著雪茄漸行漸遠。)
旅客想要得到認可,不愿像氣態的幽靈一般,在單調的社會稠液里消融。而這正是瓦萊里在《我的浮士德》中所表達的形而上的東西:
“世界的盡頭在哪里?我多想到彼一游,好確信自我的存在。”
【注釋】[1]白呂納(1869—1930),出生于圖盧茲,法國人文地理學家,法國科學院院士。
[2]維達爾·白蘭士(1845—1918),法國地理學家,法國近代地理學奠基人。
[3]德爾斐是一處重要的“泛希臘圣地”,即所有古希臘城邦共同的圣地。在希臘神話中,德爾斐是世界的中心。德爾斐位于福基斯(希臘西南部的一個州),現在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
[4]麥加是一座歷史名城,是沙特阿拉伯西部省省會,是伊斯蘭教最神圣的城市,因為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誕生于此地而聞名,非穆斯林不得進入。
[5]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這座人口不到10 萬的彈丸小城是基督教中與羅馬、耶路撒冷齊名的三大圣城之一,并由于地理位置的偏遠,在中世紀被人們稱為世界的盡頭。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位于法國南部,跨越多個大區省份。沿路有1800 座建筑,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都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6]十六至十七世紀對法國新教徒加爾文派的稱呼。教徒多為下層群眾和部分資產階級,主張宗教改革,反對國王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