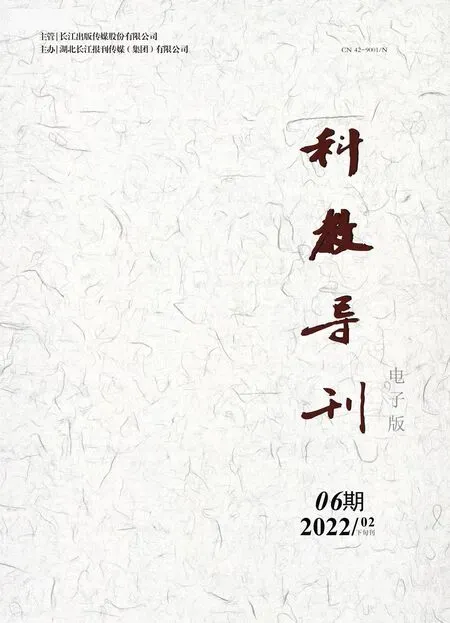淺析余華小說《活著》的悲劇意義
趙怡琳
(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山東·曲阜 273165)
《活著》講述了一個人一生的故事,它是一個經歷世事磨難與滄桑的老人內心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繹世間人生苦難的精彩戲劇。它以一位叫福貴的老人自述的口吻平淡的敘述了自己坎坷苦難的一生,身邊的親人都相繼離他而去,最后只與一頭老牛相依為命,呈現了中國八十年代的人民生活景象。文中的福貴經歷種種打擊之后仍然堅強的活著,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去面對生活的磨難,給予我們以深刻的生命啟示,也帶給我們對悲劇對苦難人生的別樣思考。
1 悲劇的時代背景
小說《活著》講述的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主人公福貴在國共內戰、“文革”動亂、生活災難的背景下艱難生存的故事。福貴的生活故事串起了從新中國成立前至“文革”期間的時代背景,反映了在動蕩的時代背景下,普通群眾人們命運的跌宕起伏。
福貴和書中其他人物的命運與當時的時代脫不開干系。少年的福貴是個家庭富裕,吃喝嫖賭,不學無術地主家少爺,因為賭博把家產都輸給“龍二”以后,“龍二”就在土改中成為福貴的“替罪羊”而槍斃了,而福貴陰差陽錯下進了軍隊,迷迷糊糊參加了解放戰爭,免去了一死,但當他回到家中,卻聽聞母親已經去世,鳳霞也因為生病變成了啞子,再之后的之后,自然災害、大躍進、“文革”的波濤仍不斷掀起,福貴和他周圍的人們生活也變得天翻地覆。
人們的非自然死亡深受當時那個時代和時局的影響,作者的寫作動機也是來源于時代的大背景中。從國民黨統治后期到解放戰爭、土改運動,再到大煉鋼鐵運動,自然災害時期等,社會的變遷造成作者經歷了從大富大貴到赤貧如洗的物質生活的巨大變遷,又一次次目睹妻兒老小先他而去,經歷了種種大變革后,在無意間聽到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時,作者深受觸動,于是創作了《活著》這一文學作品。
作為先鋒派作家的余華,進入90年代后,他逐漸認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1]“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于是就有了1992年的《活著》。在《活著》這部小說中余華以一種非常廣闊的視角,去描繪書中存在的每一個勞苦大眾,這種俯瞰的視角可以使我們在福貴的身上看到那一輩中國人民的眾生相。四十年代到八十年的中國,像福貴這樣的人有很多,對于他們而言,即使生活一次又一次給他們開起了玩笑,但是生活還是要繼續過下去的,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
每個人的命運都被裹挾在時代的洪流里,個體的悲劇其實也是時代的悲劇。時代發展的車輪不斷前進,必須努力活著才能順應這時代的潮流,處于社會大變革中,社會底層人民對社會變革毫無抵抗力。面對著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自己面前死去,無疑是非常殘酷的,對于他們的死感到無力卻還要繼續努力的活著,無疑是痛苦的,到頭來只有一頭老牛陪著自己,無疑是最大悲劇。在經歷種種過后,福貴能夠堅強的活著,平淡的面對生死面對著悲劇的命運,就是“為了活著而活著”,使我們感受到生命的強大力量。同時,小說的悲劇意義在時代這一背景下體現為底層人民的悲劇生活一大方面來源于社會的變革且不得抵抗。
2 苦難背后的生存困境
悲劇的定義簡單來說就是人與占優勢力量(命運、環境、社會)之間沖突。西方社會學家馬斯洛曾提出人的需求的五個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小說中因為福貴的好賭,導致了大家庭的敗落,為了養活一大家子人福貴開始迅速適應自己的新身份,擺小攤找龍二租地,這都是本能的為了解決一家人最基本的生理生存需求。再到后來跟著軍隊打仗,在戰場上賣命逃生,小說中福貴是這樣說的,“我是一遍遍想著自己的家,想想鳳霞抱著有慶坐在家門口,想想我娘和家珍”,這便是歸屬與愛的需求。在家庭敗落的開始,福貴還有著重振家族的雄心,但隨著生活的繼續,這種自我實現的需求便消失殆盡了。當一個個親人相繼離去,父母妻兒以及女婿外孫都去世之后,留給福貴的便只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這一點,在福貴講述自己的故事時露出的微笑可以看出,他已經無欲無求了,在經歷這么多苦難之后,他終于選擇了平靜面對。
對于一般人來說,家庭敗落親人去世孤獨終老無論哪一個都是人生的悲劇,而福貴的一生,就是接二連三的悲劇。《活著》充分體現的一種生與死的悲劇美學,因為生和死是任何人都不能決定和避免的,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不能改變現實,被命運所安排,成為命運的傀儡,這本身的確是一種悲劇。[2]文章中感觸最深的便是福貴一家七口人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從一大家子人變為孤獨一人,讓人感到無法言說的難過與唏噓,每當福貴認為日子就要好轉時,迎接他的就是更大的苦難,人民公社時憑借勞動就可以得到相應的糧食,這對于農民來說是極大的機會,在當他們認為生活就要變好時,家珍不幸得了軟骨病,日子又變得困難了,這就恰如即將見到希望的曙光時又重新籠罩在黑暗的囚籠下,在這之后有慶的死又為這個家庭雪上添霜,這種希望的破滅帶給人們的不光是心靈的極大空虛也是對人生命運的無奈。就像福貴即使沒有因賭博導致家庭破產,也會在打倒地主中被抄家,人仿佛被困在籠子里,生死都有籠里的大手操控,陷入生命的困境。
3 序言中探求悲劇意義
悲劇的意義在于“引起恐懼與憐憫”。在這部作品中,作家余華為這部書一共寫了五個序言,其中可以提取出三個關鍵詞,即樂觀、堅韌、幸福。從提取的關鍵詞中可以使讀者更好的從福貴的一生中探求悲劇的意義。
樂觀即是面對生活的苦難,始終持有一個樂觀的態度。在序言中余華是這樣寫道“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活著”表達的是一份淡然超然的態度,是即使面對生活的一次又一次磨難仍然持有的一個生活態度。回首福貴的一生,他從容地經歷過劫后余生,感受過浪子回頭的澄凈,享受過天倫之樂的溫馨,擁有過人生百味,已經足夠了。福貴是樂觀的,在經歷大風大雨后仍然不被打倒,這已經很厲害了,在生命的余暉里,他微笑的看著他身邊的老牛,嘴里喊著妻兒的名字,他們在陪伴著他。
堅韌即是堅韌地活著,忍受生命賦予的責任,承擔現實給予的一切。這在序言里是這樣表現的,“‘活著’的力量不是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現實給予我們的種種,我們都需要默默地學會忍受。”福貴是能忍的,他沒有因為家境破落,家人離世而墮落,相比于《駱駝祥子》中的祥子,他忍受著生命賦予的責任,堅韌地活了下去。在生活中,像不堪忍受生活的挫折而自殺墮落的人不計其數,有一期的《譚談交通》的主人公是一名違章載人的三輪車車主,父母妻兒全都死光了,只剩他和他的傻弟弟以及一條狗相依為命,他被稱為“現實版福貴”,面對提問的他回答是:活著要向前看,這便是堅韌地活著。
幸福是從“幸存”里捕捉“生活”,在苦難中咀嚼幸福,從一個人的眼眸里看透整個時代。“生活,是一個人對自己經歷的感受;幸存,是旁觀者對別人經理的看法。福貴是講述自己的故事,對于他而言,那只是生活。”在外人看來,福貴是可憐的,他的一生充滿著苦難,早年家境敗落,父母妻兒以及女婿外孫相繼離世,兜兜轉轉,最后福貴只有一頭老牛與自己為伴。但在富貴看來,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相信自己的兒女事實上最好的兒女,還有他的女婿外孫都是頂好頂好的,還有一頭牛過完自己的余生,回想自己的一生,回想到以前的親人朋友,回想到父母給予他的溫情,他覺得自己還是幸福的,至少,在于“我”講述的時候,他是釋然的、滿足的、幸福的。
“苦難”和“救贖”是這部小說的兩個主題。有人認為,余華的小說《活著》是刻意堆砌的悲劇,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活著本身沒有任何意義,有意義的是生活”,福貴在經歷一系列的苦難過后,真正實現自我救贖,以超越苦難的達觀和超越絕望的平靜悠然地生活著,領悟“活著”真正含義,這便是這部小說真正想要表達的主題。
作家余華用福貴的一生對“活著”一詞進行了解讀,在使人們感受到生命的魅力的同時,也引起了讀者的思考。“人總要生存,我們還是會選擇活著”。樂觀堅韌地活著,雖然難免有挫折與苦難,但直面苦難,在苦難中也會咀嚼出生活的美好與幸福,順其自然地與生活融為一體,將好與壞照單全收,站在與自然萬物同等的位置上看自己,這便是悲劇帶給我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