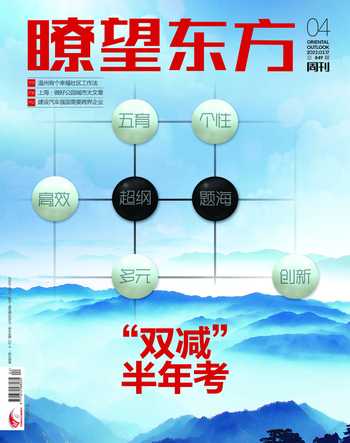讀懂孩子抑郁
李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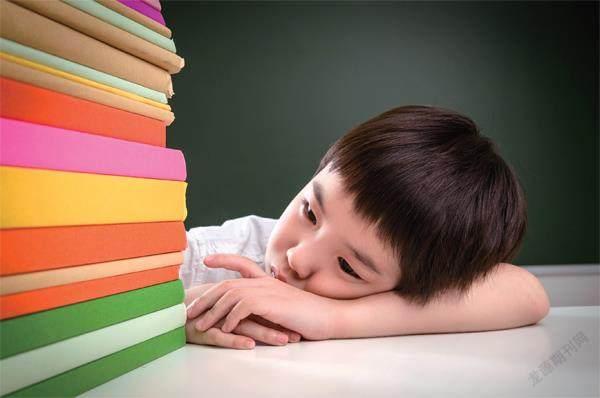
開學季快到了,孩子們正在享受最后幾天假期。但在合肥某校就讀初二的小西(化名)卻并不開心,他說:學習壓力大,想起返校便心煩。
殊不知,在孩子們稚嫩的面容下,可能潛藏著他人不知的抑郁。近期,中國兒童中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兒童藍皮書:中國兒童發展報告(2021)》指出,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嚴重,抑郁癥狀發生率超26%。早在2021年3月,《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也指出:中國青少年2020年抑郁檢出率為24.6%。
這樣的結果令很多成年人想不通:孩子們為什么煩惱?我們該怎么辦?
“為什么我考了前十名,他們還要罵我?他們永遠對我不滿意。”小西煩惱地說,父母對他的高期望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江蘇省鎮江市精神衛生中心曾對鎮江市12歲至16歲的3544名學生進行研究,發現學習情況、家庭教養方式、父母關系、與家人的關系、與周圍人的關系、父母的期望都會對青少年抑郁產生影響。其中,學習情況、與周圍人關系不和以及與家人關系不和是造成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原因。
“如果孩子表達了一些想法而被鎮壓的話,他們可能會失落、心情郁悶,最后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形成‘習得性無助’的心理和行為,進而形成抑郁狀態。”
“家庭、家長的原因是排在第一位的,比如很多家長對孩子的關注維度太單一、對孩子的期望過高或是跟孩子的溝通方式不對等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孩子的抑郁情緒。”心理咨詢師、兒童青少年行為及情緒問題專家、腦軀力團隊負責人尹建民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孩子的抑郁問題主要從青春期開始顯現。隨著當代兒童的早熟,孩子大約從八九歲開始,就可能出現抑郁相關問題。
“其實,兒童是有自主意識的,只是家長和學校常常忽視,可能孩子還來不及表達,就被新的東西所填滿。抑郁問題在青春期的集中爆發,可能與之前所積累的情緒有關。”心理咨詢師楊彩蓮告訴本刊。
從發育開始,孩子們身心發生了跨越性變化,依賴性與獨立性并存。他們開始了對成人世界的探索,身體成長并發生明顯變化,自主意識慢慢發掘,對同伴和群體的需求更大了。但同時,青少年在經濟上依賴家庭,生活經驗不豐富,很多問題難以解決。這讓青少年的心理問題錯綜復雜。
“根據我們的臨床咨詢情況,大約六成孩子因學習成績下滑而被家長帶來接受心理咨詢,結果卻發現了孩子的抑郁心理。”尹建民表示,很多家長主要關心孩子的學習,對孩子其他方面關注過少。
孩子的生活有成長中的各種喜怒哀樂。“如果孩子有一些特殊經歷,會產生‘創傷’。創傷沒有得到及時處理的話,到了青春期可能就爆發。”楊彩蓮表示,被同學孤立、遭遇性侵、家庭變故、痛苦的搬家經歷等都可能給孩子留下心理創傷。在校園,青少年需要適應身邊的同學,這可能帶來“同伴壓力”。楊彩蓮認為,與同學間進行比較帶來的壓力,也可能導致孩子的焦慮和抑郁。
“我覺得青少年與家庭外的人際關系,還是可以追溯到原生家庭。如果媽媽焦慮,孩子也更傾向于有抑郁心理。”尹建民認為,青少年如何看待和對待周邊人際關系,與他的家庭教育、家庭關系分不開。尹建民接觸過諸多抑郁癥“小患者”,發現其家長在心理狀態、家庭關系、教育方法上存在不同的問題。“如果孩子表達了一些想法而被鎮壓的話,他們可能會失落、心情郁悶,最后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形成‘習得性無助’的心理和行為,進而形成抑郁狀態”。
“他們都不會聽我說話,我跟他們沒什么可聊的。”小西認為父母并不在乎他的想法,所以他更愿意在QQ群里“擴列”交友,與網絡上的好友聊天。
而且,家長認為的正確教育方法、方式,可能并不適合自己的孩子。“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個體,如果家長的教育方式不能得到孩子的認同,可能就無法取得預期效果。”楊彩蓮認為。
有的孩子雖然早就出現了抑郁心理,但父母一直未察覺到。“在早期,家長要留心孩子性格上的改變,如果孩子主動暗示,比如表示最近壓力很大,那就不能忽視,要繼續深挖。家長也可以通過老師、同學等第三者對孩子的觀察去了解是否有異常情況。”楊彩蓮表示。
如果孩子的抑郁進展到了一定時期,可能出現身體異常,例如肚子疼、頭疼、嘔吐、頭暈等癥狀。“我們與醫院的神經科也常有聯系,有孩子一到學校就肚子疼,很多時候是心理問題導致的。”尹建民說。
小西甚至嘗試過割手。“這是割得最輕的一次,割手讓我覺得爽。”他發來一張照片,手指割得不深,但有兩道很短的痕跡。在臨床診斷中,這種行為被稱為“非自殺性自傷”,可以幫助抑郁癥患者釋放壓力,獲得自我存在感。
當家長和老師發現孩子們的異常狀況時,就要高度重視并了解緣由。《柳葉刀-精神病學》在2021年9月發表的《中國抑郁障礙患病率及衛生服務利用的流行病學現況研究》顯示,我國抑郁癥的終身患病率為6.8%,超過9500萬人一生中得過抑郁癥,而只有9.5%的抑郁癥患者接受過至少一種衛生服務機構的治療,得到充分治療的患者僅為0.5%。
“兒童青少年時期的創傷不會自動療愈,這是我做十幾年咨詢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創傷可能伴隨一生,因為他從來沒有真正地治療過。有時候,時間只是把其封起來了,但并沒有改變它。只有幸運的人,才能隨著生命的進程獲得自動療愈。所以,我會建議尋找專業人士的介入。”楊彩蓮表示。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幸運兒可能遇到了一個有滋養的環境,遇到有價值的人和事,也可能抓住了人生轉折的機會,有了一個有意義的新身份。
“如果孩子抑郁情況很嚴重,要去醫院服藥,而不僅是心理咨詢。”楊彩蓮建議。
對于青少年抑郁癥患者在得到治療后多久能恢復,尹建民認為“取決于抑郁癥的嚴重程度和家庭的配合程度”。朋友、老師等周圍人的鼓勵和支持也有助于他們的康復。

“當我們幫助孩子建構出有機發展的未來,幫助他找到發展資源,他的生命就流動起來了,創傷也會隨之流走。其實,當孩子出現這些心理問題或者癥狀的時候,家長們也可以一同進行自我清理。幾年之后,也許就有了一個大的蛻變。”楊彩蓮表示。當孩子的情緒具有穩定性,更有信心,社會關系更正常更和諧,他就可能銳變了。
孩子一旦患上了抑郁癥,就難免帶來家庭資源和社會資源的消耗。因此,抑郁癥的預防尤為重要。
“在學校,我們針對孩子本身和家長、老師制定相應的預防措施,形成‘三位一體’聯動。”尹建民表示。例如,提升家長的育兒理念和教育方法,對老師給予相關的專業指導,通過專業訓練提升孩子的抗壓能力。尹建民特別提到,“家長要給予孩子多方面關注,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要培養孩子的自主能力” 。
和諧的家庭關系和有效的教育方式,都有助于孩子形成健康心理。面對孩子的表達和訴求,家長應做到“一聽二說三做”,先傾聽,再表達,最后才是行動。
“針對不同孩子的特點,還應該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在家庭教育過程中,需要讓孩子與父母之間、夫妻之間達成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局面。”楊彩蓮認為,“而且,不要‘妖魔化’抑郁,我們要正視抑郁和焦慮在青春期的發生,通過度過它得到生命的升華。”
做到這些,需要多方力量支持。“大部分心理咨詢師屬于成人方向,用成年人的思路在做咨詢。針對兒童青少年的專業咨詢師非常少。”尹建民呼吁更多專業咨詢師進入兒童青少年領域。2021年10月發布的《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報告》顯示,近五千萬兒童青少年因患精神障礙需要專業治療,而兒童精神科醫生不足500人。這意味著,大約每10萬名患兒才配備一名專業醫生,且這些醫生主要分布在一二線城市。專業醫療資源亟需加強。
更重要的是,我國要為兒童青少年心理問題防控提供廣泛社會支持,提升家庭教育和校園教育。2022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開始實施,正為家庭教育的更新提供重要契機。
248350078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