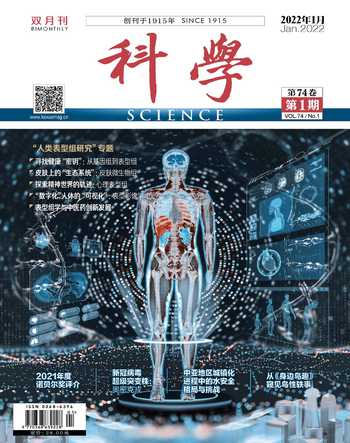新冠病毒超級突變株:奧密克戎
王萍 郭陳君 劉冀瓏
從2019年開始至今,新冠病毒引發的肺炎(COVID-19)在全世界已肆虐兩年多了,造成全球累計3億多人感染、550多萬人死亡。全世界科學家在應對致病元兇——新冠病毒(SARS-CoV-2)的同時,新冠病毒自身也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產生了多種突變株(亦稱變異株),其中,世界衛生組織(WHO)密切關注的突變株是alpha、beta、gamma、delta和omicron(名稱以希臘字母表依序命名)。
傳播力和毒力較強的突變株delta,首次在印度發現,它比其他變體更容易傳播且可能導致比其他突變株更嚴重的疾病。雖然已完全接種疫苗(即二次接種)的人可能會出現突破性感染,但疫苗還是能有效預防疾病加重和死亡。有證據表明,感染delta突變株的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可以將病毒傳播給他人。所有美國FDA(以下簡稱FDA)批準或授權的疫苗都對預防嚴重疾病、住院和死亡有效。在治療方面,幾乎所有在美國流行的變異株,都對FDA授權的單克隆抗體治療有反應。
然而,2021年11月早些時候,新出現的超級毒株——奧密克戎(omicron)正以超強的感染力迅速傳播,在南非已看到它攻城略地的蔓延態勢。隨著感染人群急劇增多,各國之前采取的防疫策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各國科學家和政府機構也正以積極的態度應對,僅在一個多月時間里就涌現出幾百篇研究文獻。
奧密克戎變異株的特點
相比新冠病毒原始株,奧密克戎變異株表面的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又稱S蛋白)發生了30多種變化,S蛋白通過識別并結合宿主細胞上的受體入侵細胞,S蛋白也是免疫反應中被抗體攻擊的主要目標。其中許多變化已存在于alpha和delta等變異株里,它們與病毒的傳染性、逃避抗體中和的能力有關。特別地,奧密克戎綜合了其他幾個突變株最關鍵的突變:alpha、beta、gamma中的N501Y [S蛋白第501位天冬酰胺(N)殘基突變為酪氨酸(Y)殘基,這可能導致病毒與宿主受體間接觸面的變化],alpha中的P681H [第681位脯氨酸殘基(P)殘基突變為組氨酸殘基(H)]。這使奧密克戎有可能成為“超級毒株”。其具體的突變有:①受體結合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有15個突變,是RBD中突變最多的,這會影響抗體識別和疫苗接種;②弗林蛋白酶(一種廣泛參與前體蛋白切割的內切蛋白酶)切割位點附近有H655Y+N679K+P681H突變(K是賴氨酸殘基),這可能增強了病毒的復制力和傳播力;③其中一個蛋白(nsp6)缺失105—107位氨基酸,這可能會影響人體的固有免疫和T細胞免疫;④核衣殼蛋白(N蛋白)具有R203K/G204R,可能會提高病毒毒力。由于病例數較少,目前與該變異相關的疾病和死亡嚴重程度尚不清楚。在治療方面,一些單克隆抗體治療可能對它的感染無效。

奧密克戎研究論文發表情況
2021年11月25日,《自然》(Nature)周刊首先發表《嚴重突變的奧密克戎變異株讓科學家們警惕起來》(Heavily Mutated Omicron Variant Puts Scientists on Alert)一文,表明科研人員正在爭相確定奧密克戎突變株是否對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性構成威脅。此后,該領域的發文熱度持續增長,增長速度亦有加快趨勢。相關的主要研究團隊有中國的香港大學、 瑪麗醫院、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美國的哈佛大學麻省總醫院、麻省理工學院、密蘇里大學、洛克菲勒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惠康人類遺傳學中心,以色列的舍巴醫療中心,日本的金澤大學,沙特阿拉伯的費薩爾國王大學等。
奧密克戎的傳播力

2021年12月2日,南非斯泰倫博斯(Stellenbosch)大學普利亞姆(J. Pulliam)等在medRxiv上傳了第一篇關于奧密克戎的研究論文[2],指出南非出現的新冠病毒重復感染風險增加與奧密克戎突變株相關,并描述了奧密克戎引起重復感染的流行病學情況。這顯示出奧密克戎的免疫逃逸現象更為顯著。
2021年12月7日,香港大學考林(B. J. Cowling)等報道了奧密克戎在中國香港隔離酒店中的可能傳播[3],并預估了奧密克戎輸入的風險[4] 。
2021年12月16日,丹麥學者在《歐洲檢測》(Euro Surveill)上發表了785例丹麥的奧密克戎感染者的流行病學特征,并與同期的delta突變株感染者進行了比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5,6]。由于其所用的病例來自全國范圍內的檢測數據,不是來自醫院的數據;也就是說,其病例是通過逆轉錄酶—聚合酶鏈鎖反應(RT-PCR)或全基因組測序(WGS)手段確定的感染者。這揭示了真實世界中的病情嚴重程度。



同日,科爾蒂(D. Corti)團隊研究了證明奧密克戎免疫逃逸能力或強于之前的新冠病毒譜系[15]。他們檢測了奧密克戎受體結合域(RBD)與人血管緊張素酶2(ACE2)受體的結合情況,即RBD是刺突蛋白的一部分,能幫助新冠病毒進入宿主細胞,而ACE2受體是RBD的一個主要結合目標。研究顯示,相較于武漢的原始分離毒株,奧密克戎的RBD與人ACE2結合的親和力有所增強(增強了約2.4倍)。他們還研究了目前已獲批或正在研發中的針對新冠病毒感染的單克隆抗體對于奧密克戎型假病毒(一種新冠病毒模型)的活性。在研究測試的8種治療性單克隆抗體中,5種完全失去了對奧密克戎的中和活性;兩種單克隆抗體(聯用)的效力只有原來的約1/100,一種單克隆抗體(sotrovimab)的效力只有原來的1/3。研究團隊還擴大了篩選范圍,只有6種對奧密克戎依然具有強效的中和活性:sotrovimab、S2K146、S2X324、S2N28、S2X259和S2H97。研究人員還比較了用疫苗或感染誘導的抗體,來抑制奧密克戎假病毒的活性和抑制來自武漢的原始新冠病毒假病毒的活性。康復期患者或接種強生疫苗、俄羅斯Sputnik V疫苗或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個體的血漿,對奧密克戎的中和活性很低或根本沒有。美國莫德納、輝瑞—生物科技和阿斯利康疫苗接種者對奧密克戎的中和活性,比對武漢分離株的中和活性分別只有原來的1/33、1/44和1/36。
2021年12月15日,法國巴斯德研究院舒爾茨(O. Schwartz)團隊從比利時一名個體分離到奧密克戎病毒,分析了該病毒對于目前已批準臨床使用或仍在開發中的9種單克隆抗體的敏感性[10]。結果發現,奧密克戎突變株能完全抵抗或部分抵抗實驗中所有單克隆抗體的中和作用。其中,5種抗體(bamlanivimab、etesevimab、casirivimab、imdevimab和regdanvimab)對奧密克戎無效;2種抗體(cilgavimab和andintrevimab)對奧密克戎的中和活性比它們對德爾塔的活性降低到只有原來的1/20;sotrovimab抗奧密克戎的活性比抗德爾塔的活性降低到只有原來的約1/3。分析結果表明,抗體療法或需針對奧密克戎進行快速調整。
2021年12月17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團隊報道了19種針對奧密克戎變異刺突蛋白的單克隆抗體的中和活性[9]。參與測試的單克隆抗體包括已獲臨床批準的治療抗體,如imdevimab、casirivimab、tixagevimab、cilgavimab、bamlanivimab、etesevimab、amubarvimab、romlusevimab以及sotrovimab。結果顯示,19種單抗中有17種完全或部分失去了中和能力。只有romlusevimab和sotrovimab保留了中和活性。他們還發現奧密克戎刺突蛋白的4種新突變(S371L、N440K、G446S和Q493R),賦予了奧密克戎較其他變異種更強的抗體抗性。
2021年12月23日,北京大學謝曉亮團隊在《自然》周刊上發文,他們利用一種新篩選技術繪制了奧密克戎刺突蛋白RBD的突變圖譜,這些突變可使其逃逸中和抗體的作用[16]。他們篩選了247種人類中和抗體,發現奧密克戎能逃逸其中85%以上抗體。這些抗體可根據其表位(抗體結合位點)被分為六類(A—F類),且奧密克戎刺突蛋白RBD上的單個突變會影響不同類別抗體的有效性。他們還發現,奧密克戎能輕易破壞多種抗體藥物的中和活性。不過,單克隆抗體VIR-7831和DXP-604仍然對奧密克戎有作用,只不過有效性會降低。
蛋白結構解析
2021年12月20日,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艾滋病病毒學家劉善慮在bioRxiv上傳了一篇關于奧密克戎突變株的研究論文[17],該文證實了奧密克戎的雙重免疫逃避策略,由于表位改變和受體結合域的暴露減少,加上因S蛋白穩定性增強導致高傳染性。
2021年12月21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者發表了第一個冷凍電子顯微鏡下解析的奧密克戎的S蛋白結構,分辨率很高,達2.79?,為了解該突變株的病毒學特征和研制相關疫苗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基礎[1]。研究解析了人ACE2與奧密克戎的S蛋白的復合物結構,發現奧密克戎RBD的R493、S496和R498與ACE2形成了全新的氫鍵和鹽鍵,這些新的化學鍵彌補了K417N突變造成的與ACE2親和力喪失。研究由此指出,奧密克戎逃逸抗體的氨基酸突變,造成與ACE2親和力下降,這將由新的化學鍵來彌補,從而使ACE2與RBD結合的交界面結構穩定。
應對奧密克戎策略的展望
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兩年多時間里,科學家對新冠病毒的研究產生了海量文獻,給人類應對全球疫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和應對線索。超級毒株奧密克戎的出現是新冠病毒與人類相互作用的結果,目前有幾個趨勢值得關注:由于奧密克戎感染力超級增強,需要制定快速應對奧密克戎或其他突變的疫苗制造策略;奧密克戎毒力及對感染者的長期影響有待觀察,在綜合生命、社會和經濟成本之后,各國政府需要重新考慮其策略的有效性;奧密克戎為下一次人類面對新的全球公共衛生事件提供實戰演練機會。
[1]Mannar D, Saville J W, Zhu X, et al.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ACE2 binding, Cryo-EM structure of spike protein-ACE2 complex and antibody evasion. bioRxiv, 2021, 2021.12.19. 473380.
[2]Pulliam J R C, Van Schalkwyk C, Govender N, et al. Increased risk of SARS-CoV-2 reinfection associated with emergence of the Omicron variant in South Africa. medRxiv, 2021, 2021.11.11. 21266068.
[3]Gu H, Krishnan P, Ng D Y M, et al. Early release-probable transmission of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in quarantine hotel, Hong Kong, China, November 2021-Volume 28, Number 2—February 2022 -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Journal - CDC.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22, 28(2).
[4]Bai Y, Du Z, Xu M, et al. International risk of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importations originating in South Africa. medRxiv, 2021, 2021.12.07. 21267410.
[5]Espenhain L, Funk T, Overvad M, et al.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ation of the first 785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cases in Denmark, December 2021. Eurosurveillance, 2021, 26(50).
[6]Brandal L T, Macdonald E, Veneti L, et al. Outbreak caused by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in Norway, November to December 2021. Eurosurveillance, 2021, 26(50).
[7]Schmidt F, Muecksch F, Weisblum Y, et al. Plasma neutralization properties of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medRxiv, 2021, 2021.12.12. 21267646.
[8]Lu L, Mok B W Y, Chen L L, et al. Neutralization of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by sera from BNT162b2 or Coronavac vaccine recipients.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2021, ciab1041.
[9]Liu L, Iketani S, Guo Y, et al. Striking antibody evasion manifested by the omicron variant of SARS-CoV-2. Nature, 2021.
[10]Planas D, Saunders N, Maes P, et al. Considerable escape of SARS-CoV-2 omicron to antibody neutralization. Nature, 2021.
[11]Yu X, Wei D, Xu W, et al. Pseudotyped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exhibits significant escape from neutralization induced by a third booster dose of vaccination. medRxiv, 2021, 2021.12.17. 21267961.
[12]Cele S, Jackson L, Khoury D S, et al. Omicron extensively but incompletely escapes Pfizer BNT162b2 neutralization. Nature, 2021.
[13]Garcia-Beltran W F, St. Denis K J, Hoelzemer A, et al. mRNAbased COVID-19 vaccine boosters induce neutralizing immunity against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medRxiv, 2021, 2021.12.14. 21267755.
[14]Wang K, Jia Z, Bao L, et al. A subset of Memory B-derived antibody repertoire from 3-dose vaccinees is ultrapotent against diverse and highly transmissible SARS-CoV-2 variants, including Omicron. bioRxiv, 2021, 2021.12.24. 474084.
[15]Cameroni E, Bowen J E, Rosen L E, et al. Broadly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overcome SARS-CoV-2 omicron antigenic shift. Nature, 2021.
[16]Cao Y, Wang J, Jian F, et al. Omicron escapes the majority of existing SARS-CoV-2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Nature, 2021.
[17]Zeng C, Evans J P, Qu P, et al. Neutralization and Stability of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bioRxiv, 2021, 2021.12.16. 472934.
關鍵詞:新冠病毒 奧密克戎 傳播力 疫苗有效性單克隆抗體藥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