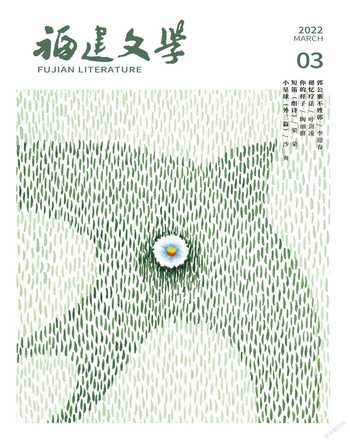湖耿村224號
黃明安
一、武打書
父親晚年不務農活,就愛上武俠小說。我從城里借了一回又一回。阿燦是個老司機,文化執法大隊收繳非法出版物,武俠小說裝滿后備廂。阿燦笑說,讓我運到收購站,我半途拐個彎,全都運回家了。阿燦抱出一箱書放地上,打開一看,金庸、古龍、梁羽生,應有盡有。盡管是盜版的書,但不妨礙閱讀。我運回家給老父看,父親大喜,他架起老花鏡,坐在門檻上,就翻起書來。沒過多少日子,母親電話說,他把書當飯吃,什么事都不管了。我安慰母親說,他老了,就讓他看吧。母親說,這樣看書,魂都會看丟了!
父親最后幾年,確實處在一種現實與夢幻的中間地帶,這個地帶有天龍八部、神雕俠侶,還有他早年的記憶,他的行為也變得古怪了。
最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是,父親在抽水煙的時候,竟然不用打火機、火柴,而是用起了我早年記憶中他經常使用的原始擊火技:把紙引夾在左手虎口中,放石頭上,右手抓一塊生鐵,使勁往石頭擊打過去,火星濺起,落在紙引上,再把火吹起來。
擊石取火產生于舊石器時代。父親從哪找到的火石?我驚訝地看著父親——他的臉龐被濃煙籠罩著,兩只眼睛像夜晚的星星發光!他抬頭看了看我,臉上露出一絲羞澀甚至愧歉,“我知道書都是人編的,可就放不下。”
“您喜歡就看唄,這箱還了,再借不難。”
我到阿燦家不知道借了多少書,直到有一天,阿燦問我說,你父親每一本都看嗎?我說是呀,一箱子書拿回去,不用看多少時間。阿燦露一下嘴里的假牙,又問我,他沒說什么嗎?我搖了搖頭。阿燦突然用無限同情的語氣說,人老了,記憶在頭腦里不會留痕,我哪有那么多武打書,我重復換書,他都不知道嗎?!
有一天我問父親,看過的書都記得嗎?
父親抬起老花鏡,目光從鏡框上方對著我說,我正想給你說一件事呢,你借書的時候,是不是每回都空手去呀?我說,是單位的老司機,借個書,還用帶什么?父親突然指著木凳說,你坐下來,給我一支煙吧。
父親一般不抽我的煙,他開口要煙,一定是有重要的事。
我給父親一支煙,用打火機幫他點上。
父親說,《西游記》中,唐僧師徒西天取經,最后到了藏經閣,如來佛安排阿難和迦葉帶他們進閣,到門口,阿難和迦葉開口要人事(禮物),你記得嗎?
我隱約記得唐僧四人西行取經,歷盡千辛萬苦和千難萬險,取經的時候,什么禮都沒帶,被攔住索禮了,空手只借無字經,無字經是真經,可真經人不識,最后送上一個紫金缽盂,才換得有字佛經帶回大唐。
我不知道父親要說什么。父親嘆了一口氣說,你這孩子,老大了還不懂事。你到人家家里借書,肯定都空手去。不然不會我看過的書又借回來呀!
啊!
我回城特地翻一下《西游記》,“好,好,好!白手傳經繼世,后人當餓死矣!”
吳承恩寫二尊者這句話,是父親教我的人情世故。
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
父親不知道盜版書,他對書籍之尊重,是我一生之教誨。
二、地拉網
從前漁網是用苧麻絲織造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尼龍線或塑料絲。
這種網在海里捕魚,需要用一種傳統的染藝染網,才不易腐爛而經久耐用。
湖耿村224號老屋最外邊的耳房,就是一間染網房。
我記得十來歲那時候,放學回家,經過堂叔家的耳房,就會聞到一股特殊的味道。堂叔在靠窗的大灶臺下,把一個個龍眼樹頭劈開成塊,放在水里浸泡,再投入大鍋里蒸煮,一個上午燒火,打開鍋蓋一看,大鍋里染料已經煮好。那水棗紅色,像血漿一樣。
堂叔和他的合伙人,把染料倒進一個木桶里,合力抬木桶到埕頭,就開始把漁網塞進木桶里浸染,之后攤在太陽下曬干。
這是一種地拉網,如今已經失傳了。
可那時候,地拉網是捕取漁獲的重要工具。我家靠海邊近,我常到沙灘上游逛,看到大人們在春天夏天的上午,十幾個人分成兩排,一個挨著一個,在沙灘上對著退潮的海拉網。漁網從海的深遠處慢慢地往灘邊拉,到了接近水邊的時候,網里的魚開始跳起來。它們是馬鮫魚、鯽魚、黃魚,春天霧茫茫的海水里,還有烏賊、章魚和丁香魚。
收網時分,最激動人心!
只見大魚小魚不停地跳躍著,它們被網困住了,正在拼命逃亡掙扎。大多數魚跳起落在網里,可也有魚從水里蹦上來,由于力氣夠、射角好或被風助吹,居然落到網之外。魚能跳出網了,所以要加快拉網速度。大人們大聲吆喝著,聲調拖得長長的,像是唱一首歌。那時尚無遠海捕撈,木帆船時代,這種地拉網也能捕到豐富的魚蝦呀!
那時魚多,拉一網上來,就要換一處撒網。很多捕獲的魚就這樣擱在沙灘上。
我們在海邊看熱鬧,被大人喚來看魚。我們守在沙灘上,魚們還張著嘴,有的還會蹦跳幾下,最后都不動了。魚們不動了,可我們的小心思卻動了。大我兩歲的遠親阿哥是一個六指人,他左手多出一節的手指常遭我恥笑,可那天我不但沒有笑他,還很聽他的話,跟他一起在沙灘上埋下兩條魚。好不容易等到大人來收魚,有人說這倆孩子聽話乖巧,要不要獎勵魚?父親看了看我們說,不要,小孩子貪小便宜不好。
大人們都回家了,我們還在海邊溜達。
海水慢慢地漲上來,等到它漲到那塊地方,我們齊身奔跑過去挖魚。兩條大馬鮫魚被埋在沙層下,它們被清洗干凈,魚眼亮晶晶,對著我和六指瞪著。
我把魚拿回家,天已經快暗了。
我把魚給了母親,以為父親不知道。
可是當晚父親就知道了。父親看母親在井臺上殺魚,他只輕聲問了一下母親,我就被他叫到墻邊站立。父親不打我,也不罵我,他吆喝我的小名,指著那堵墻說,你給我好好站著,告訴我那條魚怎么來的!
我小時候是個犟種,在墻邊站了好久,咬緊牙關,回答父親的查問就是一句話,我撿來的,大人收魚時漏下來的。
我不哭,也不跑,因為有母親保護著。
母親的保護起先是好話勸解,試圖減少父親的憤怒;接著就是與父親爭論,聲音比父親高;母親用身體擋住沖過來要揍我的父親,她叫我趕快逃跑,可我一點也不想跑掉,我在心里打定主意,一向八面威風的父親,他怎么拿到我偷魚的證據?如果沒有證據,看他還有什么辦法!
父親沒能打到我,卻一拳頭打在母親身上。他走出去了,一副泄氣的模樣。
我還站在地上,月亮出現在墻頭上。
一會兒工夫,父親回來了。父親說:“你把魚埋沙里!”我就哭了。
我哭了,也是輸了。我被擊中要害,我是一個偷魚的孩子。
他去了六指家。六指都招了。
從此之后,我再也不跟六指玩。我恨他,更瞧不起他,整個童年,盡管同在一所小學讀書,但我從不跟他結伴同行,他也不說什么,我們之間隔著一堵厚墻。
直到我考上大學的那一年夏天,父親看我扛著漁具從海邊歸來,從背簍里倒出不少魚蝦時,他才對我說:你要離開村莊了,有一件事我對你說。
我看了看父親,等父親發話。
你考上大學,六指沒考上,你要去安慰他一下。
我不去!我脫口而出。
父親撲嗒撲嗒地抽著水煙,他吐出一口煙霧,徐徐說道,你雖然是大學生了,可這做人的學問,一輩子都學不完。你大了,我說不動你,只盼望你省思。
我省思良久,先在路上跟六指打招呼,接著跟他說話。
我去讀大學,六指成為一個漁民。
我讀大學乃至工作若干年,回家都跟六指玩。我們一起吃魚喝酒,在他家醉過,就睡在他的床上。他到我家喝酒,從來沒有醉過。他酒量比我好,身體比我壯,對我尊尊敬敬,對我客客氣氣。
六指后來在臺風中遇難,尸體漂到很遠的地方。
我每次回家鄉,都要到他墳頭去,有時站著抽一支煙,有時只是來瞧一瞧,隨手拍幾張墳頭的照片,如草木或野花,天空和云朵。
回城后,我還看照片,遵照父親的話,做一番省思。
三、寶殊庵
湖耿村224號是父親出生那年建筑的,或者說,老屋建造那一年父親出生了。
這是一座閩中傳統民居,土名叫“五廂廳”。大廳居中,兩側為前廂房和小后房,外兩側是小廳和大后房,主建筑前兩邊是耳房。院子就在門斗、圍墻與耳房中。其居住格局是:大廳為大客廳,小廳為小客廳,這三間用于待客,其他房間都可住人。耳房為廚房。水井打在墻根外,花從井臺上攀緣,如果照顧得好,會爬到墻頭上招搖。
父親出生于1925年,也就是說,湖耿村224號是一座百年老屋。
老屋原來住六家,現在一家都不住了。
不住不等于都放空。每年元宵節,老屋大廳擺滿供品,菩薩游村進戶,迎神放炮擺轎子和跳火堆,都是在老屋舉行。那時候一族人都回來了,大家從各自的家出來,全部集中于老屋里,手里夾著煙,臉上堆著笑,口里說著話,無論年老年少,男女孤寡,都是團圓喜慶的節日氣氛。我每次回家過年,都感覺元宵節比春節熱鬧,老屋比新房更聚人氣!
可老屋除了那幾天,一年都是寂寞的。
我回老家,喜歡做三件事,一是到海邊散步,二是參觀各家各戶的新房,三是開門進去看老屋。這三件事連起來也是一件事。我在觀察和研究村莊的生存狀態、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命運安排。我在散步的時候,遇到狗和小孩、田野里勞動的婦女、至今還蓄水的池塘,走過新修的水泥路,碰上垃圾運輸車、流動賣肉車、挑魚擔子。我走進生產隊隊部原址上的小店鋪,買一包煙,與店主說話,了解他的生意和家庭,讀書,治病,娶媳婦,生孩子。長一句,短一句,我敬他一支煙,他回我一泡茶,我們抽煙喝茶,就都親近了。
可親近村莊其實是要與村莊拉開一定距離看。
我也像一個異鄉人、田野調查者,對村莊歷史做深入的考究,對村莊任何變化都想知道和考量。我發現我的村莊是有文化積淀的,起碼從“湖耿”二字的起名上,我就佩服古人的貼切和詩意。湖耿灣是一片滿月形的潮間帶,漲潮時海水注滿了海灣,波光粼粼,像湖水一樣安靜發亮。退潮的時候,海灣里面是灘涂地帶,海灣外面是黃金沙灘。我在海灣里散步,有時走過橫跨兩鎮四個自然村的堤壩,有時只是在沙灘上躑躅,看天高云低,聽濤聲依舊。我在夜晚散步,發現村莊里新蓋的樓房大都黑燈瞎火,入住率實在太低了,開燈的樓層實在太少了。為了驗證我的這個發現,第二天早上,我還特地走了幾戶新房。主人在聽清我的問題后,用一種無奈的口吻笑著說,人家都蓋大房,我蓋小了,會被人瞧不起。
辛苦蓋房,為何都不住呢?
年輕人誰還長住鄉下?蓋一幢給人看嘛!
可你為什么不裝修好?
我哪有錢呀?已蓋五年了,欠的錢還沒還清呢!
村民們都是樂觀開朗的性格,他們說到欠錢笑嘻嘻。我與屠宰手八弟攀談,他斜眼,一輩子殺豬,身上有一股怪味。我回家,那股怪味還附在我身上。大哥說,八弟呀,生癌兩年了,還天天殺豬,一點都不怕死,命硬得很!
村里人信命更信神。村莊幾座廟宇,分布在五個地方。儒道釋聯合辦公,民間的神祇更多,每年祭祀之事甚多,初一十五每座廟都燒香。蓋新房的人家,每家都要定做一個土地廟,廟里長年擺著供品。村莊后山有一座寶殊庵,主神為觀音菩薩,香火之旺,十里八村,無人不曉。我每次走到庵前,都可看到跪拜的人。殿堂里煙霧裊繞。他們抽簽解簽,用兩塊卜片,占卜吉兇。村里上了歲數的老人,都在庵里飲茶打牌,小賭怡情。父親還在的那些年,我開車回家,經過這個寶殊庵,都會看到他坐在桌前打麻將。父親見我不抬頭,只低聲說,回來了,煙撒一圈吧。
我分了煙,站在父親身后,我看不懂麻將,也久站不離。
父親走后,寶殊庵再無他人,我回老家,就常打開老屋看。老屋里堆滿了草木雜物,墻上掛著一面算盤、一領蓑衣和一張我小時候捕蝦用的三角網,我知道這些物件如今都用不上了,可我就是喜歡它們。我站在樓上窗戶邊,借著光照看土墻,用手悄悄摸土墻,抬頭看屋頂的橫梁和檁條。高處掛著蛛網,網上結滿灰塵。我曾聽父親說,祖輩蓋這房的時候,家里有兩條船,那船走遠海,賣掉生豬和桂圓干,買回來布匹和藥材,老屋屋頂的大梁,還是從臺灣運回來的呢!
224號登記的是我的名字。我喜歡這座老屋,勝過任何一座樓房。
責任編輯 陳美者
1830501705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