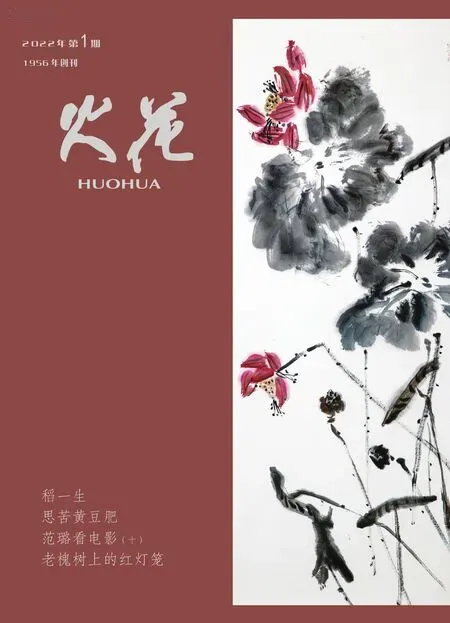荒原之夜
陶詩秀
秦箭
2月14日晚,接到“110”的通知,我們刑警隊立即出警。
事故地點位于石板路至電報路方向的雙白段。我們刑警隊到達現(xiàn)場時看到,兩輛車應該是發(fā)生碰撞后,同時沖下公路南側(cè)。兩輛車分別是奔騰陽光轎車和奔騰商務車,均受損嚴重。
黑色奔騰轎車的后備箱撞在一棵樹上,車后體扭曲變形。商務車歪停在公路下的緩坡上,駕駛員側(cè)的車門是打開的。
看起來是交通事故,但“110”稱有人報警,所以交警和我們刑警隊都趕了過來。車毀人消失,找不到受傷人員,駕駛員不見蹤影,也找不到報案人。這茫茫荒原上,發(fā)生過什么事?蹊蹺。
我們刑警隊到達時已是晚上十一點以后,立即展開現(xiàn)場勘查,有了驚人的發(fā)現(xiàn)。
陽光轎車被擠在兩棵樹中間,后備箱的門因受擠壓裂開,露出十公分左右的縫隙。我們的警員打著手電,透過縫隙往里看,似乎有一條類似人腿的物體。
“想辦法打開后備箱!”
打開一看,里面是一具尸體,完全沒有生命跡象。
把尸體從后備箱移出,法醫(yī)周民上來做初步鑒定。
“男性,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雙手被捆綁,胸部有銳器創(chuàng)口,頭部有多處鈍器打擊傷……顯然不是死于交通事故。”
周民粗略察看一遍,得出了結(jié)論。即使不是法醫(yī),也能看得出是兇殺。
他是誰?車主還是乘客?跟這起交通事故有什么關系?
“秦隊,在轎車里發(fā)現(xiàn)了這個。”警員朱丁遞過來一本行車證。我翻開一看,轎車車主名叫唐孝果,證件發(fā)放地為河北。
周民對比了死者與行車證上的照片:“應該是他。”
“這么說,車禍之后,車主死在自己的后備箱?”我更不懂了,回頭吩咐朱丁:“立刻讓局里查找唐孝果的信息,最好找到近期的照片。另外,仔細搜查兩輛車內(nèi)部。”
在商務車大開的車門邊,有一串步幅比較大的足跡,雜草上有明顯的踩踏痕跡,顯示商務車車主在車禍發(fā)生后,慌張離開了駕駛位置。
他去哪兒了?他為什么沒在現(xiàn)場?
“報案人聯(lián)系上了嗎?”
“他目前在距離現(xiàn)場西側(cè)五里路的一個村子,打了幾十遍電話,才打通他的手機。”朱丁正在手機地圖上定位。
我們馬上趕往村子,十多分鐘后到達。報案人曹鐵男正躺在村里的醫(yī)務室輸液。
曹鐵男
“我是報案人,也是商務車的車主。”不等警察多問,我搶先告訴他們。
“你受了什么傷嗎?”警察拿眼看我輸液吊瓶上的標簽。
“別看了,葡萄糖。沒受傷,可是真他媽折壽,我要壓壓驚……”
“事故是怎么發(fā)生的?”
“事故?這哪兒是事故!純粹是謀殺!我是受害者。”
“從頭說,到底怎么回事?”單眼皮、姓秦的警官拉了把椅子坐在床邊。
“昨天,我去太白山郊游,下山晚了,在山下的小飯店吃了飯,晚上八九點吧,往回走的。
“在雙白路段,我發(fā)現(xiàn)有兩輛車緊跟著我,離我越來越近。我加大油門,試圖甩掉他們。但他們玩命地追我,就像警匪片里一樣,一左一右夾擊著,‘哐哐’撞我的車,把我往公路下逼。”
一想到那情形,我仍心有余悸,抓起水杯大口喝水。
“你認識那兩輛車嗎?你有沒有想到他們會是誰?”后面站著的警察問。
“不認識!我熟人朋友太多了,平時說話、做事一個不小心,難免得罪個把人。誰知道哪個孫子記了仇,跟我狹路相逢,分外眼紅。”我意猶未盡,滔滔不絕,“……為了躲避這兩輛車,我拼命踩油門,車撞得火星四濺。我也是急了,心想跟你們拼了。我不能白死,死也要帶走你們給我墊背。帶一個走夠本,帶兩個賺一個。
“我的大腦一片空白,根本來不及報警和求助,只想快點開到附近的村落……被兩輛車夾擊著行駛了十多分鐘后,意外發(fā)生了,有一輛車的保險杠和我的保險杠掛上了,我的方向盤失靈了。兩輛車一起沖下公路。
“我的車體積大、重量大,落地顛了幾下穩(wěn)住了。另一輛車被甩得打了個轉(zhuǎn),著地后在地上轉(zhuǎn)了三圈,卷著塵土揚起一股旋風,最后撞樹上了。
“那風猛啊!跟龍卷風差不多……我在第一時間棄車逃跑。在逃離現(xiàn)場幾十米時,我聽到了槍聲。”
“什么?有槍聲!”秦警官提高了嗓門,緊張了。警察也沒見過世面,郊外是大片牧區(qū),有獵槍的人多了。
“槍一響,我嚇得魂飛魄散,死命狂奔,一口氣跑到附近的村莊。
“要沒有那股‘龍卷風’,我就跑不掉了,他肯定能打著我。”
冷不丁兒秦警官問道:“你的車里還有別的人嗎?”
秦箭
口若懸河、繪聲繪色的曹鐵男突然吞吞吐吐起來:“我被嚇壞了,一輩子沒見過那陣勢,簡直是倉皇逃命……”
“還有別人在你車上嗎?”
“我逃進這個村子才想起來,我的同伴還在車里……”他往后擼擼頭發(fā),手停在后頸脖處。
“你自己跑,把他留在車上了?”
“那時什么都顧不上了!晚一秒就沒命了!”
“你后來見過他嗎?打過他手機嗎?或者有沒有可能,他跟你一樣跑到這個村子來?”
“沒有,沒聯(lián)系。不知道,我上哪兒知道去!”他毫無愧色地說。
“他叫什么名字?把他的手機號給我!”
“王旦鳳。”
“女的?你跟她什么關系?”
“沒什么關系……”他囁嚅著,“也就是普通朋友……”
“請你好好回憶一下,你逃離之后,有沒有看見或聽見她的什么動靜?”
他雙手枕在腦后,閉上眼睛:“沒什么了,我腦仁疼,啥都想不起來……”
“現(xiàn)在我告訴你,在現(xiàn)場我們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女性的痕跡,沒見到人,也沒有與女性相關的物件。但是,在與你相撞的轎車后備箱,我們找到了一具男性尸體。這是一樁刑事案,你務必配合我們調(diào)查。”我面無表情,含威不露。
“我好像——”他猶豫再三,支支吾吾,“——遠遠地聽到她的尖叫聲,夜里,在野外,聲音特別清楚,好像是她從車里被拉出來了。”
“請把她的手機號給我!她家的地址、電話?”
我的直覺告訴我,曹鐵男的陳述可能屬實。現(xiàn)場商務車門外的那串足跡正是奔往村莊方向,與他的敘述一致。關于與王旦鳳的關系,他可能撒謊了。道德評判不在我的職責范圍之內(nèi),但我在心里還是忍不住鄙視了他一下。這個叫王旦鳳的女人兇多吉少了。
搜證警員將曹鐵男的鞋印留了樣,以供與現(xiàn)場的鞋印對比。
“先派一個人看著他。”我吩咐朱丁。
回到警局是凌晨三點半,召開第一次偵查會議。我將調(diào)查的情況梳理后,簡單匯報給局領導和全體警員:“按照商務車主曹鐵男的供述,曹鐵男和王旦鳳晚上八九點駕車從青龍山回來。在去往電報路方向的石板路雙白段,遭遇劫匪的兩輛車追擊,曹鐵男有幸逃脫,而王旦鳳很可能被劫持了。
“可以確定,劫匪駕駛的兩輛車之一屬于唐孝果。唐孝果在這起人為車禍發(fā)生之前已經(jīng)遇害,尸體藏在事故現(xiàn)場被撞壞的、他自己車的后備箱。”
留守值班的女警員陳萍匯報:“通過河北警方,找到唐孝果的家屬。家屬稱,唐孝果已從河北外出半個月左右。對比尸體與河北警方發(fā)來的唐孝果照片,死者極有可能是唐孝果本人。”
河北警方效率挺高。謝了,河北的同行們。
朱丁接下去說:“整理現(xiàn)場帶回的物證,車內(nèi)有高速公路收費站票據(jù),反映了唐孝果出發(fā)離開河北的時間、到達我省境內(nèi)的時間。根據(jù)唐孝果行車的路線,他是在2月14日進入本地區(qū)境內(nèi)。據(jù)家屬說,他是在2月14日下午突然聯(lián)系不上的。”
我說:“本案已確定是刑事案件,至于作案動機,可以排除仇殺和情殺。唐孝果的失聯(lián)有可能是遭遇了搶劫,然后被殺人滅口。被害人車上和身上都沒有發(fā)現(xiàn)現(xiàn)金、銀行卡、手機等私人物品。”
有人提出異議:“據(jù)此就定性為財殺,是不是為時過早?有些嫌犯有反偵查意識,會做些手腳,掩蓋真實動機。再說,死者身上有多處銳器傷,一般仇殺才會形成這種傷口,會不會是他的仇人從河北跟蹤過來……”
陳萍說:“我向家屬打聽過,唐孝果做服裝生意很多年了,一向和氣生財,沒有得罪過什么人,他們覺得不應該是仇殺。”
“商務車的情況呢?”局長問,“被劫持的受害人有線索嗎?”
陳萍說:“撥打了曹鐵男提供的手機號碼,一直關機。‘110’沒有接到任何叫王旦鳳的女人的報案或求救。已打通曹鐵男提供的住宅電話,證實王旦鳳確有其人。她家人說她2月14日早上離家后———據(jù)說是和朋友郊游了,就沒回家,處于失聯(lián)狀態(tài)。她的家人萬分焦急,正要報警。現(xiàn)在,我們有人每隔十分鐘打一次她的手機。”
“根據(jù)目前證據(jù),暫時定性為搶劫案。”局長下了結(jié)論,“先按照這個方向偵查吧!技術部馬上調(diào)取唐孝果進入本地區(qū)的監(jiān)控錄像,查找他是在哪里出現(xiàn)意外的。”
散會。
局長叫住我:“明天安排人跑一趟河北,提取他直系親屬的生物檢材,要百分百確定唐孝果就是案發(fā)現(xiàn)場的死者。”
六點了,我疲倦至極,在會議室的沙發(fā)上倒頭便睡。
“秦隊!秦隊!王旦鳳的手機打通了!”陳萍搖醒了我。
“什么?”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她說的是什么。一看墻上的鐘,才睡五分鐘,可是睡得真香啊!
王旦鳳
“他說的都是實話。”我說,警察趕來的速度之快,出乎我的意料。在電話里他們再三確認我的安全,我第一次有了“人民警察為人民”的感覺。
“他棄車逃跑后,我還沒反應過來,就有幾個人拿著棒子和槍站在車外。”現(xiàn)在,我想到那個人就覺得惡心,連他名字都不想提,“他們打開車門,抓著我的衣服把我拉下車,一直拽著我朝公路走。”
“總共幾個人?”單眼皮、特工臉的警官問,他可能是頭兒。
我說話時,一個年輕警官拿著筆在本子上“唰唰”記錄,另一個警官拿著小型攝像機在拍攝。所有人的目光都盯著我,像聚光燈一樣,我有點不安。
“……四個。”我說。
“然后呢?”
“然后,他們把我拉進公路上的一輛轎車,我的皮包、手機都被搜走了。”
“他們的相貌、身材什么樣?口音是哪里的?”
“……太黑,沒看清……他們戴著口罩……南方口音……”
“南方口音?南方哪里?”
“……不知道,就是南方的……”我低下頭,“我很害怕,車上有兇器,我九死一生,腦子根本不夠用。”
“什么兇器?”
“槍。”我說,“他們讓我老實點,不要喊叫,叫也沒用。他們還說,他們身上都背著幾條人命,不怕玩命。”
“他們帶你去了哪兒?”
“沒走公路,是土路和砂石路,一路顛簸。”
“方向呢,哪個方向?”
“沒有燈,看不見,不知道方向。”
“從事故發(fā)生地點往哪邊走的?往電報路走,還是回塘坊鎮(zhèn)?”
“……沒去電報路,我記得車掉了個頭……”
“最后停在哪里?”單眼皮警官催問道。
“……好像經(jīng)過了一個加油站,又走了一陣,進了一個院子。院里有兩間磚平房,他們把車停下,叫我下車。有一個人把屋子的鎖撬開,所有人都進了屋……”
“然后呢?”單眼皮警官耐著性子問。我聽其他警察叫他“秦隊”,這么年輕就當了刑警隊長,果然有一股精銳之氣。
“其中三個人商量著繼續(xù)尋找目標‘干一票’,帶著槍開車走了,留下一個人看著我。”
“后來呢?”
我抿了抿嘴唇,欲言又止。
秦警官拿來一瓶礦泉水:“別緊張,慢慢講。只要你安全,我們就不怕了。”
“……看守我的這個人顯得很疲憊,過一會兒就躺在炕上,讓我坐在他旁邊,叫我別想逃跑,說我一動他就會知道……”我一邊喝著水,一邊慢慢說,語調(diào)盡量正常自然,“……沒多久,他睡著了……過了一個小時,我確認他已經(jīng)睡熟,院子里也沒有人,這是我逃脫的好時機……
“屋子的門被鎖上了,不鎖我也不敢從前面院子出去,我怕迎面碰見那幾個人。我看見后屋有個小窗戶,就輕輕站起來,確定他沒有任何反應后,小心翼翼打開后窗跳出去……
“我一口氣跑了很遠,一直跑到加油站。萬幸我逃出來之前,偷回自己的皮包,我用手機給朋友打了電話,她和男朋友開車來把我送回了家。”
“你還記得去平房的路線嗎?”
“不記得,我嚇壞了,四周一片漆黑,我不能確定院子的具體位置。”
秦箭
“她‘不能確定院子的具體位置’,這句話她倒說得很確定。”我在車上對朱丁說。
陳萍跟王旦鳳上了另一輛車。王旦鳳慢騰騰的,好像事不關己似地漠然。
案發(fā)72小時是破案的黃金時間,她不是警察,已經(jīng)死里逃生,她當然無所謂。但是,如果我們不在天亮前抓住嫌犯,一旦讓他們逃脫,再想抓他們,會像大海撈針一樣難。
根據(jù)王旦鳳的描述,從事故現(xiàn)場過了塘坊鎮(zhèn)就是加油站。我們知道了大致方向,一路飛奔,沿公路找到了那個加油站。再走一截,看見了那個小院。同來的塘坊鎮(zhèn)派出所警察說,那是個廢棄的養(yǎng)殖場。
“準備抓捕!”天快亮了,必須加快行動。
特警先包圍了院子。因為嫌犯持槍,臨時抽調(diào)了特警協(xié)助抓捕。我和朱丁跳墻進去,拿著手電一掃,感覺不妙。院子里空蕩蕩,是不是王旦鳳的逃跑已打草驚蛇?
慢著!我碰一下朱丁,抬下巴示意他看院子東北角,那兒安靜地停著一輛面包車。
我們悄聲趨近,駕駛員位置的玻璃已破碎,用手電往里照,車座上有血跡。我們來不及細看,確定車里沒人,迅速挪到屋邊。
門上掛著鎖,但是聽見里面有若隱若現(xiàn)的鼾聲!
我一拉鎖,發(fā)現(xiàn)并沒有按死,于是把鎖摘掉,輕手輕腳推開了一條縫,側(cè)身進去,外屋沒有人。我推開里屋門,黑暗中看見炕上躺著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就不勞動特警了。我用電筒朝外晃了一個圓圈,幾個刑警悄沒聲息地進來。
炕上的人似乎被驚醒,感覺到了什么,抬起身:“誰呀?”
我們四五個人一起撲上去:“別動!警察!不許動!”
“叫什么名字?”幾個人一起喝問。
“李大清。”
“李大清,你被捕了。”
在炕上,枕頭邊有四顆獵槍的子彈殼。在院里養(yǎng)殖棚舍里,也發(fā)現(xiàn)了幾顆子彈,自制的半成品。
李大清
不可能動!幾個黑洞洞的槍口指著我的腦袋,告訴我“別動”,那還動啥啊?不可能動。
這一天遲早會來,自從跟他干上,我時刻準備著。
警察把我提溜起來,按在炕沿上:“知道為什么抓你嗎?”
“知道。”我一點不害怕,相反,踏實了。
“說!”
“撞車了唄。”
“好好說話!說老實話,不然你我都麻煩。”一個單眼皮的警察慢悠悠地說,我記得他那雙細長的眼睛,他是燈亮后我看到的第一個人。
“咱是良民,不找麻煩,想知道什么盡管問。”
“一共幾個人?”
“四個。”
“叫什么名字?”
“……小趙、小錢、小孫,不太熟,網(wǎng)上認識的南方人。”
“你叫小李是吧?”我旁邊按著我的警察用胳膊肘杵了我的肩膀一下,顯然不欣賞我的玩笑。
到了公安局,我已經(jīng)準備好和盤托出,本來也沒打算死抗到底。
“只有兩個人。”
“這個態(tài)度就對了,你以為我們刑警是吃干飯的?”用胳膊肘杵過我的朱警官厲聲說,“車禍現(xiàn)場根本沒有那么多腳印,院子里也沒有四個人的腳印。”
“是我開的車,撞了一輛商務車,我們兩輛車一起翻到公路下邊的田野。都是牛海讓我干的,我聽命于他,他讓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單眼皮秦警官問:“牛海是誰?你跟他怎么認識的?”
“他是我表連襟,他老婆和我老婆是表姊妹,就那么認識了。”
“他讓你干什么了?”
“他讓我把那個女的拽下來,送到公路上的車里去。”
朱警官敲了一下桌子:“說主要的,別避重就輕。你可別跟我說,你不知道你開的陽光轎車里有一具尸體。”
“跟我沒關系,我可沒殺他——你得讓我從頭說起……”
“從頭說,我們聽著呢!再提醒你一次,好好說話。”秦警官抱起了胳膊。
“兩個多月前,牛海找到我,讓我跟他出去做事,掙點大錢。我后來才知道,他所說的掙大錢就是搶劫。
“我這人從小到大遵紀守法,以前上學連一堂課都沒曠過。稀里糊涂跟他做完第一起,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跟他說,從今往后別找我了,這回的事我也全當不知道。
“但他這個人狠哪!黏上了就別想甩掉。我媳婦給我打電話,他把電話給我掐斷了,手機卡給我摳了。不讓我拿電話、不讓我回家,說我要是不聽他的,他就把我干的事告訴我家里,還報告公安局。他說他坐牢無所謂,他反正什么都不在乎。
“殺那個唐孝果的時候,打得那叫一個慘。我都瞅不下去,躲一邊了,不敢看,等于是活活打死。他這人心狠手辣,說不殺人滅口,后患無窮。
“2月14號那天,剛打死了唐孝果,又碰到一輛商務車。他盯上了,說開商務車的肯定有錢。
“他讓我超車到前面,再踩煞車,往商務車前轂轆上撞。不曾想,我的保險杠跟商務車的保險杠掛在一起,兩輛車都開到溝里去了……”
我一五一十回憶著,女警官走筆如飛在記錄。
秦箭
這李大清真蠢,原本端正清白的一個人,這么輕易就被人帶上歪門邪道。
根據(jù)李大清的供述,確定了牛海現(xiàn)在所開轎車的車型和顏色,很快調(diào)出相關監(jiān)控錄像,一路追蹤,發(fā)現(xiàn)牛海已經(jīng)逃出本市轄區(qū)。
持槍、駕車、命案在逃,牛海是一個危險份子,極有可能狗急跳墻。案情重大,必須立即展開對牛海的抓捕。技術部繼續(xù)追蹤牛海的行車軌跡,其他人做好抓捕的準備。任務布置下去,我還是覺得有點不對勁,像是扣子扣錯了眼、鞋子穿反了一樣別扭。
“王旦鳳在撒謊。”我終于找到了疙瘩所在,“我們必須要再詢問王旦鳳一次。”
剛要出門,技術部刑警興奮地沖進來報告:“有牛海的消息了,他在客運港。”
抓捕小組立刻出發(fā)去碼頭。
根據(jù)當?shù)鼐降馁Y料,牛海在一家小旅館。我們部署警力包圍了小旅館。當?shù)鼐脚阃÷灭^經(jīng)理,向我們指出牛海所在的房間:2樓208號。
我們在走廊聽見208房里有鼾聲。在最緊張的抓捕時刻,我還是差點笑了出來。這兩名嫌犯不愧為親戚,鼾聲都一模一樣。
朱丁用一根細鐵絲伸進門縫,慢慢移動里面的插銷。
“拉住門把手。”他停住了。
我拉著門把手,聽見“咔噠”一聲,用力一推,門開了。我們一擁而進。
“叫什么名字?”
“輕點,我胳膊快斷了。”
“叫什么名字?快說!”
“牛海。”
“抓的就是你!”
牛海
警察真可笑,這么多人來抓我一個。前面兩個、后面兩個為我保駕,一左一右倆大個兒架著我的胳膊下樓,這小破旅館的窄樓梯根本容不下三個人并排!
他們把我像麻袋一樣塞進車里。得,算我栽了,如今我也變成菜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了。
左右兩個“保鏢”又緊緊夾著我的胳膊,兩人用腳踩著我的腳背。你們怎么不拿鉚釘把我鉚在車上?
后面一個警察抓著我的頭發(fā),壓低聲音在我耳邊發(fā)問:“干了些什么?自己說吧!”
他們這是要趁熱打鐵,抓捕時趁人亂了陣腳,要第一手口供。
“你別讓我活動開!你要讓我活動開,我就一頭撞死,我沒臉活了。”我扭動著身子,想為自己爭得更多的空間。
“搶了幾次?”兩邊的警察緊緊壓著我,不讓動。
“四次。大丈夫敢作敢當,四次。”
“殺了幾人?”
“三個。”
兩邊警察找到合適位置,讓我坐得舒服一點。
“繼續(xù)說,別停下,都怎么干的?”后面的警察卻仍不放松,追著問,“時間、地點、和誰干的?”
“說來話長……”
“那就長話短說!”
“去年十一月,長春,我自己,搶了輛轎車,人給弄死了。一月,在長嶺,和李大清搶了個面包車司機,把他殺了。最后這一次,搶了個河北人,人打死了……”
“搶劫動機?”
“錢唄!搶劫還能為什么?”
“為什么那會兒那么缺錢?你平時以什么謀生?”
“賭博,以賭博為生。行了,爺們兒,你不就怕我不‘坦白從寬’嗎?我坦白,全都坦白,今晚先讓我好好睡個安穩(wěn)覺成嗎?明兒個再說。”
“行,算你是個爺們兒,別忘了自己的話,咱們明天接著聊。”
嘿喲!我算什么爺們兒?作為劫匪,真沒臉活了,兩次在女人跟前馬失前蹄。
前四次搶劫唯一一次失手,就是遇上女人。明明制服了那個小娘們兒,竟在去銀行取錢的路上被她溜了。這回,又是李大清這個熊孩子放了那個女人,招來警察。
女人太可怕,真不能招她們。我算是認栽了。
秦箭
這牛海事兒真多,一覺醒來,吃了早飯,還要求先理發(fā)刮臉,才來接受審訊。
“我欠了人家三十萬。本來想賺一點,不料運氣太差,賭輸了,債主三天兩頭來找我。”捯飭一番,他倒不像抓捕時看起來那么狼狽猥瑣了。
“什么時候開始賭博的?”
“去年底,十二月。”
“為什么殺人?”
“我跟李大清事先商量好,完事后不能留活口,李大清也同意。”
十二月開始賭博,十一月就搶劫殺人了。李大清是去年底才跟他干的。
殺了三個人還毫無悔意,死刑就是為這樣的人準備的。
“那為什么沒殺王旦鳳?”
“我倒是想弄死她,李大清想放了她,俺倆吵吵起來了。”
“李大清為什么想放了她?”我有點驚訝了。
“他看上她了唄。李大清先翻她的包,看見她的身份證,發(fā)現(xiàn)他倆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兩人就嘮起嗑來,挺有緣分。
“那女人也不是一般人,被李大清拿槍頂著,居然能面不改色跟他閑聊,說他長得像她的龍鳳胎弟弟,他倆長得是有點像——夫妻相。后來兩人談笑風生,我?guī)状螌畲笄迨寡凵屗麆邮郑技傺b沒看見。”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王旦鳳獲救后既不馬上報警,也不積極配合警方。
李大清
跟王旦鳳的談話讓我突然清醒過來。在遇到她之前,我都麻木了。
跟著牛海這兩個月,只覺得自己變成衣冠禽獸,不明白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這時候,我拿王旦鳳的眼光看自己,都不能相信這就是我。我怎么落到這步田地?我怎么像個喪家犬惶惶不可終日?以前雖然沒多少錢,日子還是過得安穩(wěn)。現(xiàn)在我連家都不敢回,看見警察就躲。我小時候?qū)懽魑模皇钦f長大想當警察的嘛!
牛海執(zhí)意要殺王旦鳳。我說:“哥,我跟你東奔西跑這些日子,做下的這些事,把后半輩子都搭進去了。我沒找你要過什么,今天一個晚上,你能給我吧?我只找你要一個晚上。”
牛海沒說行,也沒說不行,我知道這是默許了。
我們把車開到常去的廢棄小院,牛海帶著槍開車走了,說他再出去轉(zhuǎn)轉(zhuǎn),去找別的目標。臨走前警告我,兄弟,別被女人毀了,咱們有咱們的規(guī)矩,不能壞了規(guī)矩,別讓我回來再費勁。
我已經(jīng)打定主意,這件事上,我不會聽他的。
王旦鳳
我一直跟看守我的李大清聊天,他挺好說話的。如果不是在夜里、在這人煙稀少的荒原上,而是在學校、單位,我應該能很快和他成為朋友。
“看在咱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份兒上,能不殺我嗎?”我必須在他的老大回來前逃出去。如果那家伙回來,我就命懸一線了。
“我不會殺你,我也不會讓他殺你。”他說得很堅定。
真諷刺,我的命運在情人節(jié)這天,有了幾個大逆轉(zhuǎn)。先是甜蜜幸福地接受了曹鐵男的求婚,海誓山盟至死不渝,以為他就是我這輩子的真命天子。沒想到,幾個小時后的生死關頭,他竟棄我而去,自顧逃命了。
本以為在劫難逃,不死也會慘遭蹂躪,卻碰到一個特別的劫匪,讓我在對人性失去信心時,忽然又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真遺憾,我們怎么會在這樣的場合認識。”我說的是真心話。
“是啊!要是我們上了同一所學校,說不定會在一個班。那我剛才拉開車門時就會說,好久沒見,請你吃飯唄。”
我笑了,他也笑了。我跟他盤腿坐在炕上,聊得挺投機,這哪像劫匪和人質(zhì)?
“你懂八卦嗎?男女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話,八字的前六字相同,但男女性別不同,大運是相反的。”
“你的意思是,我是劫匪、你是被劫的,所以相反。”
“我的意思是,我是受難的、你是來救我的。”
他竟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對不起,剛才嚇著你了吧?”
“不是說了嗎,這就是緣分。”我現(xiàn)在一點都不害怕了,“你結(jié)婚了嗎?”
“結(jié)了。”
“挺愛你老婆的?”
“一般吧!能過日子。”他反問,“你結(jié)婚了嗎?”
“沒有,也不想結(jié)。”
“不想結(jié)?”他壞壞一笑,“那今晚那個男的是誰?你不至于說那是你的同事,是普通朋友吧。”
“我就是今晚才不想結(jié)婚的。說起來,我還得感謝你,要不是你們出現(xiàn),我就準備嫁給他了。人哪,真不知道誰是披著狼皮的羊,誰是披著羊皮的狼。”
“我是披著狼皮的羊,今晚我指定放你走。”
“放我走了,你老大回來,你怎么辦?他不是說,不能壞了規(guī)矩嗎?”
“放心吧,沒事。”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走吧!別跟他干了,逮著了要判刑的。”我真的有些替他擔心了,想到他的老大,我還是覺得要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
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你快走吧!別管我了。后面有個小窗戶,跳出去往加油站方向跑。”
他跳下炕,把先前搶走的東西還給我:“這是你的皮包和手機,不過你的錢都被他拿走了。”
他掏出兩張票子給我,“這兒有兩百塊,你拿著,路上以防萬一。千萬別搭男人的車!”
我站起來,卻邁不開腳步。他又找出一件黑色的大外套:“你的羽絨服是白色的,夜里太顯眼。把我的衣服套在外面,別嫌臟啊!”
他把外套披在我身上,推我:“走啊!”
我眼淚滾落,一把抱住他……
秦箭
朱丁看著王旦鳳的背影:“要對她提起訴訟嗎?她畢竟對警方做了偽證。”
我沉吟一下:“算了吧!她也是受害人,心理上受了刺激。”
朱丁還是一腦門問號:“弄不明白這王旦鳳到底怎么回事,來三四回了吧?哪有人質(zhì)替劫匪求情的?”
“不奇怪,斯德哥爾摩癥候群。”
“什么呀?”
陳萍拿筆敲敲朱丁腦袋:“嘿!你這個人,咱們不是在同一個教室,聽同一個老師講過嗎?1973年斯德哥爾摩銀行搶劫案,人質(zhì)對劫匪產(chǎn)生感情,拒絕與警察合作。人質(zhì)之一還愛上了劫匪,在他服刑期間嫁給了他。”
“我發(fā)現(xiàn),只要涉及談情說愛,你的記性就特別好!”朱丁回應。
牛海
說什么都沒用了。老話說養(yǎng)兒能防老,父親是兒子最好的靠山。我給不了我兒子什么了,也給父母帶來那么大傷害。你們體會不了我的心情……
李大清
我沒有非分之想。雖然沒有親手殺人,但我知道我這輩子算是完了。
王旦鳳
警察,他們除了破案抓人,啥都不懂。
秦箭
王旦鳳根本沒有龍鳳胎弟弟,她倒是有超出常人的機智冷靜。
她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個情人節(jié)吧?
幸好她與曹鐵男分手了。
唐孝果
我死得太冤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