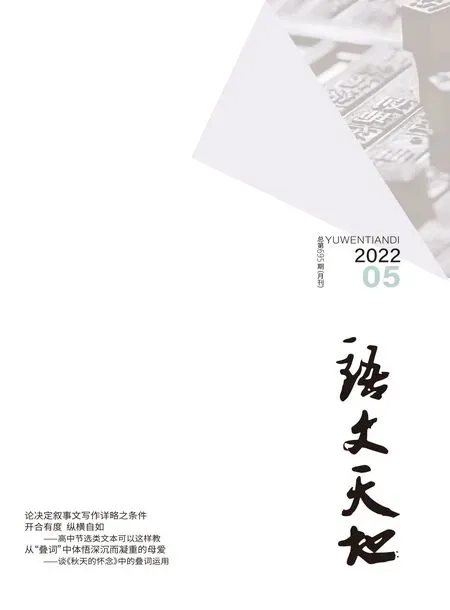于無聲處聽驚雷
——談《橋邊的老人》敘述視角的選取
林 君
1954年,海明威被授予諾貝爾文學(xué)獎。理由是“因為他精通于敘事藝術(shù),突出地表現(xiàn)在《老人與海》之中,以及他在當(dāng)代風(fēng)格中所發(fā)揮的影響。”作為小說創(chuàng)作大師,其精湛的敘事藝術(shù)在許多作品中都有所體現(xiàn),本文且以《橋邊的老人》一文來做一個管中窺豹。
《橋邊的老人》是一部短篇小說。作品取材于上個世紀(jì)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內(nèi)戰(zhàn)。從標(biāo)題可知,本文將敘述的重點放在“橋邊的老人”身上,刻畫了一個疲憊不堪、孤苦無依的老人形象。他一動不動的“鎮(zhèn)定”姿態(tài)與開頭營造的緊張忙亂的戰(zhàn)前場面形成強烈的反差。原因不僅在于他“太累了”“走不動了”,更是因為他的身后有故鄉(xiāng)的牽絆(“我是最后一個離開圣卡洛斯的”),身前卻是一片迷茫(——“巴塞羅那。”我告訴他。——“那邊我沒有熟人”)。在戰(zhàn)爭與死亡陰影的籠罩下,老人非但沒有表現(xiàn)出強烈的求生欲,反而顯露出“木然”的神情。這種情況下,老人與生無可戀之間只有幾只動物的距離。動物是老人與這個世界之間唯一的牽掛和維系,動物越是前途未卜,老人與這個世界的聯(lián)系就越顯得細若游絲、脆弱不堪。作者在這里譴責(zé)了戰(zhàn)爭的殘酷性,同情弱小者的痛苦,充滿了對生命的悲憫。
然而,問題也隨之出現(xiàn)。就表現(xiàn)反戰(zhàn)主題而言,從“老人”的視角或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入手,自然也是可以的。小說卻引入了“我”這一角色,從“我”的角度來敘述這一切,作者的意圖何在,其中包含著怎樣的敘述藝術(shù)?
當(dāng)然,從閱讀效果上看,“我”作為事件的見證者、參與者,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娓娓道來,這就能夠有效地拉近讀者與作品之間的距離,使敘述顯得真實可信;作為老人經(jīng)歷的局外人,摒棄了老人視角的主觀性,使敘述更加客觀有力;從結(jié)構(gòu)上,“我”充當(dāng)線索人物,又能有效地以所見所聞組織情節(jié)內(nèi)容,使敘述更加緊湊。
不過,除此以外,我們更應(yīng)該關(guān)注“我”是誰?我的身份形象有何特征?“我”的存在是否能進一步豐富(深化)小說主題?
首先,“我”是誰?文中交代:
“我的任務(wù)是過橋去偵察對岸的橋頭堡,查明敵人究竟推進到了什么地點。”
“我凝視著浮橋,眺望充滿非洲色彩的埃布羅河三角洲地區(qū),尋思究竟要過多久才能看到敵人,同時一直傾聽著,期待第一陣響聲,它將是一個信號,表示那神秘莫測的遭遇戰(zhàn)即將爆發(fā)。”
可以推測“我”很可能是一個普通的偵察兵。有人認為“我”也可能是一名戰(zhàn)地記者,此處筆者是存疑的。雖然海明威曾經(jīng)以戰(zhàn)地記者的身份參與過西班牙內(nèi)戰(zhàn),但這里的“我”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而應(yīng)該理解為作者所塑造的人物。記者與偵察兵的“任務(wù)”及關(guān)注點存在很大的不同,對于記者而言,戰(zhàn)場內(nèi)外的人間百態(tài)都是關(guān)注點,而文中的“我”顯然更關(guān)注戰(zhàn)場的局勢,不那么在意戰(zhàn)事以外的內(nèi)容。
其次,“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從“我”與老人的談話內(nèi)外,可以總結(jié)如下:
1.盡忠職守,關(guān)注遠方的戰(zhàn)事,具有戰(zhàn)爭的使命感。
2.不能理解老人對小動物的關(guān)心。
3.內(nèi)心有人性化的一面,關(guān)注卡車的信息,事實上是關(guān)心老人的撤離。
4.這種人性化的一面有強弱之分。從一開始交談時的“期待第一聲炮響”,到結(jié)束后戰(zhàn)事未起,卻感慨“這是老人唯一的幸運”。對生命的關(guān)注由弱變強。
因此,可以看出,“我”的身份帶有明顯的矛盾沖突特質(zhì),與老人形成對立的兩極。第一層是與老人之間身份的對立沖突。除了暴力與和平的區(qū)別外,還體現(xiàn)在他們之間價值觀念的差異。士兵的價值序列是以推動戰(zhàn)爭獲得勝利為首(期待炮聲),所以他關(guān)注戰(zhàn)爭局勢,這種情況下他并不能真正低下頭去理解老人對弱小生命的關(guān)切和珍視。我們就可以認為,當(dāng)一切以宏大正義口號為由的戰(zhàn)爭發(fā)動的時候,它就注定無法關(guān)切到那些弱小無辜的生命。這就是士兵與老人產(chǎn)生錯位對話的原因,這也是為什么老人最終放棄了與“我”的對話,變成自己的喃喃自語(“可不再是對著我講了”)。
第二層沖突是士兵內(nèi)在的矛盾沖突。士兵形象中包含人性的一面(人性的一面始終都在,但有強弱之分),從最初的“期待”到最后的“幸運”,可以看成是交流之后的余響,是士兵真正能在殘酷的戰(zhàn)場廝殺中停下腳步,為弱小無辜的生命而慶幸的一刻。但當(dāng)他感受到這一點的時候,卻也是他內(nèi)心矛盾沖突最強烈的時候,是他內(nèi)心價值秩序動搖的時刻。
所以士兵的形象可以作為窗口看成是作者對戰(zhàn)爭的一種思考:戰(zhàn)爭的殘酷就在于,它的宏大主題是以淹沒人性、無視弱小生命為代價的。他不但殺死生命,也對無辜弱小者(老人)和士兵進行精神的掃蕩,讓戰(zhàn)爭中的每一個人都陷入迷茫的境地。
這樣一來,小說的主題就得到了深化。如果是從老人的角度來敘述,固然可以體現(xiàn)反戰(zhàn)的主題,然而這樣就不能深入到對戰(zhàn)爭殘酷本質(zhì)的思考,也不能感受到戰(zhàn)爭對于參與者(士兵)精神上的掃蕩。
事實上,上個世紀(jì)20年代初,美國一批初登文壇的青年作家們帶著玫瑰色的幻想?yún)⒓恿说谝淮问澜绱髴?zhàn)。但他們所看到的盡是殘酷的廝殺和恐怖的死亡,他們幻想破滅,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他們憎恨戰(zhàn)爭,但不知如何才能消滅戰(zhàn)爭,心情苦悶,對前途感到茫然。加之戰(zhàn)后資本主義世界的動蕩不安和社會危機,又加重了他們心靈的空虛和苦悶,他們在文學(xué)作品中表達自己的迷惘和痛苦,失望和不滿,形成了“迷惘的一代”文學(xué)流派,海明威就是這一文學(xué)流派的代表作家。本文就具有這一文學(xué)流派的鮮明印記。
值得注意的是,常見的第一人稱視角可以作為感受者來自由抒發(fā)個人主觀感情,不同的是,海明威摒棄了這一層便利,本文的“我”只是充當(dāng)故事中的一個觀察者,并不發(fā)表議論和流露感情,不做任何判斷,這就是其創(chuàng)作中的“冰山理論”的體現(xiàn)。海明威認為冰山在海里移動很莊嚴宏偉,因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他認為應(yīng)該把思想、情感乃至語言與動作等八分之七的內(nèi)涵隱藏起來,所有這一切被省略的東西,讀者會通過自己的想象加以聯(lián)接與彌補。事實也是如此,馮·麥特爾·艾姆斯《小說美學(xué)》中說:“無所不知的作者不斷地插入到故事中來,告訴讀者知道的東西。這種過程的不真實性,往往破壞了故事的幻覺。除非作者本人的風(fēng)度極為有趣,否則他的介入是不受歡迎的。”有限視角、簡潔的敘述、克制的情感,賦予了小說更為廣闊的審美空間,就像繪畫中的留白一樣,令人回味無窮。
“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選擇不同的視角,站在不同的位置,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世界就有了不一樣的縱深。魯迅《祝福》中的“我”是進步青年身份,“我”的猶疑不決事實上也展示了知識青年的軟弱無能,“我”的自白就是一場自我解剖。芥川龍之介的《竹林中》(電影《羅生門》)每個敘述者對同一個事件的敘述各不相同,因為他們都是從自己的視角來敘述,都對自己進行了充分的美化——從而引發(fā)讀者思考。總之,小說視角的選取是一門有趣的敘述藝術(shù),讀懂小說,不僅僅是能讀懂主題,也要讀懂作品通往主題的寫作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