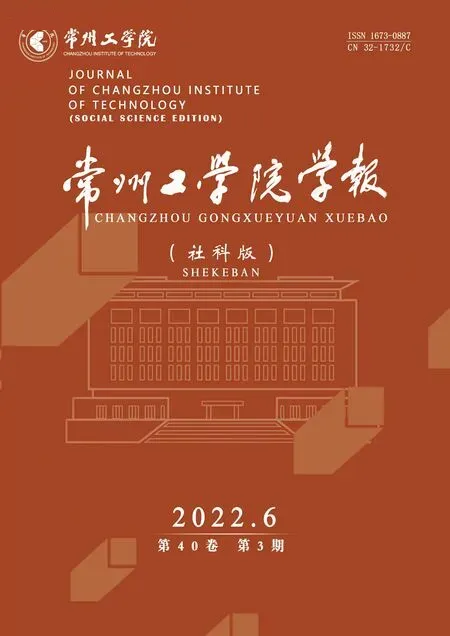空間理論視域下的《變形記》異化主題與倫理困境
袁意
(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對于卡夫卡,英國大詩人奧登1941年有過一句著名的評價,他說:就作家與他所處的時代關系來看,“卡夫卡與我們時代的關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與他們時代的關系”,“卡夫卡對我們至關重要,因為他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1]。某種程度上,卡夫卡可以稱得上是現代主義小說家中的第一位重要人物,人們對卡夫卡作品的批評研究也層出不窮。20世紀以來,“空間轉向”成為研究現代小說的重要命題。不少研究者開始借助空間理論闡釋卡夫卡的作品。張德明從互文角度考察卡夫卡作品中出現的3種不同的敘事空間,指出空間不但為主人公的活動提供背景,也象征著主人公的存在狀態[2]。馮亞琳分析了卡夫卡小說中兩種典型的空間模式——囚室式空間和交疊式空間,指出卡夫卡的小說以空間感知的方式“再現了現代人的危機體驗”[3]。曲林芳、曾艷兵兩位研究者按照隱喻的特性將卡夫卡小說中的空間分為3種類型——變形之所、骯臟之所、隔離之所,并且對這些荒誕空間的功能和特點進行了梳理[4]。這些研究者對卡夫卡小說的空間研究從宏觀著眼,按照不同特征以空間劃分的方式對卡夫卡小說作出整體把握,而對微觀的空間命題則較少涉及。事實上,微觀意象作為形式化空間的結構部分,是生發意義與擴充小說容量的重要單位。卡夫卡以現實而又精準的手法描寫荒誕,這種描寫離不開對微觀意象的表述。他的代表作品《變形記》即是其中之一。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中提到,在《變形記》中,“開門”與“關門”的動作貫穿故事的始終,并由此注意到“門”的主題[5]。從現象學的角度看,“門”作為一個空間符號,恰是隱喻個體生存境遇的特殊意象。通過“門”,我們注意到格里高爾的生活空間,以及該生活空間的變化:這是個生活著一只大甲蟲的房間,而且幾乎不被打掃。房間里充斥著腐爛的食物氣味,到處沾滿甲蟲爬行的污漬、粘液。家具被搬空,房間重新塞進老舊的、無用的家具。這是個隱喻著疾病的空間,是蘇珊·桑塔格筆下的“生存的另一面”。“疾病”將格里高爾放逐到這個空間中。格里高爾在這狹小的天地中自由地生活,卻與曾經生存的社會空間失去了聯系。他只能通過門遠遠地觀看世界,無法走近世界。而導致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一個認知倫理的佯謬,類似于魔術師的魔術:頭天晚上進入臥室門內的是格里高爾,第二天早上出來的卻是一只甲蟲。如何證明甲蟲(格里高爾)就是格里高爾成了《變形記》倫理的關鍵命題。某種程度上,這個命題意味著拉康鏡像理論的新解,意味著“自我”的現代轉型,也同樣表現出現代人的生存與認知困惑。
一、空間敘事下“門”意象分析
“門”作為滲透著強烈的感情與價值意味的時空體,“總是表現出一種隱喻義和象征義”[6]450。“門”作為意象,首先體現的是其空間屬性,時間在這里“只不過是瞬間,這瞬間似乎沒有長度”[6]450。卡夫卡之所以能夠以無比精確的方式描寫荒誕事物,原因正在于《變形記》的描寫集中于事物的空間屬性上。線性的時間體驗在這里放緩。尤其在《變形記》的第一節,卡夫卡用了大量篇幅描寫3個小時內發生的事情。從格里高爾醒來,到他掙扎著起床、開門,卡夫卡事無巨細的描寫讓時間的推進變得極度緩慢。而經驗、回憶、變形、想象得以以空間的方式再現。由此,“空間中塞滿具體可見的時間。空間中充滿了真實的活生生的意義,與主人公和他的命運形成了至關重要的關系”[7]。其中最為關鍵的空間意象是那扇臥室的門。約翰·威克曼以統計學的方式指出:“在《變形記》中,門(Zimmer)這個詞單獨或以詞組的方式一共出現了151次,其中有68次和格里高爾的臥室有關。”[8]反復出現的意象不僅使作品的主題得到了很好的復現和深化,而且賦予作品很強的敘事張力。重復的意象凝聚成一個空間意義上的統一體,使小說呈現出空間面貌。
齊美爾在《橋與門》中寫道:“分離和統一只是同一行為的兩個方面。”[9]“門”正是這樣一個特殊的空間結構,它同時擁有隔絕和聯通的功能。它的存在限制了個人的內部空間,又將其引向無限的外部空間,形成內與外的辯證。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門”的存在意味著隔絕、束縛、監禁。而對于主體來說,那扇隱含著誘惑、欲望、不安全感的門又會引發室內之人對室外世界的想象,從而讓精神空間變得無限大。這其中自然隱含著非理性的因素,同時也反映了人所特有的幻想維度。對于卡夫卡來說,這扇門的隱喻意味著人與世界的偏離與共生,意指人與世界相互聯系又相互隔絕的生存狀態。這扇門打開著,人卻無法走進門內,只能像坐井觀天的青蛙那樣在被放逐的井底徘徊,像《城堡》中的K,像《在法的門外》中的鄉下人。這是卡夫卡式的寓言悖論,也印證著他的那句名言:“目的是有,道路卻無。人謂之路者,乃躊躇也。”[10]
在《變形記》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描寫:格里高爾被蘋果砸傷以后,幾乎喪失了靈活行動的能力。它爬行遲緩,在高處爬行已是不可能,“可是他為自己狀況的這種惡化還是得到了一種在他看來完全足夠的補償,就是每到傍晚時分那扇他慣常在一兩個小時前便加以嚴密觀察的起居室的門便會打開”[11]140。格里高爾“躺在自己房間里的暗處,不為起居室里的人所看見。它可以看見全家人坐在照亮的桌子旁邊,可以傾聽他們的談話”[11]140。在這樣的場景中,那扇傍晚時分打開的門成了格里高爾和外界連接的橋,這座橋承擔著格里高爾對外界的想象的重量,也暗示著家人對格里高爾容忍的底線。格里高爾甚至無法對外界展示自身,只能遠遠地躲在暗處。在家人看不到的地方,觀察它那被燈光照亮的家人們。那扇門所連接的一明一暗的空間景象并非僅僅是對資產階級壓迫的反諷,也同樣從經驗、幻想維度表達著對世界的認知與渴望。“門”作為一種空間結構成為人物的心理表征。
不久,格里高爾又開始重新思考是否應該回到曾經的社會結構之中,“夜晚和白晝格里高爾幾乎都是無眠地度過。有時他想到在下一回開門時要完全像從前那樣把家里的擔子挑起來;經過長時間之后,他的腦海里又出現了經理和秘書主任……”[11]142。就這樣,變形之后的格里高爾與這個世界,透過門,通過想象再一次連接起來。而當他試圖復歸原先的生活空間中的時候,穿過那扇門卻成了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當門始終處于人與世界的分界點時,它也就成為了主體自我的象征。“門”從他者的世界分隔出了自我的獨立空間,人與人借助門來溝通。《變形記》開篇大量描寫了敲門的動作,格里高爾的房門分別被父親、母親、妹妹敲響,他們借此了解主人公的安危。敲門意味著對主體的探尋,推開房門則意味著對主體的窺探或入侵。在文本的后半部分,女仆被辭退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一早一晚來干些最粗重的活兒”的老媽子。老媽子并不害怕格里高爾,還對他滿懷好奇。她“不失時機經常在早、晚稍稍打開房門,匆匆朝里瞥一眼格里高爾”[11]144。她還和格里高爾打招呼,這是文本中僅存的幾句對甲蟲的稱呼。“過來吧,老屎殼郎!”對格里高爾來說,它的房門被推開,展示出他變形后的柔弱,此種柔弱深藏于人的本性之中。卡夫卡沒有讓他變成一頭老虎,而是很有意味地讓他變成了一只令人厭惡卻沒有什么實際危害的甲蟲。必須要強調的是,每一扇私密的門背后都意指一個主體。格里高爾的房門背后是一只甲蟲,這成了外部世界的共識。
“門”也成了主體身份的象征物。開門與關門,進門與出門應和著外部世界對主體身份的接受或拒絕。與之相對應的是文本中另一非常精彩的描寫:當格里高爾嚇跑秘書主任,眾人發現他變成一只甲蟲之后,他遭到父親的無情驅趕。他緩慢地向自己的房間里退去,卻因為“身體太寬,一下子擠不進去”[11]121。他不顧一切地“擠進門里去。身子的一邊拱了起來,他斜躺在門口,他的一面腰部完全擦傷了”[11]122。而這時,他的父親從后面狠狠地推了他一把,“他當即便血流如注,遠遠跌進了他的房間里。房門還在手杖的一擊下砰地關上了,隨后屋子里終于寂靜了下來”[11]122。
父親將格里高爾推進門的動作具有強烈的放逐意味。盡管在此之前格里高爾還做出巨大的努力,請求秘書主任讓自己回去工作。但這一切絲毫不起作用,冷酷的現實將他重新拋回自己的房間里。門在這里起到限制和庇護的功能。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詩學》中提到:“‘人投身于世間’的形而上學可以具體沉思家屋是如何投身到狂風暴雨當中”,“這棟與世隔絕的家屋,讓他充滿強烈的意象,亦即驅使他抵抗”[12]。這些空間信息暗示自我和他者的空間共生關系,受庇護的存在終會感覺到其庇護的有限,被放逐的過程也即抵抗的過程,或者說,異化的過程。
不僅如此,門隔離出一個獨立的內部空間,這個空間也承載著居住者對自身的想象和回憶。格里高爾變成甲蟲之后,他的妹妹想要將他房間里的家具悉數搬出,“盡量為格里高爾在爬行時提供方便”。事實上,妹妹的做法幾乎抹殺了格里高爾的存在。空間,就價值層面來看,它形成了一個意象和想象的共同體。意象具體地呈現了人類在世間的處境。人對空間的感知決定了人的生存意識和生存狀態。當格里高爾的家具被搬出后,他也就失去了對那些承載著想象的意象的感受能力。他的母親同樣意識到這一點,“干嘛格里高爾就不會有這種感覺呢,他早就習慣了這些房間里的家具了嘛,他在空落落的房間里會感覺到孤獨的”[11]133。不過母親的反駁并沒有起作用,格里高爾房間里的家具被悉數搬空,當它從沙發下爬出來試圖守衛最后一個象征物——一幅掛在墻上的畫像的時候,他的母親被嚇得昏厥過去,自己也被父親的蘋果砸傷。
從“門”的隱喻來看《變形記》,人與世界的“區隔”成了這部作品的主題。人在門內,退省自守于一個孤獨而自由的空間;世界在門外,充滿想象與誘惑。通過“門”,人與世界既共生,又偏離。這種狀態帶來了豐富多彩的現代生活,也使作為主體的人被放逐出世界。凡事一體兩面。從這個角度來說,《變形記》可謂是對人類生存境遇的寓言。正如瓦根巴赫所言,卡夫卡面帶沉靜禮貌的微笑打開外面世界的大門,但卻對這個世界緊緊鎖住了自己的心扉[13]。
二、空間敘事下的認知悖謬與倫理困境
“門”從外界空間中隔離出象征自我身份的內部空間,生活在內部空間的人自然也就成為空間的一部分。黑格爾明確指出:“人要有現實客觀存在,就必須有一個周圍的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沒有一座廟宇來安頓一樣。”[14]空間某種程度上正是作為人物表征而存在,也由此獲得自我生發性。格里高爾的變形發生在臥室這個最為私密的空間中,變形意味著主體面對外界發生的異化和偏離。而對于主體來說,變形則意味著“疾病”的發生。從床上艱難地爬起來打開房門的格里高爾,正如一名重病患者那般行動不便。事實上,這只遲緩的、巨大的甲蟲本身即傳達著關于疾病的聯想。它的丑陋與不潔給人帶來強烈的拒斥感,也與他被放逐的處境相應和。在《變形記》第二部分,卡夫卡寫道:“清晨那會兒,所有的門全鎖著,大家都想進來見他,現在他開了一扇門,其余的門顯然在這一天里已經打開了,卻又誰也不來了,而且鑰匙反插在外面。”[11]124格里高爾的房間成了關押他的監獄和觀察他的病房。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寫道:“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盡管我們都樂于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15]5在現代人的眼中,疾病的發生是一重古老的禁忌,它向人們傳達恐懼,也意味著對正常的偏離。蘇珊·桑塔格指出,疾病“不是上蒼降下的一種災禍……它沒有‘意義’。也未必是一紙死亡判決”[15]91。疾病只是一種身體現象,屬于正常的生理范疇。然而,人們對疾病表現出強烈的排斥和恐懼態度。當格里高爾的妹妹推開門看見他時,“她大吃一驚,以致她竟情不自禁地從外面又砰地把門關上了。可是仿佛她后悔她的舉動似的,她馬上又打開門,像是來看望一位重病人或者甚至一位陌生人似地踮著腳尖走了進來”[11]125。一面是傳統的家庭倫理道德,一面是疾病、變形、異化的發生。對于格里高爾的家人來說,如何面對這只房間里的甲蟲成為他們首先要面對的認知困境。而他們對房門的反應也暗示他們對格里高爾的態度。
在生的意義上,人和甲蟲并沒有多大區別,或者說,患病者和健康人并沒有多大差距。所以,格里高爾的視角總是非常純真的。他變成甲蟲后,口氣中少有驚慌、絕望、憤怒。盡管他承受著常人無法忍受的苦難,他的變形是那么徹底,外貌、聲音、行動全都發生了變化。對此他卻表現出十分冷靜的態度,他保留著作為“人”的清晰完整的意識,他的主觀視角是正常而人性化的,這一點非常值得重視。他變成了甲蟲,依然想著要繼續承擔家庭的倫理責任。“只要一談到這種出去做工掙錢的必要性,格里高爾便放開門,一頭撲到門旁那張涼絲絲的沙發上,因為他羞赧和傷心得渾身燥熱。”[11]130以金錢維系的道德倫理依舊困擾著他,他也同樣還做著讓妹妹去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的夢。然而,真正的邏輯問題并不在于格里高爾自身的本體自我識別,而在于主體如何使他者確認自我的身份,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如何面對這只甲蟲成為家人們的首要認知困境”。進一步說,對于格里高爾的家人來講,頭天晚上進入臥室的是格里高爾,第二天早上出來的是一只甲蟲,那么如何確認甲蟲就是格里高爾?
唯一能夠起到證明作用的是那間臥室。《變形記》中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描寫,當變為甲蟲的格里高爾剛剛把門打開一個縫隙,露出一個腦袋時候。他不僅嚇暈了母親,嚇退了推銷員,而且“父親惡狠狠地捏緊拳頭,仿佛要將格里高爾打回房間里去似的”[11]117。所有人都被這個怪物嚇壞了,他們無法確認甲蟲就是格里高爾,直到父親“猶豫不定地掃視了一下起居室”[11]118,他們才似乎接受了這個事實。父親“用雙手捂住眼睛哭了起來,寬闊的胸膛顫抖著”[11]118。
父親對臥室的掃視,起到一個確認的作用。對于家人來說,這一切像一個惡俗的魔術。格里高爾走到簾幕后面,出來時成了一只甲蟲。家人們在潛意識里拒斥這個結果。當送飯的妹妹從臥室中開門出來時候,父親和母親會等候在格里高爾的房門口,向她詢問“房內的情形,格里高爾吃了些什么,這一回他行為舉止怎么樣,是否多少有些好轉的跡象”[11]131。而當格里高爾爬出房門,試圖尋找母親的時候,“父親無情地驅趕并發出噓噓聲,簡直像個狂人”[11]121。發出“噓噓”聲是人類驅趕動物的常見做法,父親本能地發出這個聲音,某種程度上也暗示著家人無法接受這個現實。在家人的潛意識里,生活在臥室里的是一只見不得人的大甲蟲,而不是格里高爾。
空間作為人物的表征,以符號式的語言承擔著敘事的功能。當格里高爾發生變形的時候,臥室的空間屬性也隨之轉變。對于家人來說,臥室具有了不祥的意味。曾經的家具被搬空,重新搬進老舊、無用的家具。并且,父母希望臥室的門緊緊關上,甲蟲永遠待在里面不要出來。而他們又會偶爾將門打開一個縫隙,為格里高爾與外界聯系留下一個微小的空間。同樣,對格里高爾的放逐也促使家人彼此間建立了新型的人際關系。他的妹妹取代了格里高爾的位置忙進忙出,母親和父親也都開始承擔曾經本應格里高爾承擔的責任。變化最顯著的是父親:
從前每逢格里高爾動身出差,他便總是疲憊不堪地蒙頭躺在床上;晚上回來時他總是身穿睡袍坐在靠背椅里迎候他;壓根兒就不太能站得起來……可是現在他身板挺得相當直……濃密的睫毛下一雙眼睛射出活潑、專注的目光;那一頭平時亂蓬蓬的白發梳成整整齊齊、油光閃亮的分頭……雙手插在褲袋里,板著面孔朝格里高爾走去……腳抬得老高。[11]138
格里高爾的變形促使所有人都發生了變化。這不僅反映了個體面對他者所發生的異化,也意味著家庭倫理的重新建構。事實上,也正是這種重新建構的家庭倫理殺死了格里高爾。當格里高爾多次爬出房門,給家人帶來麻煩之后,他的妹妹終于崩潰了。妹妹的一番話宣告了格里高爾的死亡。“他必須離開這兒……這是唯一的途徑,父親。你只需要拋開以為這是格里高爾這個念頭。我們這么久一直相信這一點,這是我們真正的不幸。可是這怎么會是格里高爾呢?如果這是格里高爾的話,他早就會認識到,人和這樣一頭動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就會自愿跑掉了。我們就沒有哥哥,但是能繼續生活下去,會緬懷他。”[11]150顯而易見,新建構的家庭倫理關系并不需要格里高爾,格里高爾被當作一個犧牲品。而格里高爾必須通過自我犧牲的方式,才能回歸到這種家庭倫理當中。他必須通過自我犧牲來確定自己的身份。換句話說,如果甲蟲(格里高爾)和家人待在一起,那么他就不是格里高爾。而如果格里高爾(甲蟲)自我犧牲,那么他就恢復了格里高爾的身份,然而卻永遠不能跟家人待在一起。家人對格里高爾的認知悖謬就這樣延伸到格里高爾的自我主體認知上。
拉康在其鏡像理論中認為:自我是在與另外一個完整的對象認同過程中構成,而這個對象是一種想象的投射:人通過發現世界中某一可以認同的客體,來支撐一個虛構的自我感[16]。事實上,卡夫卡筆下的本體建構不僅仰賴自我對外界的想象,也受到外界對自我要求的影響。自我生存在某種程度上有著不受控制的被動和無力。關于這一點,卡夫卡有一句名言:“我寫的和我說的不同,我說的和我想的不同,我想的和我應該想的不同,如此下去,則是無底地黑洞。”[17]所以,在《變形記》的結尾,有一種解構的聲音出現了。父親、母親的稱呼再也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是薩姆沙夫婦。他們的女兒也將要成長為一個美麗、豐滿的少女了,一家人開始重新面對生活。而格里高爾的境遇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們覺得這猶如是對他們新的夢想和良好意愿的一種確認。”[11]156
關于這一點,除了多次出現在文本中的“門”“臥室”之外,還有一個深層的線索可以說明,即“房子”。房子、家屋作為主體生存不可或缺的意象,對人物在社會空間中的分布起著框限與定位的作用。家屋是人物的生存背景,也同樣參與文本的內部建構。在文本的末尾,格里高爾死后,家人立刻開啟了一場郊游。他們各自請了假,并且立刻打算辭退掉老媽子。父親喊道:“你們來呀。別管那些陳舊事兒吧。你們也稍許關心關心一下我吧。”[11]155他們彼此詢問各自的工作,發現“原來都還蠻不錯,而且特別有發展前途”,而最能改善他們狀況的,“當然是搬一次家;他們想退掉現在這幢還是由格里高爾挑選的寓所,另租一幢小一些,便宜一些,但是位置更有利尤其是更實用的寓所”[11]156。毫無疑問,離開原來的家是他們的首要任務。原來的公寓由格里高爾所選,那時格里高爾也負擔著家里的種種開銷,是家里的主心骨。原來的倫理系統建立在這樁“不小、不便宜”的公寓里。而現在,格里高爾消失了。一個新的家庭倫理關系的建立以搬一次家為標識,只需要“小一些、便宜一些”,一個新家就能建立,而且“特別有發展前途”。格里高爾的家人通過這種方式完成了自我的建構。
“房子”意象的重復有著動力學上的意義。從住進格里高爾選擇的公寓,到最后拋棄格里高爾,重新搬家,最終人們放棄主體認知,完成了自身的重新建構,以最大限度地維持彼此的倫理關系。而這個限度是什么呢?“我若不是為了我父母親的緣故而克制我自己的話,我早就辭職不干了。”[11]107自我的主體自由與家庭的責任負擔形成生存的悖謬,而主體、個體成為集體、他者的犧牲品。這意味著現代人生存的被動與無力,以及他們自我界定的困難與認知困難,這也同樣呼應著異化的主題與身份危機。尼采早在上帝之死的呼聲中就預言了現代社會下虛無主義的降臨。“一個教條出現了,一個信仰隨之流行:‘一切都是虛空,一切都相同,一切都曾有過’。”[18]人類面對新時代、新主義、新教條時候如何界定自身成為一個重大難題。這個難題直至今天仍未解決。卡夫卡以小說的方式回應這個問題,而他的小說也始終處于闡釋的流變之中。
“空間轉向”是研究20世紀現代小說的重要命題。《變形記》充滿強烈的空間感和空間意識,其中幾乎看不到卡夫卡追尋時間的身影。然而,這并非意味著時間的“不在場”。時間被包容到廣闊的空間,或者狹小的意象之中。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門”的意象。正如海德格爾所言,“界限不是某物中止的標志,相反,按照希臘人的說法,界限正是某物開啟其存在的標志”[19]。門具有既聯通又隔絕的性質,它以“區隔”的方式將本體框限在這個世界中,體現著生存的一體兩面。與此同時,門、臥室、家屋這些空間也具有了個體的屬性,成為生活在其中的本體的身份標識。它反映著主體命運的變化,也映射著主體與他者之間的倫理關系。《變形記》的空間描寫深層次地反映了倫理困境下的自我本體認知困境。卡夫卡似乎無意于解決這個爭端,他寓言似的充滿悖謬的描寫再一次將這個問題投射到讀者心里,以待讀者去再思考、再理解、再發掘、再反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