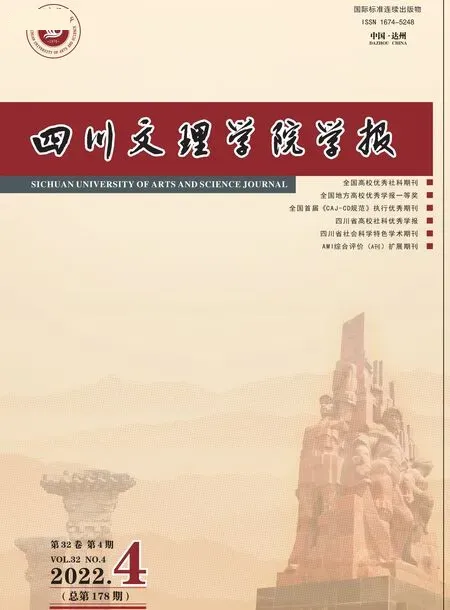李白詩歌中的“胡風”與絲綢之路關系探析
席 蓬,湯 洪
(1.四川文理學院 巴文化研究院,四川 達州 635000;2.四川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6)
“胡人”原指中國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區的游牧族群,它的歷史非常悠久。秦漢時期,塞北胡人統一后,它們被漢人稱為匈奴,漢初賈誼在《過秦論》中即有論述,談秦之興衰敗亡,其論有云:“乃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1]至漢代,“胡”則成為對匈奴的專指,匈奴則自稱為胡。魏晉南北朝以來,“胡”的范圍不斷擴大。這一時期,有歷史上重要的五胡亂華事件,西晉末期,北邊眾多游牧民族內遷,趁西晉八王之亂的衰弱期,陸續建立起非漢族國家,并逐步與南方漢人政權相對立,造成了互相對峙的情形。五胡是胡人部落聯盟的簡稱,包括匈奴、鮮卑、羌、羯、氐。因此,對于“胡人”,正統文化或以正統自居的文化往往對其采取警惕、防備、鄙夷、甚至對抗的態度。到了大唐,國力空前繁盛,對外交流頻繁,統治者采取開放包容的外交政策,“胡”已被用來泛指我國西北部少數民族部族——如匈奴、突厥、鮮卑、回紇、吐蕃,甚至中西亞乃至大宛、波斯、高昌、天竺等地。相比較而言,在大唐之前,“胡”進入詩中還是比較少的,類似于“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的詩作也往往體現出鮮明的地域特點,而到了大唐,關于“胡”意象的詩歌創作呈現出爆發式增長的趨勢,此類詩歌創作俯拾皆是,王維《使至塞上》有“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有“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孟浩然《涼州詞》亦有“胡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胡天”“胡地”中所涉及到的地點,無不與絲綢之路有著重要的關聯。盛唐時期的李白,其詩作中的“胡”意象則更具代表,他以其獨特敏銳的視角、高昂飽滿的熱情、灑脫不羈的個性、奇妙夢幻的想象、自信豪邁的語言,對絲綢之路上的“胡”意象予以真切關注和熱情吟詠,筆端傾注的感情足以使李白在絲綢之路上創作的詩篇古韻流芳,歷經千年依然閃爍著燦爛的異域色彩。
一、李白胡族身份考辨及相關爭議
關于李白的身份,歷來研究者持論不休,李白究竟是胡族還是非胡族,實證與辨偽工作尚待推進。主張是胡人的觀點,主要以陳寅恪先生的論斷為主,詹锳、松浦友久等則成為有利推動者;主張是非胡人的,多以“李唐宗室”說為主。陳寅恪先生提出李白胡族說,他認為李白是西域胡人,“入中國后方改姓李”,胡懷琛先生則提出李白先世是為突厥所掠,故而李白是“突厥化的漢人”,郭沫若先生認為,李白能迅速而熟練地掌握漢文化、而且其詩中多有對胡人的描述與品評, 因而認為“李白肯定是漢人,而決不是西域胡人。毋庸置疑的是,所有研究李白身份的學者,無不以李陽冰和魏顥所錄文字為依據。李陽冰《草堂集序》載:“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于蜀……”;[2]1691魏顥的《李翰林集序》記云:“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于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2]1697考慮到史料中的記載,李白從西域遷入中原,或多或少會受到一些胡族的影響。清代陳其元的《庸閑齋筆記》中,有“李廣遺裔之蕃昌”一文,論及隴西成紀李氏家族的發展歷程:“司馬遷與李陵善,陵生降,墮其家聲,故《史記》于其祖李廣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廣殺降致族滅之報,其實廣之十六世孫,在晉霸有秦、涼,及薨,國人謚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孫相傳三百年,國祚與漢相等。陵之子孫至唐為戛黠斯,稱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廣遺裔之蕃盛昌熾,遠勝衛、霍。”[3]
關于李白家世世系之謎。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述說:“白本家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2]1452范傳正《碑序》說他“其先隴西成紀人……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2]1714涼武昭王之后,即李暠之后,若按此說,李白與李唐統治者則是本家,唐玄宗召見李白時“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不僅僅是因為賞識李白的才華,“以七寶床賜食于前,親手調羹”更因為是李氏宗親的關系。經筆者初步梳理,李白為隴西成紀人的記載當無誤。因李氏家族以隴西為郡望,李白的祖輩,是具有少數民族血統的。追溯歷史,李陵的后代后隨北魏南遷,北魏時期,由鮮卑拓跋燾建立政權,復歸于隴,復漢姓后取名為李富,其子便是李斌。涼武昭王李暠與李斌(居高平,今寧夏固原)共認飛將軍李廣為第16世祖,李暠與李斌以聯宗方式成為同輩兄弟,因此,李白自稱是涼武昭王九代孫的說法是無誤的,這只是因為輩分正確,并不意外著李白是涼武昭王李暠一支的直系親屬。相反,李白應該是李富、李斌一支的后人,唯有如此,才符合“隋末多難”的記載。武德元年(618年)8月,唐高祖李淵為隋煬帝造成的“李門大冤案”平反,準許流落在西域的李氏家族回關內定居,由于西域避難的李氏族人極為分散且得知消息時間各自不一,因而李氏族人先后回到了敦煌、酒泉、張掖、涼州等地。關于李白的身份,歷來有碎葉說、蜀地說、山東說、隴西說等,筆者認為,李白以隴西為宗親地,長于蜀地、流寓山東的說法較為妥當。
李白親屬的稱謂,也容易引發人們聯想,以李白的父親“李客”為例,或與絲綢之路有著緊密關聯。按說,如果其父名“客”的話,李白應該會在詩文中有所避諱,但他的詩歌中有很多直接寫出,如《客中行》《俠客行》等等,由此可見,“客”之為字,實非李父之本名。陳寅恪先生《金明館叢稿初編》指出:“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華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為名,其實非自稱之本名也。”[4]對這一觀點,筆者深以為然,因為李白的父親是胡商,在隴右及西域一帶,常常將做生意的商人稱呼為某客,前面往往冠以姓氏,至于具體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對于長年游走經商的商人而言,人們只需要知曉他姓什么、做什么生意的就可以了,考慮到經商之人在隴右或西域地區四處游走的商業性質,一個簡單的例子,如“貨郎客/呼郎客/胡郎客”,這種職業的人也是以走街串巷的形式從事商業活動,往往以物物交換的方式游走四方,完成交易賺得利潤,只是規模較小。有研究者推測說,李客可能是他舉家遷住蜀中后,是蜀地人對他的稱呼,筆者認為這是非常不合當地風俗的。
二、李白“放歸還山”時的自我身份認同
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唐玄宗召李白入宮,李白滿懷信心,高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身遇明主,備受恩遇,他所思所想便是“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后相攜臥白云”,然而好景不長,李白即遭到朝中權貴讒毀、打壓和排擠,天寶三載(公元744年)暮春時節,李白即被“賜金放還”,結束了長安的政治生活。李白在短暫的翰林任期內,對唐玄宗統治下的腐敗政治有了深刻地體會和真切地認知,面對恃寵而驕的宵小之輩肆意羅織罪名、飛揚跋扈的奸佞猖狂詆毀名聲,玄宗聽信小人張垍的讒言,致使權臣對李白的詆毀與打壓轉變成了政治站隊。他倍感國事日非,內心充斥著對奸臣弄權的鄙夷與輕蔑,詩人內心悲憤難平卻無意同流合污,大呼“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揮淚離別之際,李白寫下《秦水別隴首》,詩云:“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2]141筆者認為,李白之所以被打壓,實因他卷入了一起與張垍關系極為密切的宮廷密事,張垍是唐玄宗的駙馬,但張垍卻以有婦之夫(尚寧親公主)的身份,與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有著一段秘而不宣的交往,玉真公主又與李白熟識,此即是說,李白卷入了唐玄宗的家事。李白在長安的政治生活并不久,然而他卷入政治斗爭并弄清真相的時間都至少半年多。筆者認為,李白在長安的政治斗爭,至少經歷了以下六個階段。
(一)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是李白回憶翰林供奉期所作的詩歌,李白起初遭受到詆毀,在他眼中,饞毀他的權臣心胸狹隘,這種奸佞小人就如同蒼蠅一樣,肆意玷污白玉,此時期的李白對于饞毀歸因只是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境界不同,他認為高下已判,實難同調,內心已逐漸萌生退意,但是他對于翰林院的生活充滿懷念,以詩寄集賢苑諸學士,實因很多知音好友了解他的為人。
(二)眾女妒蛾眉,雙花競春芳
李白身遭讒毀,《懼讒》詩中便引用了先秦時候《左傳·桓公六年》中的典故,“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5]“耦”通“偶”,即配偶之意,也就是說,李白遭讒毀,實與宮中的女人有關,李白被駙馬張垍打壓和讒毀之初,便是權貴張垍欲以宮中某位女性污李白名節。王安石曾評價過李白的詩歌,其語有云:“李白詩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見污下,十句九言婦人與酒耳。”王安石的評價,更多的是一種感覺,但其核心在于他抓住了李白詩歌中婦人與酒出現頻次高的特點,然而李白卻以清真、飄逸、豪放的詩風獨步盛唐詩壇,這只能從側面說明一個問題:并不是李白自身識見污下,而是他卷入了一件污下的宮廷秘事,且這件事與婦人及酒都脫不了干系,因此王安石才有了這種感受和看法。
(三)胡為守空閨,孤眠愁錦衾
語出《相逢行》二首其一,這是關于李白出宮、李白“醉酒”經過的直接記錄,也是李白在后來逐漸明白被打壓原因后的直接回應。李白之所以離開翰林院,是因為有位女性在愁腸百結的時候來找他,李白在后來才明白這位女性實際上是因為駙馬張垍而痛切悲傷,她主動邀約并帶著李白到宮外喝酒消愁,在盤桓了很久之后,李白主動求歡,“醉酒誤事”,二人雖然并未發生實質性的關系,但這使這位身份高貴的女性對李白也心生怨懟。李白在明白真相后,他追問這位女性,當初您來找我那個時候,為什么要獨守空閨、擁著華美的錦被久久難以入眠呢?言外之意是原來您是因為別人心情不好啊,而這個人便是排擠和打壓李白的駙馬張垍。張垍尚寧親公主本是有家室之人,卻因此而打壓李白,其個中緣由則不言自明。李白清晰地回憶起了當時事情的經過,也就是說,李白根本沒有喝醉酒。“愿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李白說愿像“三青鳥”一樣,為她和她的情人傳遞愛的訊息,并以“私語”的形式勸誡她,要把握青春年華,及時行樂。
(四)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詩中李白回憶起當年在長安的生活,離別長安的時候他不禁灑下滾滾熱淚,但是他的內心充滿了對權貴的鄙夷與不屑,奸佞之人弄權,在他眼中就如同小兒科一樣不足道,但是李白對唐玄宗統治下的腐敗政治已經有了深刻地認知,盡管李白對長安生活充滿留戀,但他不愿意同流合污。
(五)胡馬顧朔雪,躞蹀長嘶鳴
《秦水別隴首》一詩,便是李白作于第二次離開長安的時候,李白在政敵的打壓和迫害下宣告長安政治生活失敗,李白受辱含冤離職翰林院。從李白的詩歌中可以大致判斷,李白是在政治站隊中被逼迫不得已離開長安的,“功名富貴若常在,漢水亦應西北流”“胡馬顧朔雪,躞蹀長嘶鳴”,李白在詩歌中無情地譏諷了統治者和生活污濁手段卑劣的權貴,從詩歌的內容和情緒上看,李白受到了極大的冤屈,感情凄楚,內心充滿含冤受辱的苦痛,可以說,翰林供奉期間的李白,由于早先就與張垍相識,李白也曾是被張垍及其政治集團拉攏的對象,只是李白在后來卻身遭冤陷,傲然抗爭,由于政敵別有用心,李白在被拉攏與被排斥的矛盾中,逐漸被邊緣化,對于張垍及其政治集團而言,李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李白甚至被視為“胡族”,其實李白之心,皎如明月,只是內心的狂傲不屑為之而已。“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更以一種思歸卻又戀戀不舍的心境,向長安的生活告別。
(六)能言終見棄,還向隴山飛
李白的《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一詩,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即李白在政治生活中被迫政治站隊后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即“還向隴山飛”。對于李白是哪里人,歷來爭議不休,有蜀中說、有安陸說、有山東說、有隴西說、有金陵說等等,但是,當他長安政治生活失敗后,在離開金門即翰林院的時候,詩中明確表達便是歸于隴山方向。他的詩作中透露出良玉被棄的落寞,所謂“賜金還山”,具指返還原籍歸于隴山,泛指遠離廟堂寄身江湖。詩人以鸚鵡自比,表述胸臆,鸚鵡本是隴鳥,當詩人“緬然含歸情”的時候,會歸往哪里呢?“還向隴山飛”。李白在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對自己的身份認定是隴山方向的人,即今天水、平涼、固原一帶人。
三、李白詩歌中的胡風及其歸因
(一)李白詩歌中的胡人形象
由于不同的生活環境和風俗民情,西域胡人和中原漢人的外貌,有著明顯的差別,尤以眼睛為突出特征。李白對此也有過詳細地觀察,《幽州胡馬客歌》中有“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猛虎行》中“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纻飛梁塵”,《經亂后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有“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等等。胡馬客、胡雛,都有著共同的特征:綠眼睛。李白對他們的觀察如此細膩,描寫如此詳細,正是基于胡漢文化的不同,說李白是胡族,實難成立。
胡姬本指胡地的女子,有以賣酒為生的,也有侍酒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賣藝為生的,也有成為妓女的。胡地女子極具異域色彩,她們性格開朗大方、熱情爽朗,服飾艷麗,芳香四溢,姿容絕美,顧盼生輝。大唐時期,胡地樂舞風行朝野,李白對此十分欣賞,例如他描述胡姬的美貌和擅樂,即有“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 (《前有樽酒行二首》)“胡雛綠眼吹玉笛”(《猛虎行》)、“葡萄酒,金叵蘿,胡姬十五細馬駝。玳瑁宴上懷里醉,芙蓉帳內奈君何!”[2]1377(《對酒》)“雙歌二胡姬,更奏清遠朝”《醉后贈王歷陽》等名句。《少年行二首》其二“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展現的是年輕時爽朗豪放、任情狂歡的李白形象;《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中“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2]944則體現出李白在胡風熾熱的青綺門置酒送別好友歸隱時的惜別留戀之情,在詩人心中,胡姬酒肆是一片自由之地,詩人的言語當中充滿喜愛之情。
(二)李白詩歌中的胡人神仙與胡風樂舞
在唐代,統治者開放宏大的胸懷與兼收并蓄的策略,使中外文化交流非常繁榮,相比于前朝,夷夏之防的觀念非常淡薄,唐太宗“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種恢弘的氣度,進一步促進了胡漢文化交融。絲綢之路上的少數民族,能歌善舞,他們自由奔放、熱情大膽、自由奇特的樂舞,不僅在長安深受歡迎,也對唐代的詩歌樂舞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李白喜好自由、生性浪漫,觀胡舞胡樂表演也常詩興大發,總能夠通過浪漫大膽的想象將其體現在詩歌創作中。
李白《上云樂》中,便直接寫到了相傳西部太陽落山的地方,胡人神仙文康就出生在那里,他生自上古,長生不死,且能歌善舞。“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戍削風骨。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圣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杯。”[2]246李白汲取了神話傳說中的養分,吸收《樂府詩集·清商曲辭八·上云樂》、南朝梁周舍《上云樂》等前人的創作,以胡人神仙文康善弄鳳凰獅子而擬作的《上云樂》,大膽想象和描繪了西域胡人攜獅獻鳳祝大唐天子秀的盛景和祝愿,并側面反映出胡人的長生愿景及其宗教思想。
《于闐采花》便是李白關于胡風樂舞的典型創作,詩作由西域傳來的胡戎舞曲《于闐佛曲》改創而成。于闐故址在今天的新疆和田一帶,但在當時泛指塞外胡地,李白在詩中這首詩歌中多次提及“胡”“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齒”,明妃指代王昭君。李太白以詩言志,借用無鹽女和王昭君的典故,闡發自己遭讒致毀的慨嘆,抒發了詩人對人才埋沒的強烈憤慨。此外,《東山吟》一詩中“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提到的青海波舞,《司馬將軍客歌》中“羌笛橫吹阿亸回,向月樓中吹落梅”寫到的羌笛……都是寫胡地的樂舞。
(三)李白詩歌中的胡化器物
李白的《靜夜思》一詩膾炙人口,“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句中“床”的涵義,就有很多學者解釋為胡床。在中外文化廣泛交流的背景下,胡地的很多工具和器物逐漸通過各種途徑傳到中原地區,有胡服、胡床、胡酒、胡食、胡器,胡樂、胡舞等。李白創作的“胡”意象,有很多內容是胡地樂器的描寫,《九日登山》詩中有:“胡人叫玉笛,越女彈霜絲”;《清溪半夜聞笛》詩中有:“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夜別張五》詩中有:“橫笛弄秋月,琵琶彈陌桑”等等。玉笛、羌笛、橫笛、琵琶、都屬于西域的樂器,后來逐漸到了中原地區,因獨特的音質,深受中原漢人喜愛,這也讓人不覺對絲綢之路上西域樂器的傳播史產生更為濃厚的興趣。胡地空曠寂寥,作者聯想到自身的遭遇和處境,借哀怨的笛聲,往往容易引發人的感傷、悲愁或相思之情。因此,胡樂并不僅僅是簡單的樂曲聲,其中也寄寓著詩人深厚的感情。
西域的美酒醇香濃郁,李白不僅在詩作中對酒大加贊賞,“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2]1238同時對酒器的描寫也極具美感。《客中作》有詩句云:“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便是寫以玉碗盛蘭陵美酒,酒的色澤鮮亮,盛在玉碗中看起來就像琥珀一樣晶瑩剔透,芳香撲鼻,讓人垂涎,比喻形象貼切;《對酒》中亦有“蒲萄酒,金叵羅,胡姬十五細馬馱”的詩句直寫酒器,金叵羅即金制的、口大扁形的酒杯,李白性情豪邁,對酒器的描寫也體現出他不拘小節的氣度。西域絲綢之路的交流和繁榮,為中原地區和長安都城帶來了胡地的優質葡萄、瓜果、美酒等,也使中原文人感受和體驗到了胡地的大漠風光與自然風情,異質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動,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他的創作。
(四)李白詩歌中的胡地邊塞風情
盛唐時期的詩歌,邊塞詩派是一個重要流派。由于邊塞戰爭時發,邊塞詩派筆下的作品,充滿壯闊宏大的邊疆風貌的描寫,如大漠孤煙直、北風卷地白草折、去時雪滿天山路等,李白也有很多描寫邊塞及戰爭的詩歌,其中大量的描寫便于胡地風情密切相關。《塞下曲》六首有:“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關山月》詩云:“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戰城南》詩則有“秦家筑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觀胡人吹笛》寫“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胡無人》詩中有“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堅胡馬驕……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胡馬客歌》詩中“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等細致的觀察和描寫便是對當時歷史的如實記錄。在這些詩里,風、霜、雪、沙、塵、火,無不通過自然現象的描寫流露出作者的思緒和情感。此外,《白纻辭三首》中寫胡風,有“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古風五十九首·其六》中寫胡天,有“金沙亂飛日,飛雪迷胡天”,《王昭君二首》中則寫到了胡沙、胡地,“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流夜郎贈辛判官》一詩中有“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永王東巡歌十一首》詩中亦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李白的詩中多次寫到胡風、胡天、胡地、胡沙、胡馬等等,這本身便是對絲綢之路的如實描寫。李白作詩鞭撻過當時的征戰多伐,胡馬、胡地、胡天、胡沙等“胡”意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詩人對朝廷失望悲涼的心緒,流露出對士兵百姓的同情,詩人也飽含深情地歌詠了邊塞的戍卒將士,嘆惋了“王昭君”式公主的和親犧牲精神。
四、李白詩歌創作與絲綢之路關系互鑒
唐代詩人一首首極富異域色彩的詩歌,如同鑲嵌在絲綢之路上一顆顆耀眼的明珠,記錄時代,反映生活,唐代統治者開明寬松的統治政策,使西域文化與漢文化進一步交流融合,繁盛的長安便是文明薈萃之地,長安西市即是一道胡商集聚的異域風情線。葛景春先生在《李白及其詩歌中的絲路文化色彩》中談論李白與西域文化的關系時指出:“李白的西域文化因子,并不完全表現在他的詩中,而是烙在他的靈魂上,溶化在他的血脈中……李白的西域文化因素,卻體現在他的骨子里。他本身就是中國文化和西域外來文化相互交融的代表性人物。”[6]葛先生對絲路文化之于李白影響之至論,毋庸置疑。具體說來,李白在絲綢之路上的創作,有以下幾點,給人啟發:
(一)李白在西北絲綢之路上的行程,是隨著先人歷經過磨難的行程
正因為李白幼年及成長的經歷,李白少有“夷夏之防”的觀念,包括他在長安政治生活中“平交權貴”的思想,都反映出李白思想的超越性,在他的思想觀念中,民族平等意識、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觀念,是很明顯的。而且這種思想,并沒有因為別人的鄙夷而改變,相反,他熱情的謳歌胡地、胡姬、胡酒,說明他深受絲路沿線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
(二)李白在長安政治生活失敗后對自己的身份認定為隴山人,與史料中其先為隴西成紀人的記載相符合
“能言終見棄,還向隴山飛”,此時的李白以“鸚鵡”自比,“隴鳥”歸山便是寫對故園的留戀之情。李白遭小人讒毀,所謂李白“胡人說”,筆者以為李白祖先確有胡人血統,但恢復漢姓后,李白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胡人。唯一有可能的是,在李白遭受權貴排擠打壓的時候,心胸逼仄權勢熏天之流將其視為胡族,這實則是在政治斗爭中排擠和打壓李白的一種手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李白既與朝中權貴乍起沖突,又恃才傲物不能為朝中政治勢力所容,唐玄宗偏聽偏信寵臣巧佞之言,漸漸疏遠了李白并將其“賜金還放”,即“為賤臣詐詭,遂放歸山”,于是李白又恢復了布衣之身。從地理位置看,李白從都城長安被放還到了隴山,長安是路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隴山”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段,作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隴山在“一帶一路”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
(三)李白胡地邊塞詩歌的創作,飽含對民族戰爭的批判之情,對和親之事報有深切的同情
李白《古風》詩:“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2]136詩中的“胡兵”,便是寫安史之亂中胡人將領的叛亂,詩人對生靈涂炭、血流成河的現狀此大加批判,正是對叛軍將領的撻伐與不滿。李白《戰城南》詩:“秦家筑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2]214反映出李白憎恨無休無止的戰爭、熱愛邊塞和平,詩歌主張不輕挑邊釁和戰爭,立意高遠,值得在處理民族問題和對外關系時思考和借鑒。
五、李白詩歌中的胡化精神及人格境界
李白“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在盛唐風云激蕩的時代背景下,詩人始終具有濟世的偉大情懷,渴望建功立業。即使政治生活失敗了,也懷抱“長風破浪會有時”的希望。關于李白想要上陣殺敵建功立業的愿望,很多詩歌中都有所表露。如《送族弟爟從軍安西》“君王按劍望邊色,旄頭已落胡天空”,《子夜吳歌·秋歌》“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詩中,有“拂劍照嚴霜,雕戈鬘胡纓”,《俠客行》中,亦有“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等等。安史之亂前后,李白對胡人將領安祿山及其軍事集團予以高度關注,戰爭爆發后,他更渴望能為大唐馳騁疆場、上陣殺敵,希望“破犬戎、平胡虜、遏戎虜、鬘胡纓”,充分展現了詩人關切現實、果敢豪邁、一往無前的壯志情懷。胡人的性格堅毅豪爽,慷慨尚武,因此,胡人的精神氣質,對李白現實主義詩歌創作影響很大,詩人渴求效力疆場、建功立業的追求與強烈的民族責任感,皆可見于詩人筆端,這也成為詩人“欲濟蒼生,以安黎元”偉大人格境界的生動寫照。
結 語
無論是李白的家庭、經歷還是詩歌創作,有不少地方沾染和表現出胡風,他的很多詩歌更是絲綢之路上民族交流與融合背景下“胡化”的真實寫照。李唐王朝的開明統治和寬松政策,讓“胡曲”“胡樂”廣為流傳,“胡舞”“胡姬”盛行朝野,“胡服”“胡風”蔚然成風,“胡妝”“胡食”深受喜愛,胡家酒肆作為娛樂消遣的地方,漂亮的胡姬、精彩的胡舞、精美的胡器、醉人的胡酒,無不讓人心馳神往,加之廣袤的胡地風光、豐富多彩的胡地文化,都為李白的詩歌描寫和創作提供了極大便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李白的詩歌是多民族文化尤其是胡漢文化交融的結晶,這也是其詩歌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