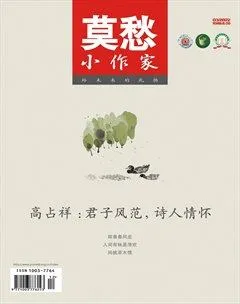閑挑草木情
又到了漢樂府辭中“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的季節。
路邊的銀杏樹,葉子已然凋零殆盡,只剩下灰褐色的枯枝向著天空伸展。紅楓的葉子也在寒風冷雨中紛紛飄落,即使還有幾片葉子卷縮著掛在梢頭,也是有氣無力毫無往日的暖麗姿態,給人幾分無奈,又幾分不舍。繁華褪盡,萬物消隱,在蕭瑟的寒風中草木展現了生命的另一面。不管日復一日包含著怎樣的意蘊, 它們都是寧靜的,每一個生命在時空的交錯中,充滿了隱忍和佛性。
我相信萬物有靈,草木同樣如此,而且屬于人類的生命只有一次,屬于草木的生命卻有可能“春風吹又生”。這種天賦與能耐,我們只能徒然艷羨。
故而在草木凋零之際,挑選宋人劉克莊的詩“薄有田園興,閑挑草木情。殷勤美年少,存問老書生”中的一句,作為標題談一談,也未覺違和。
關于花草樹木的書,在中國古代大多是放在“經史子集”之“子”里的,地位和經、史類比起來不算高,屬于飯后茶余、閑情雅致的寫作。但古人對于植物,情有獨鐘有之,博愛眾芳者亦有之,從中得到了無法替代的逸趣。
西漢著名辭賦家枚乘在《七發》中說:“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在他看來,融入自然、回歸山川草木之中,這種歡樂是絕無僅有的。
李賀的《秦宮詩》詩里有“花底活”三字。明代有個叫陳詩教的人,編了一本書,借來一用,書名叫《花里活》,還在序言里表示草木“此中有真樂”的滋味。
確實,相比于鳥獸的靈與動,中國人似乎更加偏愛草木的恒、靜、雅。草木落地生根,一期一會,天然恬淡,靜默無言,契合了靈魂最溫柔、最純樸的部分。
為一瞬的燦爛,年年歲歲,寒來暑往,努力綻放。不管你是誰,沒有算計,無須戒備,都為你而盛開。所以,有人說若有來生,愿為草木。在《詩經》里,提到草木的詩篇隨處可見。孔子在《論語》中說:“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段話意思是說,讀《詩經》,近可以侍奉父母,遠可以侍奉君王,還可以知道不少鳥獸草木的名稱。
文震亨的《長物志》、張岱的《陶庵夢憶》、李漁的《閑情偶寄》、黃圖珌的《小窗自紀》,古代文人的院中、書中、心中,也總是繞不過草木。
陶淵明愛菊,種菊南山下。梁元帝愛薔薇,芬芳襲人。王維愛蘭,滿徑種芳蘭。蘇東坡愛竹,不可居無竹。周敦頤愛蓮,出淤泥而不染。楊萬里愛荷,映日荷花別樣紅。林逋愛梅,寂寞獨自開。
“風生寒峭,溪灣柳間栽桃。月隱清微,屋繞梅余種竹,似多幽趣,更入深情。”
“山園日靜,花徑風甜,即一草一木,莫不怡人心,爽人目;況乎眾香畢具,百態娟妍,既可人憐,奚容不賞?然一甌茶、一杯酒,吟風醉月,賞必求其宜也。乃為之書。”
植物的習性,寄托了人心的向往,他們之間產生了通感。得意時寄情山水,能享云水風度;失意時寄身山林,方顯獨立自由之精神。
汪曾祺曾說:“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兒,它們很溫暖。”
在文人的眼中,草木如君子,如朋友,總在孤獨時刻,如期相伴。蕉之為蔭,時映窗外;梅之沁芳,搖曳院中,以草木閑情,度過每一寸光陰。
唐代詩人張藉,據說他性眈花卉,聽說某一人家有山茶一株,花大如盎,一心想要,估計無法得到,就以愛姬柳葉換之,被當時人稱為“花淫”。
南朝詩人何遜,曾在揚州做過官,官舍中有一棵梅花,遜常吟詠其下。他后來調任洛陽,見不到南方的梅花,因太過思念,竟懇請再次轉任揚州。到了揚州,正逢梅花盛開,于是對花徘徊,終日不能去。杜甫為此有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南朝梁時有個處士,也是個詩人,叫陶弘景,他酷愛松風,在庭院中種了很多松樹,“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則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從此“松風”成了古詩文中常出現的一個詞。
愛草木的極端例子是唐代李德裕。他擔任過宰相,一生都在政治漩渦里打轉兒,卻酷愛草木,曾寫過一篇《花木記》,鐫刻于石上。他愛花草到何種程度呢?據說他有一個遺誡:“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這是因愛生恨,近乎咒語了。
“托物雖自殊,心期俱不俗”,正如作家何頻在《雜花生樹——尋訪古代草木圣賢》中所說的那樣:“我們的文化傳統里有這樣一條永不斷線的草木之鏈,很有韌性和長度,具有十分精彩的一面,它是中國文化一個顯著的特點。”
最后摘錄幾句徐志摩的詩,《我是如此的單獨而完整 》:在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著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里/為聽鳥語/為盼朝陽/尋泥土里漸次蘇醒的花草/但春信不至/春信不至
春信不至,沒關系的,心也是快樂的。因為草木永遠在那里,大自然永遠在那里。
再過一個月,春天來臨,草木又會變得葳蕤起來。
飆搏萬里:歷史學博士,出版作品《中國高古石獅鑒賞》《遇見·古雅》等。
編輯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