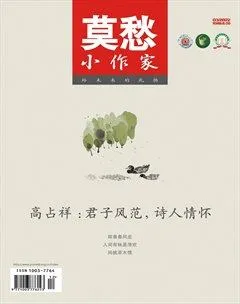鼓點飛揚
1
一個清冷的冬天,幾天前剛剛降過一場雪,大平原的田野極為遼闊。我一路走一路問,繞了幾條路,穿過幾條小巷子,才找到了要找的人。
眼前的人極為普通,三分像農民,七分像藝人,他就是楊培杰。他說,過段時間電視臺要來錄制“海安花鼓”,目前正在準備。隔壁就是排練大廳,廳內有二十多人正跟著音樂有節奏地跳著舞。楊培杰也是剛從排練中抽身,一只手持著花鼓,另一只手還握著纏著綠色大綢的鼓棒。我心內一動,開門見山:“我想看《海安花鼓》。”
音樂一出,姑娘們一手執扇,一手執鼓,踩著柔美優雅的旋律,載著豐收的喜悅,翩翩起舞。海安花鼓的鼓點飛揚,給這片原野帶來一股清新的風。
年過七旬的楊培杰是省級花鼓非遺傳承人。20世紀60年代末,他積極響應號召,打起背包從南通來到海安縣沿口公社的東升九隊,成了一名下鄉知青。那一年,他十八歲。
沒有想到,懷著一腔熱血的楊培杰,從此他鄉成故鄉。
有一天,當他忙完脫粒,拖著疲憊的身軀躺在稻堆上仰望天邊的晚霞時,田野深處的一聲富有韻味的民間小調一下子激活了他的神經。
“這是什么調呀?”他猛然一躍而起,屏住呼吸,在那個清一色樣板戲唱腔的年代,這樣的聲音是多么的可貴與生機勃勃。在這個農田連著農田、溝渠連著溝渠的平原上,農民在日復一日的勞作耕耘下,日子枯燥而單調,興許這小調便是他們生活的調味劑。
那是他第一次聽到海安花鼓小調。經考證,“海安花鼓”傳入的時間,可追溯到明代的嘉靖年間,“花鼓傳來三十年,而變者屢矣,始以男、繼以女,始以日、繼以夜,始以鄉野、繼以鎮市,始以村俗民氓、繼以紈绔子弟。”(青浦人褚聯撰著的《明齋小識·花鼓戲》)后融入寧海(海安古稱)民俗文化中,并以地域冠名。由此推算,也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了。
那時盛行的“花鼓”亦叫“唱秧歌”。秧歌,是一種與小歌劇相似的民間舞蹈,鑼鼓伴奏,拍打狂舞,豪邁粗放。當然,有的地區也表演故事。而海安地區的打花鼓,多以說、唱為主,舞蹈動作為輔,分為“角斜”“舊場”“李曹”三大流派。其特點各有側重,有的注重舞者之間的配合,講究氣勢和隊形;有的注重動作的細膩、造型的優美,講究表演的風趣與幽默;有的更注重唱腔的變化,講究戲曲表演程式。
楊培杰在中學時就是文藝骨干,能歌善舞,尤其是擅長舞蹈。難怪我面前的他,雖然人近七十,但身段、笑容,分明是一場盛大花鼓戲中閃亮出場的主角。他坐在桌前,拿著花鼓,目光堅毅沉穩望向遠方。最動人的是他臉上洋溢的笑容,不是大笑,不是微笑,是發自內心的自然、自信之笑。他不像農民,而分明是一位藝術家,是一部影片的主角,閃耀著奪目的文藝氣質。
楊培杰告訴我,清代時,打花鼓的表演形式完全是原生態的,也很簡單,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打場子”,亦稱“上秧歌”,常為八男八女之歌舞;二是“雜戲”,又稱“唱奉獻”,其劇目或為歌頌英雄豪杰,或為吟誦四季花開,或為傳說故事,或為談情說愛。至于曲子怎么譜、歌詞怎么寫、舞蹈怎么跳,反而不重要,只要用自己的聲音和動作,演出一天天的活計和想要的日子就行。后來,隨著時代的變遷,它逐漸演變,便有了“紅娘子(旦角)”“上手(生角)”“騷韃子(丑角)等主要人物之分,實際上,就是“一旦一丑一生”的三小戲形式,表演的程式也隨之變得復雜起來。
講到這兒,楊培杰用槌子敲了幾下,那聲音便悠揚高亢,奔放開闊,蕩氣回腸,與舞者一樣,是不加修飾的健康之美。
1970年初,縣文工團招人了,楊培杰以突出的表演才能博得了老師的賞識和贊許,被錄取為縣文工團的一員。
從此,他更加努力,走過一個又一個村莊,縣外、省外與花鼓有關的區域他都到訪過,他跟著鄉間藝人走鄉串村,隨著他們下地,陪著他們干農活,坐在田間,聽他們信口吟唱,看打花鼓“咚咚”跳躍的舞步。他的靈感也跟著嘩啦啦地流淌,將這燦爛的瑰寶,復制到他的筆下。
2
不覺間一走就是好幾年。無論春秋冬夏,幾乎每個夜晚他都窩在十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仔細研習海安花鼓從農民日常生活、生產中提煉發展起來的“三步兩搭橋”“蝴蝶繞花蕊”“風擺柳”“撬荷花”等舞蹈動作,并進行再創作。
海安是幸運的。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個年頭,以“花鼓調”為基本旋律,以“十月金鳳”為主題的八男八女之花鼓,作為南通代表隊的壓軸節目參加了江蘇文藝會演,獲得創作表演雙一等獎。楊培杰今天描述起來,還一臉興奮。
此后,他的心活了、遼闊了。他多少次高高低低深深淺淺,用足跡丈量著江海大地,通過傳承、借鑒,在動作設計、隊形編排和音樂創作上大膽創新,將具體變為抽象,將影像變成文字和曲譜,匯聚到他布滿皺褶的本子上。到了晚上,他不停地唱呀,跳呀。累了,便就地躺下睡會兒。從1978年開始,花鼓的創新發展為他打開了一扇明亮的窗。
1983年,他和文化館的葉光榮合作,將《海安花鼓》整理成文本,由章毓霖繪圖,收入《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江蘇版),由舞蹈出版社出版發行;1986年,以《海安花鼓》為原型,反映青年男女愛情生活的情節舞《花鼓情》,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1999年,《海安花鼓》因具有柔美靈巧之風格,被選調參加“首都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聯歡晚會”。21世紀以來,《海安花鼓》又強化了動與靜、抒情與激越的對比,將文化部的“群星獎”和中國文聯的“山花獎”一一收入囊中。
2008年,楊培杰58歲了,《海安花鼓》應邀亮相于鳥巢,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儀式前的演出。
多年積淀的海安花鼓,在這瞬間終于噴薄而出。以方言說唱為主的海安花鼓經過加工、提煉、創新,在國內多達幾十種的花鼓中脫穎而出,成了一顆耀眼的星星。
3
楊培杰忽然甩開嗓子,歡快地哼起了《花鼓調》。
他太投入了。像這樣的花鼓調,在這個時間段,按理講,他應該越唱越高興才是,可是,就在我回過神來的那一剎那,明顯感到聲調一沉、一轉,轉中抑,揚中沉,眼淚隨著他的聲調漫漫滑出。
半晌無言。許久,有人說:“楊老師太不容易了,這幾十年來持續對海安花鼓進行挖掘整理和藝術加工,實現了從‘說唱’向‘歌舞’的轉變,使海安花鼓得到升華,成為風格穩定、地方特色鮮明的舞蹈藝術。他的付出太多了!”
楊培杰慢慢抬起頭來,對我們講道:“難呢!花鼓的傳承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這當中有歌、有舞、有汗,更有淚呀。”
沒等我插話,他補了一句話:“我扎根于他鄉五十個年頭了,為的就是花鼓的傳承與發展,靠的就是內心的這份責任和堅守。”當他講到“內心”時,右手狠狠地在心臟處拍了幾下。
有人擔心這代代相傳的花鼓往后會面臨斷層。
楊培杰搖搖頭:“不會的,永遠都不可能。”
他告訴我們,多年前,自己就深入到學校、社區,積極推廣“海安花鼓”。到目前為止,已經構建成老、青、少三級傳承體系,估計有七八萬人在打花鼓、跳花鼓。縣城有、鄉村有,老人在跳,孩子也在跳。在海安,這不僅僅是用來娛樂的舞蹈,在某種意義上,海安花鼓已成為這方土地的一種精神象征。
在曠野中,鼓點飛揚,烘托起了一個雷雨滾滾的新世界。
吳曉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散文學會理事,作品散見于《鐘山》《安徽文學》等刊物,出版《逐夢金陵》《觸摸心靈的陽光》《歲月的味道》《隨風而行》等多部散文集。
編輯 木木 691372965@qq.com
3062501908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