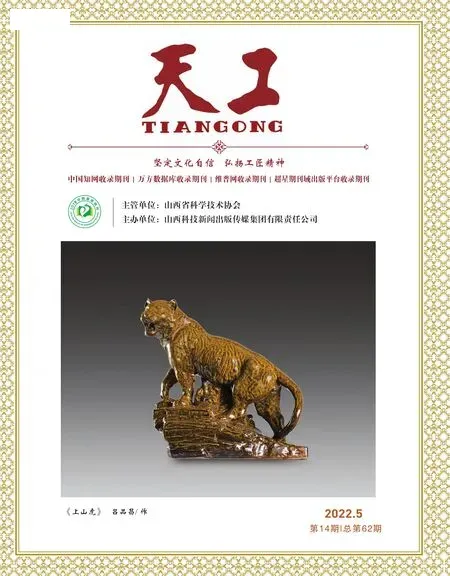淺析羅布林卡堅賽頗章宮殿壁畫中的漢文化因素
張依果 西藏民族大學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成為必然。羅布林卡作為西藏重要的有著“寶貝園林”稱號的藏式特色建筑,其中也并不缺乏漢文化因素的融入。在這座精致的建筑群中,無論是宗教文化還是建筑特色、文化風格都有著漢文化的印記。本文通過分析堅賽頗章宮殿中的壁畫內容、壁畫特色來尋找在歷史長河中漢藏文化的交流溝通印記,以及漢文化因素形成的原因。
一、羅布林卡及堅賽頗章宮殿概況
羅布林卡是西藏高原極具民族特色的藏式宮殿建筑群,有山河、水泉、草地、林木及鳥獸群集。在建造過程中不僅使用了藏式特有的藝術表現手法“雪堆白”,還融合了漢式、江南園林風格,讓羅布林卡成為了中國藏式古典園林藝術的豐碑。這里也是達賴喇嘛的專屬夏宮,從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時期開始,歷代達賴喇嘛在每年的藏歷三月至九月期間都會從布達拉宮移居羅布林卡。
堅賽頗章宮殿是羅布林卡三大宮殿之一。以堅賽頗章宮殿為主的整體建筑群由堅賽頗章、格桑德齊、其美確齊、烏斯康這四座宮殿組成,這一區域也被命名為堅塞林卡或金色林卡。
堅賽頗章宮坐北朝南,建筑平面呈“凸”字形,主殿名為“德吉俄擦白齊”,整體為三層建筑,分別是一層的德吉俄擦白齊殿堂,二層的朗瑪康、巴桑堆齊,三層的斯喜邊巴、薩松日貢、白丹堆久、貢門吉采、密吉果界。格桑德齊宮殿在堅賽頗章宮西北處,其中雕刻了許多具有漢地風格的人物題材。其美確齊宮殿位于格桑德齊的南面,在此宮殿的墻壁上也繪制了許多漢地故事、風景以及具有漢地風格的精美壁畫。這些色彩鮮艷的大型佛像壁畫,展現出了深厚的佛教文化,是人類藝術歷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羅布林卡堅賽頗章宮殿壁畫中的漢文化因素
(一)堅賽頗章宮殿壁畫的題材與藝術風格
在西藏一般都會將壁畫繪制在寺院、佛塔、洞窟、宮殿、府邸和居民建筑的墻壁上,也會繪制在天花板和藻井處。為使壁畫保存長久,繪畫的原料多采用礦物質顏料、植物顏料。
堅賽頗章宮的主殿中有許多精美的藏式宗教題材壁畫,在一樓德吉俄擦白齊殿中有佛傳《如意藤》的滿繪壁畫,壁畫講述了三十二位佛的故事,展現形式狀似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樹。二樓的朗瑪康殿的壁畫展現了黑如噶、大白傘蓋佛母、哪咖熱恰本尊像的生動形象。在巴桑堆齊殿外間的《噶當十六明點像》壁畫,運用高超的繪制手法繪制出以圣海觀自在菩薩為主體的觀世音菩薩的十六種化身。三層的斯喜邊巴殿中則繪制了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以及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壁畫。
格桑德齊大殿中繪制了《彌勒凈土》的壁畫,彌勒在藏語中稱作“強巴”,是釋迦牟尼預言的未來佛。除刻畫了彌勒佛,還有佛陀身相的彌勒、阿底峽大師、宗喀巴大師。時輪佛塔壁畫以時輪表示三時,時輪意為時間不斷輪轉。
其美確齊宮殿中宗教題材的壁畫較為典型的是二層展示出的《香巴拉王國圖》壁畫,呈現出壇城的樣子,是對未來世界的美好企盼。《羅漢渡水圖》壁畫表現近代生活的魅力,其中繪制了一位攝影師正在進行攝影工作,他使用攝像機的樣子引起了一旁孩童的好奇心。
羅布林卡中這些傳統藏式風格的裝飾雕刻、壁畫,以及運用“雪堆白”藝術手法創作的精品金銅造像、佛龕、宗教用具是人類珍貴的寶藏。
(二)羅布林卡堅賽頗章宮殿的漢文化因素
堅賽頗章宮中除了宗教題材的壁畫、雕刻、家具等內容外,還有一部分非宗教題材漢式文化因素,如五臺山、蓮花、仙桃、菩提樹、福祿壽喜圖等。堅賽頗章宮將漢文化因素與藏式風格結合,讓羅布林卡有了更加重要的意義。
二樓朗瑪康的墻壁上有一幅壁畫,將漢地的四位天神繪制得傳神生動。因這四種形象貼近民眾生活,且有吉祥如意的寓意,所以在漢族的民間廣為流傳。在斯喜邊巴殿堂中的門屏上還雕刻了浮雕,寓意人們潛心修行,積極行善,與佛教眾生平等的思想相對應。
在朗瑪康南壁約兩平方米的墻面上繪制著一幅《頤和園全景圖》壁畫,1908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進京覲見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隨從畫師帶回頤和園全景素描,在堅賽頗章宮建成之后便繪制于此,反映了藏民族據史作畫、以畫言史的繪畫傳統 。它運用極具勉唐派畫風的風格并以大面積的青綠色來表現當時的頤和園,不僅繪制出了碧云寺、長廊、佛香閣等頤和園的特色建筑,還在頤和園全景的上空用強烈的民族風格繪制了佛祖、十六羅漢等佛教風格的形象,同時對許多細節進行描繪,如一些清代官員與藏地僧人交談,孩童玩耍等畫面,向世人展現出了幾百年前的頤和園美景,以及藏族同胞眼中的漢地生活。
其美確齊宮殿中《南海普陀山風景圖》壁畫繪制于20 世紀初,上方的藏文題記意為“梁朝時期所建南海普陀山寺風景”,右上角的藏文為梁王的祈愿文。這幅壁畫將南海普陀山以及山中的建筑、寺廟通過精巧的構圖排列,運用鮮明的色彩,展現出一幅層巒疊嶂的青山圖。在圖中較細致地刻畫了僧人的生活、漁民出海、孩童嬉戲的畫面,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
三、羅布林卡堅賽頗章宮殿壁畫中漢文化因素形成的原因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民族文化的產生和發展要通過長時間的文化積累。吐蕃是公元7 世紀初建立的奴隸制王朝,這個王朝的東面便是文化、經濟、軍事實力都較強大的大唐王朝。文成公主成長于佛教底蘊深厚的城市,松贊干布向唐王朝迎娶文成公主,同文成公主一起去到吐蕃王朝的除了漢地的種子、知識、豐厚的妝奩外,還有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佛像和佛教文化。因松贊干布的大力支持,漢地佛像、佛經、佛寺形制及漢僧進入吐蕃,促使吐蕃有了佛教的萌芽。文成公主修建小昭寺供放佛像,并協助赤尊公主建造了大昭寺,將漢文佛典翻譯成藏文,佛教正式傳入了吐蕃。金城公主順著文成公主當年選擇的路線進入西藏。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帶去了大批工匠以及雜技、音樂書籍、工具,以及數萬匹繡花錦緞,延續了文成公主入藏的佳話,并且進一步密切了關系,進一步加深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康熙皇帝在西安明城墻內的西北方向修建廣仁寺。此寺廟是陜西省唯一的藏傳佛教寺,作為西北和康藏一帶大喇嘛進京路過陜西時的行宮,距今已有三百余年的歷史,也是全國唯一的綠度母主道場,文成公主也被稱作是“綠度母的化身”,和廣仁寺結下了不解之緣。
受到中原文化和其他鄰國藝術的影響,吐蕃時期的雕塑和繪畫藝術繁榮發展,壁畫內容也變得豐富多彩,一時間各大寺的墻壁幾乎都有許多精美的壁畫。其吸收外來藝術,并與當地藏族民間藝術相結合,有典型的犍陀羅藝術風格,也有明顯的敦煌唐代風格、中原雕刻風格、尼泊爾古代藝術風格,是西藏藝術發展史上的開放時期。
西藏的繪畫藝術以唐卡、寺院壁畫及經書插圖為代表。一些充滿內地色彩的圖案從內地傳入西藏。在西藏的唐卡、壁畫上均可發現以內地特色圖案、元素作為裝飾的印記。西藏的唐卡、壁畫通過這類絲織品間接受到內地繪畫和專為西藏寺院和上層人物織、繡、繪畫的唐卡藝術的影響,最終對西藏壁畫藝術產生影響。
西藏繪畫藝術歷史可追溯到史前時期,寺院壁畫藝術的起源和發展與佛教的傳入和發展同步。漢藏佛教之間交流頻繁,雙方相互學習、相互吸收。隨著時間的推移,漢藏佛教之間建立了緊密關系。漢文化在羅布林卡壁畫中的體現,表現出了中華文化就是在漢藏交流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形成的共同的燦爛而光輝的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的本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