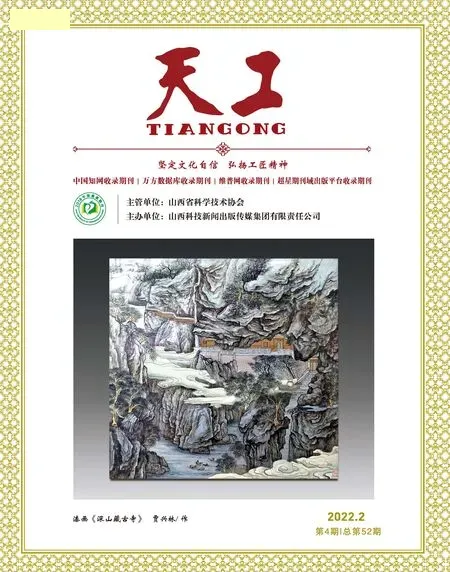黑龍江剪紙藝術風格的成因及現代表現形式
左 娜 王 澤 齊齊哈爾大學
在北國的黑龍江地區,遼闊的黑土地上,孕育出了獨具特色的黑龍江剪紙藝術。從古至今,從遠古的原始居民,到后來的鄂倫春族、赫哲族居民,再到近現代大批南方移民帶著家鄉的文化北遷,使這片土地上逐步形成了以海倫、方正、依安、綏棱各地為首的,以民間神話和薩滿宗教為主要題材的各類剪紙藝術。各地區的人們在這片熱土上所創造出的剪紙風格與其他地區迥然不同,獨特的自然地域環境加上特殊的民族因素讓黑龍江剪紙展現出不一樣的風采。
一、黑龍江剪紙風格的成因
黑龍江獨特的民俗成就了黑龍江地區獨特的剪紙藝術。剪紙來源于民間,所表現的內容更是民間民俗生活的寫照,有豐富的民間神話題材、樸實的民間生活題材,以少數民族的民族特色為題材及各類動物、植物題材。抽象的、夸張的、粗獷的造型風格是黑龍江地區擁有獨特民族民俗剪紙藝術的原因。
(一)當地少數民族創立了風格獨特的剪紙
在這片黑土地上生活了幾千年的滿族、蒙古族、鄂溫克族等少數民族是黑龍江剪紙藝術的開創者。在造紙技術傳入北方以前,當地居民雖與少量遷徙至此地的漢族有文化交融的機會,但畢竟少之又少,更多的是當地民族在白山黑水間形成的審美感悟。當地的少數民族也開創了各種剪紙藝術形式,這其中黑龍江省三江流域的漁獵民族赫哲族根據自身生活環境開創了前所未有的無紙剪紙——魚皮剪紙,游獵民族蒙古族以自身生活為題材創造了蒙古剪紙,鄂倫春族發明的樺皮剪紙和獸皮剪紙都在用材上體現著民族特色。有意思的是,鄂倫春族并沒有自己的文字,其剪紙中的圖案卻附帶了文字的功效,輔助人們傳遞信息、表達情感,遠超出圖案單純的寓意作用。少數民族根據自身的生活環境、民族風俗開創本民族的剪紙,為黑龍江剪紙藝術奠定了最原始的基礎。
(二)薩滿教對剪紙風格的影響
流傳千年的薩滿文化,源于祭祀的多神教宗教信仰。薩滿主題的剪紙作品風格區別于中原剪紙的豐富熱情,給人們傳遞更多的是神秘的氣氛。舊時黑龍江地區的剪紙作品中鮮有出現鋸齒紋等藝人們口中的“打毛”造型,而是簡單、直接地用繁復的鏤空進行對稱構圖,從而構造出詭異甚至扭曲的神怪形象,描述紛繁怪異的世界。人們的思想觀念中飽含著對神怪的敬仰與祈愿,相信通過剪紙的方式可以和神靈的世界相連接,從思想傾向上來看,人們對于薩滿主題剪紙的造型無疑是莊嚴且虔誠的,盡管造型手法略顯稚拙,但我們仍然能看到宗教所帶來的影響。
(三)民族民俗對剪紙風格的影響
宗教是民族民俗的重要方面,但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更深、更廣,是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活民俗剪紙。婚喪嫁娶,節令歲時,人們在生產之余用各類剪紙豐富美化自己的生活。剪紙藝術的產生與當地的風俗習慣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東北房屋面朝南,掛錢對聯門上粘。”過年之際家家戶戶都要在門前貼掛錢,掛錢歷史悠久,和鞭炮一樣具有驅趕年獸的作用。清朝時,掛錢技術逐漸成型,最具代表性的當數蘭西老藝人李一剪。過去,富裕人家掛起掛錢為了顯示家中富貴,而貧窮人家則是為了表達心中愿望,不單純為營造喜慶的氛圍,更是寄托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李一剪開創了東北掛錢的先河,打造了地區名片,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當地剪紙的盛行。其后的孫福生、顏憲武、梁義傳也都不同程度地發揚了蘭西的掛錢藝術。除此以外,結婚時張貼的喜花,端午節張貼在門窗上的五毒,都融合了民俗文化,共同影響著黑龍江剪紙。
(四)地域環境對剪紙風格的影響
北方地區雖受中原文化影響,但越往北方的黑龍江地區,受其影響越小,反而更多的是當地少數民族群體自身的探索。然而東北地區地廣人稀,少數民族人口較少,從人地關系上來講,人口密度直接影響人文環境密度,若是人口密度不高,那么自然地理環境無疑占據了主要影響優勢,從而奠定了黑龍江剪紙的整體風格——粗獷。剪紙是慢工細活,雖然有為了展現宗教色彩的繁復鏤空和對美好生活的祈愿,但相比中原地區剪紙,我們仍然能感受到黑龍江剪紙無論從選材上魚皮、樹皮的原始貼近自然,還是鏤空技法中的用煙“燙”,都是豪邁風格的體現。早期的東北剪紙受中原文化影響少,主題造型上十分古樸,低密度的鏤空使人物形象簡略卻流露著粗獷氣息,這無疑與人們生活的環境有著緊密聯系。
二、黑龍江剪紙審美風格的現代演變
在沒有筆的時代背景下,人們把剪出來的作品當作模板貼在布上繡,處理好的底稿再用煤油燈熏出外形,以達到傳播復制的效果。在材料技法上也由遠古時期的魚皮、樹皮作紙,到現在的形用紙筆畫,剪用剪刀刻。隨著時代發展、生產力水平的大幅提升,文人的審美意趣逐漸轉至剪紙藝術,這些都大大促進了剪紙工具、材料和具體風格紋樣的變革,技法上也逐漸豐富,燙、燒、熏、剪、手撕,甚至用煙頭去燙,極大地豐富了剪紙藝術的內涵。老一輩人過去用窗花、墻花、炕花、柵花、門花來美化自己的生活。在自給自足的經濟環境中,姑娘們給自己做嫁妝,為自己布置新房。過去,大多是勞動婦女們進行著藝術創作,創作題材也都更加樸素、貼近生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對民間藝術的保護和發展尤為看重,中國民協、剪紙協會相繼成立,剪紙藝術也逐漸變革,黑土地上的剪紙主題逐漸轉向描繪政治經濟發展,更多地反映人民群眾的工作和生活。如今,黑龍江剪紙藝術家依然秉承著原有的剪紙技藝,跟隨時代主題進行創作題材與技藝上的創新。
2009年,方正剪紙藝術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倪秀梅當選第二代方正剪紙文化傳承人。倪秀梅作為文化傳承人不僅傳承舊有的創作技藝,還與時俱進。作為黑龍江本土民間藝術家,其剪紙作品主題大多融入了黑龍江當地的民俗風情。其剪紙刀工十分精細且作品常常給人以震撼之感。倪秀梅有著自己的創作理念,她認為,創作剪紙分為兩部分:其一為從日常的積累中獲得靈感,從生活中取材,用藝術創作反映生活的本真,達到信手拈來、一氣呵成的技藝效果;其一為有構思的藝術創作,即先在紙上簡單地勾勒外形,再進行細化,由內部的細節一點點向外延伸著剪裁,從而完成整體的創作。倪秀梅的母親為山東人,又在黑龍江生活了幾十年,這使得深受母親創作技藝影響的倪秀梅的剪紙作品既有著中原地區漢族剪紙的精巧細膩,也有明顯的東北地區粗獷洗練的風格。其剪紙作品《稻花香》《雪精靈》都是漢族剪紙與東北剪紙融合的最好體現。東北剪紙從造型上直觀感受到的粗獷之感是作品呈現給我們的第一印象,若我們走近觀看,其作品中紋路繁復中暗含著規整,粗放中夾雜著細節。例如其《雪精靈》系列作品,無論是題材還是造型乍一看都是典型的黑龍江剪紙樣貌,可當我們仔細觀看其對雪精靈的身體造型和白雪的質感處理,都能隱約感受到中原剪紙的精細風格。同樣,2004年倪秀梅創作的《東北大豆香》系列剪紙作品,榮獲中國民間藝術最高獎“山花獎”金獎,2006年創作的《有喜了》系列作品獲得第三屆國際剪紙藝術博覽會金剪刀獎。這些作品的創作題材絕大多數都是以黑龍江黑土地、鄉村生活和秋收景象為主題的。其中的《東北大豆香》系列剪紙無疑是最為體現黑龍江剪紙特色的主題性剪紙,有《俺們東北那嘎達盛產大豆》《用石碾子磨出的豆汁兒可細發兒了》《買豆腐了》《咱東北的大豆可有名兒了》《俺們習慣在每年的二月二烀醬塊兒》《在四月初八、十六下醬,打醬缸可是個力氣活》《有小蔥蘸醬,這飯吃得可香了》等。
《東北大豆香》系列作品以東北農村地區家家戶戶都制作的黃豆大醬為主體,描繪了黑龍江農村地區吃大豆、制黃豆醬這一生產生活場景。從標題上我們也能感受到濃厚的東北氣息,作品對大豆的采摘、制作等一系列生產生活場景進行了描繪,對割大豆、采大豆所用的工具,磨黃豆的磨盤,買豆腐的推車以及燒煮豆漿所用的器具,做大醬的醬缸,吃大醬時的場景都做了活靈活現的情景再現,仿佛帶著我們走進了熱情洋溢的當地生活,具有極強的感染力。作品中的人物采用的是傳統的粗獷風格,其造型、人物動作以及表情全都做了夸張處理,對于生產所出現的磨盤、醬缸等工具也都洗練明快地用簡單幾刀剪出輪廓,對于作品的四周,作者都加以大豆穂進行畫面填充,構圖緊實不留空白,整體上給觀者以活躍明快的氣氛。
《北方風情》系列作品則是記錄了北方民俗生活的另一些場景。比如展現兒童游戲生活場景的《嘎拉哈耍起來》,展現大人生活場景的《舍飯不舍二人轉》《東鄰西舍抽煙帶》《養活孩子吊起來》《靰鞡草鞋腳上踹》《大火炕上養爺太》,當然也有同樣表現食物生產場景的《粘豆包凍起來》《大缸小壇漬酸菜》。倪秀梅的作品最大限度地表現了現代黑龍江農村地區人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絕對稱得上是黑龍江現代剪紙的典型代表。
中原藝術大多以熱情洋溢的氛圍為作品的主基調,而東北傳統剪紙大多是粗獷風格,并不能給人以熱情的感受,但倪秀梅做到了將兩者融合在一起,用洗練的造型手法豐富內容,使得作品整體洋溢著類似于節日般熱鬧的生活氣氛。傳統東北剪紙大多以畫面左右對稱、突出主題人物分布為主,并且大多數作品為宗教主題,能讓人們明顯地感受到畫面的主要人物與作品主題,而現代黑龍江剪紙畫面更加飽滿,方形的剪紙作品中更多地對空白地方進行作品主題的細節填充。
與方正剪紙一樣具有黑龍江地域剪紙特色的藝術家還有許多。齊齊哈爾市的戚玉恒老先生所傳承的崔氏剪紙藝術,活躍在當今時代。2021年新年之際,他所創作的牛年系列迎春作品在齊齊哈爾市博物館進行展覽。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72歲生日的作品《中華騰飛》、慶“八一”建軍節主題的作品《放飛和平》、展現軍民情深的作品《保衛祖國安寧》、展現喜迎豐收題材的作品《今年又是豐收年》,都是其傳承傳統技法與融合新時代主題的成果。當然,在現代用傳統技藝表現時代與生活主題的藝術家還有許多,比如蘭西縣傳承掛錢創作的董驥,其繪畫功底扎實,創作的掛錢剪紙作品風格熱烈、內容飽滿,在傳統掛錢的基礎上對內容進行著豐富。在綏化傳承海倫、方正剪紙藝術的劉卓,傳承薩滿剪紙的劉延山,以傳統的“嬤嬤人”為主要元素,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今天的黑土地進行著美好的書寫。每一位藝術家都緊隨著時代的步伐,不斷演化的剪紙藝術讓我們感受到黑龍江剪紙在新時代藝術體系中生生不息、與時俱進。回顧黑龍江剪紙藝術的成因,其宗教因素也在今天成了最為貼切、最能夠表現藝術緊隨時代,且最能夠聯系古今的一個方面。新興的剪紙藝術家們也在繼承著傳統,隨時代變革發揚著傳統。
三、結語
黑龍江的剪紙藝術生生不息,我們在今天能夠看到的融合了傳統技藝表現形式和傳統風格的藝術作品,無論是從題材還是造型手法上都能在今天的藝術作品中看到傳統黑龍江剪紙的影子。這無疑是區域性民俗宗教文化所帶來的延伸影響,也許早在黑龍江剪紙風格形成的過程中,就已經奠定了現代黑龍江剪紙的藝術基調。現代的藝術家傳承著傳統文化,用舊有的傳統元素塑造藝術,面對新時代的挑戰,表達藝術家內心對傳統、對生活的熱愛,表現手法是巧妙且奇妙的。仿佛穿越到遠古時期感受到巫術信仰與民俗文化對當時人們的影響,這不僅僅是一種古老的信仰和單純的民俗風情,也不僅局限于當代的藝術形式,而是形成了一種文化,一種黑龍江獨有的文化,不斷地吸引著藝術家用剪紙藝術塑造本土文化。現如今的黑龍江剪紙作品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內涵豐富且緊密聯系時代,不斷地創作出新的作品,讓我們明白剪紙藝術是文化的載體,它所承載的正是這片黑土地上幾千萬年來積累的文化藝術底蘊,它在不斷地調整自己,順應著時代的發展推陳出新,煥發著新時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