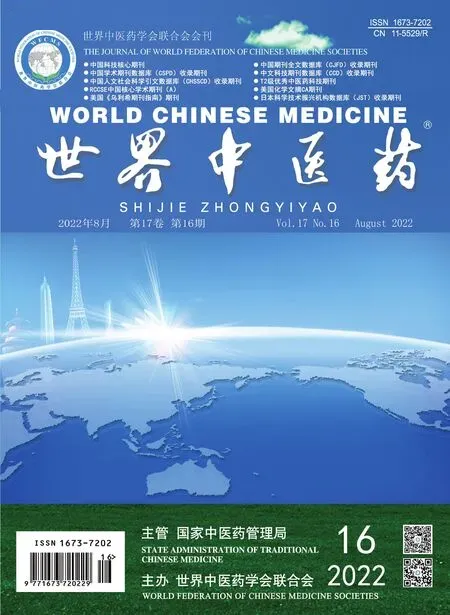針感量表的研究現狀及新量表的設計思路
閆 巖 張春紅
(1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天津,300381; 2 天津中醫藥大學,天津,301617; 3 國家中醫針灸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天津,300381)
“針感”,即進行針刺時的感受,是針刺臨床研究中可獲取的重要主觀信息。針刺的臨床療效不可否認,而針感往往是針刺發揮臨床效能的重要反映,將針刺治療時的主觀反饋與實驗室檢查或影像學檢查等客觀信息結合,能夠較完全反映人體在進行針刺時內外的交互作用。在針刺研究時加入對針感的要求,并完整、準確地記錄針感,不僅是對針刺預期效果的評價,同時也有利于學者對針刺作用機制的深入探討;完善對人體的探究,提高針刺治療的標準化和可行性,有助于臨床的推廣應用。
刺激量是針刺研究時需要重視的,但其大小常難以把控,針刺方式的不統一是關鍵所在。規范醫者的技法,以求醫患針感反饋的統一,擬達到效應器官變化的一致,這有助于科研工作的開展。針感評價量表是最有效的規范與評價手段,目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層出不窮。本文從探討針刺效應原理出發,結合現有量表的使用經驗,制定適用于現階段臨床研究的最佳量表,尋求更佳的針刺研究方案。
1 針感的物質基礎
針感與其臨床效能的關系歷來被中醫學者重視,不斷進行相關理論探討或臨床研究。從傳統中醫理論來看,“得氣”與“氣至”是醫者對療效的判斷,是綜合辨證診斷與治療之后的結論;而“針感”更具體,更可被描述,故現今也被廣大針灸從業者認為是針刺療效的體現[1]。
針感可分為針刺者感受和受刺者感受,針刺者可在得氣時感到針下沉緊,而受刺者則有酸、麻、脹等多種不同的感受,通常稱之為“他覺針感”與“自覺針感”[2];又有針刺雙方均有感覺的“顯性針感”,或僅針刺者有針感的“隱性針感”[3]。以往有關經絡實質研究多從神經生理學角度入手,認為針刺作用是基于“得氣”后外周感受器沖動傳入與中樞神經系統沖動傳出間的興奮不斷交互反饋的結果,強調得氣感與臟腑功能調節的一致[4-5]。而針刺治療正是加強了中樞與外周的聯絡,使神經系統功能得以正常發揮,“針感”則是此過程中可信的反映。近年神經影像學方法如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也被運用到得氣與臨床療效的研究中[6-7],不同性質的針感在腦區的反映確實存在差異,針刺得氣可引起不同腦區結構的激活或負激活效應,并參與針刺療效機制。但當前的fMRI研究內容相對單一,研究方法仍處于探索階段,且結果多為得氣反應于中樞層面的現象,亟須通過現象總結出得氣與中樞效應的本質聯系,揭示得氣針感的作用機制[8]。
現代西方學者對中醫理論掌握較少,認為針感是針刺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影響臨床療效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在思考針刺效果是否和患者的針刺感受具有相關性[9-10]。針感作為伴隨針刺必不可少的主觀化指標,具有一定研究價值,在現代針刺臨床研究中應被收集記錄。為了方便研究,提出針感的量化記錄,針感量表則是其專用工具,先后出現主觀針感量表(Subjective Acupuncture Sensation Scale,SASS)、馬薩諸塞州總醫院針感量表(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cupuncture Sensation Scale,MASS)、南安普敦針感問卷(Southampton Needle Sensation Questionnaire,SNSQ)等針感記錄量表,并參考一些生理指標、影像學指標等進行相關研究[11]。
2 針感量表特點
早期針感量表由疼痛量表改良而來,1989年Vincent等[13]進行的針感評價及量化研究,參考了疼痛評估專用McGill疼痛問卷(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MPQ),在資深針灸師協助下完成并應用于臨床測量。量表對每一分項進行從無感覺至感覺很強烈的4級不同主觀評價,得到結論:1)牽拉感、麻木感、沉重感是得氣時的針感;2)除此可伴有擴散感、放射感;3)應過濾掉強烈的穿刺感、痛感等進針時的感受。這也是針感記錄或針刺原理研究時應當注意的幾個方面。Park等[14]再次利用此量表進行針感評價,確認了針感的多維度性。試驗將患者針刺前的針感預期與針刺的實際針感作比較,發現實際的穿刺、刺痛感是小于預期的;且試驗中的安慰針刺組預期針感與實際針感則相似,這也說明假針刺是可作為安慰劑應用于臨床研究的。
SNSQ是綜合以上研究并結合專家意見發展而來的[15]。該量表著重于區分針刺時的痛感和實際效應針感,在制作量表時將疼痛相關針感取消,采用候選式而不是訪談式的針感詢問方式,也建議將視覺模擬測量引入測量中。
SASS首見于Kong等[16]對于不同針刺模式鎮痛效果的研究。量表包含刺痛、跳動、麻刺、熱、重、滿、麻木、酸、痛感共9項,在患者進行針刺后對每個針刺穴位進行測量,評分方式則是在10 cm長度標尺上由輕微到強烈標出自身感覺所處等級,并且同時對患者精神緊張程度進行評價。試驗結果也確認了針感的出現與針刺止痛效果間正相關,且麻木感、酸脹感是主要的針感。
MASS由SASS發展而來,是目前應用較廣的、較為成熟的針感量表[17]。表中針感項目被擴增至13個,并加入了針感擴散范圍測量,余項相似。此版量表也首先建議要在針刺前、中、后3次對針感進行測量;同時研究者也考慮到了針刺施術者的手下感覺是否應當納入針感觀測的范圍。此研究還引入了量表相關指標MASS指數對重要針感加權求得平均針感值。Yu等[18]將MASS翻譯成中文在臨床研究中實施,評價其信度效度,也證明其是一個有效的針感專用評價工具。近期臨床隨機對照試驗也將MASS引入其中[19-21],判定真針刺與安慰針、針感與臨床療效之間的關系[19-21]。
3 量表制定的注意事項
3.1 針感項目的確定 針感評價應利用專用量表,描述項目的確認應公認、準確全面且項目之間獨立互補。Vincent等[13]利用MPQ確認幾種主要及次要的針感,包括牽拉感、麻木感、沉重感、擴散感和放射感。MacPherson和Asghar[22]收集了國際上20位針灸專家對針感的認識,篩選總結主要項目,包括痛感、重滯感、麻木感、放射感、擴散感和麻刺感。郭崢嶸等[23]利用循證醫學手段對不同機體狀態(不同疾病)的人群針感進行匯總,發現患者出現的針感大多集中在脹、麻、傳導和酸等,常見復合針感依次為重痛麻感、酸痛麻感和重酸感等;而健康人針感出現頻次較高的為痛、酸、麻和重,常見復合得氣針感依次為脹酸感、重酸麻感和重麻感等。不同人群的針感頻次排列與關聯分析結果有較大差異。值得注意的是,臨床效應針感是必須區分出針刺破皮時或由于操作失誤引起的穿刺痛、刺痛等。
綜合以往研究可以發現,臨床針感項目雖然復雜,但存在幾個關鍵事項:1)相同主體所采集到的針感項目范圍是相對集中的;2)量表設計與詢問時應使患者從已有備選項目中選取最主要或次要針感,并進行相應量化評價;3)針感評價時應過濾掉強烈的穿刺感、痛感等進針時的感受;4)應認識到針感會因患者狀態、針刺穴位及針刺方式的變化而不同,且應考慮到針刺受試者對針感或混雜針感描述的不統一;5)針感量表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6)量表評分在進行數據分析時依然會發生偏倚。
3.2 針感評分規則 MASS引入的10 cm條帶視覺模擬評分法簡單易行,相對較客觀,且敏感,在患者進行標注后進行長度測量和數據分析。但使用前應向患者作詳細解釋,讓患者在直線上標出自己疼痛的相應位置;同時MASS提出的MASS指數仍是很好的嘗試,此算法將主要針感加權后平均得到描述針感強度的單一數值,使結果數值更有利于統計。
3.3 施針者手下針感的測量 受試者針感的出現和變化不應遺漏針感的激發者,“自覺針感”會與“他覺針感”聯合出現。傳統針刺操作手法是復雜的,手法的進行離不開醫患溝通,醫者會根據患者語言或體征的反饋調整針刺方式與手法。電針等新興針刺方式不能完全代表針刺作用的全部,多年來,該問題一直在被重復提出,進行著理論方面的探討,但缺少深入研究[24-25]。而不同進針方式(不同針感)對人體內在功能的影響確實存在差異[26]。Yin等[27]首次對“自覺針感”與“他覺針感”間相關性進行了研究,設立“他覺針感”量表,包括厚重感、糾纏感、堅硬感和空虛感4個項目,記錄針刺深度,結果顯示“自覺針感”與“他覺針感”有顯著相關性。“他覺針感”會根據不同針刺方式發生變化,且當針刺深度加深時,患者針感也會加強,體現出醫者為針刺效應發起者。
3.4 針感的測量時點 針感的測量應有3個時點,即手法操作得氣前、患者得氣時和留針過程中。普遍認可患者在得氣時和留針過程中應記錄針感,針刺的臨床效應也是在這時體現的。但針刺行為在進行時,術者在使患者自覺效應針感出現的過程中是需要時間的,此段過程受試者也會產生復雜的、不同于得氣的針感,此類感覺的記錄也可為針感產生及其效應的研究提供線索。
3.5 基本信息的記錄 量表設計應加入對研究對象疾病及針刺穴位的記錄。臨床針刺研究具有目的性,體現在針刺選穴或針刺方式的不同上。因此,在分析研究結果時,應考慮到單一量表的普適性與不同穴位、手法特異性等引出針感變化的重要元素之間的關系[28]。針感量表作為工具僅是為了提取針感信息,承擔過多任務反使其復雜化,故須明確研究目的和方法,必要時也應對量表的細節進行調整。
4 針刺量表的應用與思考
綜上所述,對針感量表的應用建議如下:1)試驗為包含假針刺的隨機對照試驗;2)應多用于病理狀態下療效機制的研究;3)針刺方式為手針針刺;4)應用于特殊針刺方法的記錄及臨床教學。
針感,是現代針灸研究的新名詞,是從傳統“得氣”“氣至”的概念中分離出來的[1,29]。《靈樞·九針十二原》載:“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云,明乎若見蒼天。”其中“氣至”是對效果的判斷,指人體經絡被刺激后氣血變化、身體趨向健康的狀態,是通過醫者對整體的認知和豐富的臨床經驗體察到的[30]。而“得氣”的概念更廣,針刺過程是為了“調氣”,施手法以求氣至,留針以調和氣血,至出針時不同的操作,最終為達得氣、氣調的狀態[31]。《靈樞·小針解》有云:“空中之機清凈以微者,針以得氣,密意守氣勿失也。”可見“得氣”是針刺治療的最終目的,得氣的含義不等于“氣至”或“針感”,而是包含了針感與氣至二者在內的過程。現今的“針感”研究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針感量表的設計初衷是服務于針刺原理研究,而現今嚴謹的研究設計思路為大樣本的對照試驗,其研究對象應有一致的身體狀態、癥狀或體征。針刺研究的臨床效能及針刺對人體病理生理狀態下的作用更應受到重視,而不應僅局限于健康人群,如此才能體現針法對疾病的特異性,有利于后續研究的開展。在針刺臨床研究時,需要進行多次針刺行為,而非單次針刺,故有無針刺經歷對研究來說也非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先前的針刺經歷并不會對接下來針刺的感受產生影響[14,32]。而且無針刺經驗時會對刺入肌膚這一操作產生不良的主觀認識,這種視覺的、非真實的主觀感受會影響人們選擇針刺治療[33]。況且針刺組穴研究及針刺對疾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針刺客體為病理狀態基礎上的,此時的主要矛盾應為針刺作用與病理狀態間的矛盾,對于針感的記錄的目的應轉向為其與治療效果的比較,由此也可淡化對針刺客體的要求。
針刺量表同時可為臨床提供一種可量化和對針刺效應可重復的手段。通過對自覺與他覺針感的量化規定,形成一種針刺方法刺激量的標準,可使不同針刺者操作統一,使干預方法統一,并有利于針刺方法的教學、推廣及傳播。作為量化指標,針感量化可與其他可視化指標相結合,如fMRI、正電子發射斷層成像(Positi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技術等,以便探尋針刺在中樞或外周的作用原理。
現今國際上普遍進行針刺研究方法大多依靠電針,這主要是由于手針或針刺手法具有復雜的操作性及醫患之間眾多不可控因素,但如此卻和中醫傳統針刺的理念不同,很多指導性的思想如候氣、補瀉等被無形中舍棄,而系統全面的針刺研究對這一方面也是需要顧及的。針感量表相應評價方法的出現恰恰能很好地規避這一點,進一步將針刺研究系統化,使之有跡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