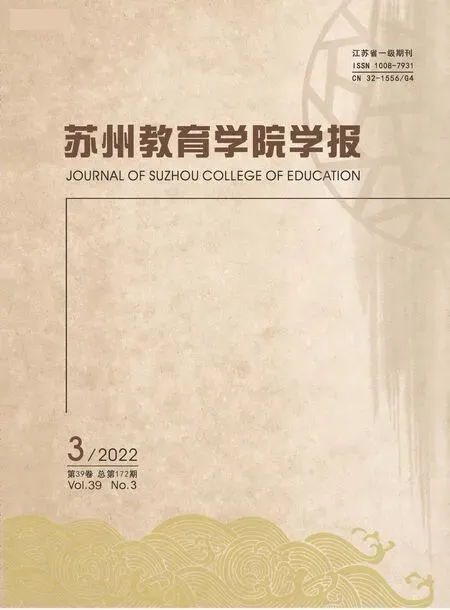為現(xiàn)實(shí)尋找語(yǔ)言
——小海詩(shī)歌的啟示意義
宋寶偉
(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提到詩(shī)人小海,人們很自然會(huì)想起他在20 世紀(jì)80 年代中期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成就,也會(huì)“順理成章”地自動(dòng)將他歸入到“他們”詩(shī)派,并在這一視角下觀照、評(píng)析小海的詩(shī)歌成就。“第三代”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大潮早已湮滅在“靜水流深”的詩(shī)歌汪洋之中,重新檢視“第三代”詩(shī)歌“遺產(chǎn)”則會(huì)發(fā)現(xiàn),盡管那代人經(jīng)歷了20 世紀(jì)90 年代的“沉寂”和新世紀(jì)的“喧囂”,但還有許多詩(shī)人依然堅(jiān)持自己的詩(shī)歌理念和詩(shī)歌寫作,持續(xù)不斷地為詩(shī)壇輸送詩(shī)歌文本,保持著強(qiáng)勁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活力,而小海就是這樣一位詩(shī)人。文學(xué)評(píng)論最忌“先入為主”,在被一種先驗(yàn)的思維控制之后,人們往往會(huì)產(chǎn)生很多偏見(jiàn)與誤讀,也就很難辨清事物的真相。我們只有將詩(shī)人小海從“第三代”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背景中“抽離”,使其遠(yuǎn)離那些曾經(jīng)屬于詩(shī)歌社團(tuán)的詩(shī)學(xué)理念的先驗(yàn)視角,還原為詩(shī)人個(gè)體的身份,小海詩(shī)歌寫作的獨(dú)特性與創(chuàng)造性才能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lái),才能準(zhǔn)確地把握他在詩(shī)歌的日常性寫作、原鄉(xiāng)情結(jié)以及詩(shī)歌語(yǔ)言的本真追求等方面的特征。
一、日常性寫作的詩(shī)意堅(jiān)守
日常性寫作是當(dāng)代詩(shī)歌最大的貢獻(xiàn)和成就之一,它使詩(shī)歌終于放下自己的身段“俯就”生活的同時(shí),更讓詩(shī)歌找到了“自我”,擺正了詩(shī)歌與日常生活的關(guān)系,置身于生存的現(xiàn)場(chǎng),建構(gòu)日常化的詩(shī)歌美學(xué)。從日常生活的場(chǎng)景和現(xiàn)場(chǎng)進(jìn)入到人的感受和感覺(jué)之中,完成對(duì)生活的詩(shī)意化書(shū)寫,在生活的縫隙和褶皺中讓詩(shī)意澄明,并且從某些生活的先驗(yàn)和意義中逃離出來(lái),獲得一種本真的體驗(yàn)和領(lǐng)悟。小海詩(shī)歌從“出道”之日起,就顯現(xiàn)出日常主義詩(shī)歌的特征,盡管當(dāng)時(shí)正是“朦朧詩(shī)”象征詩(shī)學(xué)方興未艾之際。“一場(chǎng)暴雨/海邊小城的色彩/洗得鮮亮/孩子在奔跑/孩子的笑聲是永久的檸檬黃//一陣風(fēng)來(lái)/所有的木房子都扁了/孩子們又矮又胖/——一個(gè)瘦高個(gè)兒漫畫(huà)家/悄無(wú)聲息地走過(guò)去了”(《K 小城》)[1]11,這首詩(shī)頗有“印象派”繪畫(huà)的氣質(zhì),詩(shī)歌中呈現(xiàn)的就是詩(shī)人看見(jiàn)的“自然”的樣子,色調(diào)、構(gòu)圖、動(dòng)靜關(guān)系同時(shí)存在,完美地復(fù)現(xiàn)了瞬間視覺(jué)“印象”。詩(shī)歌沒(méi)有作那個(gè)時(shí)代常見(jiàn)的“價(jià)值判斷”,也不需要將詩(shī)歌內(nèi)涵“升華”,一切都是如此自然、平淡。“下午,你搭車/來(lái)我這兒/你跟我說(shuō)過(guò)的話可不要忘記/是或者不是/這樣的天氣承蒙你來(lái)看我//你看我變得花言巧語(yǔ)/善于幻想而終歸現(xiàn)實(shí)/看見(jiàn)你,我打心眼里高興/你沒(méi)變,還是老樣兒”(《搭車》)[1]19,一次老朋友之間的相會(huì),沒(méi)有興奮,沒(méi)有激動(dòng),然而平淡的敘述中卻也深藏著朋友情誼。口語(yǔ)化的敘述毫無(wú)滯澀之感,詩(shī)歌語(yǔ)言與日常口語(yǔ)同質(zhì)同構(gòu),呈現(xiàn)出語(yǔ)言的天然性和原生態(tài)。在小海的詩(shī)歌中,經(jīng)常能發(fā)現(xiàn)這樣簡(jiǎn)約的語(yǔ)言形成的“白描”的藝術(shù)效果,不用層疊累加繁復(fù)的意象去營(yíng)造朦朧、晦澀的“意境”,而完全依靠日常中的細(xì)觀靜察提煉生活的詩(shī)意,語(yǔ)言簡(jiǎn)約而含蓄,早已超越了20 世紀(jì)80 年代初期的意象化語(yǔ)言策略,對(duì)日常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詩(shī)意的轉(zhuǎn)化和處理。筆者認(rèn)為當(dāng)一個(gè)詩(shī)人注目日常、取材日常時(shí),他必須有不同于其他詩(shī)人的基因,唯有這樣,才能確保詩(shī)意的流動(dòng)。這不一樣的“基因”表現(xiàn)在小海的身上也許就是對(duì)生活的超級(jí)敏感,以及透明、簡(jiǎn)約并富有熱度的表達(dá)。“這風(fēng)多么宜人/像一件爽身的新衣/我不知它來(lái)自何方/它聲音微弱/或者干脆一聲不響//我愛(ài)這風(fēng)/同時(shí)我還呼吸到它的氣息/這陣風(fēng)剛剛長(zhǎng)成/它越過(guò)欄桿/在草坪上/一遍又一遍梳理自己的羽毛/我試探著把窗關(guān)上/在它離去之前/我無(wú)法進(jìn)入睡眠/這樣的時(shí)光/我純潔的身體/就像剛剛灑落的花瓣/被風(fēng)吹起/而不知道怎么躲避災(zāi)難”(《風(fēng)》)[1]31。日常化寫作看似簡(jiǎn)單,其實(shí)同樣需要詩(shī)人豐富的想象力作為支撐,詩(shī)歌中這種超級(jí)細(xì)微的身體感覺(jué),只有經(jīng)過(guò)詩(shī)人的敏銳的感知和近乎冷靜而理性的表達(dá)才能在讀者這里形成感同身受的認(rèn)知,而這理性纏繞的依舊是人的感性與情愫。“現(xiàn)在我坐在窗前/很多事物顯現(xiàn)在我面前/這往往是我忽略的生活/它們溫靜地出現(xiàn)/又不至于馬上消失/在我的窗前/我注視它們很久/毫不驚慌/這是生活值得炫耀的部分/它們不鳴叫/但我聽(tīng)到它們嘩嘩流動(dòng)的喧鬧/這聲音也能安撫我/我熟悉它/像熟悉睡夢(mèng)中妻子的聲息/這可不是虛假的事物/誘惑我,穿透我/直到我收攏翅膀/落在它們身上”(《窗前》)[1]28。對(duì)生活的一切事物的理解并坦然而熱情地接納,哪怕是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生活,都是生命中真實(shí)的組成部分,唯有對(duì)生活充滿真意并誠(chéng)摯擁抱的人,才會(huì)有如此細(xì)膩的內(nèi)心感受。詩(shī)歌中有強(qiáng)烈的畫(huà)面感,盡管是口語(yǔ)化的語(yǔ)言,但是詩(shī)人的言說(shuō)顯現(xiàn)出一種控制力,使得靜謐之中的“玄想”自然而真切。
從先鋒寫作轉(zhuǎn)向日常性寫作,詩(shī)歌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存在方式,重新建構(gòu)了語(yǔ)言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聯(lián),疏通了語(yǔ)言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阻礙,這是當(dāng)代詩(shī)歌帶有革命性的“新發(fā)現(xiàn)”。日常主義詩(shī)歌不再“執(zhí)著”地探詢抽象、絕對(duì)的“在”,而是打量生存、常識(shí)的事物的“此在”,回到凡俗、瑣屑、自然的本真狀態(tài),恪守當(dāng)下,執(zhí)守日常。但小海詩(shī)歌中的日常性并非只停留在生活的表層,而是在日常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思考,這種不可復(fù)制的完全個(gè)人化的生命感知,也許這就是小海詩(shī)歌與當(dāng)下普泛的日常性寫作的最大區(qū)別。“黃昏時(shí)分/靜默得如同處子/所有的光都追逐你/讓你無(wú)處藏身/這一刻的溫暖/訴說(shuō)了你一生要碰上的事情/但現(xiàn)在想起誰(shuí)/都不能記起/熟悉的面孔都陰暗如灰/幾十年以后/如果還能重復(fù)同樣的光景/既不喧嘩也不溫柔”(《黃昏》)[1]26。詩(shī)歌中有一種生命的“達(dá)觀”,相見(jiàn)不喜,分離不悲,頗有人生通透的境界。又如詩(shī)歌與事物之間的關(guān)系一樣,不可以為了“感情”而肆意宣泄,不能有超越生存狀態(tài)所應(yīng)該有的感情狀態(tài),二者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是既不喧嘩也不溫柔的,這才是當(dāng)代詩(shī)歌必須追求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和語(yǔ)言境界。“在一個(gè)早晨/我讀到你的詩(shī)/我想你現(xiàn)在正走回家/走過(guò)一片木柵欄/推開(kāi)花叢//你寧?kù)o的家里沒(méi)有外人/你妻子一個(gè)人坐在窗前/此刻她已放下手上的活計(jì)/是聽(tīng)到你的腳步聲/還是在回想那愛(ài)戀的日子//那扇門早已讓風(fēng)吹開(kāi)/窗戶一塵不染/詩(shī)人站在門外//這情景讓我熱淚盈眶/我想看清詩(shī)人的面容/可詩(shī)人此刻已經(jīng)進(jìn)門/可詩(shī)人此刻已經(jīng)把門關(guān)上”(《讀詩(shī)》)[2]208-209。這是詩(shī)人小海想象著另一位詩(shī)人常態(tài)化的家庭生活,平凡、普通卻充滿溫馨和感動(dòng),這首詩(shī)歌的力量在于表現(xiàn)了瞬間生活的真實(shí)。誠(chéng)如耿占春先生所言,詩(shī)是追尋個(gè)人生活中意義的瞬間閃爍的一種方式。[3]小海在20 世紀(jì)80 年代中期的詩(shī)歌已經(jīng)準(zhǔn)確地調(diào)整了詩(shī)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在平凡的生活中發(fā)現(xiàn)詩(shī)意,而且并沒(méi)有因?yàn)槿鄙倬嚯x感而流于平庸瑣碎。同時(shí)也沒(méi)有走入現(xiàn)代主義的陰郁、晦暗,更沒(méi)有走向后現(xiàn)代主義的喧囂、癲狂,而是自覺(jué)地追尋與開(kāi)掘日常生活的神性,從這個(gè)意義來(lái)說(shuō),小海的詩(shī)歌對(duì)當(dāng)下的日常性寫作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當(dāng)下日常性寫作確乎存在一些問(wèn)題,譬如,日常主義詩(shī)歌多數(shù)呈現(xiàn)為一種對(duì)生活現(xiàn)象的簡(jiǎn)單描摹,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盡管也不乏詩(shī)意,但總是缺少詩(shī)歌的蘊(yùn)藉與回味。日常性寫作極易陷入一種感官的破碎性的泥淖中,詩(shī)歌語(yǔ)言對(duì)生活經(jīng)驗(yàn)的梳理也往往走向混亂,甚至低俗,這是當(dāng)下日常化寫作面臨的困境。“他們常用隨意性言語(yǔ)來(lái)表達(dá)他們對(duì)話語(yǔ)權(quán)的強(qiáng)烈關(guān)注,并以此回避自身缺乏基本訓(xùn)練的學(xué)術(shù)漏洞,而表面貌似激進(jìn)的態(tài)度則對(duì)涉世不深者具有極強(qiáng)的誘惑性。”[4]有些日常性寫作盡管滿足了市民趣味的需要,對(duì)俗世生活也有很深的介入感,但因?yàn)閷?duì)口語(yǔ)缺少有力的控制,語(yǔ)言泛濫恣肆,趣味低俗,使得詩(shī)歌文本缺少了使人“再讀”的沖動(dòng),詩(shī)歌成為了“一次性”的消費(fèi)品。當(dāng)下詩(shī)歌雖然能在細(xì)小瑣事上翻檢“詩(shī)意”,但是很少能做到將生活的本真、自由的詩(shī)意釋放出來(lái),仍然存在著某種外在的遮蔽,譬如,詩(shī)學(xué)理念、社團(tuán)意志、語(yǔ)言暴力等。“日常經(jīng)驗(yàn)向意義體驗(yàn)的轉(zhuǎn)化是一首詩(shī)的誕生之地。或許還更進(jìn)一步,某些詩(shī)歌還能夠在日常經(jīng)驗(yàn)的表達(dá)中呈現(xiàn)出某種神秘經(jīng)驗(yàn)或異質(zhì)經(jīng)驗(yàn)的可能性”[3]。如果一首詩(shī)只是單向度地呈現(xiàn)生活的原生性而缺少提升表象的意識(shí)和能力,那么這首詩(shī)只會(huì)流于平庸、乏味。而小海的詩(shī)歌表面看來(lái)是素樸的、不事張揚(yáng)的,但是詩(shī)歌的內(nèi)部卻蘊(yùn)藏著詩(shī)人對(duì)事物的思考,對(duì)某種“神秘”的追尋,同時(shí)也充溢著對(duì)生命的敬畏與憧憬。“今天,當(dāng)我見(jiàn)到有人用腳尺量這塊地/我有個(gè)預(yù)感/就像風(fēng)雨之夜向我開(kāi)啟的大門/我確信,在這附近/還沒(méi)有誰(shuí)有這樣的一雙大腳/而且,在這個(gè)季節(jié)/匆匆穿過(guò)這不成形的荒蕪的坡地/這是只有我才能感知到的/一只神奇的大腳/而不是慣常/我一早起來(lái),僅僅收獲它的薄霧”(《勸喻》)[2]57。詩(shī)人從“一雙腳印”那里得到了某種“啟示”,這樣“跳脫”事物表面的背后隱匿著“形上”的詩(shī)意思考,這在當(dāng)下很多日常性寫作中是少見(jiàn)的。小海的日常性寫作充溢著詩(shī)與思之美。
二、原鄉(xiāng)情結(jié)與生命意識(shí)的個(gè)性表達(dá)
許多小說(shuō)家都有自己的“文學(xué)的故鄉(xiāng)”,如美國(guó)福格納的“杰弗遜小鎮(zhèn)”、莫言的“高密東北鄉(xiāng)”、賈平凹的“商州鄉(xiāng)村”、蘇童的“楓楊樹(shù)鄉(xiāng)村”、劉震云的“延津世界”,等等。詩(shī)人和小說(shuō)家一樣,也會(huì)創(chuàng)造出屬于自己的“標(biāo)簽化”的文學(xué)世界,云南之于于堅(jiān)、雷平陽(yáng),平墩湖之于江非,小海的詩(shī)歌中也有屬于自己的“家鄉(xiāng)”——海安。可以說(shuō),小海的詩(shī)歌里有濃濃的原鄉(xiāng)情結(jié),這是他詩(shī)歌中非常鮮明的特征,是其詩(shī)歌“母題”之一。他曾這樣談道:“早年傳統(tǒng)鄉(xiāng)村生活的簡(jiǎn)單、閉塞、貧瘠、粗糙,剔除了其中生存狀況的艱難、終年勞苦的艱辛磨礪,還有就是自然的生活、古老的價(jià)值對(duì)我心靈的滋養(yǎng),也培育了人性中的溫潤(rùn)、柔和的部分,未來(lái)的寫作依然可以從之前人生啟示錄的序篇中汲取力量,是個(gè)人精神成長(zhǎng)史上的一份厚重禮物。”[5]與家鄉(xiāng)相關(guān)的人、事、景、物成為他詩(shī)歌的不變的“主題”。“五歲的時(shí)候/父親帶我去集市/他指給我一條大河/我第一次認(rèn)識(shí)了 北凌河/船頭上站著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十五歲以后/我經(jīng)常坐在北凌河邊/河水依然沒(méi)有變樣//現(xiàn)在我三十一歲了/那河上/鳥(niǎo)仍在飛/草仍在岸邊出生、枯滅/塵埃飄落在河水里/像那船上的孩子/只是河水依然沒(méi)有改變//我必將一年比一年衰老/不變的只是河水/鳥(niǎo)仍在飛/草仍在生長(zhǎng)/我愛(ài)的人/會(huì)和我一樣老去//失去的僅僅是一些白晝、黑夜/永遠(yuǎn)不變的是那條流動(dòng)的大河”(《北凌河》)[2]27-28。小海的詩(shī)歌總是能帶給讀者很多感受,盡管時(shí)間在飛速地流逝,每個(gè)人都變了模樣,但是家鄉(xiāng)的那條河流卻依然如故。這其中既有對(duì)生命流逝的某種“喟嘆”,更多的是對(duì)家鄉(xiāng)深深的依戀。小海詩(shī)歌中這種情感的抒發(fā)絕不同于浪漫主義詩(shī)歌的浮泛與濫情,而是“智性”地傳達(dá)出對(duì)時(shí)間的思考和對(duì)家鄉(xiāng)“無(wú)言”的熱愛(ài)。如果說(shuō)《北凌河》是小海對(duì)家鄉(xiāng)的“外向觀察”的情感流露,那么《田園》則顯示出詩(shī)人對(duì)故鄉(xiāng)情感表達(dá)的內(nèi)在與深沉,“在我勞動(dòng)的地方/我對(duì)每棵莊稼/都斤斤計(jì)較/人們看見(jiàn)我/在自己的田園里/勞動(dòng),直到天黑/太陽(yáng)甚至招呼也不打/黑暗早把它嚇壞了/但我,在這黑暗中還能辨清東西/因?yàn)樵谖业奶锏?我習(xí)慣天黑后/再堅(jiān)持一會(huì)兒/然后,沿著看不見(jiàn)的小徑/回家”[2]23。詩(shī)人對(duì)家鄉(xiāng)的親近是通過(guò)時(shí)間的“拖延”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并滲透出深沉的情感,猶如孩子對(duì)父母的依戀一樣。《田園》有一種樸素之美,語(yǔ)言自然順暢恰如呼吸一樣,這是詩(shī)歌在語(yǔ)言方面的本體性的自覺(jué)意識(shí)的體現(xiàn)。“晨光把街道變成凜冽荒涼的運(yùn)河//清冽的氣流漫過(guò)乳頭/醉漢的懷里摟滿空酒瓶/腦袋像一坨生鐵疙瘩//岸上的燈光雪花般打著旋/像無(wú)形的針刺/狗去咬豬/棍子打狗/火燒著棍子/街上面對(duì)面/道別著的鄉(xiāng)村公共汽車/人造的春天,地圖上的郵差/轉(zhuǎn)過(guò)街角,走入寓所/成千的煙囪開(kāi)始呼吸”(《故鄉(xiāng),二月早春》)[1]54。相比那些需要抒發(fā)激情以喚起讀者情感的詩(shī)歌來(lái)說(shuō),這首詩(shī)更接近于“新寫實(shí)”風(fēng)格,不動(dòng)聲色,也很少作“價(jià)值”判斷,只是如實(shí)地描繪故鄉(xiāng)生活的場(chǎng)景,而這種如實(shí)的表達(dá),很大程度緣于小海對(duì)“真實(shí)”的追求。詩(shī)歌僅僅圍繞家鄉(xiāng)“早春二月”的清冷,在清晨冷冽的氛圍中平靜地將目之所及的現(xiàn)實(shí)“客觀”地呈現(xiàn)出來(lái)。但是,在這略顯寒冷的清晨里卻彌散著詩(shī)人對(duì)家鄉(xiāng)的情感認(rèn)同,這不同于底層寫作視角,無(wú)所謂同情,無(wú)所謂批判,它只是故鄉(xiāng)生活的某一瞬間的真實(shí)再現(xiàn)。
小海的詩(shī)歌呈現(xiàn)出一種生命與語(yǔ)言的同構(gòu)狀態(tài),既不是對(duì)生命本質(zhì)作提升式的“贊嘆”,使之成為某種抽象的理念,也不作貶抑式的批判,讓人產(chǎn)生悲涼與憤懣之感,而是在語(yǔ)感的流動(dòng)之中構(gòu)造出一種智性的空間,將對(duì)生命的理解與感悟彌散在這空間中。“黃昏,疲憊的戀人返回村子/牛還在公路上,小心的莊稼漢牽回棚圈//黑暗中的牛郎卸下軛頭/終于和白天隱匿的紡織女相見(jiàn)//藍(lán)色畫(huà)境里的公雞跳出圍墻/去召喚一位夜晚的甜蜜伙伴//不馴服的羊抵觸著老實(shí)人的腰/泥潭里的鵝化作黑身體的引路人”(《黃昏之后》)[2]215,從詩(shī)歌的結(jié)構(gòu)來(lái)看,這是一組黃昏中的鄉(xiāng)村各種常見(jiàn)事物的組合情景,但事物彼此之間并不構(gòu)成一種“升階”的關(guān)系,而是一種“蒙太奇”般的平行關(guān)系。每一種事物都帶有很強(qiáng)的動(dòng)感,并且賦予其某種未知與神秘,契合人在黑暗之中的隱秘的內(nèi)在精神的“真實(shí)”。盡管每一種事物都是獨(dú)立的,但每一個(gè)體的生命卻是有機(jī)的,事物之間并沒(méi)有因?yàn)椤蔼?dú)立”而失去天然的呼應(yīng)關(guān)系,這就是詩(shī)歌《黃昏之后》帶給讀者的智性思考。“雨后的大街/車行道開(kāi)始泛白/快要干了/像一條新鮮的海帶/平攤著/魚(yú)腥氣/外加汽車輪胎上的泥巴/可憐的香樟/像一排病婦/立在路邊//天氣就要轉(zhuǎn)好/我的鄰居也將匯入樓下/匆匆上班的人流/那從前農(nóng)藥廠的工人/而今中外合資/保健品企業(yè)的員工”(《鄰居》)[2]76,詩(shī)歌描寫的是一位普通的“鄰居”,他(她)的身份從國(guó)內(nèi)企業(yè)“工人”變成中外合資企業(yè)的“員工”,這種身份的轉(zhuǎn)化在當(dāng)下似乎早已司空見(jiàn)慣,并不能帶給讀者太多的感受。但是詩(shī)歌的全部信息并非這樣簡(jiǎn)單,而是凝聚在詩(shī)歌的前部,也就是用一種“象征”的手法寫出“鄰居”此時(shí)的生命狀態(tài)——海帶、魚(yú)腥氣、泥巴、病婦,這些語(yǔ)匯無(wú)不暗示著一種讓人深感悲哀的生命。詩(shī)人用前后看似沒(méi)有關(guān)聯(lián)性的兩部分形成一種暗示關(guān)系,但并非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物”與“人”的一一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而是一種整體性的暗示,是“多”對(duì)“一”的關(guān)系。整首詩(shī)呈現(xiàn)為一種簡(jiǎn)單、平實(shí)的風(fēng)格,前后兩部分都是在陳述事實(shí),這種專屬于詩(shī)人小海的“私設(shè)象征”里潛藏著對(duì)個(gè)體生命的體驗(yàn)和感悟,客觀敘述中充滿著同情和悲憫。
我們知道,詩(shī)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來(lái)源于世界賦予他心靈的無(wú)窮奧妙。小海的詩(shī)歌總體來(lái)說(shuō),是深沉的,而非明快的,也許這是由詩(shī)人的氣質(zhì)決定的。正是由于詩(shī)人的敏感和內(nèi)心的激情,以及不事張揚(yáng)的性格,小海的詩(shī)歌總是呈現(xiàn)出一種“壓抑”的力量,其情感的內(nèi)核與語(yǔ)言的外殼之間的張力也處于一種平衡狀態(tài),雖然詩(shī)歌追求一種生命與語(yǔ)言的同構(gòu)性,但是因?yàn)樘N(yùn)含著對(duì)生命的深刻領(lǐng)悟,往往顯現(xiàn)出一種情緒低沉和智性深邃的復(fù)雜美感:“螢火蟲(chóng)/撒滿了河面/縱橫、壯觀/像打開(kāi)了桎梏的囚犯/找到了身體的語(yǔ)言/也像令我們心酸的母愛(ài)/一閃、一滅、一閃、一滅/電擊著我們?yōu)l死的心臟//遠(yuǎn)離了故鄉(xiāng)冰涼的水井/就像口對(duì)口的方言/準(zhǔn)備熄滅//哦,這溫柔而苦難的心……”(《螢火蟲(chóng)》)[2]102。從詩(shī)歌的意味來(lái)看,現(xiàn)代詩(shī)就是一種對(duì)生存的領(lǐng)悟,這種領(lǐng)悟不僅有對(duì)已知事物的理解把握,還有對(duì)未知事物的預(yù)見(jiàn),甚至是焦慮。忽明忽暗的螢火蟲(chóng)隱喻了詩(shī)人對(duì)家鄉(xiāng)和親人的懷念,“一閃、一滅”之間是無(wú)盡的感傷和深深的憂慮。當(dāng)“還鄉(xiāng)”的“通行證”——方言——慢慢被忘卻乃至消亡之時(shí),詩(shī)人“這溫柔而苦難的心”將如何安放?原鄉(xiāng)情結(jié)與生命意識(shí)是小海詩(shī)歌中兩個(gè)重要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原鄉(xiāng)”意味著其詩(shī)歌不是來(lái)自“烏有”,而生命意識(shí)則顯示出詩(shī)歌沒(méi)有導(dǎo)向虛空。換句話說(shuō),小海詩(shī)歌有堅(jiān)實(shí)的“此岸”,也有可以引渡靈魂的彼岸。與虛無(wú)對(duì)抗,不僅體現(xiàn)著小海詩(shī)歌的品質(zhì),更是考驗(yàn)著一個(gè)詩(shī)人的情懷和洞察生命的深度,以及穿透生活本質(zhì)的力量。
三、口語(yǔ)化與戲劇化:語(yǔ)言的持續(xù)探索
詩(shī)歌的生命力不僅取決于它對(duì)這個(gè)世界的態(tài)度,即對(duì)人的生命(包括人性)探索的深度和廣度,而且還取決于它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傳達(dá)程度,而后者意味著詩(shī)人對(duì)語(yǔ)言的掌控能力,即能否準(zhǔn)確地表達(dá)出自己對(duì)事物本真的理解和觀照。小海及那一代人的詩(shī)歌在20 世紀(jì)80 年代最大的意義就在于率先進(jìn)行了語(yǔ)言變革的探索,為人的此在生存狀態(tài)找到契合的語(yǔ)言表達(dá)方式,更確切地說(shuō),就是語(yǔ)言與此在的同質(zhì)同構(gòu)。此時(shí)的語(yǔ)言絕不是事物外在的附屬和工具,而是擁有本體地位和意義的。布朗肖在《文學(xué)空間》一書(shū)中提到,詩(shī)歌的話語(yǔ)不再是詩(shī)人的話語(yǔ),此時(shí)詩(shī)人是沉默的,只有話語(yǔ)在“自言自語(yǔ)”,語(yǔ)言成為一種本質(zhì)的東西。[6]布朗肖的觀點(diǎn)至少傳達(dá)出這樣的信息,就是詩(shī)歌寫作要避免詩(shī)人像浪漫主義那樣過(guò)度地操控語(yǔ)言,語(yǔ)言應(yīng)該是一種自動(dòng)的呈現(xiàn),這樣才能真正達(dá)到與此在生活的同質(zhì)同構(gòu),如《自我的現(xiàn)身》一詩(shī):
我看見(jiàn)田野里一把被遺忘的工具
為了能夠找到我
我走向田野
這是一個(gè)發(fā)明事物極限而組成的黃昏
填空那么寧?kù)o
為了再次找到
那觸怒土地后
尚未分類的軀體:工具
那把銹蝕的鐵鍬
緊咬著一條細(xì)窄的田埂
正如我目前所見(jiàn)的最佳方式
就是禁閉自我
隨后而來(lái)的
蠶食鐵鍬的雨水
將形成一個(gè)自我獨(dú)自留在外面
無(wú)人問(wèn)津
我為我所見(jiàn)的事物
現(xiàn)身[1]31-32
詩(shī)歌中鐵鍬作為一把“被遺忘的工具”,究竟是被“我”發(fā)現(xiàn),還是它完成“自我現(xiàn)身”從而找到了“我”。詩(shī)歌不僅包含深刻的“主客體”相互轉(zhuǎn)換的哲理意蘊(yùn),從另一個(gè)角度也道出了語(yǔ)言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也就是說(shuō),這首詩(shī)我們可以將它解讀成一首“詩(shī)論”詩(shī),以詩(shī)歌的方式傳達(dá)了詩(shī)人自己的詩(shī)學(xué)主張。或者換個(gè)角度來(lái)看,此時(shí)的詩(shī),即詩(shī)人詩(shī)學(xué)理論的“實(shí)驗(yàn)品”。在詩(shī)歌寫作中,究竟是詩(shī)人發(fā)現(xiàn)了語(yǔ)言,還是語(yǔ)言發(fā)現(xiàn)了詩(shī),不同的答案將導(dǎo)向完全相反的兩極,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詩(shī)歌理論范疇,誠(chéng)如陳超先生所言:“語(yǔ)言在詩(shī)人手中不是工具,他和語(yǔ)言在展開(kāi)另一空間時(shí)完成了互相的選擇和發(fā)現(xiàn)。表面的語(yǔ)言效果不能代替詩(shī)人對(duì)詩(shī)歌內(nèi)在肌質(zhì)的創(chuàng)造,它是一種靈魂的自白!”[7]現(xiàn)代詩(shī)歌發(fā)展到20 世紀(jì)80 年代,乃至當(dāng)下,更多地強(qiáng)調(diào)詩(shī)歌語(yǔ)言的本體自覺(jué),詩(shī)歌重視聲音,注意語(yǔ)言的走勢(shì),追求像呼吸一樣自然的詩(shī)歌寫作,詩(shī)人的“地位”逐漸趨向于弱勢(shì),甚至“消失”。“無(wú)法分別/兩只杯子/它們構(gòu)成/潔白的一對(duì)//一只杯子/已經(jīng)摔破/它的殘骸/盛滿/另一只杯子”(《悼念》)[2]120,這是小海獻(xiàn)給已故詩(shī)人海子的詩(shī),杯子隱喻兩人名字中共有的“海”,一只“杯子”已經(jīng)“摔破”,而另一只“杯子”,也就是自己將“承載”所有的不幸、懷念和精神遺產(chǎn)。這首詩(shī)在手法上屬于事物的純客觀的再現(xiàn),此時(shí)詩(shī)人已經(jīng)消失不見(jiàn),仿佛是事物在自我言說(shuō)和自動(dòng)呈現(xiàn),也許這就是小海乃至“第三代”詩(shī)歌在語(yǔ)言方面獨(dú)到的藝術(shù)魅力。“雨水/我們慣常愛(ài)說(shuō)成南方的雨水/就如一種消逝的足音/互相撕扯,彼此吞咽/山水草木,我用雨水的語(yǔ)調(diào)說(shuō)話/傾倒在,一樣的天空……/你們用明亮的話語(yǔ)在談?wù)摫狈?就像看著鏡子中的自己(溫?zé)岬臏I水)/慢慢習(xí)慣,與殘酷現(xiàn)實(shí)的聯(lián)系/永別了,畫(huà)境南方/再見(jiàn)吧,煙水江南/故鄉(xiāng),是雨水棺材上的最后一枚鐵釘”(《雨水是棺材上的最后一枚釘子》)[1]164-165,在這首詩(shī)里,或許震撼人心的只在一句話,或一個(gè)語(yǔ)詞,一滴雨猶如一枚釘子,深深楔進(jìn)詩(shī)人的情感深處,只因?yàn)檫@是江南的雨,更是故鄉(xiāng)的雨。詩(shī)人緊緊抓住事物的特征,將兩個(gè)現(xiàn)實(shí)世界離得很遠(yuǎn)的事物進(jìn)行了耦合,而其中的黏合劑就是對(duì)故鄉(xiāng)永遠(yuǎn)割舍不掉的情感。這首詩(shī)的語(yǔ)言和結(jié)構(gòu)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詩(shī)歌的前部顯得有些“情緒化”,情感抒發(fā)得很熱烈、很濃郁,但是結(jié)尾處卻以“悖離”的語(yǔ)言方式予以收束,留下空白,顯得干凈、利落。小海就是依靠這種嚴(yán)謹(jǐn)?shù)慕Y(jié)構(gòu)營(yíng)造出渾然一體的詩(shī)意氛圍。
語(yǔ)言如何進(jìn)入或接近事物?語(yǔ)言以何種方式呈現(xiàn)自明的現(xiàn)實(shí)?小海對(duì)此進(jìn)行了積極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他采用語(yǔ)言的戲劇化方式,讓語(yǔ)言與生活形成一種對(duì)稱關(guān)系,戲劇化的獨(dú)白或?qū)Π壮搅嗽?shī)人“獨(dú)語(yǔ)”式的抒情:“‘把它鋸了真可惜/它是老大的/逢到陣雨呀,躲都來(lái)不及’//‘遲早會(huì)被雷劈了/生這么大個(gè)兒/還能讓它戳破了天’/垂彎下來(lái)的老槐聽(tīng)了/漸漸由枯變黃/懷中的鳥(niǎo)巢也開(kāi)始一無(wú)遮擋//兩個(gè)人往村里來(lái)/頭頂上一群鳥(niǎo)收了翅膀呱呱叫//‘這兒,從前是棵大槐樹(shù)/垂彎了腰好讓人喘口氣,歇歇腳……’//‘真叫活見(jiàn)鬼,我在村里長(zhǎng)大/從沒(méi)見(jiàn)識(shí)過(guò),空蕩蕩一望到頭……’”(《老地方》)[2]68-69。《老地方》一詩(shī)完全符合詩(shī)歌戲劇化的原則——表現(xiàn)的客觀性與間接性。詩(shī)人的同情、無(wú)奈、感傷、憤懣等情緒滲透在人物的對(duì)話上,而不是直接袒露,以此表明詩(shī)人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這樣就使得詩(shī)歌的節(jié)奏、語(yǔ)調(diào)、姿態(tài)以及對(duì)話者的神情等因素參與到詩(shī)歌之中,成為一個(gè)有機(jī)的立體的組織。“留下那片土地/黑暗中顯得慘白/那是貧瘠造成的后果/它要照顧我的生命/最終讓我什么都看不見(jiàn)/陌生得成為它/饑腹的果物/我的心思已不在這塊土地上了/‘也許會(huì)有新的變化’/我懷著絕望的希冀/任由那最后的夜潮/怕打我的田園”(《田園》)[2]23-24。同樣,《田園》中一句“也許會(huì)有新的變化”的獨(dú)白的插入,將客觀描述引向了主觀想象,看似與詩(shī)歌整體的語(yǔ)言效果并不吻合,顯得很突兀,然而,正是這句獨(dú)白使得詩(shī)歌原本壓抑、悲哀、絕望的情緒有了很大的緩解。這種“畫(huà)外音”般的處理,使詩(shī)歌戲劇性的沖突效果得到強(qiáng)化,顯示出詩(shī)人深層心理的變化軌跡。
另外,小海在處理詩(shī)歌戲劇化手法時(shí)多傾向于詩(shī)歌結(jié)構(gòu)的營(yíng)造,體現(xiàn)了一種詩(shī)歌本體意識(shí)的自覺(jué):“我沉浸書(shū)卷/一股肅殺之氣/我們本來(lái)的身體/就像堤壩,抵擋著洪水/給我安寧/將無(wú)欲的老年提前/改變這奴隸的命運(yùn)/終日打著妄語(yǔ)/無(wú)恥地等待/但明天決不會(huì)輕易到來(lái)//一只蝎子在草叢中跳躍/一個(gè)犧牲的貂蟬——當(dāng)代美狄亞//那群山起舞的夏天/萬(wàn)物之美啊/放蜂人孤獨(dú)而明亮的眼睛/他承受貧苦/像暴雨沖毀了一切/雷電震顫的雙手:/一個(gè)大千世界的輪廓和它的倒影//我的朋友/正守在鋼鐵廠的機(jī)器旁/他的身邊/翻滾著/這個(gè)時(shí)代的鐵水”(《登月者的障礙——送楊鍵》)[2]113-114。一般來(lái)說(shuō),完美的詩(shī)歌應(yīng)該是和諧與平衡的,這需要語(yǔ)言的條理化和適度感來(lái)實(shí)現(xiàn)。但是現(xiàn)代詩(shī)歌也許追求更具沖擊力的美感,往往需要打破和諧與平衡,制造出語(yǔ)言的緊張關(guān)系。而《登月者的障礙——送楊鍵》采用了戲劇性結(jié)構(gòu),詩(shī)中明顯存在著多層次的對(duì)立矛盾元素——肅殺與安寧、無(wú)欲與妄語(yǔ)、明亮與暴雨等,這些語(yǔ)詞之間構(gòu)成了強(qiáng)烈的語(yǔ)言張力,使抽象的語(yǔ)詞顯現(xiàn)出一種感性的力量。
當(dāng)代詩(shī)歌呈現(xiàn)出多種風(fēng)格,其中很多詩(shī)歌走向了日常化寫作,記述日常生活,注意對(duì)事物的描摹,具有口語(yǔ)化的特征,并且不失詩(shī)意和想象力。詩(shī)歌越來(lái)越重視語(yǔ)言,但是日常性寫作也存在著很大的危險(xiǎn),也就是語(yǔ)言的潔凈度面臨著沖擊,大面積的語(yǔ)言次生災(zāi)害正在威脅著詩(shī)歌的“純正”,語(yǔ)言粗鄙和詩(shī)意匱乏讓無(wú)數(shù)人再次懷疑詩(shī)歌的“合法性”。對(duì)當(dāng)下詩(shī)歌來(lái)說(shuō),不對(duì)語(yǔ)言施暴既是一種底線,也是一種阻遏詩(shī)歌墮落的力量。小海的詩(shī)歌語(yǔ)言充滿明澈和安靜,同時(shí)也不缺少切入生存的力度。語(yǔ)言在小海詩(shī)歌里是作為生命的呼吸一樣而存在的,自然平靜,節(jié)制而虔誠(chéng),這在泥沙俱下的當(dāng)下詩(shī)壇無(wú)疑具有示范意義。
我們從小海的詩(shī)歌中既能體會(huì)到他對(duì)生命、生存的深刻理解,也能感受到他對(duì)語(yǔ)言的敬畏,作為日常化寫作的先行者,他并沒(méi)有將詩(shī)歌語(yǔ)言導(dǎo)向極端通俗,也沒(méi)有走向純粹修辭,而是尋找通俗與修辭的平衡,給語(yǔ)言找到最佳的切近生活的路徑。探索語(yǔ)言與現(xiàn)實(shí)的同構(gòu)性,重建詩(shī)歌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聯(lián),避免朦朧詩(shī)那種因?yàn)橐庀蠡侄味鴮?duì)現(xiàn)實(shí)造成的變形和傷害,無(wú)疑是小海對(duì)當(dāng)下詩(shī)壇作出的非凡探索和貢獻(xiàn)。韓東曾說(shuō)過(guò),真正的好詩(shī),就是那種內(nèi)心世界與語(yǔ)言的高度合一。[8]只有內(nèi)心充滿了對(duì)現(xiàn)實(shí)和語(yǔ)言的雙重敬畏,詩(shī)歌才真正獲得信任,而小海詩(shī)歌的啟示意義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