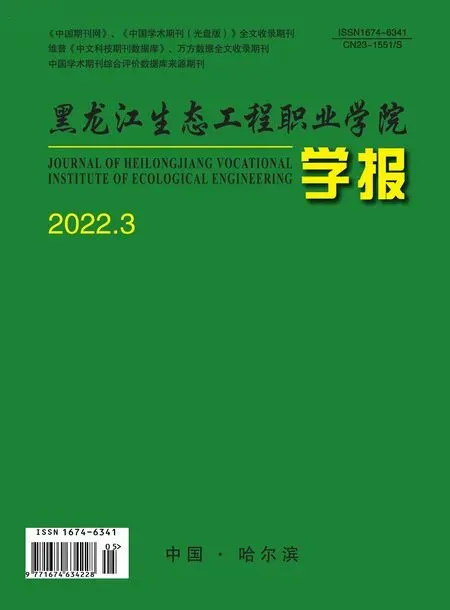算法推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戰與應對
曹玉佳
(南京師范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0)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發展,算法推薦深刻影響了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信息分發的模式,即由過去的“人找信息”變為現在的“信息找人”。從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機遇來看,算法推薦拓寬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傳播空間,但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算法風險。算法已經主宰了信息的傳播,沖擊了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混淆了人們的價值觀念。鑒于此,本文力圖通過分析算法推薦給思想政治教育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嘗試提出一些應對性策略。
1 算法推薦的技術原理
在計算機領域,“算法”是為了解決某個或某類問題按要求進行輸入并能夠在有限時間內獲得輸出的一系列清晰規范的操作指令。而算法推薦則是在此基礎上,通過收集分析用戶的個人喜好、瀏覽的信息、消費行為等一系列數據,打造出量身定制的“私人數據庫”,從而對用戶進行精準“畫像”,精確推送用戶想看到的信息。算法推薦憑借其精準性、個性化、效率高的特點大大滿足了用戶對于信息的需求,贏得用戶青睞。算法推薦之所以能夠投用戶之所好,存在其自身的技術原理。
具體而言,一個完整的算法推薦系統由三個模塊構成: 記錄模塊(收集用戶信息數據系統)、分析模塊(勾勒用戶偏好系統)、分發模塊(過濾、篩選和推送信息系統)。在這三個模塊中,分發模塊處于核心地位,對整個算法推薦運行效果起決定作用[1]。通過三個模塊的運行,完成信息的收集、處理與分發。處于核心地位的分發過程則決定了算法推薦的成功與否,其主要存在三種流行模式:基于信息內容的推薦模式、基于關聯規則的推薦模式、基于熱點流量的推薦模式。基于信息內容的推薦模式是以個人喜好為基礎,以“你瀏覽過的信息是你感興趣的信息”為理念,通過收集瀏覽過的視頻、圖片、文字等信息數據,提取這些信息的共同特征并賦予標簽,再為用戶推薦具有共同標簽的信息族群。基于關聯規則的推薦模式是以社交群體為基礎,以“你的社交群體瀏覽過的信息是你感興趣的信息”為理念,通過收集用戶的社交好友圈的數據,如微信、QQ等好友列表的好友經常瀏覽的信息,來為用戶推送想看到的信息。基于熱點流量的推薦模式則以社會熱點為基礎,以“大家都看的信息是你感興趣的信息”為理念,如微博的熱搜榜則是典型代表,其中的點擊數、評論數、轉發數、閱覽數等數據都會成為進入熱搜榜的標準與依據。
2 算法推薦對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挑戰
21世紀伴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大數據在武裝了強算力的情況下變得“威力無窮”,因此也被稱為“算法利維坦”。這種“算法利維坦”將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蓬勃興起而擴張為一種新的霸權。算法成了上帝制造的“技術神祇”,方便人們在浩瀚的數據海洋中恣意遨游。它在給人類提供便利的同時,也會操控乃至吞噬人類[2]。算法推薦憑借精準性、個性化、效率性等特點在為人們推送信息的同時,也對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挑戰。
2.1 算法裹挾的“資本邏輯”沖擊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地位
馬克思說: “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3]在資本主導下,粉絲和流量成為了獲取資本的利器,商業媒體只能看到流量帶來的利益,而忽略信息的價值,一味迎合用戶需求推送無價值的信息。低俗娛樂信息筑成圍墻將人們包圍,鑄就了尼爾·波茲曼所說的“娛樂之城”,人們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是人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4]。
一是算法在資本溫床里催生“工具崇拜”,混淆價值觀念。與以往不同,現代資本擴張的邏輯展現出了新的特點——技術化。通過把資本附著在不斷更新的科學技術工具上,以此來作為實現利潤最大化這一理性目標的最佳手段。在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等不良浪潮蔓延,誘導網絡用戶特別是青少年,持續產生著各種各樣的需求。而算法作為被資本挾持的工具,則撫平了人們的心理浪潮,迎合了人們的精神需求,使人們在通過精準持續推送種類繁多的“網絡商品”來滿足人們的攀比心理、虛榮心理,使人們在網絡上得到了現實生活中體會不到的優越感,進而使人們深陷算法推薦的狂歡之中。身心的暫時愉悅麻痹著人們的神經,認為“算法能夠解決一切”的工具崇拜致使人們沉溺在自己打造的假想空間中,混淆了虛擬與現實,放棄了正確價值觀的養成,主流價值信息的作用被忽視。而這一切沖擊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地位。
二是資本助推商業媒體興起,改變了傳統媒介結構。流量經濟的背后隱藏著資本的雙手,遵循著資本邏輯的算法作為“流量收割機”需要載體才得以落地,由此帶動了商業媒體的壯大,也悄然改變了傳統的媒介結構。在算法主導時代,作為節點的商業媒體發展壯大并脫離中心形成相互聯系又彼此競爭的關系,大大降低了社會對傳統主流媒體的依賴程度。而這些不計其數的新興商業媒介將“利益最大”作為準則,把“流量至上”奉為圭臬,利用算法將用戶喜愛的信息呈現在其眼前,全然不顧信息的公共價值。泛娛樂化、虛假低俗、淫穢色情等信息鋪天蓋地席卷了網頁、軟件、桌面,博取著人們的眼球,引誘著人們的點擊,麻痹著人們的思想。而主流媒體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發布的主渠道,在數量上與商業媒體相比存在劣勢,也不會像商業媒體把利益作為目標,更沒有意識到要充分利用算法來吸引用戶。在推送環節上不能把控受眾喜好,存在盲區與漏洞,因此發布的信息往往被湮沒在魚龍混雜的信息汪洋中,無人知曉,更無處尋找。
2.2 算法賦權的“網絡文化”消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認同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而網絡文化作為社會意識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主流意識的責任,對我國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然而借助算法推薦而衍生出的網絡文化質量上良莠不齊,重形式輕實質,由此產生的相關文化安全問題在新的歷史時期日益突出。
一是算法對文化信息進行碎片化處理,肢解文化本身語義。以紅色文化為例,紅色文化本身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其蘊含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堅定的革命信念、厚重的歷史內涵需要整體而宏觀地敘事表述,厘清并使其呈現出內在完整邏輯。而算法為了迎合受眾需求,追求簡短,提取出描述該紅色文化信息的碎片詞匯并進行標簽化處理,而從中剝離出的詞語只強調信息的某一方面,呈現信息的局部特質,從而割裂了紅色文化整體邏輯的連貫性,打破了原本的語義結構。算法推薦下的碎片式處理使受眾的思維邏輯出現斷層,對紅色文化進行片面性解讀和傾向性釋義,降低了受眾對紅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認同感。
二是西方國家通過算法對文化產品進行包裝輸出,利用算法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中,網絡意識形態斗爭形勢日趨復雜嚴峻。西方國家利用算法將帶有華麗包裝的網絡文化推薦給用戶,大量西方文化產品攻陷了用戶的瀏覽界面,如充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美國電影獲得了大量用戶的喜愛。這種被包裝的網絡文化背后隱含的是西方價值觀的輸出,沖擊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做意識形態工作就是在人的頭腦中“搞建設”,網絡文化中隱藏的自由主義、享樂主義、人權主義等腐朽思想浸潤著人們的頭腦,造成網絡社會中意識形態的混亂,使得錯誤思潮在網絡中暗涌,消解了人們對主流意識形態內容的認同。
2.3 算法定制的“圈層結構”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凝聚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功能在于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把人民緊密結合起來形成社會吸引力和社會凝聚力,激勵人們投身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之中。而算法對信息進行選擇性和目的性推送,形成了“圈內火熱、圈外冷漠”的圈層結構,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功能。
一是算法對同質性信息的推送造成“圈內火熱”,引起“群體極化”。群體極化理論是由美國傳媒學者詹姆斯·斯托納在1961年提出的。他認為,當一個人身處于某個群體時,他所作出的決策更容易受到這個群體的影響,進而作出比原先更為過激的決定[1]。群體極化主要有兩種形成途徑:信息影響途徑和社會比較途徑。而算法則是通過信息影響這條途徑,把對相似信息感興趣的用戶聚集起來,形成以信息為紐帶的趣緣圈層。圈內成員所感興趣的和接受到的信息是同質的,對彼此的觀點是認同支持的,因此在面臨決策時,群體意見支配群體行為。例如“網絡意見領袖”的發聲得到大批粉絲的盲目支持與擁護,這種“飯圈”追星使未成年人背離主流價值觀,一旦受極端情緒影響,就容易造成不理智的行為,其影響和危害遠遠大于個人。
二是算法對異質性信息的屏蔽造成了“圈外冷漠”,產生“過濾氣泡”。算法總是將用戶喜愛的信息進行推薦,自動屏蔽或忽略異質性信息的推送。遵循資本邏輯的算法很少推薦思想政治教育的相關信息,即使用戶偶然瀏覽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也會自動產生“過濾氣泡”效應,如此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不能發揮。長此以往,用戶只能接受和瀏覽到同質性信息,認知思維不斷窄化和固化,自身陷入一個狹隘境況,進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信息繭房”當中,停留在“舒適圈”里只看自己想看的信息,成為與世隔絕的獨行者,降低了社會粘性。從微觀來看,圈內成員抱團取暖,一心同體,增強了成員自身圈層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宏觀來看,社會分裂為一個個圈層,這些圈層處于互不干擾、斷絕聯系的狀態,建筑起一道觀念上的“隔離墻”,加劇了社會割裂。
3 算法推薦下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機遇
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的不斷發展使得變局中“危”和“機”同生并存,危中有機,危也可轉機。算法推薦為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諸多挑戰,也給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機遇。
3.1 算法推薦拓寬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空間
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32億,較2020年12月增長4 296萬,人均每周上網時長達到28.5個小時。也就是說,網民規模的不斷擴大和互聯網的逐漸普及使得網絡空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算法推薦的雙面性迫使思想政治教育拓寬其話語傳播空間,而不是僅僅局限于線下。
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在話語傳播的過程中,其運行模式重點以線下傳播為主要空間,以人際溝通為主要途徑,以書本材料為主要載體,而對于網絡這一新生空間的引領與關注較少。算法推薦的發展不僅節省了人們尋找信息的時間,加快了人與信息之間的聯系,更助推了思想政治教育傳播的網絡空間轉向。在網絡空間中,思想政治教育以議題引導為主要育人途徑,以網絡平臺為主要傳播載體,生產大量優質教育內容,能夠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持續供給,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在網絡平臺中發揮著凝聚人心、立德樹人的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夠在現實生活中進行傳播,也能夠在網絡空間中得到發展,從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在多維場域的引領性、浸潤度和感染力。
3.2 算法推薦延伸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功能
每一種技術架構、每一行代碼、每一個界面,都代表著選擇,都意味著判斷,都承載著價值[5]。也就是說,算法本身蘊藏著價值,從不存在“價值中立”的算法。智能算法如果遵循資本邏輯,則會在商業利益的驅動與誘導下,推送不良信息。一些低俗無效信息缺乏正確價值引領和正確導向,網絡受眾通過長期瀏覽這些不良信息導致價值觀畸形發展,影響自身價值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高度的價值導向與價值引領作用,是成員之間相互聯系和加強溝通的橋梁。思想政治教育能夠不斷增強人們的群體意識,形成群體凝聚力,從而激勵人們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建設當中。互聯網的崛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信息爆炸”,算法推薦的信息中所包含的價值取向會影響到網絡用戶的價值取向。算法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結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引領功能得到延伸,范圍不再僅局限于人,還增添了由人支配與掌控的工具。算法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密切聯系,其價值合理性更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賦予。因此,算法的內在價值的提升和網絡用戶對信息有效程度的判斷與選擇都離不開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引領。
3.3 算法推薦助推思想政治教育精準高效育人
從傳播學角度看,人與信息之間是彼此聯系、相互作用的[6]。立德樹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而精準育人則是實現立德樹人目標的重要保障。大腦只有通過接受與處理滿足自身需求特征的外界有效信息,感受信息蘊藏的內在價值,通過信息傳遞出的正確價值導向在潛移默化之中熏陶與升華人的政治認同素養,才能達到立德樹人的最終目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也是進行精準定位的過程。
在這個信息紛繁復雜的時代,由于每個人的思想狀態、心理結構、年齡特征等方面的差異導致每個人對有效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如何尋找符合受教育者特征需求的信息并判斷其有效性成為了難題。而算法的最大優勢則是通過人與信息相匹配的機理滿足了信息推送的因人而異,實現了精準定位,成功地將“人找信息”改變為“信息找人”。借助算法分析數據、精準決策、建模預測的獨特優勢,思想政治教育可在相關內容上進行“精準生產、精準過濾、精準推薦”。在精準生產環節,利用算法收集的事件熱度并結合時事政治,用正確的價值導向精心設置滿足訴求的教育議題,使符合主流價值觀的議題登上熱搜,引導用戶進行解釋型、辯論型等多種形式并存的內容討論,廣泛凝聚社會共識,形成多維度的價值引領。在精準過濾環節,及時把握用戶的意見傾向,解構輿情事件的風險因素,阻止西方文化產品和網絡亞文化的肆意傳播。通過“人機結合”的主流意識形態算法權力模式,精準過濾錯誤信息,戳破西方算法媒體所構建的意識形態“過濾氣泡”[7]。在精準推薦環節,通過算法為用戶描繪的精準“畫像”提高信息的精準度與流動性,改變傳統的“千人一面”分發模式,做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分發的“千人千面”,實現精準高效育人的目標。
4 算法推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應對之策
技術本身不是問題,但人應時刻將對技術的使用以及技術后續發展的控制權握在手中[8]。算法推薦為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機遇,我們要抓住機遇,積極采取有效策略應對挑戰,努力實現算法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算法推薦下能夠與時俱進、不斷創新。
4.1 優化算法生態:利用主流價值引領算法發展
一是堅持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算法推薦下各種思潮在網絡空間中暗涌,極大沖擊了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混淆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因此,要守住思想輿論陣地,在多元并存中堅持一元主導,必須要堅持黨管媒體、黨管輿論的原則,把講政治守規矩貫穿到算法運行的全過程。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應堅定黨性立場,在網絡上廣泛宣傳并調動受眾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積極性,做到“因事而化、因時而進、因勢而新”。另一方面,要旗幟鮮明地抵制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不良文化,鞏固馬克思主義在網絡空間的領導地位,傳播正能量,弘揚主旋律。
二是引導算法人員的價值理性。流量市場的自發性、盲目性的弊端使得算法成為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算法自身沒有意識,它是由人創造的,但也是被人利用的。而意識形態治理本質上是對人的治理,是對人的社會行為的評判、引導和規范化[9]。因此,從根本上改變算法人員的功利主義思維是保證算法堅持正確方向的根本策略,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來提升相關責任主體的職業倫理素養,使相關人員認識到“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10]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應與相關人員定期探討算法價值理性的話題,明確算法承擔的社會責任,將主流價值貫穿于算法的設計與推薦中,自覺糾正價值偏差。
三是加大算法推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占比。算法很少對主流價值信息進行推薦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信息池”中所涉及的相關信息占比太小。目前“信息池”中多是根據用戶喜好投入的信息,存在信息同類、內容單一的情況。而“信息池”是算法進行分發的來源,也是用戶接收信息的源頭。因此,在主流價值引導下,應加大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投入,重點注入關于社會熱點與引導個人發展的正能量信息,重新調整各類型信息的占比,將內容單一的“信息污池”變為豐富多彩的“信息凈池”,使用戶在獲得優質的使用體驗時還能提高思維能力,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與算法推薦的有機結合。
4.2 規范算法運行:重塑把關權,實現算法價值平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無論什么形式的媒體,無論網上還是網下,無論大屏還是小屏,都沒有法外之地、輿論飛地。”[11]因此,有關部門應履行把關責任,構筑算法法律體系來規范算法運行,實現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雙向平衡。
一是承擔把關責任,提高算法透明度。把關人理論認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社會價值的信息才能進入傳播渠道,把關人的立場會影響信息的質量。算法受資本影響具有不透明性、隱蔽性的特征,這使得用戶失去對被過濾信息的知情權,造成了算法主宰用戶。因此,要加強把關人的社會責任,主動向用戶公布算法描繪的畫像,介紹收集的數據特征、普及運行的機制原理,使受眾對隱性信息具有知情權,對顯性信息具有判斷力。同時,有關部門還應制定嚴格的信息準入和審查制度,引導把關人員的價值取向,使其堅定主流意識形態,提高自身的專業素養,做到不僅對初始信息進行把關,更要在信息過濾后進行二次篩選,能夠敏銳辨別誤導性的信息并加強對這類信息的監測與處理力度。
二是健全法律法規,規范算法行為。相比于算法發展的速度,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立法滯后,關于算法推薦的相關執法依據不足。因此,在立法方面,從源頭上掌握立法的主動權,組建專家團隊對算法風險進行預估研判,加強前置立法,規范算法的行為邊界,做好專業法與普通法的配合。在執法方面,對網絡用戶實行實名登記制度,對于傳播虛假信息、負面信息的網絡亂象要敢于亮劍,嚴肅處理,對混淆主流意識形態的網絡行為要予以堅決打擊。
三是提高媒介素養,識別算法本質。算法不僅需要法律法規、工作人員的把關,更需要網絡受眾能夠形成對算法的正確認識。媒介素養是指用戶對媒介信息的認知、傳輸、判斷和理解能力。目前算法與用戶處于支配與被支配的地位,兩者是割裂分離的狀態,用戶的媒介素養普遍較低。因此,要提高用戶的媒介素養,使其深入了解算法,有效識別算法本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應普及算法推薦的機制原理,使用戶在了解的基礎上認清算法推薦下由于信息的盲目信任所造成的危害,認清算法背后的本質邏輯,使用戶認識到“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10]同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主動開展對社會熱點事件的理性議題設置,引導用戶對其深入思考,積極制造、瀏覽、點贊、轉發優質信息,減少對負面信息的瀏覽和傳播,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環境。
4.3 促進算法轉型:加強媒介合作實現效益共贏
看待技術的態度是在技術洪流中掌握主動權的關鍵因素[8],算法造成的利弊關鍵取決于對待算法的態度。算法與人類并不是零和博弈、你贏我輸的關系,而是彼此依賴、共同促進的關系,應主動擁抱算法使其為我所用,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
一是算法優化技術路徑為媒介合作奠定基礎。雖然算法能夠對用戶的“外貌”進行精準畫像,但卻無法描繪用戶的“內心”。因此,通過優化算法推薦的技術路徑使算法不僅看到用戶的顯性需求,更能深入挖掘其隱性需求才能為媒介合作提供基本保障。對于記錄模塊,“用戶不會瀏覽的信息”“每天在哪個時間段進行瀏覽”“瀏覽一次所花的時長”等都應成為記錄的內容,而不是僅僅關注“用戶經常瀏覽的信息”這一指標。分析模塊則在記錄模塊的基礎上,對收集到的信息進行深入挖掘,探尋用戶的內心。分析用戶經常瀏覽的信息層次,找到與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聯結點。同時判斷這些信息是否具有正確的價值導向,如果導向錯誤,則應及時推薦正確導向的信息;對“不會瀏覽的信息”要總結背后的原因并及時反饋以便日后改進;對于時間的分析則是為了在適宜的時間對信息進行推送,使用戶能夠有足夠的時間接受完整的信息,而不是碎片化的信息。在分發模塊上,分發人員應搭配不同類型的信息推送,打造一個立體信息族群。同時對不同類型的信息進行質的把關和量的選取,使用戶有能力有時間對信息內容進行接收。
二是主流媒體應主動擁抱算法進行轉型升級。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在思想政治教育面臨挑戰的情況下,主流媒體不應故步自封,而應有所作為,把握信息發展的趨勢,主動擁抱算法。首先,主流媒體要將算法技術引入其中,利用算法的優勢屬性了解用戶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需求和原因,制作富有吸引力與形式多樣的優質信息,改善媒介運營方式,創新信息產品形態,提高信息傳播效率,提高用戶粘性,努力走出當前困境。例如在2020年全國兩會報道中,新華社緊緊圍繞兩會報道主題,充分運用5G和AI等新技術新手段,創新推出“5G+8K+衛星”超高清新聞直播、3D版AI合成主播、新聞互動微紀錄片等全新報道形態,有效提升了新聞報道的受眾體驗[12]。其次,加強與商業媒體的合作。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不是取代關系,而是迭代關系;不是誰主誰次,而是此長彼長;不是誰強誰弱,而是優勢互補[11]。官方媒體要牢牢掌握輿論的主導權,積極與商業媒體溝通并入駐其中;商業媒體應優選推送官方媒體發布的優質信息,實現二者的互利共贏。
三是商業媒體有效利用算法創造紅色產品。雖然商業媒體以盈利為目標,但是不妨礙其通過算法來創造更多的紅色產品。在網絡空間上,商業媒體可以通過算法收集用戶對紅色文化的偏好,根據偏好特征開發紅色資源數據信息庫。例如,利用AI、VR等先進技術打造紅色旅游景區、革命文化、革命事跡等虛擬空間,使用戶獲得身臨其境的沉浸式體驗;設置紅色文化資源板塊,定期推送紅色文化的視頻。在實體空間中,商業媒體可以積極尋找與廠商的合作途徑,制作紅色文化衍生產品。同時商業媒體也應加強與主流媒體合作,主流媒體為其做好引領,提高大眾的信任度,從而使各類媒體能夠插上一雙“算法翅膀”在信息時代的天空中展翅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