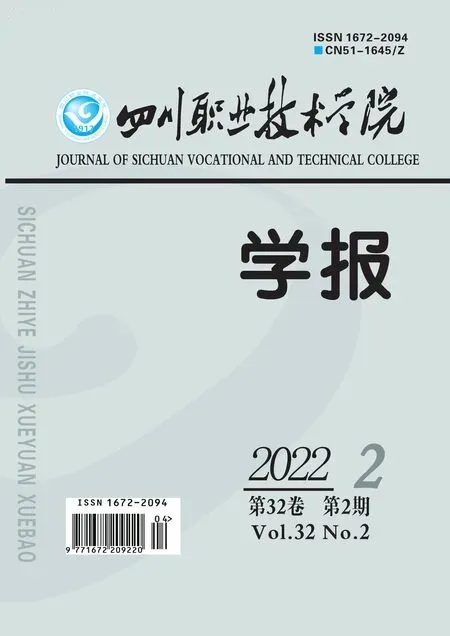新高考改革的研究述評
焦夢玲
(重慶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重慶 沙坪壩 401331)
舊高考制度存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應試教育下培養的人無法適應現在社會的發展,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也無法平衡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與教育水平之間的矛盾。而新高考旨在促進社會公平,并選拔更優質的人才為國家發展服務。自2014年頒布文件后,各地進行試點研究已有7年,積累了不少經驗,為了使后續的高考改革更加順利,豐富新高考相關研究,對已有學者的研究進行梳理總結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通過在中國知網(CNKI)以“新高考改革”為主題詞進行2014-2021 的檢索,分析幾年間有關“新高考改革”研究的發展特點,以期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
本文通過檢索發現相關研究有2296 篇期刊文獻,其中核心期刊僅有336 篇,約總數的15%,且研究數量從2014年開始突然增多。通過可視化分析,新高考改革政策的相關研究集中于新高考政策的考試內容、評價方式、新錄取方式、新高考政策40年或70年的回顧以及高考政策區域試點成果等方面。
一、新高考政策中的考試內容
基于對高考與高中學習知識的關聯度的考慮,高考總分數的構成由6 個科目組成,分別是全國統考的語文、數學、外語,以及考生根據自身特長、興趣與期望報考學校的專業要求在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6 科中自主選擇確定。
考試內容的改革,超越了以往單純就文理分科與否的表層討論,進入了實踐探索階段,改變了學生只能接受改革結果的被動狀況,使自由選擇權得以有效發揮,彰顯了生本價值。張銘凱、靳玉樂等學者認為選課考試不僅增加了學生在考試科目選擇上的自主權,充分發揮學生的興趣和特長。而且自學選考,學生還可以學完就考,減輕了由于科目累積應考而帶來的過重負擔,也減小了學生的備考壓力[1]。袁振國、柯政等學者也認為6 選3 的選考制度,增加學生的選擇權,促進學生有個性、有特色地發展[2]。于世潔等學者從高考設置改革的影響分析角度進行研究,認為選課對學生的影響在于提高了學生的專業性以及對最后高考總分的選擇權;而對中學的影響在于教學模式、課程結構和師資設置等方面[3]。綜上所述,幾位學者認為選課制有利于學生的多樣化發展。
而竺麗英、王祖浩和全微雷等人從科目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角度出發,認為影響學科選擇因素按影響力大小從大到小是學科基礎水平、學科態度、教師及其他因素和生活學習等發展需要[4]。王新鳳學者則從學業表現結果出發,認為選課制可能會導致學生進入高校后專業水平的欠缺,有的理工科學生可能因為高中沒選理化生,而導致缺乏基本知識儲備[5]。而周彬也認為當學生進行教育選擇的主要依據不再是個人的興趣與愛好時,學生及其家長進行選擇的主要考慮就會成為教育利益。正是“育人導向”和“利益導向”在教育選擇依據上的沖突,使得高考改革從原本促進學生個性成長的政策意圖,異化成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博弈;甚至為了在高考新政中獲取更大的利益,在極端情況下,大家反倒會放棄或者違背自己的專業興趣與職業愛好[6]。例如有的學生就會因為自己擅長什么,哪個科目有優勢而選擇哪門,而不是根據自己的發展興趣,所以導致試點期間出現了物理無人問津,化學熱等情況。綜上所述,學者們認為選課制會突出學生的功利化傾向,而沒有達到高考改革的初衷。
對于新高考改革政策的考試科目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了訪談和理論分析的方法,且研究結論主要有兩個觀點,其中一種觀點認為改革能增進學生的選擇權和自主性,促進學生的多元發展;另一觀點則是認為學生會選課“功利化”,違背了新高考選課制的初衷。
二、新高考政策中的評價方式
新高考的評價方式做出了很大的變革,改變了以往“一考定終身”的評價方式,采取綜合素質評價、成績等級評定和英語一年兩考的評價方式,促進學生多元發展,旨在改變學生分分計較的功利心態。其中綜合素質評價指通過“學生成長檔案袋”,以學生、同伴、家長和老師為評價主體,針對學生道德品質與公民素養、學習與創新能力、交流與合作能力、運動與健康和審美與表現五個方面,對學生進行評價的方式;成績等級評定是指學業水平測試是按成績區間劃分等級,綜合素質評價也是按等級評定的評價方式;而英語則采取一年兩考的方式,避免一考定終身。
袁振國學者以實際數據說明通過參考綜合素質評價成績,能引導素質教育,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而且還能提高學生們的錄取率[2]。張銘凱、靳玉樂等學者也認為“一考定終身”違背了學生身心發展的歷時性和教育的長期性、復雜性等特點,認為綜合素質檔案和學業水平測試相組合的方式能更加凸顯評價方式的人性化和過程與結果并重,多元綜合評價的方法[1]。鄭若玲、孔苓蘭等學者根據第三批省市改革的調查,從綜合素質的特征、困境和突圍等三個方面進行論述,認為綜合素質評價過程更規范、科學,明確了評價主體;評價的制度化水平有所上升,內容穩定、過程規范、結果透明[7]。饒燕婷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綜合素質評價方式和英語一年兩考的評價方式有利于促進課程順利變革,促進多元化招生模式建立,改變“唯分數是舉”的應試心理,有利于改變“重甄別,輕發展”的傾向[8]。綜上所述,這種評價模式體現了我國新高考評價更加注重學生的發展性,重視評價過程的公開透明性,不斷落實量化評價和質性評價相結合的特點。
而趙靜宇等學者則從新高考改革的問題及對策出發,探討了新高考評價方式中,有的學校會為了學生通過,而降低試題難度或者根據學生考后的成績劃分合格線,大多學校采取兩種方式并舉,這樣的做法使學業水平測試形同虛設,與國家的改革初衷相違背[9]。饒燕婷學者還從綜合素質評價的困境出發,敘述了該評價具有客觀性、真實性難以保障;缺乏統一標準,區分度低;對處境不利的學生而言,易造成教育不公平;容易成為腐敗的土壤等不利因素[8]。羅立祝學者通過研究表明等級賦分,由于試題難度差異、科目原始分沒有可比性、分數不能直接相加求和等原因,而具有起始等級分不合理、催生學生選課工具化、相鄰分數等級差異化、不能滿足考生分數區分度的需求等明顯的缺陷[10]。綜上所述,學者們認為這種評價方式還不完善,不具有完全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對于新高考改革政策的評價方式研究結果主要有認為該評價方式可以促進學生的多樣化發展,是高考的重點,有利于促進此次高考改革;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評價方式會導致腐敗滋生,缺乏統一的標準,在實施過程中容易與國家改革初衷相悖逆。
三、新高考改革政策中的錄取方式
新高考政策中高考的錄取方式也更加完善,采用多元錄取方式,基于統一高考成績、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參考綜合素質評價的錄取機制,且考生選考科目中的一門與高校專業相對應,則可以報考。并且此次改革,對自主招生方式也做出了相應的規范。
董秀華、王薇等學者認為綜合錄取、三位一體招生方式是高校招生踐行“兩依據一參考”的最大亮點,在試點地區的院校中高考成績、面試成績和學業水平測試成績按比例劃分,共同作為錄取的參考依據;其次取消了院校批次,將錄取更加聚焦于專業;再次將“+3”科目折算后計入高考成績;最后認為綜合素質評價也是招生的重要參考依據。學者認為這樣的錄取方式更加凸顯了多樣性[11]。范國睿學者則從政策藍圖出發,認為這樣的錄取方式有利于破除高中教育“唯分數”和高校招生“唯”分數的現象,有利于高中教育的分層與分類相結合的發展,并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改變了以前單純用考生成績錄取學生的現狀[12]。劉海峰學者則從新高考成效角度出發,認為高校錄取學生的多樣化帶來明顯的變化,倒逼高校重新審視學科專業優勢,通過專業調整提升高校在招生錄取中的競爭力,以吸引更多優質生源報考[13]。綜上所述,學者們認為錄取方式的變革,凸顯了其多樣性,有利于降低高考和錄取的功利化傾向,能倒逼高校發展。
而劉海峰學者同樣從高考改革的實踐中發現,錄取方式的變革在實際操作中過于復雜,無論是科目組合、選考學考、成績賦分、等級換算,還是高校不同專業選考科目要求、中學走班排課表等等,都相當的紛繁復雜,家長和教師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弄明白[13]。而吳根洲與劉海峰兩位學者則從高中教育“唯分數”和高校招生“唯”分數的角度,具體論述了兩者關系,認為高中教育的“唯分數”并不是導致高校招生“唯”分數的唯一條件,因此高考錄取方式的轉變,不一定能完全改變高校招生“唯”分數的狀況[14]。綜上所述,學者們認為高考錄取方式的變革在實際操作中較為復雜,需要進一步完善,并且不能完全改變高校招生“唯”分數的現狀。
綜上所述,評價方式的改變推動著錄取方式的變革,同時也給高校帶來了挑戰,促進了高校的更新發展,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變革操作過于復雜,而且不能完全改變高校招生“唯”分數的功利化傾向。
四、對高考政策的歷史回顧研究
由于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2019年是我國建國70 周年,因此在這兩年涌現出了許多以40年或者70年為范圍的教育研究,高考改革的政策研究也不例外。
首先是關于四十年的政策回顧,劉恩賢學者從改革開放以來重大事件發生或重要文件發布的關鍵節點為界,以政策問題、政策制定、政策執行的邏輯過程作為分析框架,將其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987-1997年是高中會考與標準化測試為特點;1998-2009 是擴招、高考科目設置與命題方式改革為特點;2010年至今是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為特點[15]。周光禮、姜尚峰兩位學者從文化模式變革的角度解釋高考政策的變遷,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一個階段1977-1991是公平競爭和賢能治國,高考政策定位為精英篩選機制;第二個階段1992-2011 是崇尚自由和追求卓越,高考政策變遷表現為國家本位的政策范式向市場本位的政策范式轉變;第三個階段2012年至今是提高質量和實現公平,高考政策變遷表現為向國家本位政策范式回歸。可見,我國高考政策的變遷始終以公平和質量為兩條價值主線[16]。馬健生和鄒維兩位學者,則從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出發,對高考的功能定位、目標定位、價值定位和技術定位等多方面都做出了建議[17]。
其次是關于七十年的政策回顧,項賢明學者從經濟政治與教育之間的關系出發,將高考政策變革分為從悸動到驟停的17年和40年改革的變量轉換兩個階段,其次論述了影響和制約高考改革的因素,并提出了未來展望[18]。葛新斌和付新琴則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將高考政策按歷史順序劃分為1949—1966年制度新建期、1967—1984年中輟—恢復期、1985—2009年改革探索期和2010年至今的試點深化期,以此客觀分析高考歷程中的經驗與教訓[19]。李芳學者則是根據考試內容劃分階段,將高考改革劃分為了文理分科固定考試科目階段、“3+X”階段、固定科目+自選科等3 個階段[20]。
綜上所述,學者大多從四十年和七十年的角度對我國新高考改革政策進行梳理分析,以此幫助后面的研究者們理性地對高考政策的變革進行理性的分析和研究,也有效地幫助研究者們從縱向角度把握高考的變革。
五、新高考試點成果探討
2014年國家頒布了《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文件后,各地開始試點研究相關政策,2014年在浙江、上海兩地開始啟動,之后2017年,北京、天津、山東、海南四省市也啟動新高考3+3 模式,2018年河北、遼寧、江蘇、福建、湖北、湖南、廣東、重慶是全國第三批啟動改革試點的八個省市。而浙江、上海兩地的試點實行取得了不錯成就,但同時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因此不少學者針對這次的試行進行研究,以期為后面的政策實行提供經驗幫助。
其中根據時間從早期到最近的順序進行梳理,邵光華和吳維維兩人為試點地區學生高考的選課的現狀未達到政策預期,不能為學生進入大學的專業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改進措施[21]。王森和劉世清兩人則研究了新高考政策為老師帶來的影響,具體有任課教師負擔加重、教師對政策的具體實施的正向反響較低等問題,據此提出了明確考試難度及范圍,并保持政策穩定;以教學為中心協調教師工作,系統完善“選課走班制”等兩個措施[22]。張雨強、陸卓濤和賈騰嬌三位學者,則是從學生角度出發提出了“新高考政策真的讓學生減負了嗎”的問題,并通過研究發現,新高考下高中生考試負擔整體偏重,并未完全實現新高考改革的“減負”初衷,并且文化資本、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等優勢、選科了解度的“馬太效應”、考試內容和學生身心影響都與考試負擔有聯系,并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了相應的研究建議[23]。而樂毅、溫莉莉和李文倩三位學者則通過對上海、浙江兩地試點成果的研究,發現改革舉措的實施也產生了相應的問題,包括學生自主選科后如何實施與之配套的教學組織形式改革,如何化解走班制引出的課程管理與教師和教室配置問題,如何設計更科學合理的選考科目賦分制計分方式,如何避免多次考試機會可能帶來的學業負擔加重與資源浪費問題,如何應對科目選考與大學專業報考掛鉤以及“先選專業再選學校”填報志愿改革產生的問題等,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應對舉措[24]。徐娜學者則把研究聚焦于改革后入學的性別差異分析上,經過研究發現上海男生群體的普通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相對于改革前大幅提升,但在各層級高校入學機會方面,男生獲得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機會多于女生。但整體而言,新高考改革促進了男女生入學機會均等,契合了教育公平的價值追求[25]。
綜上所述,學者們大多通過問卷法和訪談法進行新高考改革試點成果的研究,經過時間的積累研究角度愈加豐富、多元和全面,從政策的選課制輻射到新高考的評價制度、招生方式等。除此之外,研究內容也從新高考政策實施成果,廣泛到新高考政策帶給老師、學生等的影響,更加靠近人的角度,凸顯以人為本的研究價值觀。最后各位學者,都針對自己發現的研究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為后面的新高考順利全面推行提供了重要參考。
六、研究不足與展望
(一)研究不足
1.研究對象學段有待擴大:高考是承上啟下重要時刻,對中小學和大學的教育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研究對象應該涉及該類教育階段的學生,而目前現有的研究對象主要以高中生為主,對其他年齡段的學生研究較少。
2.研究方法有待拓展:目前有關新高考政策的研究主要用的是理論分析的方法研究新高考政策的各個方面,但是訪談、實證和問卷等方法用得較少。
3.研究范圍有待擴大:研究范圍主要集中于試點地區,整體而言試點地區的文章數量偏多。如上海和浙江等地的優秀中學,因此在研究結論上存在代表性不夠、有偏差等問題,缺乏一定的說服力。
4.研究維度有待全面:首先對新高考政策的研究主要局限其政策內容的各方面,而較少地關注學生和老師,但實際高考改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其次對新高考政策的實施問題研究較多,雖然學者都提出了相應的改進措施,但是新高考的試點實施有很多成就,也能給我們諸多啟發,一味的問題研究容易造成我們心理上的改革困難。
(二)研究展望
1.擴大研究對象學段:將對象擴大到小學初中,如研究高考對他們課程開展、教育內容和考試方式所帶來的變革等;擴大到大學生,如研究高考變革對大學生專業適應性的影響等;擴大到學生的家長,如研究他們對高考變革的支持度等,以此完善關于高考變革的相關研究。
2.拓展研究方法:采用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研究方式,使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
3.擴大研究范圍:將研究范圍擴展到中西部地區,如重慶即將迎來第一次新高考,也許有很多改革的成功經驗和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值得我們探究;將研究范圍擴大到鄉鎮,做到城鎮結合,如可以研究新高考政策是否真的是大家的、各個地區的公平,這樣的研究結論才會更具有說服力和代表性。
4.完善研究角度:首先多關注新高考背后人的發展研究,如教師負擔研究、學生負擔研究以及教師意見研究等,彰顯教育的人本價值;其次增加對新高考改革的成就研究,為我們后續實施提供模范參考,促使新高考在全國范圍內順利施行。
近幾年關于新高考改革的文獻一直在增長,凸顯了社會對新高考政策的關注和重視,雖然從目前的新高考政策相關研究來看,新高考改革還具有一些不足和不完善的地方,但是高考的改革是社會發展潮流的必然,也是歷史的必然。正如馬克思說新事物的產生總是伴隨著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也總是會經歷曲折的,而新高考是國家發展的需要,但是我們還需要對此進行不斷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