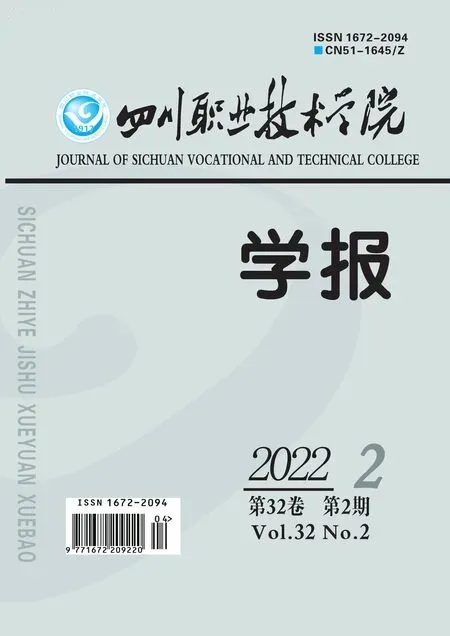“巴”族字探析
盧芮青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對漢字字族的研究可上溯至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所用“從某,某亦聲”之法,隨后西晉楊泉、南北朝顧野王相繼作出研究。據沈括《夢溪筆談》載:“王圣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1]可知,在北宋時王圣美提出的“右文說”有了進一步發展。在宋高宗時,王觀國提出的“字母說”更是對王圣美“右文說”一脈相承。近代學者沈兼士、劉又辛的“因聲求義”理論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古人雖尚未有明確的“字族”概念,但在著作中對這一方法卻運用已久,如劉熙《釋名·釋水》:“山夾水曰澗。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水草交曰湄。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注溝曰澮。澮,會也;水溝之所聚會也。”[2]29-32《太平御覽》:“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3]皆是這種理論與方法的現實運用。
所謂漢字字族,就是說漢字在發展中,最初記錄根詞或源詞的“母文”,因同時記錄了根詞或詞源的若干引申義或派生詞而導致表義功能復雜化。為了解決詞匯的“同源派生”所導致的漢字表義功能復雜化即單個漢字記詞過多的問題,于是在漢語詞匯積累發展的“派生階段”,人們便逐漸在這個載義較多、兼職較繁的“母文”的基礎上,先后加注與母文特定意義(即準備用后孳乳字記錄的源詞的某項意義或某個引申義)相關的輔助性類屬標志符號而形成了一系列意義相對單一的孳乳字。這一系列的孳乳字都是在母文的形、音、義的基礎上分化孳乳的,有共同的發生源,因而,在形、音、義三方面都與母文有“血緣關系”,但由于與母文的關系有遠近之分,而形成了不同的層次[4]2-3。于是,就把這種文字現象稱作“字族”,“字族”內部的各個字就是“同族字”[4]3。這一系列源于同一母文的孽乳字也就構成了漢字字族。
本文根據漢字字族理論,歸納分析《說文解字》和《漢語大字典》中以“巴”為母文的十七個字,并探析其與母文之間的內在聯系。
一、母文“巴”字釋義
對于“巴”字本義的解釋,歷來看法不同。許慎《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中說:“巴,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凡巴之蜀皆從巴。”[5]310曹定云認為其本義應是“婦女懷孕”[6]。谷斌指出其本義是“五步蛇”[7]28。張秉權釋“巴”,以為像人形[8]。劉興均認為本義為“爬”[9]。“巴”字甲骨文作“”①形如蛇狀,兩根豎線恰好就位于字體上部的蛇頭內,讓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蛇的兩顆令人恐怖的毒牙[7]24。篆文作“”,像蛇蜷曲之形。隸書“巴”承篆文而定體。《山海經·海內南經》載:“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東晉郭璞注曰:“今南方蚦蛇吞鹿,鹿已爛,自絞于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10]281據郭注可知,巴蛇即現實中的蚦蛇(即蟒蛇),巴蛇吞象,蟒蛇亦可吞鹿。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釋:“謂蟲名。《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11]741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更是詳細列舉古文獻《楚辭·天問》《淮南子·大荒北經》《淮南子·海內南經》《淮南子·本經訓》《吳都賦》《博物志》《金樓子·志怪》《師子賦》《尋陽記》及《爾雅翼》來證明“巴”是一種食象蛇的一種大蟲[12]。
關于“巴”字的本義尚無定論,學界更是百家爭鳴。本文就“巴”的本義,根據其字形變換以及查閱古籍兩方面,謙認其本義應指“古代傳說中的一種大蛇”。因蛇是善于附著在物體上曲折爬行的,又引申指緊貼著、挨著、靠近;又攀附、依附,附著、黏著;由“巴結”義又引申指盼望;又有挖,刨之義。也可用作名詞引申指干燥或黏附著的東西。
二、“巴”族字釋義
(一)以母文本義“蛇”為義核的“巴”族字
把,《說文·手部》:“把,握也。從手,巴聲。”[5]252段注曰:“握者,搤持也。《孟子注》曰:‘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11]597篆文作“”。該字左邊作“扌”形如手,右邊“巴”本義是大蛇。“把”字本義是指一手握著、抓住。《戰國策·燕策三》:“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13《]史記·殷本紀》:“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14]在義核為“蛇”的母文“巴”上加類屬標志字“手”,孳乳出“把”字代表捕蛇時一定要緊緊握住蛇頭才能把蛇捉住。因此“把”的本義一直沿用至今有握、持等之義。
(二)以母文引申義“挨著、靠近、緊貼著”為義核的“巴”族字
妑,《玉篇·女部》:“妑,栢麻切,女名也。”[20]69《集韻·麻部》:“妑,女名。”[19]60《廣韻·麻韻》:“妑,《字林》云:‘女字也’。”[17]47貴州省東北部的一些地區(如印江縣等地),方言里對“奶奶”稱呼音“[pa]”(聲調介于陰平與陽平之間),可見“妑”在方言中有晚輩對于女性長輩的稱呼之義。在以母文“挨著、靠近”為義核的基礎上加類屬標志“女”字,就孳乳出“妑”,表示晚輩與女性長輩的親密關系,從而引申出女名、女子稱呼之義。
爬,《廣韻·麻韻》:“爬,搔也。”[17]48《集韻·麻韻》:“爬,搔也。”[19]60又《說文·手部》:“搔,括也。從手,蚤聲。”[5]254段注:“搔,刮也。刮各本作括,今正。括者,絜也。非其義。刮者,掊杷也。掊杷,正搔之訓也。”[11]601《禮記·內則》云:“疾痛苛養,而敬仰、搔之。”鄭玄注曰:“苛,疥也。仰,按。搔,摩也。”[21]728-729《漢書·枚乘傳》:“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顏師古注曰:“搔謂抓也。”[22]2360-2361《諸病源候總論》:“搔之生痕。”[23]可見,“爬”字本義是指搔;爬疏、搔抓之義。在以母文引申義“緊貼著”為義核的母文“巴”,加類屬標志“爪”,代表著用手緊貼著搔抓。后又引申為伏在地上向前移動,實則也有母文“巴”在其引申義中起作用。
粑,在古籍中無具體釋義。《中華字海》(1999:1292)《漢語大字典》(1990:3144)等現代字典都有收錄。“粑”多見于南方,指的是一種用大米蒸熟后捶打而成,或用糯米面加水后糅合而成的口感軟糯、粘糍的食物,多是餅狀,另有塊狀、條狀等。江蘇文人馮夢龍在《醒世恒言》第十五卷寫到:“一個揖作了下去,卻像初出鍋的糍粑,軟作一塌,頭也不伸起來。”[24]可見至少在明時就有糍粑這一食物。《楚南苗志》卷六載:“每歲于臘月二十四日作米餅。注:俗謂打粑粑。”[25]清人桂馥的《贈查三》中的“餌塊粑”至今在西南地區都是常見的。《貴州通志·卷六》中記載著貴陽有個地方叫“湯粑鋪”,湯粑在方言中即湯圓的意思,湯圓是軟糯的,湯粑亦是。在方言中,“粑”也有緊緊貼上、依戀義。如“獎狀用漿糊粑在墻上”,“小娃娃粑他自家媽媽”。以母文引申義“緊貼著”為義核的母文“巴”,加類屬標注“米”不僅代表粑這種食物是使大米經過捶打后更加緊實的,也引申為緊貼,依戀義。
豝,《說文·豕部》:“豝,牝豕也。從豕,巴聲。一曰一歲,能相把拏也。”[5]194段注:“一曰二歲豕,能相把拏者也。”[11]455《詩經·召南·騶虞》:“彼茁者葭,壹發五豝。”毛注:“豝,豕牝曰豝。”[26]102《爾雅翼·釋獸六》:“豝,牝豕之小者,故又謂之小豝。”[27]又《廣雅·釋獸》:“獸,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肩,四歲為特。”[28]388可知豝是母豬之義,并且是小母豬。從豕,從巴。“豕”豬之義,“巴”引申義作“挨近”之義,加類屬標注后表示幼小的母豬總是依附挨近在母豬身邊。
杷,《說文·木部》:“杷,收麥器。從木,巴聲。”[5]117《釋名·釋用器》:“杷,播也,所以播除物也。”[2]202《玉篇·木部》:“杷,步牙切。收麥器也。”[20]236《急就篇》:“捃獲秉把插捌杷”顏師古注曰:“無齒為捌,有齒為杷,皆所以推引聚禾谷也。”[29]可知,杷是一種聚攏鋪散谷物的農具。《廣韻·麻韻》:“杷,枇杷木名。”[17]48當“枇杷”連用時指果名。“杷”多用竹制作。王褒《僮約》:“屈竹作杷,削治鹿盧。”[30]在義核為“挨近”的母文“巴”上加類屬標志“木”,表示把麥子收攏的農器。
在母文“巴”的引申義為“挨著、靠近、緊貼著”的詞義上,通過加類屬標志“女”“爪”“米”“豕”“木”后,得出此類“巴”族字在字形上有共同的發聲源,讀音上相同或相近,字義上都是在“巴”的引申義上孳乳而成。其中“妑”字在方言書中,筆者尚未查詢到,但在貴州印江鄉鎮方言中有將“妑”字,表“奶奶”義。
(三)以母文引申義“干燥或粘結著的東西”為義核的“巴”族字
疤,《正字通·疒部》:“疤,邦如切。音巴。俗呼瘡痕曰疤。本作瘢。”[18]705《說文·疒部》:“瘢,痍也。從疒,般聲。”“痍,傷也。從疒,夷聲。”[5]152可知“瘢”“疤”義通。因此在義核為“干燥或粘結著的東西”的母文“巴”上加類屬標志“疒”,表示創傷或瘡癤等痊愈后留下來的痕跡。
耙,形聲會意字。篆文從金,罷聲。隸變后楷書寫作?。異體作?,從耒……如今規范化,以耙為正體[31]。可知,?為耙的源字,《說文·金部》:“?,?屬。從金,罷聲”[5]297《樹藝篇·蔬部》講了種蒜的要點,并說清楚了耙與犁的相互搭配使用,“每畝上糞土數十擔,再用犁翻過耙,勻手持木橛。”[32]《國脈民天》記載了耙的作用是“其耕、種、耙、耢,上糞俱加數倍,務要耙得土細如麪。”[33]《王禎農書》指出其在農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與其他工具使用的先后順序:“耙功不到,土麄不實,下種后雖見苗,立根在麄圖,根土不耐旱,有懸死、蟲咬、干死諸病……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耙之,欲其土細;再犁再耙后用勞,乃無遺功也。”[34“]耒”篆文作“”形體像木叉狀的農具,以母文引申義“干燥或粘結著的東西”為義核加類屬標注“耒”,表示軋碎粘結成土塊使土地平整的農具。
羓,最早記載于《集韻·麻韻》:“羓,臘屬。”[19]60《說文·肉部》:“臘,冬至后三戌,臘祭百神。”[5]83段注:“臘本祭名,因呼臘月、臘日耳。”[11]172“臘”本是指年終祭祀,古代祭祀常用牛、羊、豬等。至今各地在春節時都保留了準備香腸臘肉這一風俗習慣。據《集韻》所載可知,羓亦是臘屬類。后經過演變指的是干肉,《韻略易通》:“羓,干肉。”[35]《新五代史·四夷附錄第一》:“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焉。”[36]這與后人制作臘肉略有相似之處。“羓”從羊,從巴。在以“干燥或粘結著的東西”為義核的母文“巴”字,加類屬標注“羊”后孳乳成“羓”。最開始是指羊肉又從“巴”后演變成經過加工后變干的肉,類似于現在春節的臘肉。
(四)以母文引申義“依附、攀附,附著、黏著”為義核的“巴”族字
笆,《玉篇·竹部》:“笆,竹有刺。”[20]274《集韻·麻部》:“笆,竹之有刺者。”[19]60《正字通·竹部》:“笆,竹之有刺者,卷曲繁猥。”[18]791這是一種帶刺的竹子,堅固牢靠。在古代常用來保護院子、分界等作用。《廣韻·麻部》:“笆,有刺竹籬。”[17]47笆竹也就是棘竹,晉人戴凱之《竹譜》:“棘竹生交州諸郡,叢初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實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彼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棘竹)一名笆竹,見三倉,筍味,落人須發。”[37]《酉陽雜俎》所載大致相同,不同之處云:“棘竹,一名笆竹……南夷種以為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翁,縱橫相承,狀如繰車。食之落人齒。”[38]《水滸傳》第四回寫到:“須籬笆用棘荊編。”[39]《今古奇觀》卷十二載:“見矮矮籬笆,圍著一間草屋。乃推開籬障,輕叩柴門。”[40]在母文“巴”以引申義為“附著,黏著”的義核,加代表竹子的類屬標注“竹”,表示一種帶刺的竹子沿著分界線種植而形成的籬笆。且“巴”的本義指一種大蛇,大蛇盤旋在一起也像棘竹的根系盤根錯節。
跁,《玉篇·足部》:“跁,跁跒,不肯前。”[20]133《廣韻·祃韻》:“跁,跁踦,短人。”[17]123《正字通·足部》:“跁,今俗謂小兒匍匐曰跁”[18]1117陸龜蒙《報恩寺南池聯句》:“跁跒松形矮,般跚檜樾矬。”[41]9020在義核為“攀援、依附、攀附”的母文“巴”上加類屬標志“足”,表示小兒匍匐。
弝,《廣韻·祃韻》:“弝,弓弝。”[17]123《正字通·弓部》:“弝,肘中手執處”[18]338《射學》卷一“執弓”中指出:“即以掌心頂弝,猶如握卵,不可橫把”[42]元稹《酬樂天東南行》:“當心鞘銅鼓,背弝射桑弧。”[41]4542。在義核為“攀援、依附、攀附”的母文“巴”上加類屬標志“弓”孳乳出“弝”,表示弓背中央手附著的部位。
(五)以母文引申義“盼望”為義核的“巴”族字
爸,《集韻·祃韻》:“爸,吳人呼父曰爸。”[19]355王念孫的《廣雅疏證》:“爸者,父聲之轉。”[28]200。在漢語文獻中對父親最早的稱謂不是“爸”而是“父”,早在《詩經·小雅·蓼莪》就已出現:“父兮生我,母兮鞠我。”[26]670《儀禮·喪服》:“父至尊也。”[43]對于從“父”過渡到“爸”許多學者都討論過,章炳麟在《新方言·釋親屬》中說:“今通謂父為爸。古無輕唇,‘魚’‘模’‘轉’‘麻’,故‘父’為‘爸’。”[44]清代學者錢大昕提出了一條漢語聲母演變規律“古無輕唇音”[45]今人李新魁先生有更明確的說明。他說:“古人稱父為‘父’,口頭上一直保留[pa]音,[pa]就是‘父’字上古的讀法,但‘父’字屬古音的魚部字,后來它的讀書音隨著其他魚部字一起變為[u]的音,聲母也從重唇變為輕唇,但口語(特別是楚方言的口語)仍存[pa]音,結果,人們即在‘父’字下加上一個表示讀音的‘巴’。”[46]“巴”有期盼、盼望之義,加上類屬標注孳乳出“爸”,代表父親在家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是威望,全家對他都是有所期待的,在口語中也多以“爸爸”來表示父親的意思。
(六)以母文引申義“挖,刨”為義核的“巴”族字
三、聲符“巴”僅表音與字義無關
邑,《說文·邑部》:“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卪。”[5]127甲骨文作“ ”上部是一個方框,指封地。下部似人形,義為民。可會出有土地、有人民的方國之義。篆文作“”,訛以人為卪,失其形。隸書、楷書沿篆文之形而定體,偏離其原形甚遠。因此,此字不屬于“巴”字族。琶,《說文·珡部》新附字:“琶,琵琶也。從珡,巴聲。義當用枇杷。”[5]267“琵琶”又稱“枇杷”。漢代的劉熙《釋名·釋樂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2]207同是漢人的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記載:“批把,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弦象四時。”[49]在最初的枇杷,是一種直柄圓形的共鳴箱。南北朝時,通過絲綢之路與西域進行文化交流,現今的曲項琵琶就是由古波斯語“barbot”的音譯而來。
肥,《說文·肉部》:“肥,多肉也,從肉,從卪。”[5]85徐鉉注曰:“肉不可過多,故從卪。”篆文從肉表示與人體有關,從卪。“肥”為肉多,必須節制,所以從“卪”。隸書從篆文來。楷書右邊由“卪”誤變成“巴”。
以上所列之字,由于時間久遠,這些字當初如何得義難以考證,也難以分析其與母文之間的內在聯系。在此列出,暫且看作母文表音之字。
四、結語
漢字字族是漢字在歷史發展中為適應詞義的引申派生而形成的,其出現非偶然而是事物發展的自然很規律,是漢字適應漢語發展的一個特殊標志。以母文的本義、引申義及假借義為義核,加上不同的類屬標志后,其意義更加具體化、標簽化、貼切化,增強了漢字之間的區別度。
本文通過“巴”族字的探析,以求發現漢字孳乳分化的內部規律,它們在字形上有共同的發生源,讀音上相同或相近,在后面的孳乳后雖無顯性聯系,實則本同末異。就如同人類的宗族關系一樣,通過每一代人的生育繁衍,雖看似不相干,但追根溯源會發現其源自同源。筆者學識尚淺,對“巴”族字的研究廣度深度有限,不足之處懇請方家指正批評。
注釋:
①本文所錄的甲骨文、篆文均出自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