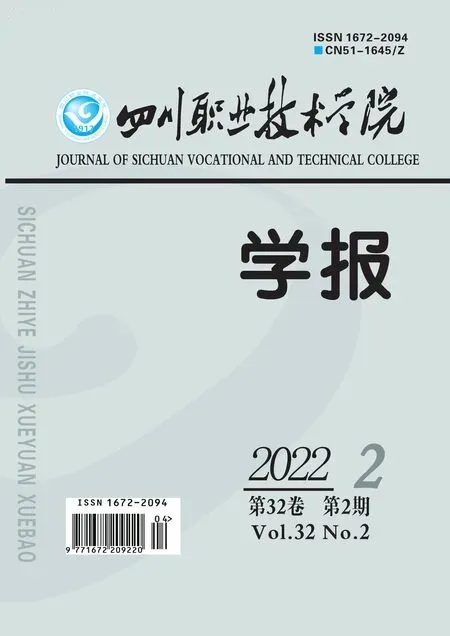論《竹坡詞》的俳諧書寫
黃夢瑤
(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所謂徘諧詞,指是的運用隱喻、反諷、夸張、嘲謔等手法寫成的,以一種游戲調笑的面目來凸現詼諧、幽默意趣的詞作。……詞史上又有滑稽詞、戲謔詞、諧謔詞、徘體詞、戲詞、幽默詞等諸多表述不盡相同的說法。”[1]作為宋詞的一種特殊的類別,俳諧詞的產生和發展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則由于俳諧在我國傳統的文學創作中源遠流長,到了宋代,詞的創作迎來盛況,不免深染其風;二則受到“詞為小道”的傳統詩文觀的影響,用作娛賓遣興的詞最終與俳諧所秉持的審美意趣相契合。王毅的《中國古代俳諧詞史論》認為“宋代是俳諧蔚為大觀的時代,數量多,作家多,而且好的作品多……”[2],俳諧詞的創作伴隨著整個宋代的進程得到了長足發展。北宋前期的俳諧詞多文字游戲和游冶艷情之作,中期則隨著國勢日危,詞人入世憤世的主觀情志漸深,從專事日常嘲戲諧謔過渡為嬉笑怒罵式地抨擊時弊與干預現實;后來在南宋詞人的手中進一步雅化,南宋末年則詞中更多借俳諧以感江山覆滅之哀音,痛發黍離之悲。無疑,南北宋之交是俳諧詞發展的重要階段。
周紫芝,生于南北宋之交,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字少隱,先后號竹坡老人、靜寄老人、妙香寮老人、二妙老人等。他的一生著述頗豐,見于著錄的著作達12 種之多,今存詩文集《太倉梯米集》、詞集《竹坡詞》(又名《竹坡老人詞》)以及《竹坡詩話》《詩漱》4 種。雖不屬于聲名顯赫的大家,但他的詞作依然十分可觀。周紫芝詞作取法秦觀,有“嬉笑之余,溢為樂章,則清麗宛曲”[3]537之譽,即使在宋南渡之后,他的詞中也少有感時之作。由于長期沉淪下層、茍存亂世,周紫芝后來依附于秦檜,阿諛獻媚地大唱贊歌為眾多文人所不齒,晚年則選擇歸隱廬山。《竹坡詞》是他特殊的心靈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證,俳諧則作為一種文字遣懷游戲出入于這百余首詞作之間。
一、《竹坡詞》中俳諧的呈現方式
(一)標明戲作
最直接的呈現是詞人在序中或題目中明確交代的帶有“戲作”“解嘲”字眼的詞作。這些詞作往往先交代背景,再點明為戲作,俳諧的用意十分明顯。
如《木蘭花》,在清麗詞句中暗置的巧妙俳諧:
長安狹邪中,有高自標置者,客非新科不得其門,時頗稱之,予嘗語人曰:相馬失之肥,相士失之瘦,世亦豈可以是論人物乎!戲作此詞,為花衢狹客一笑。
嫦娥天上人誰識。家在蓬山煙水隔。不應著意眼前人,便是登瀛當日客。
雙眸炯炯秋波滴。也解人間青與白。檀郎未摘月邊枝,枉是不教花愛惜。[3]539
這首詞寫的是長安某妓女自置清高,要求客人必須是新科進士,否則一律拒之門外。詞人作詞調侃此事,將這位妓女比作天上嫦娥,而她接客的這一規定,難度之大就像隔著蓬山煙水。整首詞表面曲辭甚雅,背后卻充滿了俚俗之味,這種有趣的對視,使得俳諧的意味大大增加。不僅借此表達了詞人對這一“時人稱之”的現象的不解與鄙夷,也似乎有仕途多舛的詞人被“新科”二字被冒犯之后,故意在詞中流露出的一種嘲諷與不屑。
又如《千秋歲》,是標為戲作但俳諧意味并不突出的一類:
春欲去,二妙老人戲作長短句留之,為社中一笑。
送春歸去。說與愁無數。君去后,歸何處。人應空懊惱,春亦無言語。寒日暮,騰騰醉夢隨風絮。 盡日間庭雨。紅濕秋千柱。人恨切,鶯聲苦。擬傾澆悶酒,留取殘紅樹。春去也,不成不為愁人住。[3]548
這首詞是周紫芝集社時所作,春日將近,詞人用對話的口吻挽留春色。先問春歸何處,春既然不回答,人也只是憑空懊惱。就算再感時傷春春天也已經離開,是不會為我們這些“愁人”而停留的。讀來只覺清麗婉約,寓有情趣,頗有晏、秦遺風,雖題云一笑,卻全然不入調笑媚俗之流。
(二)游戲對話
除了直接點明為“戲作”的詞之外,周紫芝的其他詞作中也有不同的俳諧意趣,特別是他的部分贈友詞和唱和詞。
周紫芝一生交游甚多,“《竹坡詞》中涉及到的交友唱和人數多達20 個”[4]。戲謔調侃是周紫芝與朋友交往中常有的筆調。如《鷓鴣天·和劉長孺有贈》中“閑院靜,小桃開。劉郎前度幾回來”[3]540,“前度劉郎”一詞是化用劉禹錫的《再游玄都觀》中“前度劉郎今又來”[5]之句,劉禹錫本意是表達其被貶謫多年歸來仍然不改初衷、堅持斗爭的倔強意志,周紫芝則取用了桃花與劉郎之間形成的語典聯系用作調侃之意。而恰好周紫芝的這位劉姓的朋友,此前也歷經了“追其官,囚之百日,長孺終不屈”[6]13332的一場劫難,周紫芝此番用意,俳諧之外又有勉勵。但“劉郎”一詞在《竹坡詞》中多次出現,像“武陵春盡無人處,猶有劉郎去后蹤”[3]540、“前度劉郎,莫負重來約”[3]542“劉郎前度,空記來時路”[3]546幾乎全出自同一語典,也未免有重復之嫌。
“兩宋詞人的壽詞創作并非是純粹的藝術活動,正如沈松勤在《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中所說:‘它主要是一種風俗行為,是社交生活中不可或卻的禮數之一。’”[7]周紫芝的祝壽詞中極少有迎合和俗套的祝壽語,往往寄以對朋友的真情實感,表達對友人的祝福,訴說內心的想法。語言凝練自然又富有哲理,顯得生動幽默。如《鷓鴣天·李彥恢生日》中“新來學得長生訣,寫就黃庭不換鵝”[3]540,再如《鷓鴣天·沈彥述生日》中“瓊林不逐春風老,安用丹砂巧駐顏”[3]540。還有詞人向朋友孫祖恭求蘼酴,先說“老去惜春心,試問孫郎知否”[3]545,意為我雖然已經老了但是仍有一顆憐惜春意的心,然后再問“剪取一枝重嗅”。在周紫芝的諸多祝壽詞中,有兩首是寫給妻子的,在同時期的詞人中比較少見。與贈友詞有所不同,夫妻關系的親密性讓詞人能更加自由的呈現出真實的心境,在語言上更是無需顧及太多必要的斟酌。如《點絳唇·內子生日》
人道長生,算來世上何曾有。玉尊長倒。早是人間少。
四十年來,歷盡閑煩惱。如今老。大家開口。贏得花前笑。[3]546
這首詞顯然更像是一首回憶詞,采用更加口語化表達,細數與妻子相處的四十年的時光,歷盡了人世間的各種煩惱,現在已經年老了,卻仍不忘在花前互相逗樂打趣,篇幅短小卻真摯感人。
(三)談笑自嘲
除了作有大量的贈友贈親詞外,周紫芝還有部分嗟老自嘆詞,其中一首為自己所作祝壽詞《水調歌頭》寫得極妙,雖言祝壽且筆調悠然,實際上皆是詞人對生命的思考與人生的感懷,亦有對自我的反思與諷喻。
十月六日于仆為始生之日,戲作此詞為林下一笑。世固未有自作生日詞者,蓋自竹坡老人始也。
白發三千丈,雙鬢不勝垂。人間憂喜如夢,老矣更何之。蘧玉行年過了,未必如今俱是,五十九年非。擬把彭殤夢,分付舉癡兒。 君莫羨,客起舞,壽瓊卮。此生但愿,長遣猿鶴共追隨。金印借令如斗,富貴那能長久,不飲竟何為。莫問蓬萊路,從古少人知。[3]539
上闋開篇即為自嘆,白發已老,人間的憂傷和喜悅其實最終都如同夢幻一般。可嘆自己空長了五十九歲了,原來期望像彭祖一樣長壽的人其實都是一些“癡兒愚夫”,而自己又何嘗不是曾經的一個。現在已經不再懷有這樣的期待,就將這個愿望分給那些還沒有醒過來的人們。在下闋中,告別了彭祖夢的詞人,更加向往那閑云野鶴的生活,既然富貴不能長久,那就只管飲盡杯中酒罷。戲言之間,句句嘲諷癡兒同時又是句句嘲諷從前的自己。
這種獨特的解嘲方式,在《鷓鴣天·年少登高意氣多》中還有更深的體現。
年少登高意氣多。黃花壓帽醉嵯峨。如今滿眼看華發,強捻茱萸奈老何。
千疊岫,萬重波。一時分付與秦娥。明年身健君休問,且對秋風卷翠螺。[3]540
詞人先是回憶自己年少的意氣風發、插花游山的得意情景。轉眼又是重陽登高卻是滿頭白發了,只能捻一棵茱萸無可奈何。極目遠眺,看到的是重巖疊嶂、萬里江波,不要問明年我的身體會怎樣,姑且對著秋風梳起翠螺一樣的發飾。實際上,無論是飲盡杯中酒還是對秋風束發,周紫芝的嗟老自嘆詞中,俳諧常常是一種“帶淚的笑”,對年華逝去的遺恨和留戀,在詞人的心中通過不同的排解方式實現了情感自洽,而這種自洽的方式,正是得益于俳諧。
既要講俳諧,就不能不提到“笑”。“笑”字的多次呈現,是周紫芝俳諧意趣的生動表現,而“笑”的不同含義,是詞人在俳諧語境下不同心態的呈現。如《水龍吟·須江望九華作》中:“堪笑此生如寄,信扁舟、釭來江表。”[3]538和《水調歌頭·雨后月出西湖作》中:“問明月,應解笑,白頭翁。”[3]540是詞人自嘆身世飄零的可笑與無奈;如《小重山·方元相生日》中:“一笑且踟躕。會騎箕尾去,上云衢。”[3]541是詞人年華逝去的達觀與解嘲;縱觀詞集,詞人筆下提到的“笑”大多記錄的都并非是真正值得開心的事,恰恰是愁悶難解時和悲嘆命運時更喜用“笑”字,其俳諧的表象后面是詞人復雜的內心活動。
二、《竹坡詞》中俳諧的創作特點
(一)喜用詞序
周紫芝作詞喜用詞序,用于交代創作緣由、動機、背景、心態等,“內容比較簡約,篇幅短小,但是涵蓋的內容比較廣泛,一與詞本文交相輝映,相得益彰。”[8]38如前文提到的“戲作”詞基本上都可以通過詞序中得到提示。除了客觀的交代寫作的情況,詞序與詞本身也構成了詞人對整個事件的態度、想法和情感等。如《漁家傲》:
重九前兩日,游真如、廣孝二寺,木犀方盛開,而城中花已落數日矣。郡人以扶疎高花絕勝水南,因為解嘲,呈元壽知縣。
路入云巖山窈窕。巖花滴露花頭小。香共西風吹得到。秋欲杪。天還未放秋容老。
誰道水南花不好。猶勝金蕊渾如掃。留取光陰重一笑。須是早。黃花更惜重陽帽。[3]543
從序中可知,此詞創作于重陽節的前兩天,詞人在真如寺和廣孝寺游玩,看到木犀花開放,但是此時城中的花早已凋謝,這些枝葉茂盛,高低疏密有致的花朵雖不在城中,但亦不失為佳景,詞人將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通過詞序傳達出來,將詞作諧在何處做了充分的點明。
如前文提到的《木蘭花》的序:
長安狹邪中,有高自標置者,客非新科不得其門,時頗稱之,予嘗語人曰:相馬失之肥,相士失之瘦,世亦豈可以是論人物乎!戲作此詞,為花衢狹客一笑。[3]539
由于這首詞中全部借嫦娥比妓女,如果不借助詞序,就難以理解詞意。
再如《浣溪沙》三首的序:
今歲冬溫,近臘無雪,而梅殊未放。戲作浣溪沙三疊,以望發奇秀。[3]538
也只有讀完詞序后,方能對詞中借“嫦娥”、“潘玉奴”比喻梅花有更深刻的感悟。
(二)雅俗共賞
周紫芝的俳諧詞作并不俚俗,與宋代前期和民間的俳諧意趣追求不同,周紫芝的俳諧中帶有一種詩意的情趣與幽默。周紫芝的詞善用典故,初讀不甚著意,很難讓人一眼就領悟到俳諧的幽默感,是一種文人專屬的詼諧。如“戲作”的《浣溪沙》中“便須千杖打梁州”[3]538語,用唐玄宗揭鼓催花之事典,意在期待梅花早日開花;再如《浣溪沙·和陳相之題煙波圖》中“一尺鱸魚新活計,半蓑煙雨舊衣冠”[3]538一句,用了西晉張翰因思念家鄉妒魚羹而棄官歸鄉的事典。
善用典故,同時又能避免太過于典雅的詞作喪失掉詼諧的情趣,將日常的口語化入詞中時,周紫芝十分注意到分寸和火候,能恰如其分的使用這些口語卻不會墮入俚俗的圈套中,讀來令人感到鮮活生動,實現雅俗共賞。如他的《感皇恩·無事小神仙》:
竹坡老人步上南岡,得堂基于孤峰絕頂間,喜甚,戲作長短句。
無事小神仙,世人誰會。著甚來由自縈系。人生須是,做些閑中活計。百年能幾許,無多子。 近日謝天,與片閑田地。作個茅堂待打睡。酒兒熟也,贏取山中一醉。人間如意事,只此是。[3]547
先是在詞序中說明了此篇為“戲作”,首句化用了周邦彥的《喜遷鶯》:“此時情緒此時天,無事小神仙”[3]187的句子,想到如今自己已經是來去自如的閑散之人,百年之中,追求閑暇似乎才是真正的快樂。于是詞人把種一方小田、在茅屋里酣睡、山中飲酒醉看作是人間的如意事。其中“須是”“做些”“作個”等口語化的表達,幽默但不失理趣,閱盡世事后的隱逸閑適之情躍然紙上。這些口語化的句子,詞人都能信手拈來,隨意而發,不事雕琢,自然生動。這種口語化的輕松姿態,在其他的詞中亦有生動的體現,如:
你去也,今夜早來么。(《小重山·溪上晴山簇翠螺》)[3]541
照得人來,真個睡不著。(《醉落魄·江天云薄》)[3]542
無人共說,這些愁寂。(《西地錦·雨細欲收還滴》)[3]542
難受。難受。燈暗月斜時候。(《宴桃園·簾幕疏疏風透》)[3]545
不如辦個,短蓑長釣。(《感皇恩·殘月掛征鞍》)[3]547
杜鵑只解怨殘春,也不管、人煩惱。(《憶王孫·絕筆》)[3]548
(三)小令為主
周紫芝所處的南渡時期已不是小令詞的天下,但詞人仍然喜用小令調。“<竹坡詞>156 首,其中小令108 首,中調30 首,長調18 首,小令詞的比重占全詞的三分之二以上。”[8]32周紫芝的俳諧詞作中,亦多以小令為主。由于小令篇幅較短,含蓄蘊藉,語言節奏明快、精煉,最能營造“語意高妙”之境。因此,俳諧意趣在小令中能發揮最大程度的藝術效果,使人讀來能啞然失笑,或在最精彩的時刻戛然而止,使俳諧效果余味無窮。如前文提到的兩首周紫芝為妻子所寫的祝壽詞,都是小令,字數雖少卻情意深長。另如《好事近》:
簾外一聲歌,傾盡滿城風月。看到酒闌羞處,想多情難說。
周郎元是個中人,如今鬢如雪。自恨老來腸肚,誚不堪摧折。[3]547
上闋簾外歌聲,伴著酒酣,一番快活自在景象。下闋“周郎元是個中人,如今鬢如雪。”自己曾是此景中人,然而早已青春不在,迅速從一種酒酣興盡的快樂中陷入了青春易逝的感傷,然而詞人沒有繼續放大這種感傷,“自恨老來腸肚,誚不堪摧折。”卻調侃遺憾自己老了肚腸,經不起這種折騰了。用極為幽默的寥寥數語將上一秒的感傷掩飾過去,且該詞篇幅極短,無需反復掩飾,達到了一種點到即止的排解之效。
三、《竹坡詞》中俳諧的現實功用
(一)自遣療傷
雖然幽默是一個舶來詞,但中國的古人從來就不缺乏幽默感。俳諧作為在詞史中并不受重視的一種風尚,卻綿延傳遞且韻味獨特,這與其自娛的功能性是分不開的,實際上我們也正是通過這些帶有自遣性質的詞作去了解詞人的內心世界。周紫芝的俳諧詞作創作的時間不一,反映出他不同時期的特殊心理活動,從早年的意氣風發到最后遠離官場,周紫芝的人生在跌宕中起起伏伏,行藏之處和內心懷抱于詞中隨處可見。就俳諧一種而言,還是他晚年所作的幾首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在短暫的為官生涯結束后,周紫芝意識到從前夢寐以求的官場的真實模樣,是自己不惜以年老與人格為代價進行的交換,屢屢在詞中發出嗟老自嘆和悔意。如:
“如今始信從前錯。為個蠅頭,輕負青山約。”(《醉落魄·柳邊池閣》)[3]542
“丹砂豈是神仙訣。世間生死無休歇。”(《醉落魄·云深海闊》)[3]542
“人生長少。富貴應須致身早。……假饒真百歲,能多少。”(《感皇恩·除夜作》)[3]547
詞人巧妙地將這種自遣之句化為幽默之詞,通過俳諧對自己的身心進行調節,試圖掩蓋內心的一種真實的悲傷和哀嘆,對自己人生的重新思考與定位。特別是在困境中的笑,于身心而言都是一種良好的療傷手段。
(二)社交娛友
文學遣興娛情的功能早已有之,雖然有時被文學的政教功用所掩蓋,但文學用于娛樂的作用始終沒有消失過。人們的交往常常離不開幽默的言辭,真正的朋友之間更是常常互相調侃而不慍怒。幽默是人際交往過程中的潤滑劑,不僅可以增進友人之間的感情,還逐漸成為文人日常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竹坡詞》中的交游詞數量較多,是周紫芝一生廣交朋友的佐證,他選擇各類可以調侃的話題入詞,即使是鄙俗粗野的話題,甚至是格調低下的狹邪惡趣,有些俗不可耐,有些雅俗共賞,還有些以雅掩俗,無論以哪種面貌現身,都帶有十分鮮明的文人氣息。雖然并不是所有的俳諧都是為了開心,笑聲背后有時候往往帶著尖銳的批判利器。如前文提及的妓女接客新規,雖然讀來使人發笑,這何嘗不是對當時活在才名焦慮下的士子們的一種無形的嘲諷與摧殘。但是縱觀整本《竹坡詞》,周紫芝依然慣以個人的生活日常入詞,這種批判也極為少見,更鮮見對當時已經山河破碎的家國之關懷。
四、結語
《竹坡詞》雖然存詞數量不少,在創作藝術上也并不遜色,但鮮有人重,無疑這與周紫芝晚年依附秦檜的經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然而,我們能否簡單將周紫芝與“老而無恥”的名聲完全聯系起來,答案是否定的。回到文學發生的現場,周紫芝的處境,當是我們對于理解周紫芝的這種選擇時必須要考慮的。作為一個出身貧寒的文人,周紫芝的科場生涯是坎坷的,而對于仕途之路的渴求,讓周紫芝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換句話說,秦檜為周紫芝的出頭之日提供了唯一的希望,而秦檜的欺世行為卻把周紫芝一起拖入了為人所不齒的行列,這種復雜的情感伴隨著周紫芝的的生命。“在他的詞中,我們看到的是在命運擺弄下一個靈魂不斷尋求慰藉和不斷掙扎的過程。”[9]生活在南北宋之交這一特殊時期,周紫芝也沒有像部分的南渡詞人一樣創作憂國豪壯的詞篇,“和朱、李、向等南渡詞人抒發離黎之悲的作品相比,在格調上是有高下之分的。……周紫芝雖有國破之悲,但無家亡之痛。”[10]周紫芝所書寫的俳諧意趣或許來自于他先天的幽默,或許有一些后天的無可奈何,但他的出現,是俳諧詞風開始向曠達自適和逐漸雅化的特點轉變的重要代表。于是,他要真正呈現給世人的,并非他世俗的本相,而是經過了一系列情感加工后的詼諧感。這種情感,我們不能簡單斷言不夠真實,而是需要對其撥繭抽絲,才能看到詞人試圖營造景象背后的秘密,至少我們看到了正襟危坐的文人墨客們,也有游戲人生的普通之處,一個人,從來不應該被簡單地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