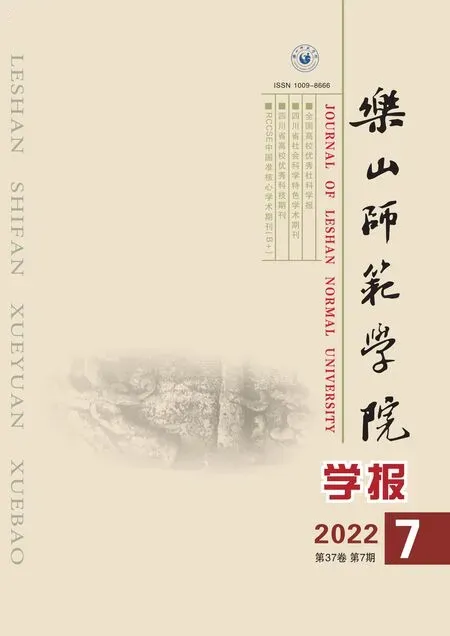麥卡錫主義語境下垮掉派文學電影改編策略
邱食存
(1.四川文理學院 外國語學院,四川 達州 635000;2.四川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1)
20 世紀50 年代,“垮掉的一代”文學與文化運動在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橫行美國之際勃然興起。作為美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教徒(WASP)天命觀(Innate Mission)與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等核心價值觀的當代翻版,麥卡錫主義是美國盎格魯一致性(Anglo-conformity)價值觀體系的極端表達,其極端性就在于“一些機會主義無良政客為了獲取政治利益而不惜將普通美國民眾推向歇斯底里絕境,并進而利用民眾這種歇斯底里心理毫無根據地攻擊對手”[1]13。而以克魯亞克(Jack Kerouac)、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為主要代表的垮掉派作家與美國一些獨立制片人、爵士音樂家等先鋒藝術家則拒絕同流合污,堅持以邊緣人視角對盎格魯一致性主流話語敘事不斷地進行著背反性書寫。
鑒于“垮掉的一代”運動有著文學與文化運動雙重屬性,從文學與文化雙重維度來考察垮掉派文學應予以足夠重視。從垮掉派文學電影改編來看,先后有克魯亞克的劇本《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小說《地下人》(The Subterraneans,1958)、《在 路 上》(On the Road,1957)以及金斯伯格的長詩《嚎叫》(Howl,1956)、巴勒斯(Williams Burroughs)的小說《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1959)等不少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然而,國內外相關研究顯得較為薄弱。國外方面,隨著20 世紀50 年代末美國新電影的興起,以泰勒(Parker Tyler)為代表的傳統派與以梅卡斯(Jonas Mekas)為代表的改革派之間爆發了激烈論爭,而以劇本《垮掉的一代》為藍本的改編電影《拔出雛菊》也成為論爭的一大焦點。梅卡斯一直將《拔出雛菊》視為美國新電影的典范之作,寫有多篇文章探討了該片與原著之間的互文關系。馬林斯(Patrick Mullins)則撰文深入分析了好萊塢同名改編影片《地下人》背后的收編策略[2]。國內相關研究則更為稀缺。金雯的碩士學位論文從反文化視角簡略地考察了《赤裸的午餐》的改編情況,認為電影《赤裸的午餐》在某種程度上是“同名小說的傳記”[3]。碩士學位論文《電影<嚎叫>的去神秘化》(2014)則從視覺、聽覺、史料三個視角,檢視了影片《嚎叫》如何從抽象和具象兩個方面詮釋同名詩歌并最終再現詩歌背后的時代背景[4]。兩篇論文都注意到作品時代背景的重要性,但對時代背景的歷史與文化根源的挖掘還有待深入。
總體來看,現有相關文獻對“垮掉的一代”運動中相輔相成的文學與文化雙重屬性的剖析還遠遠不夠,“垮掉的一代”運動對麥卡錫主義以及冷戰文化的背反書寫還有待進一步挖掘。本文力圖剖析美國當局推行的冷戰文化與麥卡錫主義的理論淵源與精神實質,并進而回答,在絕大部分民眾甚至是現代主義權威作家都采取隨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的做法之時,垮掉派作家作為冷戰文化中的異類,是如何以獨立電影的形式來消解好萊塢影視對垮掉派文學同化性電影改編策略的。
一、麥卡錫主義:美國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的極端表達
作為一種典型的教化理論,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要求每個移民都接受美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群體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徹底放棄自己祖先的文化”[5]77。從美國社會歷史進程來看,WASP 文化中的天命觀與白人至上主義業已成為美國國家性格而不斷得到強化。天命觀是指美國清教主義信徒相信自己作為“上帝選民”(Chosen People)負有上帝交托的傳播基督福音的使命。身負天賦使命的新教徒在開拓北美大陸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為美國早期擴張辯護的白人至上主義論調。作為一種典型的白人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白人至上主義“主張白人的利益高于其他有色人種的利益,要求維護白人在美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中的主導地位”[6]。在這種價值觀的指引之下,美國建國之后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也充斥著種族主義色彩,尤其是歷屆美國政府所強制推動的“西進運動”對北美印第安人近乎種族滅絕的宰制政策以及對黑人系統性的種族歧視與剝削。通過這種系統性的剝削和殺戮,WASP 群體牢牢地掌握著主宰性地位。
與天命觀與白人至上主義同根同源,麥卡錫主義是美國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在當代的極端表達。1950 年,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堅稱他已經“掌握”一份已滲透到民主黨政府內部的“205 名”共產主義間諜名單,但僅11 天之后,這份“虛構的名單”就變成了“81名”[7]16。1954 年12 月2 日,民主黨占多數的參議院通過正式譴責麥卡錫的決議,麥卡錫黯然退場。可以說,麥卡錫主義是朝野兩黨黨爭以及美國當局為轉移國內種族主義矛盾與工會抗議浪潮而將共產主義當作替罪羊的必然結果。通過將反共與維護國家安全掛鉤,激發民眾所謂的愛國主義從而達到強化盎格魯一致性同化的目的。以麥卡錫主義為核心,冷戰被塑造為一場抗擊所謂共產主義“異教徒”的“圣戰”[8]12。美國在國際上采取的“全面遏制”政策對美國國內政治與主流價值觀體系也起到了全面重塑的作用:先是聯邦政府雇員遭到大規模調查,數千人遭解雇;不久,這類調查擴散至美國全境,“不允許任何不信仰美國意識形態的人居住在美國”,極力慫恿美國民眾“告密”以便讓“顛覆分子”無處藏身;由于政府當局的欺騙與誘導,當時有幾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即便沒有真憑實據,任何人都有責任向政府揭發可疑者,由此,美國政府當局把“整整一代美國人都變成了密探”[9]8-9。
二、“垮掉的一代”運動對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的背反
從文學與文化思潮的角度來看,“垮掉的一代”無疑是冷戰文化中的異類。在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看來,現代主義屬于一種可以“給政治運動、社會制度、思想方式等提供權威的功能”的“宏大敘事”[10]57。這種宏大敘事把一切個別性與差異性都統攝于具有整體性與一致性特質的絕對精神之中,使之喪失自身的獨立性。于是,以艾略特(T.S.Eliot)為代表的現代主義創作得到了美國官方支持,成為當時絕對意義上的主流文學與文化。
與此相對,克魯亞克與金斯伯格等垮掉派作家是“為主流文化所唾棄”的“異端邪說的絕妙象征”[11]3-4。與主流文化所極力塑造的具有崇高品格的英雄形象不同,垮掉派作家大多屬于反英雄。他們不但多數有著少數族裔身份,而且還有著“反常”的性取向。事實上,二戰以來,由于黨爭的需要,美國共和黨一直將民主黨政府治下的美國建構為易于受到共產主義攻擊、孱弱的女性形象,必須受到強有力的男性的保護。因此,麥卡錫主義者將同性戀視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行為反常者(perverts)”[12]577-594,是有損于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的共產主義“同情者(fellow traveler)”[13]197。為了擺脫美國國會及政府當局所采取的所謂理性、技術以及體制上的全面壓制,垮掉派作家則竭力主張性自由甚至公開自己的同性戀性取向。垮掉派作家不相信政府、教會以及文學機構等一切形式的權威,他們吸食毒品,沉湎于比波普爵士樂與搖滾樂,試圖以感性的無政府主義生活方式來實現自我解放和個性自由。
具體到文學而言,后現代主義文學也與垮掉派作家有著莫大的關系。卡林內斯庫(Matei Cǎlinescu)在其名著《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明確指出,包括垮掉派詩人在內的美國后現代詩歌流派最早在20 世紀40 年代后期提出并實踐“后現代主義文學”[14]138概念。文學是反映社會意識與文化氛圍最為重要的表現形式之一。后現代主義文學體現了一種二戰以來突顯差異性與多樣性的時代精神,它批判統一性與整體性等現代主義理性思維,要求人們以新的思想與行為方式去思考、感知并采取相應的行動。面對美國當權者借冷戰由頭對國內政治、文化和思想等領域采取全面壓制的保守政策,現代主義主流文學日趨保守。作為曾經的前衛詩人,艾略特在1947 年卻公開反對革新:“在文學上,我們在接下來的生活中不能老是處于無休無止的革新狀態之中。”[15]570而作為曾經的反法西斯斗士,奧登(W.H.Auden)也愈發趨于保守。20 世紀40 年代末,他曾告誡青年詩人:“別再參與什么運動。別再發表什么宣言。每個詩人都要善于獨處”[16]176;1951 年,奧登寫道,現在不是“革新藝術家”在藝術風格上“進行重大創新”[17]125的時候。時代精神突變,而美國當局所推行的盎格魯一致性高壓政策又日益反動,這些都迫使處于邊緣人位置且不斷遭受排擠打壓的垮掉派作家,與同樣遭受宰制但拒絕同流合污的爵士音樂家以及美國新電影小組結成背反同盟。
三、垮掉派文學電影改編策略
(一)好萊塢影視對垮掉派文學的同化性改編
20 世紀50 年代,由于麥卡錫主義所發起的“獵巫行動”強迫眾多好萊塢編劇和導演就自己以及同事們的“共產主義”活動出庭作證。因此,對美國主流意識形態提出批評的劇本很難獲得生存的空間。為了保持政治正確,大部分好萊塢電影往往采用“正義”戰勝“邪惡”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來支持美國的愛國主義價值觀。一直以來,好萊塢對于拍攝垮掉派題材電影的濃厚興趣有著中和“垮掉的一代”反叛精神的考量。20世紀50 年代末到60 年代早期,很多像《多比·吉利斯的眾多情人》(The Many Loves of Dobie Gillis)之類的電視劇將垮掉青年簡化為“親切的滑稽丑角”[2]。同時,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量將“垮掉的一代”當作反面典型來塑造的影片。哈斯(Charles Haas)執導的《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1959)、科曼(Roger Corman)執導的《一桶血》(A Bucket of Blood1959)、萊斯(Ron Rice)執導的《花賊》(Flower Thief1960)以及齊默曼(Vernon Zimmerman)執導的《檸檬心》(Lemon Hearts1960)等影片都極力突顯垮掉青年不負責任的一面。此類影片展現出影視媒體強大的滲透力,這種滲透力可以逐漸消解垮掉派運動所特有的反叛精神,從而將垮掉派運動中那些具有反叛意識的“不正常”歸于“公眾常識中某個合適的地方”;而正是通過“這種持續的復原過程”,社會中那些“發生斷裂的秩序得到了修復”,垮掉派背反文化精神也就“以一種令人愉悅的方式被主流神話所收編”[18]94,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體系的同化策略也隨即得以完成。下文將以好萊塢對克魯亞克小說《地下人》的同化性改編為例予以簡要闡釋。
1953 年,克魯亞克與非裔美國人艾琳·李(Alene Lee)分手,不久便開始創作《地下人》。對于這段戀情,小說只是通過虛擬的男女主人公(里奧和瑪竇)予以呈現。小說體現了克魯亞克對于非裔美國人“絕望的傷感情緒”[19]193。首先,小說一直是把瑪竇作為種族“他者”來呈現的。例如,里奧主動與瑪竇分手是因為他覺得他的“白人的生活”受到了瑪竇的長期威脅:“某種意義上她真是一個賊,因此要偷我的心,我白人的心,一個女黑人(Negress)在世界上鬼鬼祟祟地潛行,在神圣的白人中間鬼鬼祟祟地潛行。”[20]47可以說,種族主義問題讓作者猶疑不定,甚為困擾。一方面,生活中有酒,有女人,有詩歌,有很多值得他去發揮想象進行創作的東西,這是一種極具誘惑力的“白人的生活”,克魯亞克很難放棄它。另一方面,克魯亞克也從中看到自己虛偽的一面。其實,早在小說出版的當年,就有學者曾撰文指出過小說中的種族“他者”問題:“作為個體,瑪竇被黑人擁有真正生命力這種刻板化的神秘感所吞噬,不過,這種神秘感終究只是一個將黑人女性刻板化為終極性欲的幻想版本。”[21]
然而,在20 世紀50 年代的美國,種族歧視問題還遠未達到爆發的痛點。當好萊塢巨頭米高梅電影制片公司改編并上映同名影片之時,很難想象會不經過任何“改良”就直接向那些懷揣著主流價值觀的觀眾真切地展示克魯亞克這種猶疑的心態。
由麥克杜格爾(Ranald MacDougall)執導的電影《地下人》(1960)自公映以來一直受到猛烈批判。直到1999 年,該片仍被桑迪森(David Sandison)定位為“難以原諒、愚蠢的電影”[22]125,而《杰克·克魯亞克詩歌合集》(2012)的編者也認為該片是“批評和商業上的雙重失敗”[23]705。影片與克魯亞克原著嚴重不符之處主要集中于兩點:首先,采用白人女演員卡倫(Leslie Caron)飾演非裔女主人公瑪竇。影片特意抹除原著中女主人公的“黑人元素”,從而“支持那種可以預料得到、強行白人化的老套電影,這無疑是好萊塢關于種族偏見最令人遺憾的歷史”[24]20。其次,與小說中男女主人公關系最終破裂不同的是,影片以里奧迎娶瑪竇作結。這些篡改主要是時代氛圍使然:在20 世紀50 年代的美國,種族問題本就是白人主流社會一大禁忌,而且,只有合法夫妻才能進行跨種族性愛更是當時普通民眾必須遵守的社會慣例。
不過,這些基于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所做出的調整與克魯亞克甚至是整個垮掉派作家群不與主流價值觀同流合污的反叛精神恰是背道而馳的。馬林斯認為,該片“貶低”垮掉派“特有的反叛性精神氣質與生活方式”,體現了一種“文化收編策略”[2]。為了配合并維持當時美國所采取的國內外全面遏制政策,決意貫徹主流意識形態的各級政府機構都竭力阻止各種“社會異見”的發展與蔓延。因此,小說《地下人》中那種陰暗、混亂、道德感缺位的波西米亞生活場景是遵循主流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的主流觀眾所不能接受的。最終,呈現在觀眾面前的“地下人”群體早已是經過改造并轉而開始對戰后美國主流文化流露出無比興趣的“改良人”。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該片這一系列的篡改也從反面證明原著《地下人》對于美國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體系具有極大的顛覆性意味。在馬林斯看來,該片就是一幅顯示著兩種對抗性的價值觀在“不斷地抗爭與協商”的“時代文化地圖”[2]。不過,與文學作品相比,作為一種更為大眾化的傳播媒介,影視平臺更能給主流公眾產生直接而有效的影響。因此,公眾通過眾多改良過的垮掉派題材影視作品所了解到的、碎片化且充斥著好萊塢偏見的垮掉派,早已不是那個在20 世紀50到70年代一直都有著相當批判意識的垮掉派了。
(二)《拔出雛菊》:拒絕同流合污的美國新電影
20 世紀50 年代,麥卡錫主義橫行美國,為了保持政治正確,大部分好萊塢電影往往采用“正義”戰勝“邪惡”這種簡化的二元對立模式支持美國的愛國主義價值觀。然而,即便如此,50 年代的好萊塢電影仍然危機四伏。從平均每周電影上座率來看,1948 年是90 億美元,1959 年則跌至40 億美元。[25]
可見,好萊塢商業化電影在20 世紀50 年代遭受重大危機并最終與美國主流話語體系媾合,而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霸權主義思想開始受到廣泛質疑,美國青年地下“垮掉”文化蓬勃興起,美國社會生活中各類異端思想與行為也隨之發展壯大,這些都為美國新電影的革新提供了恰切的思想、美學與社會基礎。
20 世紀50 年代末到60 年代早期,在英國的新電影、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電影以及法國的新浪潮電影的影響之下,一群先鋒制片人發起并成立了新美國電影小組。有別于好萊塢那些為配合美國當局宣傳策略而一味拍攝有著濃烈消費主義傾向、表現繁榮美國的商業化電影,新美國電影小組倡導制作一些低成本但不受商業控制的獨立電影來自主表現那些被忽視被壓抑的邊緣人群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感所作所為。這類電影主要是一些“避免采用傳統意義上線性的戲劇敘述結構和對話方式”從而力求打破“電影與藝術之間隔閡”的“家庭自制電影”[26]。對于新美國電影小組而言,作為身處于20 世紀50 年代的美國藝術家,“有必要以局外人的身份對美國以國家的名義設定體制性的霸權主義標準表達深切懷疑”[27]。
在先鋒制片人看來,好萊塢商業電影早已是跟不上時代潮流的“美麗的死亡”,因為這些電影都是用“金錢、攝像機和接片機制作出來的”,“沒有熱情、激情與想像”;所以,只有寄希望于新一代電影制片人“別無選擇”地對“官方電影品位進行全面清算與重排”從而“打破電影行業的僵局”[28]。于是,1960 年9 月28 日,梅卡斯和艾倫(Lewis Allen)聯合召集包括萊斯利與弗蘭克在內的23 名先鋒派獨立制片人在紐約舉行新美國電影小組成立大會并發表《新美國電影小組的第一篇聲明》[29]。《聲明》強調:由于“道德腐壞、審美老氣、主題膚淺、氣質乏味”,世界范圍的“官方電影正在消失”;越過主流電影那些虛偽的道德,新美國電影小組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人”(Man)身上。
記錄短片《拔出雛菊》(Pull My Daisy1960)是美國新電影的代表性影片。該片改編自克魯亞克劇本《垮掉的一代》,由美國新電影小組成員萊斯利(Alfred Leslie)和弗蘭克(Robert Frank)聯合執導。該片演繹的是20 世紀50 年代一幫窮困的垮掉派藝術家在“猶如當代荒原的”紐約東城貧困地區中的日常生活片段。作為“美國新電影的化身”[30]101,《拔出雛菊》完美地體現了美國新電影精神:反叛乃至厭惡好萊塢電影所一味凸顯的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主題,從而聚焦于當代邊緣人群的情感境況,自由地探求那些受到商業化與技術化的好萊塢電影損害的自發性創作。可以說,《拔出雛菊》是20 世紀50 年代美國新電影運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31]54-55。
為了降低電影制作成本,《拔出雛菊》起用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專業演員:三位本色出演的垮掉派詩人有金斯伯格、奧洛夫斯基(Peter Orlovsky)和柯索(Gregory Corso);音樂家阿姆拉姆(David Amram)飾演爵士樂手麥吉利卡迪(Mezz McGillicuddy);畫家利弗斯(Larry Rivers)飾演“丈夫麥洛”。從內容上看,《拔出雛菊》突顯了當時主流文化所看重的平穩的家庭生活與垮掉派詩人不受約束率性而為的波西米亞生活方式之間的矛盾。電影開場展現的是在20 世紀50 年代美國頗為典型的家庭生活場景:麥洛妻子忙而不亂地收拾房間,準備送兒子去上學。這時金斯伯格和柯索敲門進來,沒和女主人打招呼就徑直來到窗前抽煙喝酒,神情專注地討論詩歌創作。女主人似乎也一直沒在意他們的存在,直到她離開閣樓來到街上她才想起這兩位“闖入者”,并向窗戶這邊看了看。但此刻攝像機鏡頭一直對準的是金斯伯格和柯索。通過他們的視角,鏡頭展現了街道上單調沉悶的日常生活。影片似乎是有意識地將這種固定不變的庸常性日常生活與垮掉派詩人跳躍而變幻莫測的內心世界進行對比,從而映射麥卡錫主義時代先鋒藝術家對于美國主流社會所倡導的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的反叛。于是,這節配音最后說道:“所以,給它丟根火柴吧。”[32]這莫不是垮掉派詩人對于摧毀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這一愿望的沖動表達。
梅卡斯一直將《撥出雛菊》最為美國新電影的典范來推介。1962 年,梅卡斯在回顧美國新電影的發展歷程時,仍將該片看成是“即興創作與自覺編導”完美融合之作,因為這部“虛構影片”所體現的“在場感(being there)”已然達到了“極致”,“從來沒有”哪部影片中的情節比它“更有說服力”[33]。片中,垮掉派詩人、先鋒制片人、爵士樂手等先鋒藝術家所展現的那種“沒有造作、沒有謊言、沒有教化”[34]的日常生活,顯然是對20 世紀50 年代美國中產階級崇尚消費、追求安穩的平庸生活方式的拒斥與不屑。隨著美國二戰以來社會異化現象日益嚴重,以垮掉派詩人為代表的前衛藝術家普遍將50 年代美國主流盎格魯一致性價值觀與保守主義視作“彌漫在戰后美國夢里的精神毒素”[24]xi。
影片中的日常生活場景包含了導演弗蘭克攝像機鏡頭與克魯亞克的配音所指向的所有物體及其顯在的事實表象。同時,這類日常生活場景也包括那些彌散在電影敘事之中的自我表達與社會性互動。例如,柯索有意拿佛教話題讓主教尷尬;奧洛夫斯基也故意拿類似于“棒球是否有神性”等問題讓主教難堪;最后丈夫麥洛不顧憤怒妻子的情緒而一腳踢開一把破椅子并下樓在朋友們面前即興而歡快地舞蹈,這些日常生活場景莫不是對20 世紀50 年代美國社會那種充滿異化與沖突的大環境的絕佳反映。事實上,從《撥出雛菊》公映之前的新聞稿來看,麥洛妻子邀請主教一行前來赴約主要是“希望通過精神救贖將她的丈夫轉變為中產階級信仰者”[35],但這一預期目標遠未實現。片中,當被問及“是否萬物神圣”等一系列問題而主教難以回答之時,主教母親略顯“宗教意味”地在一架腳踏風琴上演奏,導演萊斯利似乎是有意通過這一場景來展現一種“普通家庭景象”[36]。不過,麥吉利卡迪和麥洛很快針對性地吹起了法國圓號和薩克斯,觀眾很難不將這場爵士音樂即席演奏會當作是對前者的對抗性反叛。在先鋒派藝術家看來,正如影片開頭同名主題歌曲所唱的那樣,如果“我所有的門都打開”,人們對爵士樂和風琴也應該同等對待。與好萊塢所拍攝的那些商業片相比,《拔出雛菊》可以說是一部“真實與詩意并存、美麗與靈魂同在”的影片,因為該片本身就是“生活、真理以及受到上帝之手觸摸過的現實存在”[37]。
四、結語
美國政府歷來所宣揚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本質上是由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群體所享有的。正如《美國的本質》一書所述,“美國人所熱衷推行和維護的自由、人權、民主的價值觀和制度,看起來是世俗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但實際上起源于基督新教的價值觀和宗教改革,體現著基督新教的信念”[38]7。然而,正是由于美國所謂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主要由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群體所享有,才會不斷助長美國主流社會中的白人至上主義情緒,從而成為美國國內種族歧視與信仰歧視最大的內在誘因。在麥卡錫主義語境中,垮掉派文學有著一種絕不同流合污的背反性精神訴求。為了中和垮掉派文學所特有的反叛精神,好萊塢影視改編采取的是同化性收編策略。而美國新電影小組則采用直接呈現的策略,倡導消解麥卡錫主義話語霸權,進而打造出凸顯受到極力打壓的邊緣人群另類但真切的生命體驗的獨立電影。囿于二戰以來美國社會、歷史與文化背景,崇尚非暴力的“垮掉的一代”必然難以找到出路,但“垮掉的一代”所展現的不被盎格魯一致性主流意識形態所洗腦從而拒絕同流合污的背反精神,成為其后美國黑人平權運動、搖滾樂風潮、反越戰運動等背反運動不斷回望的主要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