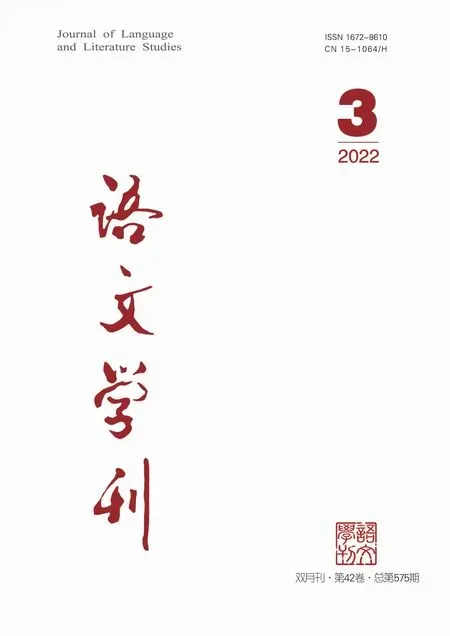論多爾小說中的社會生態學思想——以《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為例
○ 趙瑩
(北京外國語大學 外國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089)
一、引 言
《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AlltheLightWeCannotSee以下簡稱《所有》)是美國小說家安東尼·多爾(Anthony Doerr)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該小說2014年一經出版便收獲大量好評,成為《紐約時報》的暢銷書,并于2015年獲得普利策獎。莫林格(J. R. Moehringer)評價多爾“用科學家般的眼睛觀察,卻如詩人般感受這個世界”[1]。斯特德曼(M. L. Stedman)認為這本書“溫柔地探索了這個世界的悖論:自然法則之美以及被戰爭顛覆的可怕結局、人類心靈的脆弱和復原力,以及瞬間的不變性和時間的治愈能力”[1]。在故事中,一名叫做瑪麗-洛爾·勒布朗(Marie-Laure Leblanc)的法國盲人小女孩和一名叫做維爾納·普芬寧(Werner Pfennig)的德國孤兒小男孩的命運,通過收音機電磁波的牽引交織在一起。在戰爭中,他們相互傳遞力量和關懷,尋找內心的安寧與救贖。
該小說的思想內涵十分豐富,研究者們從不同角度對其展開論述,主要觀點有:《所有》中蘊含豐富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體現出作者深刻的生態關懷和女性意識[2];從新歷史主義角度來看,《所有》在與歷史的互動關系中體現出文本的歷史性以及歷史的文本性[3];《所有》中戰爭主題對成長在和平時代的青少年具有很大的教化作用,同時拓寬了成長小說的研究領域[4];《所有》中體現出人性中的兩大關鍵要素,即“同情心”和“寬恕”,彰顯了人性光輝的主題[5];“光”在《所有》中作為符號所承載內涵豐富,通過其傳遞、接收和接受過程,傳達了主人公在戰爭中表達出的人類共同情感[6];多爾在《所有》中以熵為隱喻,揭示出戰爭帶來的無序狀態給人造成的心理創傷以及個人身份的喪失[7]。但迄今為止,尚未有人從社會生態學的角度對這一作品進行解讀,本文擬做一些嘗試。
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理論始于默里·布克欽(Murray Bookchin),他是該領域極具影響力的學者,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直至生命結束,他一直致力于書寫該理論方面的著作。1970年,布克欽在其著作《生態與改革思想》(EcologyandRevolutionaryThought)一書中正式提出了社會生態學的概念。社會生態學家認為當前生態問題根源于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源自等級制的支配結構。“人類必須主宰自然的觀念直接源自人對人的支配。”[8]85社會生態學家相信,在20世紀和21世紀,除了那些由自然因素導致的災難外,最嚴重的生態問題均是由于經濟、種族、文化、性別等各個領域內部的沖突造成的。如果社會內部的問題得不到恰當處理的話,當今時代的生態問題便不能被人們所理解,更不用說被人們所解決。等級制度是基于命令和服從的人際關系,促成了各種形態的社會統治,從而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問題。無論是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等級制的概念都普遍存在。由于等級制植根于人類的心理結構中,因此“在‘無階級’或‘無國籍’的社會中,等級和統治仍可以很輕易地繼續存在”[9]4。布克欽認為等級制是極其危險的,并駁斥了其存在的意義:“因為等級制威脅著今天社會生活的存在…… 威脅到有機自然的完整性,因此它不能繼續這樣支配下去。”[9]37
在《所有》中,等級制觀念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令人關注:在國家政治教育學院中上級對下級的壓迫,兩次世界大戰中強者對弱者的在身體和精神方面的雙重摧殘,人類對非人類自然中的生物和非生物的掠奪和利用,以及等級制的社會結構導致人類對科技的濫用……多爾通過列舉等級制觀念給人類社會和非人類自然所帶來諸多傷痛的事實說明,只有逐步消除這樣的觀念,人支配人和人支配非人類自然的行為才會逐步消失,從而有助于人類走出現今生態問題頻發的困境。從社會生態學的視角對作品中表現出的生態社會觀、生態自然觀和生態科技觀進行闡釋,具有很大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二、多爾的生態社會觀:反對支配他人
布克欽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是互補的,而且是相對穩定的整體,即彼此需要的關系。在土著文明中,沒有人支配人或試圖使自身享有特權的觀念,這種文明具有三個特征——“不分年齡或性別地尊重個人;驚人的社會和政治一體化程度;超越所有政府形式和所有部落和群體利益與沖突的個人安全概念的存在”[10]106。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諸如血統、性別分布和年齡差異之類的生物學事實,將不同人類群體團結在一起,進而轉變為社會機構,并在不同的時期和階段逐步被改組為等級結構[11],人類社會的等級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像命令、剝削和等級這樣的詞語,實際上是描述人們彼此間如何相互聯系的社交稱謂。”[12]216在《所有》中,多爾通過對二戰前夕德國舒爾普塔的國家政治教育學院、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前線所發生的事件進行描述,揭示出社會中上級對下級以及強者對弱者的支配形式的存在,使我們清晰地看到這些等級和統治關系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在國家政治教育學院,軍官和學員之間基于命令和服從關系普遍存在,“為統治而統治的制度形式很明顯”[9]127。軍官是上級的代表,他們向下級學員下達命令。維爾納(Werner)作為學員之一,一直處于被命令狀態。在進入該學院之前,維爾納參加了入學考試,入學考試的選拔標準由軍官們規定:“我們只會選擇最純正、最強大的人。”[1]112為了通過選拔,學員們首先要證明自己體內流動的血液是“純凈的”,即沒有猶太人的血統。學員們被軍官要求填寫一份有關自身血統的一百多個問題的調查問卷,并參加了生理學測試。在證明自身血統純正性之后,他們還要證明自己是最強壯的,其中最殘酷的一項測試是從25英尺高的頂部跳下來。患有恐高癥的學員在暈倒的瞬間從高處摔下來,“胳膊先落地,伴隨著柴火折斷般清脆的聲音”[1]115。巴斯蒂安(Bastian)是學院的一名軍官,他試圖訓練學員踐踏他人生命。在一個寒冷的冬夜,他命令所有的學員將冷水潑到一個偷了牛奶充饑的囚犯身上,“囚犯的腳上鎖著腳鐐,從手腕到前臂都被繩子捆著,單薄的襯衫從接縫處崩開,他已經凍僵了,目光呆滯地注視著前方”[1]227,直至他被折磨致死。在國家政治教育學院中上級的統治下,下屬逐漸成為沒有感情的執行命令的機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冷漠。
除了上級對下級的統治外,多爾向我們展示了兩次世界大戰戰場上強者對弱者的支配。公元前9世紀,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中總結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發起戰爭的主要原因。在他看來,強者總是做他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因為他們很強大,弱者會做一些事情來改變他們的弱勢地位。現實主義學者認為,修昔底德揭示出那個時代戰爭的邏輯——強者希望變得更強大,而弱者則不得不面對強者可能在任何時候發起的戰爭,以及思考如何擊敗強者并改變他們處于弱勢地位的問題,這是人類歷史的自然選擇。在《所有》中,多爾通過埃蒂安(Etienne)和維爾納的視角為我們展示戰爭中這種心理結構給人類身體和精神所帶來的災難。埃第安是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士兵。在戰場上,他目睹自己兄弟亨利(Henry)被炮彈擊中并失去生命,然而在他向瑪麗-洛爾的講述中,戰爭奪取的不僅是自己親人的生命:“殺死你祖父的戰爭導致1600萬人死亡。其中有150萬法國男孩,大多數比我年輕。德國一方死亡人數達200萬。如果將死者排成一列縱隊行進,他們走上11天11夜才能從我們的門口經過。”[1]360維爾納是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士兵。在來到前線的第一天,他看到一輛運載著囚犯的火車從他面前駛過,成百上千的男人像稻草人一樣擠在車廂里,一堆尸體為他們組成一面防護墻,而那些活著的人只剩下“凹陷的臉頰、肩膀和發光的眼睛”[1]319。在強者壓迫弱者的戰場上,人類的生命被視如草芥,這種支配關系也進一步使人類精神蒙上陰影。經歷過一戰的埃蒂安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由于在戰場目睹了一母同胞的兄弟在自己面前倒下,他在戰后患上恐曠癥(agoraphobia),患上這種病癥的人在諸如公共交通工具上(如公交車、火車、飛機等)、開闊的空間(如停車場、大橋或超市等)、封閉的地方(如商店、劇院或者電影院等)、排隊或在人群中以及獨自一人外出等其中的兩種或兩種以上情況下,會感到害怕或焦慮。在患者心理作用下,在這樣的情形下如若產生類似恐慌或令人尷尬的癥狀時,自己不能夠輕易逃脫或不能得到幫助[13]217-218。 在這種精神疾病的折磨下,他自參與一戰之后便無法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強者支配弱者的戰爭對人類的摧殘可見一斑。
三、多爾的生態自然觀:尊重非人類自然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于人類來說,生活就像一場斗爭,“但這場斗爭不在于人與人之間,而在于人與自然之間;每個人都有責任承擔它”[14]46。在社會生態學中,人類控制非人類自然的思想史幾乎和導致支配的等級制度的歷史一樣古老。“隨著等級制度和人類支配的興起,人類開始抱著這樣一種觀念,即自然不僅作為一個獨立的世界而存在,而且是分等級地組織起來,并且是可以被支配的。”[11]在人類觀念中,非人類自然一直以來都是“低等的”,人類從非人類自然中“掠奪了許多生物世界中美麗的、有創造力的和充滿活力的事物”[11]。多爾在《所有》中表現出人類對非人類自然的支配,同時思考如何重建兩者之間的和諧。
在《所有》中,人類自認為“優于”非人類自然,將其中的生物和非生物看成是滿足自身私欲的工具,并對它們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和掠奪。一方面,多爾通過揭露人類對待海螺的殘酷方式,反對人類對非人類自然中生物的支配權。熱內法博士(Dr. Geffard)是一位年長的軟體動物專家,將這類生物視為實現自己畢生夢想的“無生命”客體。在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實驗室中,他保存了從世界各地收集的數不清的貝殼,“博物館擁有超過一萬個標本,超過世界上已知物種的一半……”[1]30。雖然他對海螺很著迷,但它們對他來說只不過是研究標本,這也是他為什么選擇收集大量貝殼而不是活著的海螺的原因。另一方面,多爾以煤礦的開采和掠奪為例,反對人類通過支配非人類自然中的非生物來滿足自身的需求。對于人類來說,煤炭是一種提供燃料的礦藏。“地球上的巨大區域越來越多地被用于特定的工業目的或淪為原材料的堆場。”[15]60在《所有》中,多爾所刻畫的德國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區“方圓四千英畝”[1]24,那里的人們從這樣巨大的“原材料的堆場”中掠奪煤炭資源。由于煤炭的工業開采,當地環境變得骯臟不堪,由煤車、活塞和皮帶形成的平穩而瘋狂的生產過程隨處可見。然而,在發動瘋狂戰爭的德國人看來,挖掘礦產資源所引發的污染并不算什么,利用能源贏得戰爭才是一切,這便是人類掠奪非人類自然中非生物的縮影。
“從人類從中獲取生存所需簡單物品的生物環境這個廣義層面上來看,‘自然’往往對于文字出現以前的民族沒有意義。”[11]對于那時的人類來說,自然正是他們沉浸其中的宇宙。在布克欽看來,非人類自然的進化和人類一樣,同樣“具有自主性和靈活性不斷提高的特點,以及不斷提高的差異化,這種差異化使有機體更加適應新環境中的挑戰和機遇,并且使生物更有能力改變自身以適應環境來滿足自身需求”[11],也就是說,“不存在沒有目的論的有機體”[16]91。在《所有》中,多爾肯定了非人類自然的主體性,并消解人類和非人類自然之間的等級差別,這都有助于重建二者之間的和諧。多爾從弗雷德里克的視角出發,通過對飛鳥的描述,顯示出非人類自然中生物的主體性。弗雷德里克(Frederick)是一名癡迷于飛鳥的孩子,他熱衷于觀察自由翱翔的鳥類,將它們視為和人類一樣具有能動性的生物。在他看來,冠小嘴烏鴉比大多數哺乳動物更聰明,北極燕鷗是地球上真正的航海家,灰鹡鸰依靠自身的信念從美洲飛到非洲。非人類自然中的非生物的主體性同樣也需要受到尊重。在《所有》中,“海之焰”(Sea of Flames)是一塊稀有的鉆石,被人類視為無價之寶,法國和德國在戰爭中爭相追蹤它的下落,但瑪麗-洛爾卻在戰爭即將結束之時,將這塊梨形鉆石扔進大海。在多爾的描述中,“它從世界炙熱的底層,兩百英里深的地下走來。它是一塊純凈的碳,每個原子有四個距離相等的鄰居,完美地構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正四面體”[1]520。多爾尊重“海之焰”來自非人類自然的事實,并且通過瑪麗-洛爾這個人物,將它的最終歸宿安排在大海之中。
四、多爾的生態科技觀:批判科技濫用
科技在當代人類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自18世紀中葉以來,現代歷史上的幾次重大科技革命直接影響和推動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大多數人對科技創新抱著一種自相矛盾的感受,他們一方面對核滅絕充滿恐懼,另一方面又向往充盈的物質、休閑和安全。”[8]107如何合理地看待和利用科技正成為一個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問題。《所有》創作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時期,在此期間,電磁波的應用是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那么,多爾是如何通過電磁波的利用,向我們展示科技的雙重效果,以及他所主張的合理利用科技的途徑呢?
多爾通過描述戰場中人類對電磁波的使用,向我們展示科技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利弊兩面。首先,電磁波的傳輸給人類帶來精神滿足和慰藉。維爾納是受電磁波影響最大的人,他通過收音機接收的電磁波接觸到自己熱衷的科普類節目。長久以來,他對于煤炭的認知一直停留在充斥著繁重勞動的煤礦區以及機器作業這些層面,而收音機中的科普節目改變了維爾納一直以來對煤炭的看法:“那塊煤曾經是一株綠色植物,或許是蕨類或許是蘆葦,生活在一百萬年前,也許兩百萬年前,甚至一億年前……”[1]48類似的廣播節目中對各種事物百科全書式的講解,使他對科學知識越發好奇和著迷,也越發渴望親眼看到外面的世界。有時候,他甚至夢想自己成為一名穿著白大褂走在實驗室的高大工程師。電磁波不僅擴展了維爾納的視野,也照亮了他的夢想。然而,電磁波也成為德國發動戰爭的“幫兇”。德國人對電磁波最殘酷的使用莫過于在戰場上,即通過“敵人”釋放電磁波的位置對其進行定位,進而將他們殺害。“這是一場更干凈、更講究的空中之戰,前沿陣地無處不在卻又隱形不見。”[1]343維爾納經過在國家政治教育學院的訓練走向戰場,并成為德國軍隊通過電磁波對“敵人”進行追蹤的關鍵人物之一。當維爾納被派往前線時,他服務的是一個特殊技術部門,所承擔的任務是搜集一切不被德國政府允許的電磁波信號。維爾納利用他從豪普特曼博士那里學來的知識,在團隊其他成員的配合下,精確定位“敵人”的具體位置,一旦發現目標,便將“敵人”擊斃。電磁波在戰場上成為殺人工具。
對于現代人來說,科技只是原材料、工具、機器和生產可用物體所需要的相關設備的集合[9]221。然而,科技、裝備和原材料在不同程度上與鞏固社會的理性、道德和制度互相聯系;就這個程度而言,科技所涉及的一切都被視為一個整體[9]223。我們不能忽視科技所產生的社會矩陣,即相應的政治、管理和官僚制度以及與此保持一致的信仰體系。在《所有》中,等級制觀念作用下的支配關系,是導致科技濫用的罪魁禍首。維爾納和埃蒂安在使用電磁波方面都很有天賦,但是作為分別服務于德國和法國政府的下屬,他們在使用電磁波時必須遵守命令,完全沒有自主權。對于維爾納來說,在戰爭之前,電磁波使孤兒院兒童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但在戰爭期間,他逐漸意識到電磁波應用所帶來的邪惡和毀滅性。但是作為下屬之一,他無法自由決定是繼續利用電磁波殺人還是放棄對其使用。埃蒂安對電磁波的使用與維爾納的經歷類似。他強烈渴望通過電磁波傳遞的收音機節目使人們的生活獲益,維爾納在孤兒院時所癡迷的便是他的節目。但是在二戰期間,由于法國受到德國侵占,作為法國人,埃蒂安開始利用電磁波傳遞情報,致使許多德國士兵失去生命。同維爾納一樣,他無法自主決定如何利用電磁波。除了認識到等級制觀念在科技濫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外,多爾還認為,現代人應當意識到“忽視技術當然不是解決方案”[8]156,并時刻謹記,科技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的便捷越多,可能帶來的災難也會越多。
五、結 語
從社會生態學視角下的三個維度,即生態社會觀、生態自然觀和生態科技觀,對《所有》進行闡釋具有很大的現實和理論意義。從生態社會觀角度來看,多爾反對人與人之間相互支配的關系。在國家政治教育學院中上級對下級的壓迫,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中強者對弱者的支配,使人類在身體和精神方面遭受雙重摧殘。生態自然觀要求人類尊重非人類自然。在《所有》中,人類對非人類自然中的生物和非生物資源進行肆意踐踏和掠奪,海螺和煤炭等均被視為滿足人類需求的“低等的”客體。為了重建人類與非人類自然之間的和諧,人類要承認諸如飛鳥和鉆石等非人類自然的主體性。生態科技觀批判人類對科技的濫用。在《所有》中,電磁波的傳播豐富了人類的精神世界,維爾納便從中得到心靈慰藉,但是在戰場上,它則被用來定位以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利,成為戰爭的幫兇。等級制觀念直接導致電磁波的濫用。維爾納和埃蒂安在戰爭期間別無選擇,只能服從上級的命令,利用電磁波幫助自己的國家打擊和摧毀“敵人”。21世紀,電磁波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更是無孔不入,這值得引起人類的注意和思考。人類對科技的態度應該是理性的,不應該忽視其對當代生活幾乎所有方面的快速滲透。總的來說,多爾在他的小說中傳達了豐富的生態內涵,其中包括人類對社會、自然和科技的生態意識,并倡導我們要努力更加接近生態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管理世界的未來,但這種管理不僅像是象棋游戲,更像是在駕駛船只。”[17]216社會生態學希望教給我們的是找到小溪的涌流并了解其方向[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