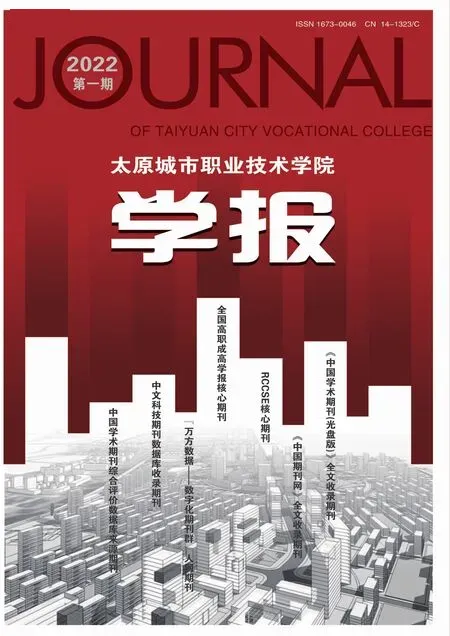人工智能技術引入民事送達的“雙相障礙”及其因應
■冉一冰
(重慶大學法學院,重慶 401331)
在信息時代,如何通過對新技術的應用促進司法制度創新發展是在理論和實踐之中方興未艾的話題。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在民事訴訟之中的運用,也是新技術助推民事訴訟的一種表現。很顯然,如同在一般意義上新技術為人類創造了便利,提高了工作與勞動的效率一樣,人工智能這一新技術在民事送達之中的應用,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送達難的問題,尤其是在提高送達的效率意義上,對于溝通當事人雙方以及法院的關系能夠起到高效簡便的作用;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人工智能這一新技術的應用是否會在送達之中產生負面影響,或者對人工智能這一新技術的普遍適用要求與部分法院的具體實踐是否會產生不兼容的情況,則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人工智能技術引入民事送達的“雙相障礙”
雙向(情感)障礙是一個來自臨床心理學的概念,一般指的是在同一個病患身上,會同時出現躁狂和抑郁的兩個相,是臨床心理學中常見但難治的心理疾病。筆者希望以這一比喻指出,就目前來看,人工智能引入民事送達中的表現與雙相(情感)障礙類似,體現為躁狂一般的極端高效與抑郁一般的極端低效同時存在,并且最終匯為“雙相障礙”這一個病癥。使得法官有時省時、省力,有時反而費事、費力。
(一)“躁狂”:人工智能在民事送達中的極端高效
人工智能技術引入民事送達之躁狂,是其高效的延伸和病態,就其危險來看,又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人工智能技術本身的極端高效帶來的自然危險。有研究指出,使用網絡進行訴訟文件傳輸,在送達過程中,可能會遭受到網絡攻擊,從而導致安全問題,所以在構建電子送達系統時,一定要針對此種可能性來設置對應的預防機制[1]。也即目前在高效之外,保證在電子送達經由互聯網的過程的安全性以及對最終送達回證的證明等問題方面的法律保護尚且不足,而由于高效的要求,這種對互聯網環境以及送達回證等細節問題的考慮顯然跟不上高效的人工智能的步伐,無論是當事人和法官都有可能面對這種由于制度跟不上技術而造成的損害。
另一方面的躁狂危險,則來自由于對高效的追求,導致在大范圍內為了推行新技術而推行新技術,為了體現民事送達中的科技含量,而采取的對不同地方法院和不同當事人群體的一刀切的“躁狂”。一方面,法院并非科研中心,在全面“一刀切”地盲目追求人工智能的高科技建設的過程之中,必然會出現某些法院出于自身技術限制而借助高校或社會化科研力量去開發人工智能程序;那么在人工智能這一技術引入民事送達的過程之中,法院雖然是技術的操作者,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并且掌握了人工智能程序的開發與設計則是值得反思的,引入社會科研力量對于人工智能程序的質量是有所保證的,在提高效率上看似是必要的,但是法院由于追求高效而使得司法權威性受到影響則是不正確的。另一方面,即使在自研技術成熟的情況下,法院對人工智能的定位尚不充分,也即究竟是要把人工智能建設視為工具還是把人工智能建設視為體現法院自身技術創新的政績是必須討論的問題,也即究竟是要建構人工智能-民事送達的工具+目的模式,還是要建構民事送達-人工智能的手段-目的模式,都是在提倡人工智能建設的高效推進意義上值得反思的問題。
(二)“抑郁”:人工智能在民事送達中的極端低效
相應地,一種出于高效追求的低效成果就有可能,也即人工智能引入民事送達反而會出現極端低效的可能性。這種由人工智能自身帶來的低效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人工智能這種高新技術尚未發展成熟,那種目前僅僅能夠在影視劇以及文學小說等藝術作品之中出現的完全能夠替代人力、能夠自主處理送達這一司法程序的人工智能在現實中還僅僅是幻想,更多的情況是人工智能在使用之中易于出現故障,容易出現系統錯亂,而使得法院尤其是具體的法官不得不既忙于系統搶修,又要忙于人力送達。其次,人工智能這種技術是一種發展中的技術,有發展就會有更新換代,有發展就有不平衡,在實踐中經常遇到的情況是,一套系統自帶的數據庫在更新為另一套系統之后就要重新錄入,或者某一套系統自帶的運行程序和另一條系統的運行程序不兼容,尤其是在現階段我國還沒有建設全國范圍內統一專業的電子送達系統條件的情況下,法院之間的人工智能系統也可能由于地方科技水平的差異而無法銜接。那么在這一意義上,法官的工作量并未減少,一方面要去進行送達工作,另一方面還要照料好人工智能系統,甚至還要對人工智能系統的各種故障有初步檢修能力,對人工智能可能出現的安全隱患有所學習——那么這到底是高效還是低效,就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去考察的問題了。
此外,就目前的智慧法院、智慧法庭的建設來看,人工智能技術的引入使得法院面臨著更多的宣傳和自我解釋工作。例如,如何使得當事人在微信、微博、微淘等賬號之中看到公告送達的內容而并不驚訝,并且認為這種公告送達不是對自身隱私權的侵犯而是出于選擇電子送達的必然,是需要法院進行更多的在人工智能程序之外的配套程序設計以使得當事人自愿接受信息,使得電子送達和人工智能技術能夠真正融合在一起;很顯然這種配套程序雖然不是人工智能建設的直接對象,卻是人工智能建設的必要補充。另外,如何讓法官去熟練掌握人工智能送達的技術,是否需要進行培訓,是否需要進行內部宣傳,都是法院內部配套程序的建設方向。因此在這一意義上,無論是人力資源的短期內的耗費,還是在社會公眾、當事人、法官內部進行相應的配套程序設計,都顯然是低效這一抑郁傾向的表現。
二、“雙相障礙”之基本病因及因應
(一)“雙相障礙”之基本病因
人工智能和民事送達在融合之中出現“雙相障礙”,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司法權威性和司法高效性之間的張力,或者進一步問:司法權威性和司法高效性,何者是手段,何者是目的?在人工智能引入民事送達的過程之中,無論是人工智能的躁狂還是抑郁,無論是極端高效帶來的邊際效應上的損害還是極端低效意味著的人力資源浪費和宣教工作落實帶來的工作量增加,都是由于上述問題尚未被認真討論而產生的后果。如果司法權威性是更重要的目的而司法高效性是致力于這一目的的手段,那么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司法的功能是有限的;民眾對司法的期望卻是百分之百的。一個案件沒有實際送達的負面效果可以沖抵一百個案件中的實際送達的正面效果[2]。那么在這一前提下,司法權威性就必須要求抑制司法高效性對人工智能的引入節奏,也即為“雙相障礙”的躁狂面相“吃下情感穩定劑”,使得法院在人工智能引進之前就設立好技術保障部門、組織宣傳部門等,然而這一代價就是可能使得民事送達永遠錯過人工智能這一新技術的風口。而如果主張司法高效性是更重要的,那么司法高效性就必定要求大力推行人工智能技術,也即為“雙相障礙”的抑郁面相“吃下抗抑郁藥劑”,這必然會促進智慧法院、智慧法庭以及智慧送達的形成,但是在這一過程之中,司法權威性可能由于過分地高效而有所損害,公眾和法院內部對人工智能的抵制聲音開始出現,外界技術部門對司法權造成直接的影響;但是如果不進行這樣的大刀闊斧的操作,那么就長遠來看司法權威性會由于錯失這一新技術浪潮的風口而被進一步地損失,極有可能的結果就是在未來司法權變成一個局限于法院之中的古板之物而被社會的發展拋在身后。
(二)對人工智能技術引入民事送達“雙相障礙”的因應
1.靈活便民的智慧送達立法保障:當事人本位與繁簡分流機制
有論者指出:(民訴法)不僅在立法體例上一直延續送達制度與期間制度并列一章的模式,將我國的民事送達制度僅僅視為一項純粹技術性的安排,而且有關送達的基本法律規定25年來幾乎沒有變化。履行民事送達職責的人民法院逐漸難以獨自承受職權主義送達衍生的高風險、高成本、高投入,終使“一個原來不是問題的問題”逐漸演變成一個難題,也不得不尋求改革[1]。這一論斷指出,送達難這一問題原本不應是一個問題,而正是由于立法上的一成不變,采取超職權主義的立法模式,將送達視為專屬于法院的自留地,從而導致立法空白對司法實踐的不適應,而使得目前的人工智能和民事送達的融合成為了問題,形成了“雙相障礙”。
強調改造立法,就是先行解決“雙相障礙”這一心理疾病的生理原因,以至于有論者直接指出:“從微觀層面而言,我國現有立法中對送達地址以及送達方式等制度供給不足,僵化于以文書是否按‘規定的送達類型’送達、當事人是否‘簽收’來評價送達的完成與合法性,極易造成送達機械化、粗疏化和當事人規避送達并存的‘怪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送達難’”[3]。因此,首先要在立法之中明確法院與當事人的合理位序,使得當事人不再被動地簽收,而是能夠通過送達來實現法院與當事人、當事人之間的合理信息交換——也即便民的立法。在這一意義上,強調信息交換就必須有能夠足以因應案件數量龐大、案件情況復雜的相應機制,這時人工智能的出場才是水到渠成的,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等新技術的集合,將送達之中的信息交流功能實現,既保障了當事人的受通知權與對案情進展的知情權,更以送達這一簡單的操作為當事人之間的辯論權提供了平臺,又能夠保證法院在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裁斷地位,也即通過對超職權主義的一定程度的立法弱化,通過對當事人本位的一定立法提倡,為新技術的介入創造立法上的空間。其次,也要通過立法去構建新的案件繁簡分流機制,通過強化調解、仲裁等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減少法院的工作壓力,促使法院集中力量辦大事——也即靈活的立法。在這種立法模式下送達的盲目追求效率的躁動也會相應減弱,而更會注重送達的質量,而在目前的情況下,強調以傳統的鄉土司法、民間調解等替代糾紛解決機制也并非不可行,但是將糾紛解決完全交由這些機制也是不可能的,這是由于社會環境出現了基本的變化,即使堅持老辦法也要選擇新方法,例如在2018年北京市開展了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改革,以地方立法的模式,通過各區基層法院的速裁庭建設,初步建立了基于人工智能、大數據平臺的線上調解制度[4]。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沒有和民事送達直接融合,但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事送達的壓力,至少也能被視為對民事送達的技術貢獻。
2.穩定暢通的信息化送達司法建設:職權主義改造與送達人隊伍建設
在心理也即法院之內的建設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為病之場所,根本上在于法院之內,以心理這一比喻去指稱法院可能并不恰當,但是如果考慮到人工智能與民事送達在根本上依賴于法院的內部推動,因此不妨將法院這一內部性類比于心理疾病的心理。這也是因為在立法上的調整最終要由法院自身來實現;在現有的司法模式下,勾連當事人雙方,進行送達的主體也是法院,是否選擇采取人工智能技術去改善送達的主體還是法院;更為重要的方面在于采取人力資源調配、配套設施和程序建設、人工智能程序設計和開發以及對內對外的宣傳教育的主導權也必須把握在法院手中。這就意味著在人工智能與民事送達的融合之中,送達人同時也是人工智能系統的操作人,他們是對送達義務的具體履行者,因此將送達人的隊伍獨立出來,在人工智能和民事送達實現技術融合的背景下將法院、送達人/操作人、當事人的三方明確出來,不僅有利于法院內部人工智能專業操作團隊水平提高,更有助于將送達作為單獨的團隊序列,通過對這一隊伍的建設為抓手,去引導信息化送達要求的法院內部整體建設。
建立送達人專門團隊的目的在于通過分工關系,建構一種穩定通暢的司法系統。首先,要以職權主義的基本改造立場去保證人工智能技術與民事送達的技術融合之穩定,有論者認為在職權主義模式下,法院是毫無疑義的送達主體;但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也可以成為送達主體[5]。也有論者進一步認為:送達主體可以是法院,也可以是受法院委托實施送達行為的相關機構,即將送達主體由法院擴大到法院以外按照法院要求實施送達的諸如郵政機構、公證機構等主體[6]。這種表述都指向了在保證法院作為當然的送達主體的同時可以向外拓展其他的送達主體,但是正如后一例證指出的,即使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抑或相關機構能夠成為送達主體,這種主體資格也必須由法院進行賦予,這是由于人工智能和民事送達的融合之穩定性來源,在于法院職權之穩定,如果法院的職權不清楚而盲目地出于高效追求,或是由于對人工智能技術的不熟練而拓展送達主體,而在法院對人工智能技術有所了解的情況下,這些被授權主體采取某種人工智能的手段進行民事送達也是在法院的把握之內的。其次,在送達主體多元且法院為主導的基本格局下,要實現這種把握,并且使得法院具有人工智能和送達的融合的技術能力,可以考慮前述建議之中送達人隊伍建設,也即在法院內部,通過對既有的技術專員的培訓,在既對法律規定有所了解,又對人工智能技術有所掌握的情況下由專門人員進行送達任務,而法院的相關配套程序、人力資源等建設方向,都可以以送達人的專業團隊建設為基點,讓信息和數據在閉環系統中運行,也可保證信息和數據安全,同時也可以負責與其他被授權送達主體的溝通和數據傳遞,這也實現了從內到外的信息交流之暢通。
3.堅實可靠的人工智能專業技術支持:社會力量和法院的配合問題
從臨床心理學的“雙相障礙”比喻來看,最難控制且最容易引發病癥的,實際上反而是社會原因,這在技術融合之中尤為明顯。而就目前來看,在人工智能和民事送達的技術融合上,必須考慮到: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仍在發展中,也會不斷面臨新案例和新問題的挑戰,單純依靠法院的技術力量,即使在送達人隊伍得以建設的情況下,也不能完全依賴法院進行系統設計、系統更新以及數據庫服務,因此引入社會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一環;另一方面,在建設過程中,還需要考慮是技術的來源決定著技術決定還是技術輔助。人工智能技術嵌入民事送達,理想的狀態是有能夠掌握人工智能技術又熟悉民事訴訟流程的復合型人才,并且依靠這些人才去識別出不同案件中民事送達中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具體情境,作出何時送達決定,甚至量身打造出合適的系統或平臺,進行后期的開發與維護——這或許才是送達人的理想樣態,然而人才的來源并不是十分確定,甚至法院面臨著相對于企業和社會力量的人才依賴。這不得不表明,采取人工智能的技術,極有可能造成社會力量影響司法的可能——即使這種可能性大于現實性,但是還會影響到司法權在群眾尤其是當事人之間的口碑。那么對此可能的一種解決方案是,將民用人工智能和司法人工智能技術區分開,將司法權的獨立性標明出來,采取向行政機關、檢察機關、監察機關以及政法委、紀檢委等黨的紀律部門尋求技術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以國家權力的統一性去防止社會力量對司法人工智能建設的過度干預。一方面,在國家機關之內尋找技術支持是可行的,例如我國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在其長期的刑事偵查過程中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技術經驗,掌握了一定的技術資源,一定程度上能對人工智能和民事送達的技術融合給予支持,同時這種技術支持來自國家機關內部,使得司法權通過國家權力能夠得到社會公信力;另一方面,就送達主體來說,在人工智能的電子送達之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例如網絡運營商、通訊運營商、社交平臺、新媒體平臺等渠道,也即在理想的主審法官、送達人團隊、其他送達主體、當事人的關系之中,還存在渠道這一因素,那么也必須保證國家機關對上述渠道進行電子送達的過程進行監督監管,建立問責機制;更為重要的方面在于,要通過高校的專門教育,為法院的智慧送達、信息化送達提供專門的人才培養,建立堅實可靠的技術人才后備軍。在這一方面,近年來在公安機關的直屬高校中開設網絡警察專業,或許是對人工智能與民事送達的人才后備軍建設提供的可供參考的模版。概言之,無論是尋找體制內的技術支持,還是對社會力量的監督監管,或是對技術人才后備軍的培養,都是要促進技術能夠最終服膺于司法,使得人工智能和民事送達之中的技術支持堅實且可靠。
目前所處的時代是信息時代,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人工智能和民事送達的技術融合,實際上是對信息時代下法院建設以及立法調整和社會支持的一個極為微小的切入點,通過以一種臨床心理學的“雙相障礙”的比喻,本文指出了要從先天的立法生理、內在的司法系統以及外在的社會技術支持三方面去對人工智能與民事送達的融合進行躁狂——極度高效和抑郁——極度低效的病證進行治療。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司法權威性和司法高效性何者更為重要,而這恰恰是病根的所在,而本文希望將這一問題懸擱并開放,因為這種價值論的討論雖然重要,卻應當是司法哲學甚至法哲學的討論對象,而如果希望通過“雙相障礙”的比喻對這一問題給出一個初步回答,那將是對這種問題的思考更為重要,也即無論選擇什么,對人工智能和民事送達的融合的基本立場的明確都是更為重要的,而就制度討論來說,從超職權主義立法向職權主義立法進行轉變,從職權立法走向職權司法進而強調送達人隊伍建設,從送達人隊伍建設走向對社會技術支持的選擇、甄別與最終的后備人才培養,是更為直接的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