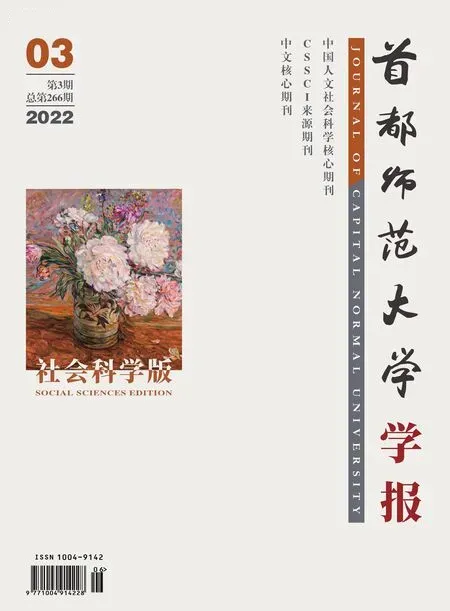論教育學-現象學視頻分析的理論基礎
彭 杰
關于現象學的基本認識構成了教育學-現象學視頻分析的認識論基礎,在此基礎上闡述現象學導向的經驗理論,即經驗的時間結構、意向性、主動性和被動性交織等成為理解教育經驗比如課堂中的消極經驗、注意經驗等的依據。在此意義上,現象學可視為通向事物自身和經驗的生產性、開放性、懷疑-批判性的路徑。那么如何盡可能貼近事物或經驗本身?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如何堅守現象學的旨趣——回到事物本身?現象學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其獨特的方法論,而理論性的方法論如何引導具體的研究實踐?如何能使不可見事物可見?在此需要一種操作化實踐:現象學的還原(Reduktion)、描述(Deskription)和變更(Variation)。基于以上問題,本文在系統介紹教育學-現象學視頻分析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上,引入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視頻分析以及由柏林洪堡大學普通教育學系研究團隊發展的教育學-現象學的視頻分析的實踐過程。
一、現象學作為通向事物本身及經驗的生產性路徑
與以演繹思維和歸納思維為基礎的研究不同,現象學研究遵循“溯因式”(abduktiv)①Charles S.Peirce,Schriften zum Pragmatismus und Pragmatizismu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6.Jo Reichertz,Die Abduktion in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über die Entdeckung des Neu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3.思維方式。作為第三種思考和認識路徑,現象學研究既不遵循從普遍法則到特殊事件的演繹邏輯,也不完全遵循從特殊事件到一般法則的歸納邏輯,而是從被看見、被展示物以及自身顯現物出發,將可能的意義或解釋“嵌入”(einlegen)②Eugen Fink,Grundfragen der systematischen P?dagogik,Freiburg:Rombach,1978,p.13.到這些事物之中。這是以教育經驗為核心主題的教育學-現象學研究的重要認識論基礎。對教育經驗的現象學理解建立在現象學的經驗理論之上,其中經驗的“顯著差異”(Signifikative Differenz)③Bernhard Waldenfels,Einführung in die Ph?nomenologie,München:Fink,1992.即經驗的“時間結構”是其他一切結構特征的基礎。
(一)現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
如上所述,溯因式的思維方式作為現象學研究和認識的基礎與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不同。演繹式研究始于既定的普遍規則、法則、定理和理論,并嘗試從因果關系的層面解釋(erkl?ren)某一現象或事物的原因,因而被觀察或研究的事物和現象可訴諸那些純粹客觀的法則、規則和理論,演繹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確定的普遍法則的應用,并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徑;演繹的研究范式可被理解為一種具有必然性的思維方式,“演繹實際是去證明某物必然如是”④Charles S.Peirce,Schriften zum Pragmatismus und Pragmatizismu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6,p.171.。與此相反,歸納式研究遵循自下而上、從特殊到普遍的路徑,從大量的特殊事件歸納式地界定某一法則和理論,或者“挖掘”(auslegen)⑤Malte Brinkmann,“Verstehen,Auslegen und Beschreiben zwischen Hermeneutik und Ph?nomenologie.Zum Verh?ltnis und zur Differenz hermeneutischer Rekonstruktion und ph?nomenologischer Deskription am Beispiel von Günther Bucks Hermeneutik der Erfahrung,”in Sabrina Schenk,Torben Pauls,ed.,Aus Erfahrung lernen.Anschlüsse an Günther Buck,Paderborn:Sch?ningh,2014,pp.199-222.隱藏在事物與現象背后的既存意義,歸納的目的不在于從因果關系的層面證明、解釋現象與事物,而在于闡釋(Interpretieren)和理解。解釋學遵循歸納的思維方式,并將“理解”(Verstehen)作為其核心概念,解釋學的理解指向隱藏在事物背后的、既定的意義世界,⑥Malte Brinkmann,“Ph?nomenologische Methodologie und Empire in der P?dagogik.Ein systematischer Entwurf für die Rekonstruktion p?dagogischer Erfahrungen,”In Malte Brinkmann,Richard Kubac&Severin Sales R?del(hrsg.).P?dagogische Erfahrung,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5,pp.33-59.在此意義上,解釋學可被視為一種“解釋的藝術”(Auslegungskunst)和“解釋理論”(Theorie der Auslegung)⑦Helmut Danner,Method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r P?dagogik,München,Basel:Reinhardt,1998,p.32.,即“意義挖掘的藝術”;在解釋學看來,某一實踐、事物、文本和所言說之物的背后存在某種隱含的、潛在的意義,它們借助于“解釋”、闡釋或重構而浮現并被理解,因而解釋學旨在對某一實踐、事物、現象的“理解”⑧Dieter Lenzen,P?dagogische Grundbegriffe,Reinbek:Rowohlts Enzyklop?die,2001,p.1198.,并因此而“偏離事物本身”⑨Helmut Danner,Method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r P?dagogik,München,Basel:Reinhardt,1998,p.32.。在狄爾泰看來,研究者的“理解”可視為對隱含的意義視域的重構、“對過往意義的重建”[10]Malte Brinkmann,“Ph?nomenologische Methodologie und Empire in der P?dagogik.Ein systematischer Entwurf für die Rekonstruktion p?dagogischer Erfahrungen,”in Malte Brinkmann,Richard Kubac&Severin Sales R?del,ed.,P?dagogische Erfahrung,Theoretisch e und empir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5,pp.33-59.或意義挖掘的過程。因此,理解意味著將某物理解為某物(etwas als etwas),但解釋學并未進一步區分感知與理解之間的時間性差異,即對表層事物的感官知覺和對事物背后意義世界的理性理解之間的差異。
現象學的研究路徑與以上兩種推理方式不同,它更多地遵循或類似于第三種思維路徑:溯因。與其他重復和再生的推理方式不同,溯因推理屬于創新性的推理模式,因為它既不屬于形式邏輯,也不遵循既定的操作化步驟;①Jo Reichertz,“Abduktives Schlussfo”lgern und Typen(re)konstruktion.Abgesang auf eine liebgewonnene Hoffnung,”in T.Jung und S.Müller-Doohm,ed.,Wirklichkeit“im Deutungsprozess:Verstehen und Methoden in den Kultur-und Sozialwissenschaft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3,pp.258-282.既不致力于從因果關系層面解釋某一事件,也不致力于理解和挖掘隱藏在事件背后的意義或將某一事件納入既定的理論和秩序,而旨在對被感知物、自我呈現物的某些可能的、非因果性的解釋,旨在生成可能的意義和發現新的解釋可能性。因此,溯因可被理解為一種“猜想式”的思維方式,具有開放性并蘊含多種可能性,正如Peirce所言,“溯因表明可能之事物”②Charles S.Peirce,Schriften zum Pragmatismus und Pragmatizismu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6,p.171.,因而并不具有確定的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證明力,只具有有限的說服力。但正是由于這種不確定性和有限性,才使得意義和視角的多元化、認識和理解視域的拓展、經驗的新維度的生成成為可能。因而,現象學作為一種溯因的思維和研究風格可被理解為通向現象和經驗的生產性路徑。
但現象學的研究路徑首先并不在于可能之意義或解釋模式的內置或嵌入,而是將自身顯現物的顯現置于中心。在海德格爾看來,現象(Ph?nomen)意味著“自身顯現者(das,was sich zeigt,das Sichzeigende)、敞開者(das Offenbare)”③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Niemeyer,2006,p.28.以及“表面物(das Oberfl?chliche)和就其自身顯現自身者(das Sich-an ihm-selbst-zeigende)……諸現象即那些自身處于光亮之中或被引入光明之中的事物的總和”④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Niemeyer,2006,p.28.。因此,現象并非直接給定的,而是在與自身顯現物的相遇中構造的。海德爾格對“現象”的界定意味著“在現象學的現象背后本質上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東西”⑤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Niemeyer,2006,p.36.,這種對現象的基本態度或假設是意義嵌入以及以現象學取向的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區分現象學與解釋學的重要維度,因為解釋學假定:在表面物或現象背后存在隱藏的意義、本質、實在、實質,存在著某些隱蔽的、符號性的或象征性的東西。
現象學作為一種思考和研究的“態度和風格”⑥Maurice Merleau-Ponty,Ph?nomenologie der Wahrnehmung,Berlin:de Gruyter,1966,p.4.,實際上是一種回到事物本身(Zurück zur Sache selbst)的、開放的態度。作為現象學的首要口號“回到事物本身”首先意味著“拒絕科學”,但拒絕科學在此并不是對科學的敵視,而只是表明生活世界的經驗應該被視為科學研究的起點,“因為科學自身源自于生活世界”⑦Severin Sales R?del,Negative Erfahrungen und Scheitern im schulischen Lernen.Ph?nomenologische und videograph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21.,“科學的世界作為整體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礎上。如果我們要在嚴格意義上思考科學本身、準確地衡量其意義和影響范圍,就要首先回到對世界的經驗之中”⑧Maurice Merleau-Ponty,Ph?nomenologie der Wahrnehmung,Berlin:de Gruyter,1966,p.4.。因此,回到事物本身并不是回到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真實或絕對客觀性,而是“回到所有認識賴以存在的世界”⑨Maurice Merleau-Ponty,Ph?nomenologie der Wahrnehmung,Berlin:de Gruyter,1966,p.5.、回到前述謂的經驗、回到那些自身向我們顯現者,即對事物自身的尊重。另外,現象學的這種回到事物本身的態度以及訴求基于以下這種基本觀點:對差異的敏感性、對世界和他者(物)以及對在感知和思考中遭遇到的陌生者(物)的開放和敞現,在此基礎上,可將同一個現象或事物感知為其他不同的事物。由此,現象學的生產性和反思性在邏輯上就變得可理解。因此,現象學作為一種認識和研究風格、作為一種回到事物本身和開放性的態度,為以經驗和經驗現象為對象的質性-實證教育研究以及理解教育理論(Theorie)、經驗(Empirie)和實踐(Praxis)之間的關系提供新的可能性。
教育科學作為“理論-實證分支學科”和“經驗科學”[10]Malte Brinkmann,“Allgemein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als Erfahrungswissenschaft.Versuch einer sozialtheoretischen Bestimmung als theoretisch-empirische Teildisziplin,”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dagogik,2016(2),pp.215-231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理論—實證(經驗)—實踐”之間的關系,并將“經驗(Erfahrung)的概念和現象置于中心地位”。①Johannes Bellmann,“Jenseits von Reflexionstheorie und Sozialtechnologie.Forschungsperspektiven Allgemein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in Bellmann,J./Müller,T.,ed,Wissen,waswirkt:Kritik evidenzbasierter P?dagogik,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11,pp.197-214.在廣義上,經驗(Empirie)等同于經驗(Erfahrung);在狹義上,經驗(Empirie)是實證經驗(empirische Erfahrung),是對他者和陌生者經驗的重構,而這些陌生經驗將成為教育質性研究的對象,它們不僅通過質性研究被觀察、描述和闡釋,還能開啟新的視域。②Malte Brinkmann,“Verk?rperung und Aufmerksamkeit in p?dagogischer Relation.Der Beittrag ph?nomenologischer Unterrichtsforschung für die qualitative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in Robert Kreitz,Christine Demmer,Thorsten Fuchs und Christine Wiezorek,ed.,Das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qualitativer Forschung,Leverkusen:Budrich,2019,pp.17-38.因而,經驗(Empirie)可被視為關于他者和陌生者經驗的研究實踐,它一方面訴諸特定的理論,另一方面借助于實證材料對既定理論進行批判、補充、再述或生成新的理論。理論與經驗(Empirie)因而處于一種螺旋式的關系之中,二者相互依賴、互為根基。在此基礎上,教育實踐(Praxis)可被理解為“被經驗的實踐”(erfahrene Praxis)③Malte Brinkmann,“P?dagogische Empirie.Ph?nomenologische und methodologische Bemerkungen zum Verh?ltnis von Theorie,Empirie und Praxis,”Zeitschrift für P?dagogik,2015-61(4):527-545.、基于經驗的實踐,因而教育實踐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實踐活動,而是一種由行動主體(師生)所進行、經歷、體驗和遭遇的實踐,由研究者觀察、參與、反思、闡述以及向研究者呈現的實踐。在現象學看來,教育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系并非始終確定不變:二者既非彼此對立,亦非單方面的理論指導實踐、理論源自實踐。相反,二者處于互為基礎的關系之中,在這種關系中,教育經驗(Erfahrung)被視為重要的連接。由于教育經驗(作為研究對象的他者和陌生的經驗)在理論-經驗(Empirie)-實踐關系中的基礎性和連接性作用,需要一種現象學取向的經驗理論,以更好地描述、認識和把握教育實踐以及與其相關的教育經驗。因此,在描述、解釋、重構行動者的經驗之前,必須首先思考:某物如何被經驗以及人們如何經驗這一問題。
(二)現象學取向的經驗理論
現象學分析始于對某一現象或事物的感知。當人感知某物或某人時,總是將其感知為某一特定的物或人(etwas als etwaswahrnehmen),其中蘊含著感知或基于感知的經驗的基本結構和特征:時間性、意向性、主動性和被動性等。
經驗與經驗表達之間的“顯著差異”蘊含著經驗的時間結構。正如胡塞爾所言:“在感知與對感知的符號性設想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本質區別。”④Edmund Husserl,Husserliana.GesammelteWerke.Band 3,in Herman Van Breda,Samuel Ljsseling,Rudolph Bernet,ed.,Den Haag:Nijoff,1950-2004,p.79.這種居于鮮活的經驗與對鮮活經驗的語言表達之間不可化約的區別,根植于身體的、緘默的、前反思的、前述謂的主體經驗與事后的符號化表達(語言化和文本化)在時間上的差異。切身體驗總是先于其事后的表達,因為人是“身體的存在,而非具有身體”⑤Helmuth Plessner,“Lachen und Weinen,”in H.Plessner,ed.,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Frankfurt am Main:Fischer,1970,pp.11-171.,他首先必須借助或通過身體(Leib)⑥在現象學領域,身體通常作為自身與世界之間交互的媒介(Hua IV,S.286)以及作為感知、行動、思考的存在基礎。因此,人不僅是理性的、思考的和行動的主體,更是身體存在的主體(Meyer-Drawe 2001)。身體不再是無生命的、物性的感知客體。正如Polanyi所言:“我們的身體(K?rper)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通常從不會稱之為對象的東西,而是將其作為世界來體驗。”在此他并非區分身體和肉體,而是在身體的意義上使用肉身這個概念。但梅洛-龐蒂和Plessner卻十分注重身體存在(Leib-Sein)和擁有肉身(K?rper-Haben)的差異,強調身體在人的在世存在中的重要性,以此試圖克服心靈與身體、精神與肉體之間的二元論以及心靈對身體的蔑視。在感知、行動、思考中,意向性或對某物的指向性都以身體為基礎。去感知和經驗某物,之后才能談論和描述他所經驗的、引其注意以及向其顯現的東西,由此可見,對經驗的語言表達和符號性呈現以具身化⑦Plessner將具身化(Verk?rperung)描述為人對自身肉體的行為,并從角色承擔的層面出發,區分了三種具身化模式:初級的、表征的和功能性的模式。Brinkmann將具身化視為一種身體的或交互身體的表達和應答形式,通過具身化經驗或實踐的不可言說的、緘默的維度得以描述,不可見的或尚未可見的事物(如注意經驗和消極經驗)在一定程度上變得可見。的經驗為前提,因而具有滯后性。在經驗的時間結構中蘊含著某種“抽離特征”:首先,我們通過遠離自身、通過由我們自身指向他者(物)和陌生者(物)的方式,去感知自我顯現物,因為人是“離(中)心”(exzentrisch)①Helmuth Plessner,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Berlin:de Gruyter,1975,p.328.存在并總是在行動中遠離自身。我們不僅以自我遠離的方式感知自我顯現物,而且在感知中也遠離了感知活動本身,比如我們在觀看的時候并不能看到“觀看”活動本身,當我們學習時,我們遺忘了自身,也遺忘了學習活動。因而,這些切身經驗只能在事后被把握,就如同學習只能在事后被意識到。其次,當我們事后借助于語言去表達和闡釋親歷經驗時,親歷經驗自身已經遠離了對親歷經驗的表達,因此對經驗事后的語言的、符號的描述很難完全契合地表達和再現親歷的、緘默的、前反思的經驗,只能盡可能地接近這些經驗。這對以學習和教育過程中的“教育經驗”為對象的質性教育研究而言意味著什么?研究者只能盡可能地從不同維度(身體、交互身體、語言、空間等維度以及這些維度之間的關聯)去觀察、描述、分析和重構具體教育情境下的鮮活的主體經驗,這正是教育現象學研究以及教育學-現象學視頻分析的首要旨趣。那么如何盡可能貼近經驗自身呢?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如何處理其自身經驗呢?對此,現象學發展出了其自身的方法論(詳見第二部分)。
感知總是對某物的感知,因而具有意向性和指向性。在早期胡塞爾看來,感知和經驗是意識的意向活動,是主體的成就,即經驗和感知由主動的、作為主體的“人”所主導,并賦予被感知物和經驗物以某種意義和內涵。因此,經驗和感知可被理解為主動的意義建構(Sinnbildung)。海德格爾批判了這種以主體為中心的意向性概念,強調“被感知/經驗物”在感知和經驗活動中的主動性:我將自我顯現物、吸引我注意的事物感知/經驗為某物。在我主動地感知和經驗某物之前,已經發生了某種被動的生成,即我已經被自身顯現物所喚醒和吸引;在感知和經驗活動中,不僅是主動的“我”(Ich)將某物體驗為某物或者某物被我體驗;同時,自我顯現物作為某物由其自身出發向“我”(Mir)顯現。因此,行動主體就具有某種主動的被動性,而自我顯現物也具有某種被動的主動性,感知/經驗活動是主動感知和被動感知的交織。在此,“主動自我之有意向的意義建構與被動的意義給予(Sinngebung)相遇,即與能賦予意義的他者、事、物和世界相遇”②Malte Brinkmann,“Ph?nomenologische Methodologie und Empire in der P?dagogik.Ein systematischer Entwurf für die Rekonstruktion p?dagogischer Erfahrungen,”In Malte Brinkmann,Richard Kubac&Severin Sales R?del(hrsg.).P?dagogische Erfahrung.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5,pp.33-59.。因而,意義并非由主動的、活動著的主體所重構,而是在意義建構與意義給予的交織中被構造。被動性意味著向與我們相遇的他者(物)和陌生者(物)的開放。③Malte Brinkmann,“Ph?nomenologische Methodologie und Empire in der P?dagogik.Ein systematischer Entwurf für die Rekonstruktion p?dagogischer Erfahrungen,”in Malte Brinkmann,Richard Kubac&Severin Sales R?del,ed.,P?dagogische Erfahrung.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5,pp.33-59.借助經驗的主動性和被動性的交織,主客二元對立以及以主體為中心的思維被打破,這為認識具體的教育經驗(如學習)以及基于經驗的質性教育研究開啟了新的可能:通常認為學習作為經驗是個體性的、主動的與他人、世界、事物交互的過程,學習必須由自身發起,而不能被強迫;但其也有被動性的一維,主要體現在“某些事情只是這樣發生在我們身上,它映入我們的視野,我們從自身所處的視角去‘看’它……學習并非總是積極主動的過程,所要認識和學習的事物、他者以及世界首先充盈我們(的身體)、與我們的身體遭遇,才為我們所見、所聽、所學、所感知、所認識”。④彭杰:《現象學視角下的學習:一種新的面向和可能》,《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0年第2期。
在經驗活動中,主動建構意義和被動給予意義均與經驗自身的“作為-結構”(Als-Struktur)不可分割。這種Als-Struktur則與經驗方式以及自我顯現物的顯現方式相關。相對于將某物經驗為某物、某物作為某物向我們顯現而言,自我顯現物作為某物向我們顯現的方式,我們將某物經驗為某物的方式更為重要。在將某物經驗為某物的經驗活動中Als-Struktur首先將經驗對象和經驗內容聯系起立,并蘊含某種方法論的差異,即經驗活動和經驗內容之間的差異。我們所見之物與事物自我顯現的方式以及與我們觀看的方式密切相關。自我顯現物并非簡單地作為某物顯現,而是作為某物向“我們”顯現。另外,此結構也表明:自我顯現物絕不會完全地向我們顯現,而總是偽裝或遮蔽地向我們顯現。當經驗對象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向我們顯現其某一方面時,當我們從某一視角或在某視域內將其視為某物時,它的其他方面在當下就淡出視野,成為不可見或尚未可見之物。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感知、描述、闡釋某一現象,并為其他可能的觀察方式和闡釋留有余地。因此,我們只能盡可能地貼近某一現象或經驗,現象的自我遮蔽式顯現成為現象學開放性和生產性的重要認識論前提。
二、通向事物自身的方法論操作
現象學的經驗理論表明,由于經驗的時間結構和自我顯現物的自我遮蔽式的顯現方式,即某物在顯現自身的同時,也遮蔽了其自身(的某些層面),我們只能盡可能地貼近、描述和把握經驗,只能盡可能地回到事物本身。作為研究者如何盡可能地貼近他人的經驗和回到事物本身?如何處理自身的經驗?如何處理現象的不可見維度或如何使不可見和尚未可見的事物可見化?現象學發展了其獨特的方法論,并具體化為以下操作:現象學的描述、還原和變更。
(一)現象學的描述(Deskription)
現象學的描述和可見性與不可見性、可說與不可說之間的差異緊密相關,并基于以下觀點:事物的表面之下和之后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東西。①Malte Brinkmann,“Verstehen und Beschreiben.Zur ph?noemnologischen Deskription in der qualitativen Empirie,”in J.F.Schwarz und V.Symeonides,ed.,Erfahrungen verstehen—(Nicht-)Verstehen erfahren,Innsbruck:Studien Verlag.2020a,pp.29-46.因此,現象學的描述性首先集中在可見的、可體驗的和可描述的東西上。這種可見的、可體驗的和可描述的東西就是身體和交互身體的表達:面部表情、手勢、目光和目光方向、姿勢、身體張力、身體運動以及笑、哭和微笑中的一些表達等。與此相反,行動者的動機、意圖以及他們的內心感受和心理過程是不可見的,它們只能借助行為的可見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把握。但不可見性并不限于以上內在的過程,現象的遮蔽式自我呈現以及研究者已有的偏見、經驗和理論認識也會導致自我顯現物的不可見(層面)。為了使尚未可見和不可見的事物可見,就需要方法的保障,而這只有通過現象學的描述以及伴隨其發生的還原和變更來實現。在此意義上,現象學的描述可被視為“讓看見”的實踐。在現象學描述中,不僅要對自我顯現物進行還原式的、內容豐富的描寫,而且要描寫其顯現方式,即不僅描述發生了什么,而且要描述如何發生,人如何對其所遭遇的他者(物)或陌生者(物)的要求做出回應。所以,現象學的描述首先既不致力于隱含意義的挖掘,也不致力于可能意義的嵌入,既不致力于闡釋,也不致力于因果性解釋,而旨在描述經驗的初級的、可見的層面,旨在看見和描述表面的事物和可見的事物。
此外,現象學的描述也是對切身、前述謂和前反思的經驗在語言或文本層面上的符號化。在文本化和語言化過程中許多東西超出了語言和語法的范疇,因而是緘默的、不可說的,很難借由語言的媒介將其完全轉化。為了盡可能地接近前語言和前反思性經驗,現象學描述需要對語言有特殊的敏感性。比如,要為所描述的行為選擇恰當的動詞和非評價性、非推斷性的形容詞,盡量避免使用因果句、目的句以及隱喻等。
(二)現象學的還原(Reduktion)
“現象學分析并不始于觀察和釋義,而始于對感知內容和潛意識解釋的還原。”②Malte Brinkmann und Severin Sales R?del,“P?dagogisch-ph?nomenologische Videographie.Zeigen,Aufmerken,Interattentionalit?t,”in Christine Moritz und Michael Corsten,ed.,Handbuch Qualitative Videoanalyse.Method(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forschungsprakt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p.521-548.在胡塞爾看來,懸置(Epoché)意味著暫時終止或推遲判斷。在還原中研究者將已有的關于所觀察現象的經驗、認識、偏見以及理論和科學的解釋模式暫時地加括弧、盡可能地懸置和批判性地反思;基于這些被懸置的個體經驗和理論模式之上的判斷、解釋、評價也應該暫時中止。雖然所要懸置的東西是感知和認識的基石,但同時也限制甚至阻礙了研究者對于事物的認識和認識的可能性。通過還原,關于所要感知和體驗之物的判斷和預先理解失去其效用,以使那些由于預先理解和判斷而被掩蓋的事物和事物的某些方面、那些尚未可見的以及未被看到的東西、那些以遮蔽的方式自我顯現的東西如其所是地顯現或可見,以豐富和拓展觀看的方式以及與此相關的對感知對象的認識,因而還原的目的并非是追求一種純粹中立的、不做任何判斷的認識。現象學的還原并非一種實際可見的操作,而是指向對現象和事物的認識的一種反思-懷疑的態度,一種使現象或熟悉的事物陌生化、自身視角陌生化以更貼近事物自身的過程;缺少了現象學的還原,現象學的描述和變更則無從談起。在現象學還原中,研究者不僅要懸置和反思自身已有的經驗、理解和理論,還要反思其觀察、感知和體驗事物的方式、角度和過程,因為其所能體驗和感知的事物與這些方式和視角密不可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存在百分之百的還原和懸置,如同無法完全將前反思、前語言的身體經驗轉化為語言表達。
(三)現象學的變更(Variation)
在接下來的變更實踐中,先前被懸置的經驗、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理解和判斷再次進入我們的視野。正是由于現象自身的遮蔽式顯現、現象學的溯因式思維以及與此相關的向世界的敞現和開放態度,研究者才可以從另一視角考察現象,并將其設想和解釋為與它開始呈現于我們的不同的事物,對此需要研究者具有相當的想象力以及與其他研究者之間交互主體的交流。借此,關于某一現象和事件的觀點、視角、意義得以豐富和多元化。借助于溯因,那些可能的說明與意義被納入感知對象之中,并由此生成關于經驗的新的認識以及新的理論。
但在現象學的分析路徑中,三種具體操作并非依次發生,而是彼此交織,并可能同時被用于某些具體的分析階段。借助于反思-懷疑的還原、還原式的描述以及基于想象的變更,才可能更加接近經驗和事物本身,補充舊有的認識,并從中溯因式地生成某些新的東西。
三、視頻分析及現象學視頻分析
現象學-教育科學在內容、方法論、學科層面上都將經驗概念置于中心,并借助于現象學方法論嘗試重構教育領域中的經驗即主體經驗。但由于教育實踐的復雜性,教育與學習過程中的主體經驗并非直接可見、可描述和可把握,身體作為自身與世界、他者關系的媒介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被視為經驗的載體。因此,個體的主體經驗可在具體教育情境中、在應答過程中借助于身體或具身化得以被觀察、描寫。但如何從不同視角充分和準確地描述、把握教-學過程中稍縱即逝的經驗、身體表達和應答過程?視頻分析,確切地說,現象學的視頻分析,借助于其自身優勢在質性-實證研究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一)視頻分析簡論
在介紹教育科學領域中現象學視頻分析及其過程之前,需要先簡要介紹一般意義上的視頻分析。嚴格來講,視頻分析出現于20世紀末,因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還是一種相對新的研究方法。但基于視聽數據的方法卻有著悠久的歷史:一方面可追溯至1830年代社會科學研究中聚焦于人類行為觀察和互動過程的圖片和影視分析;另一方面可追溯至1890年代在人類學中致力于重構和解釋異文化或原始文化的行為方式和社會文化結構的民族志電影。①RenéTuma and Bernt Schnettler,Hubert Knoblauch,Videographie.Einführung in die Video-Analyse sozialer Situationen,Wiesbaden:Spinger VS,2012,p.24.
與其他類型的數據相比,視頻數據能夠為質性-實證研究帶來什么?與其他的研究方法,如主要基于文本和言說資料且致力于意義或秩序重構的客觀解釋學和對話分析相比,視頻分析開啟什么新的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視頻其實是人類眼睛的延伸、記憶的底片,也是對現實,更確切地說是對視頻所構造的真實性的保存,因為視頻總是在特定框架、視角和研究目的下被錄制,因而可能只呈現了其自身所構造的真實或有限真實。
視頻不僅捕捉和呈現靜態、瞬時的情景,也記錄動態事件和過程;不僅記錄發生于特定情境下的交流與互動中的言說層面,而且展現言說的語氣、語調、語速等,呈現特定時空情境下人與人或人與物之間應答過程的非語言的、身體的、不可言說但可展示的方面。因而通過課堂實錄的視頻,不僅可以準確地觀察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和應答,也可以觀察人(師生)與學習材料或物品之間的應答。在此意義上,視頻作為一種媒介能夠鮮活地記錄、呈現和保存具體情境中的教育互動和應答之語言的、身體的、物質的、空間的和時間的維度。在某些課堂互動和應答中,語言自身有時是枯燥的、貧乏的,并不能夠充分表達雙方的意圖或者所要表達的事物是不可或不能言說的,因此需要借助身體去傳達與交流;有些互動和應答本身是無聲的、靜默的,只通過身體的表達(如眼神接觸、手勢等)去實現;即使在以言說為主的互動和應答中,也必然伴隨著某些其他的身體表達。身體的表達有時先于言說自身,其所呈現的東西有時遠多于言說,“我們所知的遠多于所能言說的”①Michael Polanyi,Implizites Wiss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5,p.25.。因此,視頻分析借助于視頻數據的多維性能夠呈現和把握教育互動和應答的復雜性和多模態性。
除了視頻資料的多維性,借助于視頻不僅可以觀察同時性的互動,也可以觀察課堂互動與應答的不同維度之間的交織和相互關聯,比如言說與(身體)展示、言說與行動之間的關系。因此,通過視頻不僅可以觀察在特定時刻或時間段中互動與應答的某一或某些維度,如語言的要求與應答、表情、手勢、身體姿態和身體的活動等,更能觀察這些維度之間的協調與配合,如“手-眼協調”。視頻分析作為一種研究路徑,由于視頻資料的多維性、對課堂互動與應答的同時性和動態性記錄以及對這些互動與應答的不同維度之間交織關系的呈現,能夠為觀察、描述和把握課堂互動和應答開啟新的可能,對質性-實在研究以及教-學過程中經驗的重構具有重要意義。
另外,視頻可以永久地保存其中所記錄的情景,因而研究者可以反復觀看,可以更加詳細、全面地觀察所要研究的情景,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地改進、修正、檢驗關于這一情景的描寫文本,以更加準確地描寫、貼近情景本身。通過反復觀看可以“陌生化”、反思自己對某視頻所記錄之情景的最初視角和觀點,并獲得新的認識。其中,除了反復觀看,觀看方式即視頻的播放模式(常速、慢速、加速,或有聲、無聲)也扮演著重要作用。借助于以上視頻播放技術,視頻分析不僅使更加詳盡具體地觀察成為可能,而且使得對課堂互動與應答復雜性的描述成為可能。另外,從現象學的視角看,也使得盡可能地貼近所要研究的情景以及互動性和應答性的經驗成為可能,使得關于情景的新的觀察視角、認識和理解成為可能。
但是每一種方法都有其邊界。視頻資料并不能直接向我們呈現隱藏于可見的行動和互動背后的(人的)目的、意圖、動機、感覺、情感和抽象概念(如注意、消極性、愛、自由等等)。這些通常只能從可見的具身行為、對他者或陌生者的交互主體性應答中部分地推測。通過視頻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不同模式和視角下身體和語言的表達,那些緘默的、不可言說的或很難言明但卻可展示的東西,即那些表層之物,也正是現象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起點。另外,視頻本身并不能直接呈現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實際關系,不能(完全)呈現在沒有攝像機介入下的、日常課堂生活的樣態以及師生的行為習慣等。而這只能通過前期的田野工作或參與式觀察和訪談來彌補和平衡,由此盡可能地了解視頻所不能直接呈現于我們的東西。視頻以及其他的數據類型(田野筆記、深描、訪談、教學材料以及其他物品)是后續研究的對象和材料,但它們并不只是分析的對象和客體,其自身會對應答者提出要求并期待研究者對此的應答和回應,研究者在觀看、閱讀這些研究素材時會對其產生身體的、情感的、非意向性的應答。
(二)教育學-現象學視頻分析的實踐性操作
與課堂教學研究中其他取向的視頻分析相比,現象學取向的質性-實證視頻分析遵循現象學方法論的基本操作,建立在現象學基本認識和經驗理論之上。它并不局限于互動過程的語言層面,因而,并不致力于課堂意義的重構,也不致力于重構超個體的、制度化的、普遍的教學秩序和結構。相反,它特別強調互動過程中身體、身體間、情境和物質的層面,因而,教-學過程中個體性、獨特、主體以及交互主體的經驗可以從不同的維度被觀察、描述和把握,由此,盡可能地接近主體經驗本身。柏林洪堡大學普通教育學系在批判性地接受其他視頻分析理論以及反思性地遵循現象學基本思想和方法論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教育學-現象學的視頻分析”①Severin Sales R?del,Negative Erfahrungen und Scheitern im schulischen Lernen.Ph?nomenologische und videograph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252.。
如教育科學領域中的現象學研究一樣,現象學取向的視頻研究將教育經驗置于中心,并嘗試重構在教育互動中以及在與他者、物體和材料交互中主體和交互主體的經驗。教育學-現象學視頻分析遵循現象學研究的基本假設、基本思維方式和開放性態度:在現象背后并不存在隱含的意義、本質、實質,現象即自我顯現物,現象學旨在讓事物顯現;以溯因的方式看待和思考教育現象和教育經驗;對所研究的現象和情景持開放的態度。因此,教育學-現象學視頻分析并不致力于挖掘和解釋經驗的意義,而在于嵌入可能的意義和解釋。另外,在分析具體視頻時,尤其是在觀察、描寫、解釋過程中,運用現象學的還原、描述和變更。教育領域中的現象學視頻分析并不僅關注視頻中所描繪的教育情景和事件,而且關注在單獨或集體觀看視頻時研究者對視頻自身以及對視頻所呈現之事件的應答,這種應答以響應性和非意向性為特征,既非某一原因(線性-因果)的結果,亦非對某一刺激的機械性反應,②Malte Brinkmann and Severin Sales R?del,“ P?dagogisch-ph?nomenologische Videographie.Zeigen,Aufmerken,Interattentionalit?t,”in Christine Moritz und Michael Corsten,ed.,Handbuch Qualitative Videoanalyse.Method(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forschungsprakt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p.521-548.而是身體的、情感的響應,因而可借助現象學方法論的操作被描述,并作為研究者的經驗或參與式經驗對后續關于視頻所描繪事件的分析具有重要意義。③Severin Sales R?del,Negative Erfahrungen und Scheitern im schulischen Lernen.Ph?nomenologische und videograph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253.最后,教育學-現象學視頻分析很難由某一位研究者獨立完成,需要與其他研究者交流與碰撞,尤其是在對視頻的描述和解釋階段。在與其他研究者交互主體的交流中,對視頻的深度描寫被討論、理解、質疑、改進,使描寫事件的視角得以豐富和多樣化,而對事件的解釋也被交互主體性檢驗,事件和經驗的意義因而變得多元,自身關于事件的觀點被反思和陌生化。
如前所述,在視頻錄制之前需要進行一段時間的田野工作或參與式觀察,是為了搜集其他數據資料以及參與經驗,使研究的問題更加聚焦并確定視頻錄制的時間等。通過田野工作和參與式觀察,研究者可以更好地了解所觀察學校、班級、教師和學生的概況,對課堂氛圍、師生在教-學過程中的習慣等形成初步的認識,也讓師生能夠習慣于“觀察者”的在場,以減少研究者的在場對教學、學習和師生互動產生的影響。不同于嚴格意義上的人類學田野工作,此處的田野工作持續時間相對較短,約為一個月。而在課堂觀察過程中,研究者已經對所觀察的情景、教-學互動等做出了某種身體-情感的回應,在此意義上,研究者并非“冷漠”的觀察者或旁觀者,而是作為“體驗者”,他總是處于所觀察的課堂之中,成為整體情景的一部分并體驗著所觀察的課堂情景。
在課堂觀察時,觀察和體驗的引人注意的情景被深度描寫,不僅要描寫課堂互動和應答的語言層面,也描述身體或身體間的表達。在此階段,已經使用了現象學的還原和變更。現象學的描寫其實是對前反思經驗的書面記述、符號化、語言化和文本化過程,在此過程中研究者只需描寫其所見、所經驗之事物,自我顯現物及其顯現方式,需要懸置研究者先前關于學校、學習等的經驗、偏見、預設、想象以及相關的教育教學理論等等,此階段所需要做的不是解釋和判斷,而是呈現實際的課堂情況:課堂互動以及應答、發生了什么以及如何發生等等,進而形成關于某一課堂情景的深度的、系統的、可讀的文本。這些深描文本需要與其他研究者討論:為何選擇描寫這一情景及其與研究主題的關系如何?此文本或文本中的某些句子想要表達什么?其他在場者對同一情景是如何描述的?通過討論,研究者自身的經驗得以交流和擴展,所描繪的情景更加清晰,其他可能對此情景的理解和解釋角度也隨之而來,文本自身也可進一步被完善和加工,其他研究者對文本以及文本所描繪的事件的應答被搜集,接下來研究的問題也進一步被聚焦。
視頻錄制時需要兩臺固定但可旋轉的攝像機從(前后)相對的視角對課堂教學進行錄制,以捕捉師生在某一互動過程中的同時行為。①Malte Brinkmann and Severin Sales R?del,“ P?dagogisch-ph?nomenologische Videographie.Zeigen,Aufmerken,Interattentionalit?t,”in Christine Moritz und Michael Corsten,ed.,Handbuch Qualitative Videoanalyse.Method(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forschungsprakt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p.521-548.在感知性觀看時,尤其關注研究者對視頻以及視頻所描述情景、事件及其要求的情感與身體表達,而這種身體和情感的應答可被視為一種理解方式。另外,在對課堂視頻進行“感知性觀看”時,師生的身體表達也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學生在課堂中的行為表現,他們在做什么,尤其在課堂對話中如何回應教師和第三者(其他同學)的(語言的、身體的)要求,如何對他們的應答進行回應等等。其中師生的身體表達作為具身行為(目光、眼神、面部表情、身體姿態、手勢等等)、作為對他者(物)的應答在一定意義上能表明:其注意是否被喚醒和維持,其是否專注以及專注于什么,他者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等等。
在感知性觀看之后,結合研究問題和研究視角選取和剪切接下來要詳細分析的不同視頻片段(1~5分鐘)。所選取的視頻將與其相關的其他材料(對該視頻片段的文字轉錄、深描文本,視頻片段所在的課時的教學流程表、所用教-學材料)在資料分析會或其他形式的交流中被觀看、討論,其中現象學的還原、描述以及變化在此階段被同時使用。另外,視頻選取應遵循以下原則:被選取的教育情景對師生而言應是常態化的、典型的而非一次性或偶發的情景;所選取的視頻片段應與研究主題和問題密切相關;由于現象學視頻分析尤其關注身體的、緘默的表達和經驗,所選取的教育情境應包含相對豐富的身體互動和應答。如此看來,視頻片段的選擇其實是基于對視頻所描繪的教育情景的“初步理解”②Severin Sales R?del,Negative Erfahrungen und Scheitern im schulischen Lernen.Ph?nomenologische und videograph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257.。在資料分析會或者其他交流形式中,在觀看視頻片段以及閱讀對視頻片段的深度描述時,研究者關于視頻片段及其描述的“初步理解”或“響應經驗”被表達、搜集和批判性交流,在交流過程中,自身的經驗、視頻與文本描述為他者所理解,對視頻和文本中所描述的教育情景的不同理解或不同理解角度也在此浮現。
在接下來的現象學分析階段,主要使用到現象學的還原和變更。首先,在還原階段盡可能懸置或擱置研究者主體的已有經驗、設想、理解以及研究者所具有和習得的教育教學理論知識和洞見,并對其進行批判性反思,其目的不在于實現認識和理解的絕對“中立性”,而在于使研究者已有的經驗和理論模式暫時地失效或失靈,以此盡可能地從不同角度和層面觀察和貼近事物本身,盡可能地讓教育現象按其自身呈現于人的方式顯現或被看見。加括弧或懸置并不等于排斥和消解,而且個體已有的經驗和理論作為認識的基礎也不可能被完全懸置。在變更階段,那些被懸置的東西尤其是理論方面再次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并發揮作用,一方面還原過程中對事物和現象的理解可追溯或歸于相應的理論模式,所研究的教育現象從不同的理論視角或在不同的理論模式下被說明和解釋,在此過程中再次實現了意義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存在這種情況:已有理論并不能契合或解釋實際的實證經驗,由此那些作為理論之鏡被使用和嵌入的既存理論被批判、反思、重述、補充,并結合實證經驗生成某種新的理論。在此階段,不再僅僅關注對視頻所呈現的教育現象和事件的身體的、情感的、響應式和前反思的應答和應答經驗,而是轉向反思的、有條理的觀看、判斷、評價、分類以及理論再生。③Severin Sales R?del,Negative Erfahrungen und Scheitern im schulischen Lernen.Ph?nomenologische und videograph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258.
在完成對某一視頻片段的現象學分析后,還可將其與其他視頻片段進行比較,這些視頻片段可來自于同一課堂錄像,也可取自其他教師、其他學科、其他學校甚至另一文化背景下的課堂視頻。通過比較,一方面可以探尋不同文化和社會環境下的共性和差異,另一個方面可以將教育實踐(如課堂展示和注意)進行分類,“這些類型并不是從諸多材料和資料中歸納而來,而是從反思和還原的操作中以溯因的方式獲得的;類型并非被建構或重構的,這些共性或共有物作為典型的事物以一種意義生產的方式被嵌入”①Malte Brinkmann and Severin Sales R?del,“ P?dagogisch-ph?nomenologische Videographie.Zeigen,Aufmerken,Interattentionalit?t,”in Christine Moritz und Michael Corsten,ed.,Handbuch Qualitative Videoanalyse.Method(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forschungsprakt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p.521-548.。
最后是視頻分析軟件Feldpartitur的使用。“借助于此軟件的樂譜式標注,它不僅能描繪視頻的歷時特征和序列邏輯,而且基于共時性視角考慮教育情境的復雜性。在視頻轉錄中使用圖像符號(Symbole)而非語符(sprachliche Signifikanten),從而實現了(由語言向符號的)符號化的轉換。符號在意義(Sinn)和含義(Bedeutung)上更具開放性,使人較少地依賴于語法規則。”②Malte Brinkmann and Severin Sales R?del,“ P?dagogisch-ph?nomenologische Videographie.Zeigen,Aufmerken,Interattentionalit?t,”in Christine Moritz und Michael Corsten,ed.,Handbuch Qualitative Videoanalyse.Method(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forschungsprakt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p.521-548.盡管借助于Feldpartitur研究者可以將諸多事物和現象符號化,并從不同維度歷時地觀看它們,但此視頻分析軟件并非自動解析視頻,不能將視頻中的某些事物符號化并賦予其意義,研究者在使用視頻分析軟件之前必須事先確定分析的維度和類型、所使用的相應符號,并賦予這些符號特定的含義,在軟件中觀看視頻片段時,將被賦予意義的符號添加至視頻中相應的位置。總體而言,在教育科學研究中,這一視頻分析軟件其實是研究結果外化、可視化、直觀化和符號化表達的媒介和工具,如對情感、視線、手勢、身體姿態類型的符號性轉換與表達。
四、結語
基于現象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教育學-現象學視頻分析是一種反思、懷疑、批判、開放和生產性的質性-實證研究路徑,從教-學過程中具體的教育經驗和經驗現象出發,首先聚焦于教育現象和互動的可見方面,以呈現教育互動和現象的復雜性;在此基礎上,借助現象學的還原操作以及視頻觀看模式使教育現象中尚未被看到的方面以及由研究者理論的、個人的、文化的、歷史的視域所遮蔽的方面盡可能地顯現,并將“可能的意義”嵌入到所研究的教育現象以及現象的諸多可見的方面之中,進而實現意義的豐盈和多元化:“意義”在此并非指隱含于教育現象和經驗背后的、已經存在的意義,因而意義的多元化并非通過研究者的重構、挖掘和再生產來實現,即并非完全歸于主體的成就和意志;相反,“意義”指向可能的、潛在的意義,借助于“嵌入”而實現,借此強調了具體教育現象(即質性研究對象)作為自我顯現物在意義生成中的重要作用,重新認識作為研究者以及行動者的人的被動性或“主動的被動性”,即向教育經驗和現象的開放,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克服了傳統的主客二元對立、對作為一切活動之起源和發端的主體的過度強調、對作為被動承受者客體的輕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新的人與世界關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