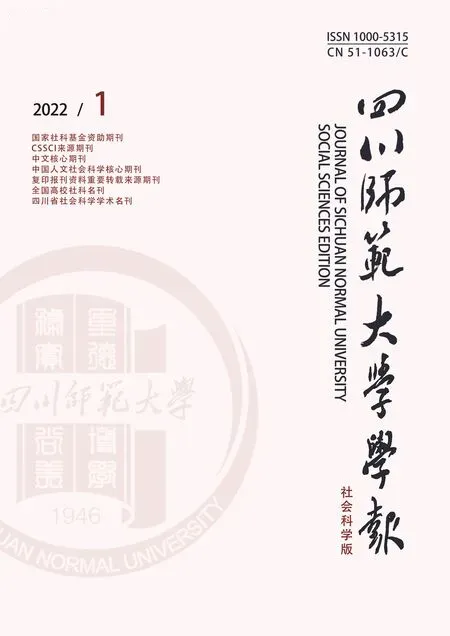論“雙減”背景下構建社會教育力與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的張力
鄧 璐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減負以及義務教育“一費制”的推行使中小學生在校學習時間縮短,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提前了放學時間,學生課后的教育和服務成為家長自由選擇、社會多元化提供資源的范疇,其中也滋生了校外培訓機構監管缺失、教育不公平加劇等問題。2017年2月發布的《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為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幫助家長解決按時接送學生困難做出了具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出了“充分發揮中小學校課后服務主渠道作用”(1)《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教基一廳〔2017〕2號),教育部官網,2017年3月2日生成,2021年9月1日訪問,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1703/t20170304_298203.html。。“主渠道”的定位強化了學校在學生課后托管、作業完成、興趣培養等方面的責任。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進一步提出要強化學校教育的主陣地作用,這是“雙減”的源頭治理,通過提升學校教育質量讓學校教育發揮其應有的育人價值和社會功能。在政策落實的過程中,要避免“強化”之后帶來的對其他教育力量的“弱化”甚至“取代”,忽視社會教育力量的形成和發揮。
一 社會教育力:概念與構成
社會有什么樣的教育力量?葉瀾提出了“社會教育力”的概念,并將其解釋為“社會的教育力量”(2)葉瀾《社會教育力:概念、現狀與未來指向》,《課程·教材·教法》2016年第10期,第4頁。。這種教育力量由兩種類型的活動產生,一種是由教育活動產生,包括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這種教育活動對人身心發展所起的作用被稱為“教育作用力”;另一種則是人類其他社會活動對人的身心發展產生的影響,被稱為“教育影響力”(3)葉瀾《社會教育力:概念、現狀與未來指向》,《課程·教材·教法》2016年第10期,第4頁。。可見,在社會教育力的構成中,學校是專門從事教育活動的機構,學校教育(正規教育)產生的是教育作用力,在“雙減”政策中,應發揮主陣地的作用。
而對于非正規教育產生的作用力以及廣泛存在的教育影響力應如何看待?社會教育力概念的提出,就是期待在理論研究與實踐中能重視并整合這部分教育的力量。這是一個新的概念,但對這種教育力量的關注早已有之。二戰之后,各國致力于恢復社會生產發展,教育的發展是其中關涉人才培養、國力提升的重要部分。因戰爭導致的學校教育的中斷、個體在青少年期學習的中斷,以及飛速發展的科技和生產方式的變化都對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個體出現了更多樣化的學習需求。人們開始反思學校教育系統是否能完全滿足這些變化帶來的新需求,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終身教育”的理念,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學會生存》的報告中提出“向學習化社會前進”,未來的社會應重新審視教育與社會的關系,教育不僅僅是社會的諸多系統之一,教育的力量應該彌散到整個社會,這就是“學習化的社會”,“教育不再是一種義務,而是一種責任了”(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編著《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華東師范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譯,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03頁。。這種責任不局限于學校系統,是社會中每一個組織與個體的責任。
我國20世紀80年代引入現代終身教育的理念,并把建設學習型社會作為社會發展的目標之一,轉化為政策實踐。在教育學理論構建上,項賢明提出“泛教育理論”,試圖突破傳統教育理論“強行從社會生活中圈出一個片斷來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5)項賢明《泛教育論:廣義教育學的初步探索》,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頁。的問題,要從廣泛的社會生活中去透視教育現象,從廣義的教育去理解教育存在的真實形態。李政濤提出教育發展的“全社會教育”路向,要“把更多社會能量與資源納入其中,轉化為教育融合力”(6)李政濤《當代教育發展的“全社會教育”路向》,《教育研究》2020年第6期,第4頁。。他以人的發展作為教育融合力可能形成的邏輯起點,不同的實踐形式和實踐主體出于自身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都會產生教育融合的需要,“社會教育力”就是其中從社會系統視角出發的一種教育力量(7)李政濤《當代教育發展的“全社會教育”路向》,《教育研究》2020年第6期,第10-11頁。。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已經關注到廣泛存在于社會中的教育活動,以及其他社會活動所具有的教育影響。關注的焦點從強調這種教育力量的客觀存在,到重視并研究他們,進而探究學校教育的力量與這種教育力量的關系以及如何進行整合。“泛教育論”、“全社會教育”、“教育融合力”、“社會教育力”等理論或概念的提出就是在進行這種探索。葉瀾基于終身教育的視界和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時空特征提出了“社會教育力”的概念,更關照實踐中教育活動的真實形態,“雙減”政策正是對產生“教育作用力”的兩種教育活動(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發展的糾偏與協調,而廣泛存在的“教育影響力”又是應該重視和開發的力量。這三種活動形態、兩類社會教育力量的關系及合力的形成是“雙減”政策落實過程中必須處理好的問題。
二 “雙減”政策強化學校主陣地作用:方向與實踐誤區
“雙減”政策直接指向的政策目標包括兩個方面:針對學校教育本身,要進一步提升教育教學質量和服務水平;針對非正規教育中的校外培訓,則是要進行全面的規范,消除校外培訓的亂象,使校外培訓的熱度逐步降溫。兩個目標都指向社會教育力構成中的教育系統的活動,一個是指向正規教育,一個是指向非正規教育。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的作用,就是要強化正規教育的作用力。相比非正規教育和社會其他活動的影響力而言,這種作用力一直是一種強勢的存在,是體現國家教育權力,培養人才的主要渠道。那么“雙減”要強化的方向是什么呢?以往存在的問題其實在于學校教育把自己的任務轉嫁給了家庭和社會,這是偽裝的“家校社”協同育人,實際上模糊了不同教育活動形態的邊界,變成了校內減負而校外增負。要打破這種減負的困局,就應強化學校教育應發揮的作用力。
因此,“雙減”政策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是要學校教育回歸育人的本質,把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制定學校培養目標的基本依據,把培養目標落實到每門課程的教學中,提升教育教學質量,確保學生在校內學足學好。換言之,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的改革方向,是指向學校教育質量的提升,包括課堂教學的質量、作業設計的質量、課后服務的質量等。
“雙減”改革的方向中,還包括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方向引領作用,即強化學校教育在學生成長成才中的影響力,這應該成為人生命成長的一種主導力量。因為這種主導力量體現了國家的教育意志,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培養什么樣的人,和怎樣培養人的要求。因此,在三種教育活動形態、兩種社會教育力的發揮中,學校教育應起到方向引領的作用。
明確了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的方向,在落實“雙減”政策的過程中,就要避免出現以下認識或實踐的誤區。
誤區一: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就是要大包大攬,讓學校教育承擔學生的所有教育活動。這種認識是模糊了不同教育活動形態邊界的表現,不利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例如家校協同教育,不是要把家長訓練成教師,像教師一樣去教育孩子,而是發掘親子之間、家庭之中本身具有的教育資源,更好地去進行開發和運用。強化學校教育的主陣地作用,不是要回到“把教育等同于學校教育”的認識中去,更不是完全用學校教育取代其他的教育形態,這不可能實現,也不符合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人的全面發展是“人的對象性關系的全面生成和個人社會關系的高度豐富”(8)丁學良《馬克思的“人的全面發展觀”概覽》,《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第130頁。。人是對象性的存在強調人與世界的關系,人是社會性的存在強調人的聚群性和合作性,前者需要學生與這個世界建立更為廣泛的鏈接,后者則要求學生能在與其他社會成員的交往過程中,實現社會關系的高度豐富。兩者是人的多種潛能素質開發的外顯活動,其中一部分需要在學校教育中完成,另外還需要與社會建立更廣泛的關系,這也是強調學生開展社會實踐、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重要原因。要真正使人的各種全能素質得到充分的發展,僅僅依靠學校教育活動是難以完成的,需要以學校教育為主陣地,整合更多的教育活動形態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中來實現。
誤區二: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就是強化學校教育的時空占有,讓學校生活覆蓋學生的全部教育生活。在“雙減”落實的過程中,延長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是一種顯性的、立竿見影的改革行為。2017年以后,各地均開始以學校為主渠道進行課后服務。“雙減”政策出臺后,課后服務時間進一步延長,要求學校做好課后服務工作,其中“保證時間”就是重要一條。推行課后服務“5+2”(每周5天,每天2小時)模式,有的地區還構建了“5+2+N”的課后服務體系,N即滿足家長或學生多樣的需求,表現為“時段擴展+學段延伸+內容拓展”(9)李自強《疏堵結合 構建“5+2+N”課后服務體系——青羊區有效推動“雙減”和“五項管理”落實落地》,《成都日報》2021年9月25日,第2版。。部分區域還在試行周末為學生提供托管服務,開展形式多樣的興趣培養活動。上述舉措具有確保學校教育發揮主導力量的作用,解決了家長課后接送孩子的問題,也滿足了學生完成作業、發展興趣的需求,但是也需要警惕不能對學生生活世界的全時空占有,將學校提供的課后服務向周末、假期不斷延展就是一個需要考量的問題。
這種延展表面上看是學校主動承擔了更多的教育責任,但實際上可能面臨兩個方面的困境。一是延長了教師在校工作的時長,教師面臨更大的工作壓力,這種壓力可能帶來負面的情緒體驗和情緒表現,不利于教育活動的開展。二是學生的生活被學校生活占滿,這種學校生活的環境有其相對固定和封閉的特征,如果學生從早到晚、從周一到周末、再到寒暑假都需要待在這樣的環境中,這和原來出了學校就進入培訓班,周末假期進多個培訓班的境況是一樣的。菲利普·杰克遜(Philip W. Jackson)曾提出課堂生活是一種高度穩定和儀式化的環境,他用“擁擠的人群”、“評價性的環境”、“不平等的權力”來概括課堂生活特點,并把它們視為隱形課程(10)菲利普·W.杰克遜《課堂生活》,丁道勇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41頁。。學校的一日生活正是由一個個課堂生活單元所構成,它們具有相似的、高度穩定的環境,課堂生活的這些特點也彌散在學生的學校生活中。但是當這種特點繼續彌散到周末、假期,占據了學生的全部教育生活,那么學生的生命成長就會完全浸入到這種環境中。尤其是擁擠的人群及其所必然帶來的嚴格的秩序要求、高密度的評價等特點,容易讓學生忽視其他的學習方式和生活體驗,尤其是失去自由探索和自我探索的興趣和體驗。
誤區三: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表現為給學校施加壓力,采用更為嚴格的管理、監督方式督促政策的執行。“雙減”政策出臺以來,各地陸續出臺了具體的實施方案,區縣一級教育行政部門具體落實實施方案,將具體的改革任務布置給學校。這是由學校的外部管理體制所決定的,體現為自上而下的“執行”的特點,即學校如何去執行區縣教育局布置的改革措施。從內部管理體制來看,我國中小學實行校長負責制,并全面加強黨對教育事業的領導,在“雙減”政策的執行中,學校不應只是被動的執行者,去完成任務,而應成為改革的主體,創造性地去解決問題。
出現這種誤區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實施方案制定過于細致,缺乏管理的彈性空間,使得學校在落實“雙減”的過程中只能按部就班去操作。例如在“雙減”政策出臺之前教育部就發文加強對學生的“五項管理”(作業、睡眠、手機、讀物、體質),“雙減”政策出臺后,“五項管理”也成為落實雙減的重要切入點。這一類政策指向的事務非常地具體明確,各地細化實施時又進一步明確了落實的方式和要求,學校管理者容易將自己僅僅視為某個具體任務的執行者而不是某個項目的完成者,這不利于發揮學校在改革中的主體性。例如個別學校或教師在延時服務中只是完成守著孩子的托管任務,并沒有真正進行教育的課后服務,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校時間的延長并不必然帶來學校教育質量的提升。二是學校在強化主陣地作用中的自我意識還不夠強烈,這是政策執行初期的正常現象。“雙減”之下,學校壓力陡增,壓力既來自“上面”的壓力,也來自執行過程中“下面”的壓力,在政策剛剛開始實施的較長一段時間里,都可能出現“應付”式執行的情況。這種“應付”不完全是態度上的“不端正”,更多地還是在調整慣性的過程中,目前學校還處于只能關注完成“表面性”指標的階段。但需注意的是,“雙減”政策的治理是系統治理,除了“減輕作業負擔”、“提升課后服務水平”兩個方面的具體任務,還應該圍繞提升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這一目標來整體規劃學校落實“雙減”政策的具體方案,這就需要學校更具有改革的主體意識,并整合更多的教育力量。
三 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與社會教育力開發的張力:引領與融合
“張力”可引申為力與力之間的關系,他們有可能表現為互相排斥與矛盾,也有可能在排斥與矛盾中彼此牽引。如前所述,社會教育力由三種教育活動形態構成的兩種教育力量(教育作用力和教育影響力)構成。“雙減”政策直接調整的是教育作用力,而間接地會涉及教育影響力。學校教育發揮的作用力是社會教育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教育作用力的一種,另一種教育作用力則是非正規教育產生的力量。強化學校教育的主陣地作用,就是要重新調整學校教育與其他兩種形態教育活動之間的力量關系,并更好地融合社會的教育力量,促進每個個體的生命成長和全面發展。
從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的視角出發,“雙減”政策落實中,應避免用學校教育的作用力弱化或替代其他的教育力量。“強化”這種力量是要把學校教育的作用力視為構建社會教育力的核心,具體表現為“引領”和“融合”兩種力量。
(一)發揮學校教育主陣地的引領作用
“引領”體現為學校教育應在各種形態的教育活動中發揮引領價值方向的作用,把“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作為一個旗幟或標桿,引領非正規教育的作用力、人類其他活動的教育影響力都朝著這一方向努力。“雙減”政策要治理的校外培訓,就是因為其偏離了“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甚至“帶歪”了學校教育的價值方向。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的作用,并不是打壓校外培訓的教育力量,而是通過端正、強化學校教育的目標、根本任務來引導包括校外培訓在內的非正規教育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雙減”的后續政策舉措,如發布《義務教育階段校外培訓項目分類鑒別指南》等都是對校外培訓行為的進一步規范。習近平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的講話就強調了這一點(11)習近平指出:“要把立德樹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識教育、社會實踐教育各環節,貫穿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各領域,學科體系、教學體系、教材體系、管理體系要圍繞這個目標來設計,教師要圍繞這個目標來教,學生要圍繞這個目標來學。”參見:《習近平在全國教育大會強調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 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人民日報》2018年9月11日,第1版。,“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應貫穿于教育的各環節、各領域。
學校之所以能發揮“引領”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其社會分工帶來的專門性和專業性,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本身也賦予了學校更多的角色期待,包括把學校視為“‘象征’機構”(12)吳康寧《學校的社會角色:期待、現實及選擇——基于社會學的審視》,《教育研究與實驗》2005年第4期,第3頁。。這種象征性體現為“其在政治方向、道德取向、知識體系、話語方式及人際關系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主流意識形態之間具有較高的吻應度”(13)吳康寧《學校的社會角色:期待、現實及選擇——基于社會學的審視》,《教育研究與實驗》2005年第4期,第3頁。。這種“象征”的角色正是學校能發揮價值引領作用的重要基礎。而且這種象征性不僅直接影響非正規教育,還會廣泛地影響人類其他活動產生的教育力量。
“打鐵還需自身硬”。學校要發揮引領作用必須加強自身的建設,這也是“雙減”政策中“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的意蘊所在。學校的培養目標是否體現了國家的教育方針,學校的教育實踐是否落實了“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這是在強化學校主陣地作用時需要檢視的問題,也是提升學校教育教學質量指向的價值方向。只有當學校教育系統內部堅定了教育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價值,才有可能使偏離育人正道的校外培訓和不良的教育社會風氣回歸正途。
(二)發揮學校教育主陣地的融合作用
“融合”體現為以學校教育為核心,形成有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復合體,這種復合體就表現為學習型社會的形態。即以學校教育的作用力來融合非正規教育和人類其他活動中的教育資源,從而使三者的力量得以整合,且通過“引領”作用的發揮,使三者合力構建的社會教育力具有一致的方向性。
學校本身就是富集教育資源的一種載體,是專門從事教育的機構。“雙減”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是要進一步凸顯其專業性,但這種專業性不是學校教育的封閉式發展,不是進一步加劇“教育實踐與其他實踐的割裂”(14)李政濤《當代教育發展的“全社會教育”路向》,《教育研究》2020年第6期,第5頁。,而是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融合更多的教育力量。在學校教育系統內部表現為構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的教育體系,從整個社會來看則是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建成學習型社會。在實踐中,以行政力量或以其他組織機構來推動社會其他系統教育力量的整合,其問題就是缺乏專業性,沒有專業性就難以吸引其他的資源。例如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倡導建立的“社區教育委員會”作為連攜學校與社區教育的組織機構,在大多數地區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為學校在其中沒有發揮主導作用,只是作為“參與者”而不是“引領者”,而社區的行政力量不具有專業性,只能提供制度的支持,難以促成長久的、真實的合作。如果以學校教育為核心來吸引其他教育力量,就使得社會教育力有了“靈魂角色”,從而具有了更強的凝聚力,使“融合”成為可能。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融合”中可能出現的利益糾葛。在現代終身教育理念轉化為教育實踐的過程中,教育資源的整合或融合就一直被提及,但是制度的條塊割裂總是捆綁著不同的利益訴求,使得資源的整合面臨較大的困難。仍以學校與社區的合作為例,學校在行政管理上并不隸屬于街(鎮)這一層面的社區,而是隸屬于區(縣)一級的教育行政部門,雖然有社區教育委員會這樣的協調組織,但其具有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力量是很薄弱的,只能是“協調”。當大家沒有共同的利益訴求時,協調就變得很困難,或者變成了表面的形式。要克服這種困難,關鍵還是要明確“融合”的共同利益是什么,社會的其他各類組織參與教育活動首先是考慮自身的利益是否與共同利益具有一致性。學校教育是培養人的活動,學校存在的物理空間以及學生生活的空間載體就是社區,當我們以學校的育人工作為核心來融合社區的資源時,要通過學校教育工作者的專業身份來宣傳和引導社區其他成員、社會其他組織認識合作中所享有的顯性和隱性的教育利益。這種利益的根本就是人的生命成長,既包括青少年學生的生命成長,這是社區中的家長們關心的,還包括成人本身的生命發展。有了對共同利益的認識,“融合”就更容易協調各種力量。
當然,融合并不是模糊不同教育力量的邊界,而是要讓不同的教育力量基于其本身的特點和優勢來發揮教育的作用。比如校外培訓只要進行規范化的發展,就可以很好地服務于個性化的學習需求。非正規教育中的社區教育、博物館等文化設施的教育,都可以在學校的全面培養體系中發揮作用。因此,“雙減”政策的實施,還應關注如何激發學校的辦學活力,使學校具有對其主陣地作用、改革主體的充分認識,關鍵是圍繞學生的全面發展,拓展學校教育與其他類型教育活動的合作,而不是包攬學生的所有教育活動。例如學生的勞動教育、德育實踐、項目式學習等都可以依托社區或其他社會組織的活動來開展。
綜上所述,“雙減”政策中提出要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不是要讓學校教育“包打天下”,這既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也不符合學習型社會建設的目標。學校教育應成為社會教育力構建的核心力量,發揮“引領”與“融合”的作用,這也是構建社會教育力的現實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