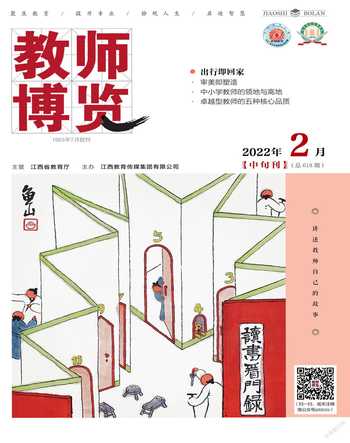回顧教育綠水間 瞻望杏子累累處
深秋時節,我倚著飄窗的靠枕,望著桂花飄香的院落,讀著:
南鄉子·綠水滿池塘
宋·李之儀
綠水滿池塘。點水蜻蜓避燕忙。杏子壓枝黃半熟,鄰墻。風送荷花幾陣香。
角簟襯牙床。汗透鮫綃晝影長。點滴芭蕉疏雨過,微涼。畫角悠悠送夕陽。
眼前忽而浮現夏天池塘綠水微漾、鄰墻黃杏壓枝的景象,聞得“荷花幾陣香”,思緒飛越,似“點滴芭蕉疏雨過”。回顧自己從教30年中最初10年的教育生活,瞻望學生的成長、成才,甚慰。
? 忽閃我的“閃電眼” ?
1991年8月,師范畢業后,我以“優分生”的成績被選入南昌市百花洲小學;9月,擔任四年級(2)班語文老師。當梳著長辮子的我出現在孩子們面前時,教室里好一陣騷動:“老師,你多大呀?”看著他們滿臉興奮的樣子,儼然班上來了個新同學,我暗想:上課時我得想辦法“震住”他們。
用什么辦法“震住”他們呢?我腦海中浮現我學生時代的兩位老師——教我一、二年級語文的潘維康老師和教我初中數學的陳望萍老師。兩位優秀的老師上課的情形像過電影一樣從我腦中掠過,我猛然間發現她們上課的共性——注重組織教學。
潘老師那雙銳利的“鷹眼”,能在我們讀書時搜索到小聲說話的同學,能邊上課邊發現混在我們當中“神游天外”的同學。陳老師講解難題解法思路時,那雙大眼睛便滿教室打量,尤其是在教室最后幾排“掃射”;只要一發現有動靜,她便停下不說話,眼睛射出去的“光束”能讓“搗蛋鬼”顯形。
想起兩位老師的“殺手锏”,我也有了主意。第二天,我走進教室,開始了教學生涯的第一課。我先對孩子們提出上課要求:“要認真聽講,老師在講課時,你們的眼睛要看著老師,手自然地放在桌上;同學發言時,你們的眼睛要看著他,對同學的發言有補充或不同意見的可以舉手說出來……”我說得很慢,但把要求說得很清楚:“我的眼睛很厲害,不管哪個同學開小差、講小話,我都能看見……”
我夸張地把頭擺了擺,眼睛快速轉了幾圈,問:“發現了嗎,老師的眼睛與你們的有什么不同?”
“徐老師的眼睛炯炯有神!”坐在第一排的女生第一個發言。
“徐老師的眼睛會說話。”坐在教室中間的女生接著說。
我都被夸得不好意思了,但“戲”還得演下去。“還有什么不同呢?”我走近孩子們。
“老師的眼睛轉得很快!”有的孩子直接湊近我的臉觀察著我的眼睛說。
“老師的眼珠是黃色的!”一個孩子好像發現了新大陸。
這句話一出,不少孩子已經顧不得在上課了,立刻圍住了我。
“真的,真的!”“老師的眼底還是藍色的!”孩子們已經興奮得不行。
差不多到火候了,我拍了拍手,說:“大家坐好。老師的眼睛與你們的不一樣,這叫‘閃電眼,天生的哦!你們以后上課要認真聽講,不然老師很快便會發現誰在走神,誰在開小差。”
自那天以后,我就一直靠“閃電眼”關注每一個孩子的學習狀態。我想,每一位好老師興許都有一雙有著“特異功能”的眼睛。因為眼睛是心靈的窗戶,眼與眼的交匯,必然能達到心與心的溝通。
? 用好“零布頭”時間 ?
我的媽媽是一名紡織廠女工。她特別能干,總能將一些看似無用的零布頭拼拼接接,做成圍裙、蘿被(現在的夏涼被)等有用的物件。伴隨著縫紉機“噠噠”的響聲,各種顏色的零布頭不一會兒就變廢為寶了。
當了5年小學語文教師后,我被任命為學校的教導處副主任,承擔一個班的語文教學,同時分管學校的教學工作。工作任務更重了,教學時間更緊張了,我便想辦法向課堂“40分鐘”要質量。
反思自己的課堂教學,我發現其中也有好些“零布頭”沒有利用好。課堂上的“零布頭”,指一些零零散散的課堂剩余時間,三分鐘、五分鐘或六分鐘、八分鐘,它們散落在課堂上,不受老師重視。這些時間就像媽媽的那些零布頭,如果能被我很好地利用起來,我就能提高課堂教學的效率。
培養興趣——學生對課外語文知識特別感興趣,我便準備了一些課外學習材料,如我小時候讀過的書籍、著名作家的趣聞軼事、自己的讀書心得等,利用課堂上“零布頭”時間講給學生聽。雖說是短短幾分鐘,卻充實了語文課堂,激發了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我發現,孩子們越來越喜歡語文課了!
分享作品——學生平日里寫的小練筆、周記,是他們自己的作品,之前總是我批改得多,點評、交流得少。有了利用課堂“零布頭”時間的意識后,我便決定花點時間來鼓勵學生交流、分享作品。我告訴孩子們:“對于自己的作品,你們享有著作權,包括傳播權、展覽權、修改權等。”課堂的“零布頭”時間,我常常鼓勵學生用各自的方式交流分享自己滿意的作品,如一篇感人的日記、一篇精彩的小作文、一個蘊含哲理的句子、一段續寫的小故事。我和孩子們在互相交流中享受分享作品的快樂。我發現,喜歡寫作的孩子越來越多了!
開展微活動——語文是培養學生語言文字實踐能力的學科,活動是學生喜歡參與并積極參與的學習生活的組成部分。課堂上的“零布頭”時間,組織大型活動不太現實,但微活動廣受歡迎,如詞語接龍、成語對對碰、我是小詩人、繞口令比賽等。活動的設計與學習內容相關,又有別于教科書上的練習,既拓展了學生的語文知識,又活躍了課堂氣氛,還培養了學生運用語文的技能。我發現,活動中的孩子們不只會鬧騰,還會凝神思考。
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用這樣的文字形容他的學生:“我凝視著那一雙雙烏黑、淡藍、墨綠、淺灰色的眼睛,覺得每個兒童此刻都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小窗口,入迷地觀看著藍天和大地、太陽和月亮、鮮花和飛鳥,而且每一個小窗口互不相同,各有特色。”我望著教室里幾十雙神采各異的眼睛,懷有與大師同樣的感受。我真切地感受到,課堂上“零布頭”時間的有效利用,培養了孩子們對語文學科的情感。
? “你們都能成作家!” ?
記得我讀小學三年級的一天,教我語文的魯宏老師在課堂上非常正式地宣布:“我們班以后會出一個作家,那便是徐承蕓!”在同學們的掌聲中,我萬分緊張地走上講臺,從老師的手中領到一支鋼筆,黑色的,英雄牌,卻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隨后,魯老師拿出一張報紙,上面竟然刊登了我前些天“三八”婦女節時寫的一篇短文《媽媽的節日》,原來魯老師幫我向報紙投稿,并且真的發表了。那是我讀書以來最高興的時候,比獲得“三好學生”獎狀、“免學費”獎狀、作業本獎品還要高興,因為美麗、優秀的魯老師竟然說我長大后能當作家。如今回想當年,這也許是老師對我的一份鼓勵與祝福,或是對其他同學的一種激勵吧。從那以后,依然有不少語文老師表揚過我的作文,甚至有老師將我的作文傳到其他班、其他年級去展示,但再也沒有老師幫我投過稿,還這么慎重地宣布我能當作家。可是,有這一次已經足夠了,后來我開始自己投稿,甚至曾在短短5年內發表了十余篇作品,其中包括散文、詩歌、故事、小小說。魯老師的話像一把利斧,把我蒙昧的心智劈開,一束耀眼的光帶著太陽的味道把我暖暖地包裹起來,直到今天。
因為感恩老師對我的培養,所以我在當老師的時候,注重對學生的培養。
我不贊同老師早早地將“作文很難”的觀點傳遞給學生及學生家長,因為對作文有畏懼心理于孩子們學習寫作而言,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初教一個班,第一次讓孩子們寫作文前,我常常會把自己從小到大寫的文字用個布口袋背到班上,然后嘩地倒在講桌上,其中有我的作文本、摘抄本、周記本,還有刊登了我的作品的報紙、雜志,以及爸爸給我做的第一本書。然后我會用一節課與孩子們分享我求學十余年間寫過的文字、發生過的故事,他們聽得饒有興趣。我告訴他們:寫作就像吃飯、玩耍那么簡單,只要如老師這般一直堅持寫下來,你們人人都可以像老師這樣,記下童年、少年時代的趣事、丑事、囧事……你們人人都可以當作家!
我還清楚地記得,每當這個時候,孩子們的眼睛都會冒出奇異的光,這光像夜空中的啟明星一樣奪目,像春天草葉上流淌的露珠一般晶亮,像長夜里的火把一樣有著倔強、活潑的力量。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難以想象會有如此震撼人心的目光,那是他們對自己的憧憬之光、期待之光、瞻望之光。
光,雖亮,但僅僅是萌芽,他們后面要走的路還很長。著名教育家葉圣陶先生說:“教育是農業,不是工業。”農業講究天時地利人和,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教師在教育的田地里精耕細作;而工業講究的是整齊劃一的流水線作業,任務沒完成,加個班就好了。我對學生習作教學的“精耕細作”便從“重講評,輕批改”開始。
講評課內容豐富,我會讓作文在學生那兒走幾個來回。第一天,我請20多個學生分別朗讀自己作文中被我畫上紅記號的好詞、好句、好段落,并組織其他同學賞析;再請整篇作文寫得好的同學朗讀,師生共賞;最后提出學生共有的幾個寫作問題,例文呈現,現場評改。第二天,學生將上次講評課上學到的本領運用到自我修改中,改后謄抄,然后與同桌互相評改,“后進生”的作文由我來面批。第三天,學生再次修改后,謄抄,我再對他們的作文及同桌的評語進行等級評定。所有評定盡可能以鼓勵為主。
時光流轉30年,我從一名青澀的教師成長為一名資深教研員。關于如何為學、如何為師,我不斷在思考、實踐、否定、肯定、再實踐的進程中彳亍前行。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我一讀再讀,手不釋卷。以下一段話,看似在分析詞的寫法,也可借鑒來用以理解語文教育: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系,互相限制。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系、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他說,自然里的東西,都是互相有關系的,都是互相限制的,可是當被寫到文學中和表現在美術中的時候,你要把它獨立出來,把它原來與現實的關系擺脫掉。那時,你雖然是寫實家,但同時也是理想家了。所以寫實都是會接近理想的。
語文教育與王國維先生寫的文字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語文系母語的獨特地位,決定了它的工具性特點,但語文教育不能僅僅圍繞字詞句段篇的訓練,語文教育者心中應有大義、大局、大境界,人文性與工具性相融合的語文教育才是理想的狀態。“發展思維能力,提升思維品質,形成自覺的審美意識,培養高雅的審美情趣,積累豐厚的文化底蘊,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提升語文課程核心素養”可謂是在語文教學中有效落實工具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教育目標。工具性與人文性,二者相輔相成,互相觀照。王國維先生在書里說,寫實與理想在作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語文教育中的工具性與人文性亦應如此。
王國維先生說:“詞以境界為最上。”我說:“教育以境界為最上。”教學有法,教無定法,好老師的教學方法都是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實學識、仁愛之心的基礎上領悟出來的,別無二法,別無他徑。
(作者單位:江西省教育廳教學教材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