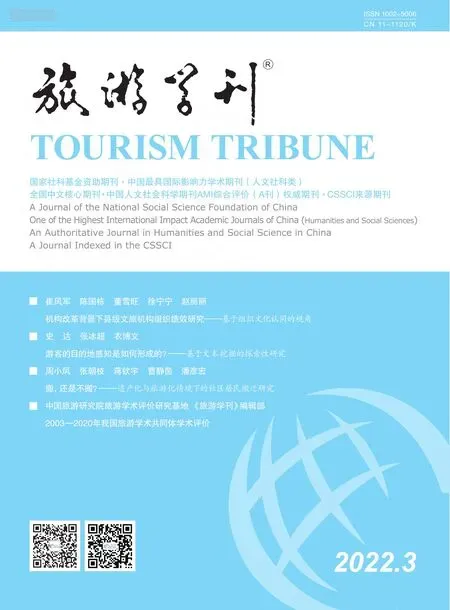創(chuàng)意、跟進(jìn)與范式化:旅游理論建設(shè)的時代使命
謝彥君
《旅游學(xué)刊》作為旅游領(lǐng)域傳播新知識的最重要學(xué)術(shù)平臺,再過三五年,就要走過它半個世紀(jì)的歷程了。在這樣一個時間節(jié)點要發(fā)表關(guān)于《旅游學(xué)刊》甚至旅游學(xué)術(shù)研究的一點感言,思來想去,還是想談一下旅游理論建設(shè)的范式化問題。
這個話題,在最近幾年,我大概以呼吁的方式談過三五次,其中最集中的一次是2019年第9期在《旅游學(xué)刊》主持過題為“旅游體驗研究的范式創(chuàng)新”的筆談,邀請張凌云、王寧、馬波、吳必虎諸君就相關(guān)話題各抒己見。我的這個倡議,可能引起了一些異議,也遭致某種誤解。今天依然要老調(diào)重彈,我個人以為,還是因為這個問題是旅游知識界中的一個大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還越來越顯現(xiàn)出是個大問題。
毫無疑問,今天的旅游界,絕非一個處于初級階段的小規(guī)模實踐領(lǐng)域,它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復(fù)雜新經(jīng)濟(jì)時代的重要實踐領(lǐng)域,迫切呼喚知識尤其是系統(tǒng)的理論知識以作為其實踐之指導(dǎo)。然而,這種“系統(tǒng)的理論知識”在哪里呢?我們到底要不要致力于系統(tǒng)的理論知識的生產(chǎn)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從科學(xué)哲學(xué)的意義上來看,必然會走向“理論的范式化”這一命題上。
在當(dāng)今的知識界,不惟旅游學(xué)術(shù)界,也包括中國的大多數(shù)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在知識生產(chǎn)過程中對“創(chuàng)意”“創(chuàng)新”的主張,從未受到任何質(zhì)疑,反而構(gòu)成社會公眾對知識生產(chǎn)原則的普遍認(rèn)知。但是,接下來,對相應(yīng)的學(xué)術(shù)“跟進(jìn)”的強調(diào),便缺乏集體自覺了,以至于在某些相當(dāng)重要的知識領(lǐng)域,比如作為社會科學(xué)皇冠上的明珠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自改革開放以來半個世紀(jì)的知識生產(chǎn),其可見的成果,也不過是一地散金碎銀而已。至于構(gòu)建足以稱為“范式”的理論,似乎在很多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都還遠(yuǎn)不見蹤跡。
達(dá)不到目標(biāo),如果是由于各種外在條件的限制使然,則尚不足論;但若是由于主觀的自覺性不夠,那便是知識界自己的問題了。旅游知識界也同樣是這個道理。
于是,這就涉及對“范式”的意涵理解和價值判斷了。
范式(Paradigm)是科學(xué)哲學(xué)家?guī)於魉褂玫淖钪匾目茖W(xué)哲學(xué)概念之一。按照庫恩本人的解釋,“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認(rèn)的科學(xué)成就,它們在一段時間里為科學(xué)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庫恩對范式一詞的界定和使用,曾引起科學(xué)哲學(xué)界的巨大轟動,也產(chǎn)生了持續(xù)的影響。然而,庫恩晚年“自暴自棄”地幾乎不提“范式”一詞,個中根由,很可能是因為這個概念被大肆地濫用了。但是,根據(jù)庫恩最初為“范式”所下的這個定義(庫恩對范式也有很多種闡釋或運用)和所給出的一些命題,我們知道,范式本質(zhì)上是“世界觀和方法論”;范式的載體是“科學(xué)共同體”(毋寧說是“理論共同體”,庫恩將“范式”和“科學(xué)革命”等概念僅僅貢獻(xiàn)給“科學(xué)”而非整個知識領(lǐng)域,這可能是他的一個局限,畢竟“科學(xué)”也僅僅是知識論中的一個范式而已);范式之間具有“不可通約性”,這意味著,范式革命或范式轉(zhuǎn)換之后,“新舊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它們之間沒有公約數(shù)。新舊范式的差別是本質(zhì)性的。”根據(jù)這些界定,再結(jié)合歷史上各種理論(不惟庫恩所局限的科學(xué)理論)所經(jīng)歷的成長過程,都可以看出,人類關(guān)于世界的認(rèn)識或知識的系統(tǒng)積累,總是經(jīng)歷著創(chuàng)意、跟進(jìn)、系統(tǒng)化或范式化及至衰亡(被革命或被替代)的過程。所有重要的理論發(fā)育過程幾乎沒有例外(包括重要的科學(xué)理論)。這也就意味著,范式化也將是旅游知識生產(chǎn)的宿命,除非旅游現(xiàn)象在未來變得不重要甚至消失。從這個角度說,旅游知識界致力于構(gòu)建不同的但為某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理論體系和規(guī)范程式,這種努力體現(xiàn)的是知識群體在旅游本體論上的志同道合,它與基于學(xué)緣、地緣、業(yè)緣、勢緣、利緣而建立的學(xué)術(shù)裙帶關(guān)系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一言以蔽之,知識界的范式化與學(xué)術(shù)上的“拉山頭”,在本質(zhì)上是不同甚至對立的兩件事。
對于旅游知識共同體(即“旅游學(xué)科”)的理論建設(shè)而言,范式化的價值究竟何在?這個問題恐怕要回到旅游學(xué)科建設(shè)的現(xiàn)實中來討論。
縱觀當(dāng)今中國旅游現(xiàn)象界,大體可以看到三重表現(xiàn):一重是如火如荼的產(chǎn)業(yè)實踐——新冠肺炎疫情只能在短期內(nèi)壓制其發(fā)展勢頭;一重是臃腫龐大的高等教育規(guī)模——全國600多所本科院校開設(shè)了旅游管理大類各專業(yè);再一重是汗牛充棟的文獻(xiàn)數(shù)量——僅在中國知網(wǎng),便可檢索到73.19萬份相關(guān)文獻(xiàn)。這三重現(xiàn)象代表著旅游相關(guān)的三個界域:產(chǎn)業(yè)界、教育界和科學(xué)界(或應(yīng)更準(zhǔn)確地稱為知識界),而它們又都與“知識”存在著休戚與共的天然聯(lián)系。產(chǎn)業(yè)界應(yīng)用知識,教育界傳播知識,科學(xué)界生產(chǎn)知識。一旦在這三重界域中出現(xiàn)“范式缺席”的情況,那么,作為一種必然的因果關(guān)系,就很可能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實:在產(chǎn)業(yè)界,可能會出現(xiàn)個人經(jīng)驗性意見盛行、不按規(guī)律辦事從而導(dǎo)致產(chǎn)業(yè)發(fā)展效率低下、效果不佳的局面;在教育界,可能出現(xiàn)教育的知識內(nèi)涵匱乏、教科書隨意編撰、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偏低、行業(yè)內(nèi)就業(yè)局面尷尬、外侵與內(nèi)卷并存、專業(yè)認(rèn)可度低的局面;在科學(xué)界,可能出現(xiàn)文獻(xiàn)數(shù)量可觀而可用知識乏善可陳、學(xué)術(shù)研究缺乏實踐相關(guān)性的局面。盡管上述3種局面未必都是現(xiàn)實(誰知道呢),但其潛在挑戰(zhàn)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在旅游學(xué)術(shù)界,我們曾提到過“旅游共同體”,主張過“學(xué)術(shù)共同體”,也曾提出“知識共同體”(學(xué)科)的概念,但還缺乏對“理論共同體”的認(rèn)可和自覺。在我看來,只有當(dāng)旅游知識界承認(rèn)并積極推進(jìn)旅游的“理論共同體”(每一個“理論共同體”以相同的理論范式為綱領(lǐng))的發(fā)展,才能夠指望作為旅游學(xué)科的“旅游知識共同體”(一個“旅游知識共同體”擁有若干不同甚至對立的“理論共同體”)的成立。當(dāng)下基于業(yè)緣(如酒店、會展、旅游)而組合的“旅游專業(yè)大類”,其與“旅游學(xué)科”或“旅游知識共同體”并非同樣的東西。依照復(fù)合性極強、現(xiàn)象屬性不具有同一性的業(yè)緣去構(gòu)建旅游學(xué)科,難免會緣木求魚,得不到預(yù)期的結(jié)果。
我期望,在《旅游學(xué)刊》這個知識傳播平臺上,能夠見到更多富有創(chuàng)意的新的研究成果;更愿意看到,這種創(chuàng)意能夠喚起更多的后進(jìn)為之做更加深入的工作;尤其盼望,有一些帶有范式化努力的學(xué)術(shù)研究,能夠借助《旅游學(xué)刊》走向旅游的“三重界域”,甚至走向世界的旅游學(xué)術(shù)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