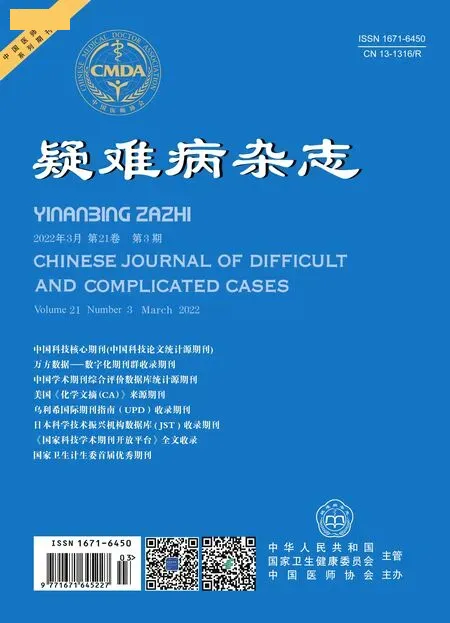具有自身免疫特征的高齡間質性肺炎2例并文獻復習
李鳳芝,郭靖,張倩,王東
例1.男,87歲,因“間斷發熱、咳嗽、咯痰1個月余”入院。既往無關節疼痛病史,曾有全身皮疹,未在意,后自行消褪。查體:雙下肺可聞及Velcro音。實驗室檢查示抗核抗體ANA陽性,著絲點型1∶1 000、核膜型1∶320、胞漿顆粒型1∶100,抗Scl-70弱陽性(+),抗CENP-B陽性(+++),抗AMA-M2陽性(+++);抗鏈球菌溶血素O(ASO)、類風濕因子(RF)無異常。血κ輕鏈12 g/L,λ輕鏈7.47 g/L。胸部CT提示雙肺下葉間質性肺炎,右肺上葉、左肺下葉背段多發鈣化灶,冠狀動脈及主動脈粥樣硬化、雙側胸膜增厚,見圖1。給予抗炎治療,仍有低熱,院內外多學科會診討論后,診斷為具有自身免疫特征的間質性肺炎(IPAF),給予羥氯喹片200 mg、每天2次,甲潑尼龍片24 mg、每天1次,每周減4 mg,減至12 mg后每2周減4 mg,直至8 mg維持,期間患者發生肺部感染,給予抗炎治療。隨訪8個月余,未出現發熱,病情穩定,復查肺部CT提示雙下肺間質性肺炎減輕,雙側胸膜增厚減輕,見圖2。

圖1 例1入院時胸部CT表現

圖2 例1隨訪8個月后胸部CT表現
例2.男,92歲,因“間斷咳嗽、咯痰伴發熱2個月”入院。查體:雙肺呼吸音粗,雙下肺可聞及Velcro音。實驗室檢查示抗核抗體ANA陽性,核顆粒型1∶100,抗dsDNA抗體(++)、抗組蛋白(++);抗髓過氧化物酶(++)、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pANCA)陽性1∶10;C-反應蛋白54.3 mg/L;紅細胞沉降率57 mm/h。胸部CT示:雙肺間質纖維化伴感染,以左肺下葉為重,雙側胸腔積液,雙側胸膜增厚,見圖3。行骨髓穿刺提示為感染骨髓象。經多學科會診,診斷為肺部感染伴IPAF,除抗感染治療外,給予甲潑尼龍琥珀酸鈉20 mg/d,后逐漸減量,1個月余后給予口服甲潑尼龍片6 mg、每天1次,維持。抗感染3周后停用抗生素,患者病情穩定,未再出現咳嗽、發熱癥狀。隨訪1年,復查胸部CT提示雙肺間質纖維化及胸膜增厚較前明顯減輕,見圖4。

圖3 例2入院時胸部CT表現

圖4 例2隨訪1年后胸部CT表現
討 論間質性肺炎(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是以彌漫性肺實質、肺泡炎和間質纖維化為基本病理改變的不同類疾病群構成臨床病理實體的總稱[1-2]。引起間質性肺炎的常見原因主要為環境因素、藥物因素、免疫因素。特發性間質性肺炎(idiopath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s,IIP)是指不明原因的間質性肺炎,而其中一類與IIP不同,除間質性肺炎的表現外,還具備一些臨床、血清學或影像學特征提示其存在潛在的自身免疫反應,但這些特征又達不到結締組織病(CTD)的診斷標準。針對這一類患者,2015年歐洲呼吸學會(ERS) 和美國胸科學會(ATS)將其命名為具有自身免疫特征的間質性肺炎(interstitial pneumonia with autoimmune features,IPAF)[3]。
IPAF的診斷要點:(1)經高分辨率CT(HRCT)或肺活檢確診有間質性肺炎;(2)排除其他已知的病因;(3)未達到現有的CTD診斷標準;(4)至少滿足臨床、血清學、形態學三方面中的任意兩方面,每方面中至少一項特征。IPAF臨床方面的診斷標準主要由肺外癥狀和體征組成,包括遠端手指皮膚裂紋(技工手)、雷諾現象、手掌或指腹毛細血管擴張、遠端指尖皮膚潰瘍、炎性關節炎或多關節晨僵≥60 min、手指背側固定性皮疹(Gottrons征)等。血清學方面,主要是指對CTD特異性較強的外周抗體,如抗核抗體(ANA)、RF、抗CCP、抗dsDNA、抗SSA、抗SSB、抗Scl-70等。IPAF的形態學包括影像學和肺組織病理學,以及其他診斷方法證實除間質性肺炎外的氣管、肺血管、胸膜等多部位受累。HRCT提示影像學類型有:非特異性間質性肺炎(NSIP)、機化性肺炎(OP)、NSIP重疊OP、淋巴細胞性間質性肺炎(LIP)。肺活檢組織病理學類型有:NSIP、OP、NSIP重疊OP、LIP,間質的淋巴細胞浸潤伴有生發中心形成,彌漫性淋巴漿細胞浸潤(伴或不伴淋巴濾泡增生)。
本組2病例的診斷均符合血清學及形態學,研究發現,臨床、血清學及形態學三方面符合的占26.4%,臨床和形態學符合的占8.3%,血清學和形態學符合者占50.7%[4]。本組2病例均無明顯的臨床特征,國外多數學者報道IPAF臨床特征最常見的為雷諾現象,而國內報道則以關節炎或多關節晨僵為主[5-6]。形態學方面,Chartrand等[7]觀察到HRCT主要表現為NSIP和OP,本組2例均符合NSIP特點。血清學方面,以抗核抗體ANA陽性所占比例最高[6,8]。本組中例1抗核抗體ANA為著絲點型,滴度明顯升高,且抗Scl-70弱陽性、抗CENP-B陽性、抗AMA-M2陽性,ANA及抗Scl-70在IPAF的血清學中屬于常見指標,抗CENP-B、抗AMA-M2在IPAF中的診斷價值,鮮有報道。例2中抗核抗體ANA陽性,核顆粒型,且抗dsDNA抗體陽性,但目前對于ANCA的排除和抗tRNA合成酶的納入存在爭議[9]。對于高齡老年人(年齡>80歲),臨床常見低滴度的風濕免疫指標升高,如此時HRCT存在間質性病變,還要注意排除是否為誤吸因素引起肺部病變,而不能過度診斷為IPAF。有研究顯示[10],大部分IPAF患者在初診時存在炎性指標升高,當伴有發熱、咳嗽、CRP升高時,尤其當HRCT表現為OP時,極易誤診為肺炎,也要注意鑒別IPAF患者是否合并感染,合理應用抗生素,把握好激素應用時機。而對于老年長期發熱患者,要注意鑒別腫瘤性疾病,以免延誤病情。
IPAF的治療尚無指南和專家共識意見,一般參考CTD的治療方法,單獨使用糖皮質激素或聯合硫唑嘌呤、環磷酰胺、羥氯喹等。本組中例1給予激素加免疫抑制劑治療,例2給予單激素治療,激素的起始用量因考慮到高齡老年人的生理特點,肝腎功能減退,以及藥物的不良反應,未使用大劑量的糖皮質激素,起始劑量偏低,療效尚可,但由于經驗不足,療程該如何掌握,是否存在未觀察到的不良反應,還需進一步研究。相關研究已發現,年齡>65歲、影像學表現為UIP、多系統受累為IPAF預后的危險因素。
總之,IPAF可能只是ILD-CTD的一個發展階段,臨床表現無特異性,需要在多學科結合肺外表現、血清學特點及影像學表現作出正確診斷,目前的研究多為回顧性研究和病例報道,無大規模的前瞻性研究,其治療無相關指南,臨床工作者應提高對本病的認識,今后尚需加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