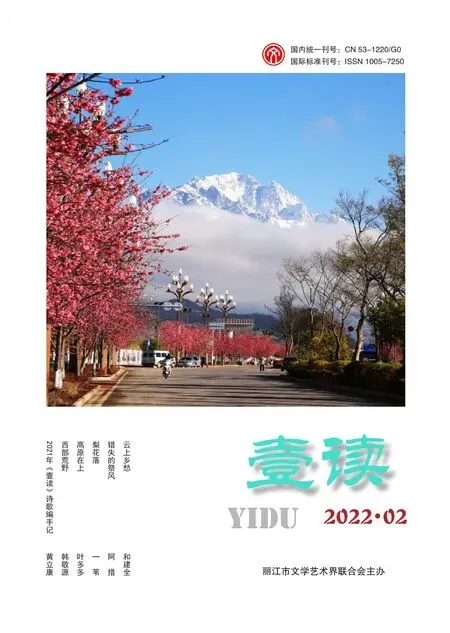高原在上
◆葉多多
眼前至今依然晃動(dòng)著他那對(duì)碩大的象牙耳環(huán)。
在墨西哥城國(guó)家宮著名畫(huà)家里維拉的壁畫(huà)前,我驚訝地看見(jiàn)了這位戴著美麗松石和珊瑚的土著墨西哥人,儼然就是一位正行走在香格里拉山道上的藏族人。
從早到晚,整整一天,在遠(yuǎn)離香格里拉的墨西哥高原,我一幅接一幅地讀著里維拉的壁畫(huà),從墨西哥的古代讀到墨西哥的現(xiàn)代。在這些彌漫著異族氣息的壁畫(huà)里,我忽然看見(jiàn)了熟悉的拉姆央措湖,看見(jiàn)了泉眼,看見(jiàn)了水波蕩漾之處的史前秘密。同時(shí),我也看見(jiàn)了屬于香格里拉的密林,看見(jiàn)了飄飛的樹(shù)胡須,看見(jiàn)了青稞,看見(jiàn)了杜鵑林根莖在泥土深處的觸須,看見(jiàn)了時(shí)間的短暫和遼遠(yuǎn),看見(jiàn)了高原盤(pán)旋起舞的靈息。斑斕的文化,冥絕的空靈,既被火接納,又為水相融。
我驚詫于世界文明如此的相通和相近,忽然間就有了一種久違的親和近。于是,我把隨身攜帶的一只純銀酥油碗,送給了當(dāng)?shù)刂挠〉诎苍?shī)人馬努埃爾,他能明白并收下我的心意。
此刻,忽然說(shuō)起這些,我想表達(dá),無(wú)論走到世界的哪一個(gè)角落,迪慶高原都能以它獨(dú)有的方式深刻地影響著我,它的質(zhì)地和重量一直在我心里。
或許,壁畫(huà)上的那個(gè)古代墨西哥人,原本就是從中國(guó)的香格里拉高原上萬(wàn)里跋涉而去的,誰(shuí)說(shuō)不可能呢。
在世界的盡頭,距離給予人足夠的清醒,我想起無(wú)數(shù)個(gè)澄明的早晨,靜靜地站在窗前,目睹著初升的太陽(yáng)飛快地染紅了松贊林寺眾生凝目的金頂。
多少年來(lái),我一次次地遠(yuǎn)行,一次次地抵達(dá),無(wú)論走得多遠(yuǎn),都會(huì)本能地回過(guò)頭來(lái),從遙遠(yuǎn)的地方,仔細(xì)地端詳著自己生活的土地。
在松贊林寺,在獨(dú)克宗古城,在大寶寺,在梅里雪山轉(zhuǎn)經(jīng)的路上,我曾默默地注視著一個(gè)個(gè)從我眼前走過(guò)的旅人,孤獨(dú)、脆弱、焦慮、無(wú)助,安詳、快樂(lè)、執(zhí)拗、渴望,透過(guò)一張張寫(xiě)滿(mǎn)各種表情的臉,我看到了人們行走在香格里拉大地上的真心誠(chéng)意。更多的眼睛,被滿(mǎn)眼的風(fēng)光和粗獷的康巴人所征服,被義無(wú)反顧的信徒和浩蕩的經(jīng)幡所征服,被無(wú)法用直覺(jué)表達(dá)的簡(jiǎn)潔、敦厚、容納所征服。
在從古龍村,我有著屬于自己的家。這是一座龐大的藏式房子,我在里面經(jīng)歷了兒子的出生和阿媽的離去。
更多的時(shí)間,我會(huì)陪著阿爸沿拉姆央措湖轉(zhuǎn)一圈,然后又沿松贊林寺轉(zhuǎn)一圈,我們無(wú)聲的腳步很容易就匯入了巨大的旋轉(zhuǎn)著的人流。修行,我還沒(méi)有達(dá)到那么高的境界,我不過(guò)是奢侈地享受著高原無(wú)處不在的緩慢和寧?kù)o。我會(huì)長(zhǎng)時(shí)間地坐在家旁邊的岡上,吹著風(fēng),看著太多的白云從頭頂飄過(guò),什么也用不去想。時(shí)間長(zhǎng)了,我發(fā)現(xiàn)歌舞和傳統(tǒng)的耕作是村莊里每個(gè)人都擅長(zhǎng)的技藝,也是旅人們頻繁造訪的動(dòng)力。其實(shí),村人們所葆有的,無(wú)非是每個(gè)普通人所應(yīng)有的快樂(lè)與滿(mǎn)足。
家里常住著一位六十多歲的韓國(guó)人,缺氧使他的嘴唇經(jīng)常呈現(xiàn)著一種疲憊的紫色,為他擔(dān)心,也許,過(guò)高的海拔并不適合他,面對(duì)勸說(shuō),他總是淡淡一笑:“不用擔(dān)心的,能夠死在這么純凈的地方,何嘗不是一種福分和造化。”
拉姆央措湖,我不由自主地再次說(shuō)起了它。遼闊的美麗蕩出湖面,搖曳出異質(zhì)的光芒。湖里,野鴨、鴛鴦、放生的鵝,各種高原水族相安無(wú)事地生活著,與炊煙,與人的溫度相伴,我想,這是人類(lèi)應(yīng)該學(xué)習(xí)的。
我從不輕易說(shuō)出神圣、圣潔、救贖這樣的詞,在我看來(lái),香格里拉對(duì)于每一個(gè)投入它懷抱里的人來(lái)說(shuō),不過(guò)是一種日常的生活方式,它的樸素和厚道,猶如那些從遠(yuǎn)古奔騰而來(lái)的偉大河流,已經(jīng)流淌了千年又千年,現(xiàn)在,以及今后也必然會(huì)川流不息地流淌下去。
有時(shí)候,距離產(chǎn)生的神奇感覺(jué)也會(huì)把人引向意料之外的地方。一天,幾個(gè)詩(shī)人朋友來(lái)到我家,晚餐后,我們一起坐在院子里靜靜地仰望著星空,女詩(shī)人木子忽然捂著臉哭了起來(lái)。半晌,她才抹抹眼睛說(shuō),這里的天空怎么可以這樣透明?
大家一時(shí)很感慨,說(shuō)起了霧霾,說(shuō)起了久被圍困的心靈。如果說(shuō)香格里拉是神投影在滾滾塵世中的一座神秘殿堂,是一顆被工業(yè)化徹底遺忘的頑強(qiáng)種子,是一抹引領(lǐng)人們奔向澄明的清晨陽(yáng)光,那么,它的力量與質(zhì)地,誘惑與激勵(lì),在不經(jīng)意的時(shí)候便顯現(xiàn)出來(lái)。
與木子一樣,很長(zhǎng)時(shí)間里,我一直嘗試著努力蛻去形形色色的“物”,尋找著重新生長(zhǎng)的種種可能。慶幸自己能夠長(zhǎng)久地?fù)碛屑儍舻目諝猓蝗缡朗来钤谶@里的人們,與繽紛,與荒蕪,與神話(huà),與冥想,與大悲為伴,任自由的靈魂在泛濫的藍(lán)天白云里飛翔,哪怕是享受片刻的虛無(wú),也已足矣。
然而我依然不可避免地會(huì)想起高原生活中的種種不容易。由于在外面工作,家里的耕地幾乎全部由妹妹一個(gè)人打理,妹夫出外打工掙錢(qián)。同事在一次喝飽了酥油茶后提出,要以妹妹為原型,拍攝藏族婦女日常生活中的一天。
第二天的晨曦中,我們扛著攝像機(jī)隨妹妹來(lái)到位于松贊林寺后面的地里,很快就擺好了機(jī)位。
我在鏡頭前靜靜地看著妹妹極為熟練地翻著地,清晨的空氣里很快就泛起了淡淡的泥土味,妹妹的身影由于與大地、灰塵、薄霧融為了一體而模糊不清,只有鮮艷美麗的紅色頭飾在迷離的陽(yáng)光中格外醒目。
不一會(huì),妹妹的額上便冒出了一層細(xì)密的汗珠,它們有著鹽的質(zhì)地和鉆石般的光澤,自然被細(xì)心的同事以特寫(xiě)的方式悉數(shù)收入鏡頭中。勞作中滿(mǎn)頭大汗的妹妹不時(shí)抬起頭來(lái)朝我們憨厚地笑一下,一會(huì)兒?jiǎn)栁覀兛什豢剩粫?huì)兒?jiǎn)栁覀凁I不餓,邊說(shuō)邊加快了勞作的動(dòng)作。她擔(dān)心習(xí)慣一日三餐的同事餓著,急著干完活回家給我們做飯。
誠(chéng)實(shí)地說(shuō),多年來(lái),我從沒(méi)留意過(guò)妹妹勞作的姿態(tài)。
眼前忽然涌起一陣濕的東西,我?guī)撞阶叩矫妹酶埃瑤缀跏怯行┛鋸埖亟舆^(guò)了她手中的工具,狠狠地砸向了堅(jiān)硬的土地。盡管握著鋤具的虎口撕裂般疼痛,但心底塵封的記憶和感官由此喚起,我相信,只有真正從事過(guò)作物播種和收獲的人,內(nèi)心才會(huì)始終充盈著對(duì)高原的感恩和信奉。
“你干什么?”同事和妹妹同時(shí)叫了起來(lái)。在家里回放鏡頭,同事對(duì)著我有些僵硬的勞作姿態(tài)指指點(diǎn)點(diǎn),埋怨我突兀地破壞了畫(huà)面的和諧。從技術(shù)的角度講,確實(shí)是不合時(shí)宜。一向好脾氣的妹妹忽然很不高興,在她看來(lái),自己承攬了家中的所有活計(jì),為的就是讓我在城里安心工作,活出個(gè)人樣來(lái)。
其實(shí),妹妹對(duì)我的好何止于此。有一年的夏天和冬天,我一直在西藏和玉樹(shù)拍攝紀(jì)錄片,回到家里的時(shí)候,疲憊和傷痛使我虛弱不堪,阿爸和妹妹一致認(rèn)定我撞上了邪惡的東西,當(dāng)天晚上,妹妹便用干凈紙包了幾元紙幣,沿著額頭一邊念誦著一邊給我全身擦拭著,第二天一早便直奔寺里去給我祈愿,這樣的習(xí)俗在我們這里叫“替身”。
妹妹相信,我從此便獲得了新生。
前不久,妹妹托人給我捎來(lái)了一幅大尺寸的綠度母十字繡,盡管我一再跟妹妹說(shuō)不用寄,我下個(gè)月就要回家了,可妹妹等不及了,電話(huà)里她反復(fù)交代,姐,你盡快掛上,度母會(huì)保佑你的。
想想妹妹四百多個(gè)夜晚穿針引線(xiàn)的不易,一陣傷感抵達(dá)心底。
兒子五歲的時(shí)候,我把他從香格里拉接到了昆明。第一次去農(nóng)貿(mào)市場(chǎng),在賣(mài)牛肉的攤子前,我買(mǎi)了一根牛尾,沒(méi)想一旁的兒子忽然冒出一句:媽媽?zhuān)蹅冑I(mǎi)這干嘛?燉湯呀。我隨口回答。兒子又豪邁地冒出一句:在我們香格里拉,這是喂狗的。在周?chē)黄等恢校野褍鹤永蛄肆硪粋€(gè)攤子。這回,買(mǎi)的是五個(gè)洋芋,一公斤,五元錢(qián)。兒子又一聲驚呼:這么貴呀,早曉得咱們從家里扛一袋來(lái)。
我家住樓上,每當(dāng)兒子動(dòng)作大弄出聲響,我總是驚得不住地讓他輕點(diǎn),再輕點(diǎn)。每每,被我厲聲喝住的兒子總是委屈地說(shuō),在香格里拉家里,幾十個(gè)人在樓上跳舞都沒(méi)事的,你怕什么呀?
我怕什么?面對(duì)兒子干凈的眼神,我竟一時(shí)無(wú)法回答。怕打擾鄰居只是原因之一,我悲哀地發(fā)現(xiàn),多年的城市生活不但束縛了我的身心,更決定了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猶如我身體里的沉重和塵埃,一有機(jī)會(huì)就冒出來(lái)。不知從什么時(shí)候起,我開(kāi)始謹(jǐn)慎了,活得小心翼翼了。
近幾年,家里條件好了許多,每年冬天我們都把阿爸送到洱源牛街的溫泉休息養(yǎng)生。酷烈的高原對(duì)于靈魂而言,說(shuō)是境界、救贖、精神的高地一點(diǎn)也不為過(guò)。很多進(jìn)藏的人就很喜歡炫耀自己在高原的種種生死經(jīng)歷,而對(duì)于肉體,無(wú)疑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考驗(yàn)和摧殘。
我的阿爸老了,充足的氧氣和健康是他需要的。有一次,站在高高的白雞寺前,我對(duì)阿爸說(shuō),阿爸,為了你的健康,你得離開(kāi)高原了。剛烈了一輩子的阿爸忽然有些傷感,半晌才俯瞰著建塘壩子和遠(yuǎn)處家的方向說(shuō),阿爸老了,離不開(kāi)這里了,只要你們健康地生活著,阿爸也就放心了。
去年弟弟買(mǎi)了越野車(chē),我和弟弟一家?guī)е謴牡岵鼐€(xiàn)到拉薩轉(zhuǎn)經(jīng)。出發(fā)前,全家來(lái)到了大寶寺,阿爸在佛前長(zhǎng)跪匍匐,一遍遍為我們的出行祈禱平安順利。阿爸始終堅(jiān)信,大寶寺是進(jìn)入拉薩的鑰匙,領(lǐng)取了這把吉祥金鑰匙,我們一定會(huì)旅途順利吉祥安康的。
回程,為了讓沒(méi)有做過(guò)飛機(jī)的阿爸也嘗試一下飛翔的感覺(jué),我和阿爸從拉薩直接飛回了香格里拉。
飛機(jī)上,我忽然想起了阿媽最后的日子。
在下關(guān)醫(yī)院的重癥室里,清醒過(guò)來(lái)的阿媽執(zhí)意向醫(yī)生提出要出院回家,驚愕的醫(yī)生不明白,求生是人的本能,哀怨,求助,驚恐,是大多數(shù)病人的常態(tài),而眼前這位奄奄一息的老阿媽?zhuān)劾锿赋龅膮s是鮮有的寧?kù)o和自信。
肅然的醫(yī)生在我們簽字后很快給阿媽辦理了出院手續(xù)。出院的時(shí)候,喘氣都困難的阿媽反反復(fù)復(fù)感謝醫(yī)生的精心治療,并讓我們把家里帶去的幾大塊酥油,全部送給科室里的醫(yī)護(hù)人員。阿媽生命中最后幾句話(huà)是對(duì)醫(yī)生說(shuō)的:真真的謝謝你們的照顧,真真給你們添了麻煩,阿媽連著說(shuō)了很多個(gè)“真真”,阿媽漢語(yǔ)不太流利,表達(dá)極致和深切的意思,她只會(huì)反復(fù)說(shuō)這兩個(gè)字。
此后,阿媽便不再說(shuō)話(huà),靜靜地迎接著死亡的降臨。疼得忍不住的時(shí)候,阿媽會(huì)喃喃地念誦幾句經(jīng)文。一個(gè)星期以后,阿媽安詳?shù)刈吡恕?/p>
即使是今天,當(dāng)我不得不說(shuō)出死亡這兩個(gè)殘酷的字眼,我的心依然顫抖不止。
面對(duì)死亡,我依然沒(méi)有阿媽那種自然而然的心態(tài),而阿媽不過(guò)是千萬(wàn)個(gè)普通藏族人中的一個(gè),對(duì)于生死,有著天然的坦蕩和不可或缺的高貴安詳。
是的,即使沒(méi)有災(zāi)難的降臨,人也終將還是會(huì)死去,從這個(gè)層面上說(shuō),死亡確實(shí)沒(méi)有什么可怕的。
每當(dāng)我想念阿媽的時(shí)候,便會(huì)去松贊林寺點(diǎn)燃一盞溫馨的酥油燈,然后鄭重地寫(xiě)上阿媽的名字。有次住家里的一位客人與我同去,他好奇地問(wèn):你為什么不點(diǎn)上一百盞呢?在他看來(lái),點(diǎn)燈的數(shù)量與孝順和超度一定是成正比的,顯然,他是另一種思維方式和生活習(xí)慣。
而對(duì)于我,時(shí)間終將在搖曳的酥油燈中遠(yuǎn)去,逝去的所有也終不會(huì)再來(lái)。
不再悲傷。
遠(yuǎn)處的大地正孕育著另一場(chǎng)轟轟烈烈的生命,作為樸素的人,為著自己樸素的日子,我將一直在這片高原上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