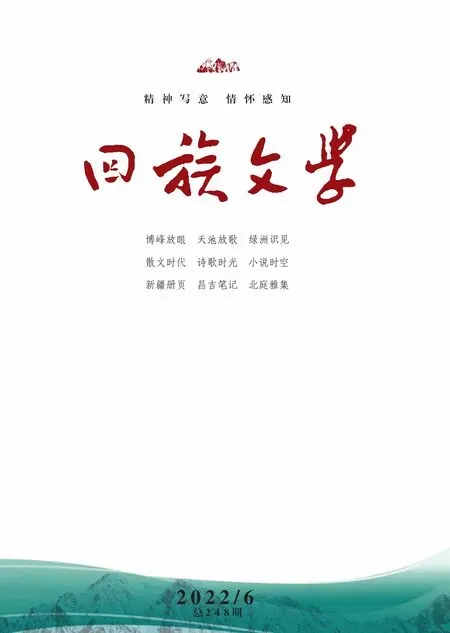火盆中的舊址(三題)
周蓬樺
青瓦與三種遐想
古街很短,依傍梅山寺。每當我路過街口,都會忍不住駐足,朝深處凝視良久,心生幾分疑慮,幾分惆悵,卻終是沒有走進去。事后思量,我只是想遠遠地感受一下那里的滄桑況味吧,聽一聽時間深處的幽寂之聲。而眼前,閃過一片青瓦。
類似的青瓦建筑,我在江南的水鄉見過多處,朱門深宅,屋檐翹立,通體氤氳神秘的漣漪,地氣彌漫到墻角——幾年前,朋友約我到揚州過春節,算是透徹地體驗了一回南方的年節。直到今天,鼻孔間依然縈繞著茴香豆和黃酒的氣味,還有瓦檐上的積雪,瘦西湖冰層下凍僵的白魚。
而這一次,又路過梅山寺,卻是怯怯地朝街里走近了些,躡手躡足地站在了那幢青瓦老屋下。稍微抬頭,便見一株發了芽的老梅樹,灰磚白墻似一幅淡墨國畫,像包漿開片的青花瓷器,令人無端地生發許多聯想,平添了些許愁緒。盡管,起初我不知曉這幢舊建筑有什么來歷,經歷了幾代主人,有哪些纏綿悱惻的故事在這個院落里發生。
斷斷續續地聽到八卦,在哪一朝的哪一個時期,有某一位心思細膩的書生在這個宅院里長大,他文文弱弱,說話慢聲細語,冬天在脖子上系一方藍布圍巾,伸出凍涼的手去烤木炭火,再飲一杯案前冒著熱氣的紅茶;他過著賈寶玉式的“公子哥”生活,每天游手好閑,偶爾被荷爾蒙吸引,到西園去與姐姐妹妹們調笑,滿身散發脂粉氣。年年歲歲,門前的車馬停了又走,恰如樹巢里的鳥雀來了又飛。那少年漸漸長大,唇間長了男人的胡須,他就要出發遠行,到遠方的城里,求學或求職,經世間的苦。他腋下夾一把發黃的油紙傘,在飄飛的柳絮下出發,途中乘坐輪船,過碼頭,進入喧嚷的街市,店鋪與酒幌映入眼簾。在戰亂年代,人的命朝不保夕,這個從富宅里出門遠行的后生,原本一日三餐都要講究,每天的下午茶也必不可少,他壓根兒就沒有應對江湖的能力,江湖人的一聲呵斥就能把他唬住,不敢作聲;幾杯水酒就能被灌得爛醉,手舞足蹈地說胡話。在那樣硝煙滾滾的亂世,他若要過得舒坦滋潤,必得經過一番蛻皮脫骨的涅槃。而在忽然的一天,他像一滴水從人間蒸發,家人再也收不到他的一封家書——像一首鋼琴曲的篇頭戛然而止,那個隔三岔五地寫信要錢要物,總是招惹討嫌的人按下了暫停鍵。家人免不了火燒火燎,女人們哭鬧一番,急急地央手下人去尋,搜遍世界,自是沒有線索,白白花了不少銀兩。時間一久,便也成了一樁懸案。當然,在那個年代,類似的案例不在少數,聽得多了,人們也并不以為稀奇。
故事講到這里,忽然想到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岔的花園》,在這篇小說中,博氏巧妙地設置了一個曲折悠長、忽明忽暗的迷宮,讓人物在歷史與現實中來回穿梭,像一根生長在墻壁上的蔦蘿花藤,或長或短地適應著時空的凹凸結構,最終抵達玄幻迷人的敘事效果。而在我看來,少年的命運具有同樣撲朔迷離的性質。如若沿時間的河流刨根溯源,甚至可以無限漫延開來,像一只盤踞在高山之巔的憤怒猛禽,實現無盡頭的飛翔。此時此刻,我呆立在現實的地面,望著青瓦屋檐上新長出的一簇春草,腦海里冒出三種遐想,附錄如下。
畫面一:隨著他的失蹤,各種混雜的消息傳來,議論是免不了的,每每從報紙上看到一則照片模糊的認尸啟事,都會給宅院帶來一陣不小的騷動,人們前往報館打探,結果都是失望而歸,讓哀傷的話題卷土重來。而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事實上,少年并沒有像傳說中那樣遭遇不測——原來,是他在偶然的一晚看了一場戲,遇到了一個民間戲班子,他和班主聊得投機,班主賞識他的書生氣質、才子佳人的容貌,便有心拉他入伙,還說他的前生乃是梨園名角云云,揀玄妙的話語哄他。他著了道,便決定加盟戲班,讓生命從頭開始,或者叫再續前緣。自此,他跟著戲班開始了漂泊流浪生涯,徹底告別公子哥的形象,他要把此生的命運與一幫走江湖的人綁在一起。這對他而言,既是宿命,又是必然。他是從心底里對自己不滿,決意要告別舊的家庭出身,把從前的一切像泥胎一樣打碎,讓風雨塑造一個全新的個體。他更姓改名,經歷脫胎換骨的蛻變,而若要完成這些,頭一樁事便是斷絕舊交,與過去做個了斷。他還年少,有足夠的時間可供消費與試錯。
他的個案,讓一句話得到驗證:“人的改變,是從討厭自己開始的。”
畫面二:在他走后不久,西園的一位女子便像被秋霜打蔫了的花,病懨懨的,提不起精神。她不再像從前那樣,每天搽粉抹黛,關心自己的容貌。在她看來,女為悅己者容。她私下里叫他“毛弟”,因為他長得像她豢養的一只花貓,毛色光亮柔軟,瞳仁閃閃。如今,她心悅的毛弟走了,美貌于她失去了意義,眼中的事物也起了變化,園里的茶坊與荷塘沒了往日的味道和光澤,連同瓦屋頂上的樹冠,都散發一種淡淡的哀愁。姐妹們約她采花或女紅,她婉言謝絕;正月十五,表妹約她去梅山腳下看花燈,她勉強去了一會兒,就溜回了閨房,被凍得牙齒咯咯打戰。在閣樓里,她抱了暖手袋,浴了足,洗了銅盆,點燃一炷香,來到花梨木的窗格前,手托兩腮,望著一輪明月嘆息。當時,東園的少爺還沒有從人間失蹤,她不過是在盼望一封字跡工整的書信。只是有一件事,始終讓她困惑:他是家族獨苗,為何偏要遠行呢?放著現成的安樂不享,丟下蜜一樣的生活,偏偏要到外面吃苦遭罪,要知道,祖上創下這么大的一攤子家業,是足夠他揮霍享受一生的呀。她聽說書人的唱詞里講,富貴不出三代,換句話說,無論你的祖上如何精于算計,蔭求祖蔭、余祈富余,但到了后輩的某個時段,家族里必定要出一位逆子,他會神使鬼差地敗了家,破了產業,讓一幢日積月累的大廈迅速倒塌,而這乃是上天所注定。她每每聽了這種話,是不相信的,認為這是貧窮的人家盼著富家敗落,是嫉妒心理作祟,當他失蹤的消息傳來后,她信服了。她結結實實地哭了一天。而此時的她,已經懷有身孕,三個多月了。她原本沒有任何經驗,萬沒想到,在他離家前兩個人僅有的一次溫存,居然能夠生根發芽。要命的是,躲在深閨里沒用,因為肚子會一天天大起來,這個秘密像一團火,會連同包裝紙一起燃燒。而她的命運,將由此改寫。
畫面三:多年之后,名滿天下的戲曲名角慕容秋榮歸故里,他帶領的團隊要在老城的梅山劇院義演七場,為當時的南方水災進行募捐。回到故鄉,眼前的一切已經物是人非,他對此態度卻顯得極為淡然。其時,他的生活已經不再依賴記憶,甚至把少年時代發生的一切早已全部清除,當地的演出組織者在宴請席間每每提及——提及他與這座城市的歷史淵源,他都顯得一臉冷漠,含含糊糊地說,記得自己的舊居是一幢深宅大院,如今已無親人故交可識。他笑笑說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他已與舊時代徹底切割。故鄉的人對之表示不解,覺得他不近人情,但也不好違了大師的態度。當然,人們不知道他究竟經歷了什么,人們看到的只是他表象的光環,而永遠無法觸及其人性深處的本真相貌。準確點說,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他曾從懸崖上跌落,在林中被劫匪追殺,七次中彈負傷,全身上下換過數十人的血漿。最后一次,他從馬背上跌落,腦袋遭到地面撞擊,得了嚴重的腦震蕩,成了植物人,躺在床榻上長達九個月零八天半,靠輸液維持生命。有人給出診療方案,對他實施了當時堪稱冒險的開顱手術,整個后腦勺都換掉了——他后面的半個腦袋是另一個人的,終身都有隱隱的排異反應。好在手術做得很成功,讓他蘇醒過來,并經過一段休養后重新登上舞臺。如今,殘存在他腦海里的,已經不再是他一個人的記憶,而是多個人的記憶雜糅夢的碎片,時而呈黏稠的糨糊狀,時而呈冰河的凝固態。在他的耳畔,回響著遙遠的幻覺,時而是子彈的嘯聲,時而是鑼鼓的喧鳴。盡管,從表面上看,他容顏光鮮,甚至是有幾分和藹可親的樣子,尤其站在舞臺上,一招一式,招招式式爐火純青,他把一種唱腔發揮到了極致。往往,聲線停止后會激起三波潮水——掌聲,掌聲,掌聲。
總而言之,天才的不凡的命運造就了他,致使他無論轉身、行走或停留,都顯得多維、傳奇與復雜。當大幕落下,他的人生已經走完,留下了一幢青瓦舊居,供后人觀瞻,也留下了重重霧靄與N種遐想——這就好比一個故事的多種講法,你無法確定它屬于虛構,或者真實。
火盆中的舊址
遙遠的夏天,風雨飄搖,一幢破敗的茅屋——雨水順著瓦檐狂瀉而下。轟隆隆的雷聲,閃電照亮雨中的天井。
那一年我六歲,接連幾天不吃東西,因為生病而哭鬧不止,身體癱軟在母親懷中。得了什么病呢?大約是肺炎,咳嗽不止,還出黃疸,似乎命懸一線。母親用臂彎搖晃著我,企圖讓我安靜下來,但我雖然雙目緊閉,卻分明聽到周圍都是嘩嘩的雨聲,還有從天際傳來的陣陣殺伐聲,腦海里出現各種畫面,險象環生。恍惚之中,聽到母親在我耳畔嘀咕:“姥姥去請大夫了,救命的人要來了。”
聽了她的話,我突然睜大了眼睛,我的視線移開了母親布滿憂愁的臉。在那一刻,我的視線掠過屋頂,望見了窗外比屋梁更大的雨柱,還望見了遠處被雨水潑打的碩大的樹冠——更為奇怪的是,我望見了裹著小腳的外婆,吃力地行走在一片泥濘的鄉道上。她的頭部頂著一塊遮雨的黑布,身后跟著一位胡須飄飄的鄉村郎中。
很快,雷聲熄滅,一場陣雨也收住了腳,青草濃郁的氣息彌漫到房間。那位胡須飄飄的人在屋內坐定,雖然留有胡須,但似乎并不太老。他用手撫摸我發燙的前額,又捉了我瘦弱的手腕把脈。我能聽到自己的脈搏突突跳動的聲音,那是向世界發出求救的信號。
接下來,郎中命母親把我抱到木床上,仰躺下來,赤裸的上身袒露出肚臍,用酒精洗凈周圍。郎中一番忙碌,從藥包中取出幾根蠟紙筒,用火柴點燃,又取出一枚銅錢,將銅錢置于臍上,錢孔對準臍心,再將蠟紙筒扣于銅錢上,蠟紙筒下端與臍相接處用濕面圍成一圈,固定密封,勿令泄氣,臍周用毛巾圍好,然后將上端點燃,待燃至離臍半寸,迅速將火吹滅,以免灼傷皮膚。
當一根蠟紙筒燃盡之后,肚臍上出現了許多殘留的黃色粉末,像一堆耳屎。外婆和母親守在旁邊,見狀都驚訝地睜大了眼睛,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問:“這是什么?”
郎中回答:“黃疸毒素。”
郎中說把這些毒素排出體外,孩子的病就好了。那一天,郎中給我灸了三針,燃掉了三根蠟紙筒。臨走時,郎中將灸法教會給母親,留下幾十根制作好的蠟紙筒,起身告辭。在我模糊的印象中,郎中的話語不多,表情比較肅穆,他離開茅屋時腋下夾著一把油紙雨傘。
天晴了,郎中消失在雨后潔凈的鄉路上。他有些駝背,遠遠看去,仿佛把整個村莊移到了肩上。
聽母親說,郎中走后,我大睡了一覺,醒來感覺病好多了,當晚便有了餓意,喝了一碗小米粥。
此后,母親依照郎中的叮囑,每天給我進行灸療,不管怎樣,眼瞅著我一天天好起來,全家人如釋重負,松了一口氣。
灸療法進行到第三天時,發生了一點意外——那一天,母親正在如法炮制,我突然感覺一陣腹疼,疼得大聲哭叫。母親停止動作,并且把在院子里收拾爐具的外婆也喊進屋來。
而我邊哭邊叫:“嗷,疼,疼。”
母親將蠟紙筒從我的肚臍移開,發現上面已經堆積了許多粉末——這是體內的毒素!每次灸療完,母親都遵照郎中的話,把灸出的粉末撥弄到一個紙片上,放到火盆里焚燒干凈,以防止病毒傳播。此時,母親望著紙片上那些殘留的黃色粉末,呆愣良久。毫無疑問,灸療引發的副作用讓母親對郎中起了疑心。接下來,她做了一個堪稱聰明的試驗:將一根蠟紙筒點燃后,放在一塊石板上進行灸治,結果不出所料——當蠟紙筒燃盡,石板上留下了同樣的一堆黃色粉末。母親驚訝地叫起來,罵了一句“騙子”。
當然,故事并沒有就此結束,這也不是事情的全部經過——發覺上當受騙后,母親氣得臉色漲紅,可惡的郎中讓她花了全家半個月的生活費不說,主要感覺太窩囊恥辱了。這個可惡的騙子,連一個小孩子也不放過,也不怕遭雷劈啊。
那一天,母親罵了能罵的臟話,還把外婆責備了一頓。
其實,外婆相當無辜,她和郎中素不相識。常言說人病亂投醫,她是在沙河鎮上打聽診所,被一個在街頭閑逛的老太太帶路,七拐八拐地穿越了好幾條胡同,最終找到了郎中的家。
好在娘兒倆發泄完畢,火氣漸漸消退,最終自認倒霉——權當這件事沒有發生。一番互相開導,她們決定接受教訓,把剩下的十幾根蠟紙筒投入火盆中,連同郎中留下的一個地址,付之一炬。
母親和外婆不再提及此事,因為這件事不讓人愉快。幾天后,我的病竟然好了,又回到了與小伙伴們一起玩耍的隊伍中。于是,與郎中再次發生交集的可能性從根本上斷絕了。
話說多年之后,我讀到一本自故鄉郵來的《沙河年鑒》,隨手翻到“地方名士”欄目,從一則詞條中了解到郎中的事跡:他用高超的醫術終身行醫,廣受鄉人稱道,享年八十七歲。其實,在成年后我就知道母親當年誤會了郎中。因為蠟灸黃療古法運用并不廣泛,人們難免對它認識不足。至于其能夠直接從石板上提煉出粉末,雖然顏色相同,但此粉末非彼粉末,也就是說,從石板上提煉的粉末不含人體毒素。
這小小的偏差,僅用肉眼是看不到本質的。
我想,當人們回首往事,會發現曾經的誤解、憤怒與爭端,往往出于認知的局限與偏差,它們導致了判斷的失靈與失誤。面對那些發生了的過往,當省悟時一切都晚了,只好將錯就錯——假如事情放到現在,我會從火盆中救出那張寫有地址的紙條。而此時,我們只能憑借想象,祭奠郎中一生風云密布的表情。
削掉的鉛筆
那天在白山腳下沿河散步,看到一個低頭的孩子佇立河邊,全神貫注地用一把小刀削一根柳樹的枝條,我意識到又一個春天到來了——這是山林里的春天,幾天后會有一個萬物花開的畫面出現。
我忽然駐足,回頭觀望河邊的少年。不知怎的,他削柳枝的樣子讓我想起削鉛筆。
當時,我們家還住在魯西平原的沙河鎮上,背景是貧窮的70年代。印象中,那里是一片白花花的鹽堿地,生長著在風中起伏不定的葦子林,還有一棵挨一棵的果樹。當夏天來臨時,一場風雨會吹落許多樹上的果子,我和伙伴們便潛入葦子林中,撿拾落果,每每從葦子林里鉆出來,赤裸的胳膊都會被荊草劃出許多血道道,好久才會結痂。
那天一大早,我被母親叫醒,我一邊含糊地答應,一邊翻身向里繼續睡覺,企圖接續一個被打斷的夢。但母親這次不客氣地掀翻了我的被子,大聲嚷嚷說:“快起床,從今天開始,你要上學了。”
我一骨碌爬起來,上學這件事讓人興奮,因為從此以后,不必再羨慕街頭那些背著書包昂首挺胸的大孩子了。母親已經把昨晚縫制好的書包遞到了我眼前,里面裝著演草本、一支鉛筆和一塊橡皮,還有一個鉛筆刀。而課本是到學校后才發下來的,至今記得新書拿到手里,一股油墨香撲鼻而至,它在鼻尖縈繞多年。
起床后,原本想體驗一下削鉛筆是什么感覺,可惜母親已經替我削好了。望著木桌上留下的一堆碎末末,我噘嘴賭氣,責備母親多事兒,猜想她是把一樁開心事攬給自己享用了。母親不清楚我心里的想法,拿出一塊抹桌布,把那堆碎木屑輕輕地掃進竹籃里。
學校離我們家不算遠,繞過兩條胡同就是,校址在一片操場上,遠遠地看到一棵老槐樹,樹杈上懸掛著一口生銹的老銅鐘。
時間過得很快,上學大約半年之后,我就改變了看法:事實證明削鉛筆是一項技術活,而我真的削不好。手持一個又細又長的怪物,不知從何處下刀,有時候好容易削出鉛芯,卻一不小心就折斷了。我把這些統統歸罪于鉛筆刀太鈍——當時,旋轉式鉛筆刀還沒有普及呢。為此,母親把一拃長的小刀往磨鐮石上蹭啊蹭,刺刺地冒火星。她神情專注,像是要完成一樁改變世界的大事情。
眼瞅著鋒刃足以達到削鐵如泥的程度了,才把小刀收回鐵鞘。不料,卻因此發生了一樁小事件:
被磨亮的鉛筆刀太過鋒利,有一次削破了我左手的食指——小刀切割木屑的同時飛快地鉆到了我的肉里,手指肚上滲出了一顆大大的血珠。我忍著疼,又怕被人發現,只好把手指頭含在嘴里,遠遠地看上去,像傻瓜的經典造型。
血流到嘴里,一絲絲腥而咸的液體。
我的同桌叫什么名字來著?一時想不起了,只知道她是個賊機靈的女孩,輕輕一瞥就發現了這個秘密,她當場“撲哧”一聲笑出來,現場頓時一陣騷動。當時正上晚自習課,聽到笑聲,全班的同學都轉過頭朝我張望,神情詭秘好奇。女老師姓戴,及時發現了問題,來到我的書桌前,她以為我在課堂上搞怪搗亂,口吻嚴厲地命我把手指頭從嘴里取出。我在張口的同時,引發了全班同學驚詫的叫聲。
因為牙齒上有血,形象可怖。我的臉一陣發燒,恨桌子底下沒有地縫可鉆。盡管,戴老師在了解情況后沒有當面做出批評,還寬慰了我幾句。但這件事卻讓我在全班同學面前出了糗,同學們議論紛紛:沒出息的笨蛋!連個鉛筆都削不好,將來還能做什么呢——一個差等生。
這話似乎沒錯,因為在剛入學的頭一個學期,全班上下就知曉我不是個好學生了,人人都知道我太貪玩,諸如課堂上偷看小人書,聽課時腦子開小差;每天的作業不好好做,考試靠“打小抄”蒙混過關。而且,老師一不留神,我就哧溜一聲跑出課堂,到校園外的小樹林里去了,那里有一灣大水塘,水塘邊飛著蜻蜓、蝴蝶和各種花翅鳥,我本打算進去捉一只蝴蝶再放飛,聽到哨子聲立馬就離開,但往往因為太忘情太投入,就把課堂的事忘到了腦后,直到放學的鈴聲響起了,我才從中驚醒,撒開腿離開小樹林往回跑。
第二天,我為此遭到罰站,但總是屢教不改。唉,這一次,戴老師一轉身就去了我家,把我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母親。
那天,放學回家,我原本欲向母親訴說委屈,哪知母親一臉嚴肅,當即下令:“晚上別睡覺了,老老實實地練習削鉛筆。”
當天晚上,我就著一盞煤油燈,把一支好好的鉛筆削成了碎屑,那只受傷的指頭在哭泣,頭發被油燈火點燃,烤出了一股焦煳味。
我一邊練習,一邊在心里責怪同桌。接連幾天,我對她不理不睬,撂臉子給她看。哪知這個女生太聰明了,很快揣摩到了我的小心思,在一天上晚課的時候,悄悄地把一支削好的鉛筆用胳膊肘“塞”給了我……
這讓我感覺很不好意思。后來,學校里筑起了一道院墻,把去小樹林的路徹底封住了,我的一顆躁動之心,也漸漸平息下來。這么著,漸漸地我迷上了課業,尤其是作文課。
多年以后,寫作的習慣讓人常常陷入回憶:童年的往事,少年的沖動,以及削鉛筆這類的小事例,都會在記憶中浮現,感覺苦澀又美好啊。去年春節,從縣城繞道,去了一趟故鄉沙河鎮,有好事者召集了一次小學同學聚會。結果,原定兩桌人只湊了一桌。席間的憶舊是免不了的,我向人打聽這位聰明女同桌的下落——僅僅因為她幫我削過鉛筆!記得我還回贈過她一塊水果味的橡皮,以示和解。
遺憾的是,人們把頭搖得像貨郎鼓,竟沒有人知道她成年后的去向。
我在心里感慨:從小學到中學,削掉了多少支鉛筆啊,砌起來應該是一堆柴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