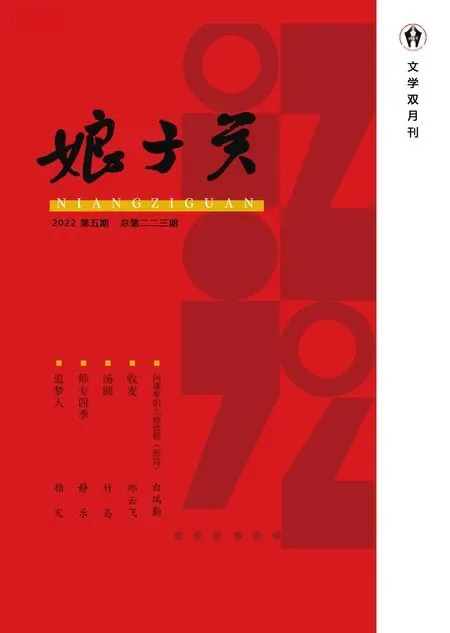老屋里的家族記憶
◇張迎
很多年前,這座房子便坐落在這里。它是名副其實的土坯房,母親在這座房子里相識了父親,姐姐和我在它的襁褓中誕生。多少年過去了,它依舊坐落在村子里,即便周圍的老屋一座座倒塌,數以百計的新房在它的四周巍然矗立,它依舊安安靜靜守望在那處原來的角落。
七八歲的年齡,我總愛出去玩。每次歸家,我總能在老屋門前的那條長長的巷子里看到紅磚壘砌成的煙囪冒著蒸騰的白煙。我知道母親一定在堆滿干柴的廚房里做起了晚飯。我推開黑漆染成的木門,踏上像鄉間土路一樣的院子,跑進廚房里,開口便問母親今晚吃什么。大多數時候,母親都會帶著一種半嚴肅半玩笑的腔調說我是一條饞蟲,一個只知道吃的熊孩子。由于廚房里的白煙飄得滿屋子都是,母親總關切地要求我到廚房外面去。我便蹲在老屋院子里靜靜看著放柴的爐口里冒出的黃亮色火焰,甚至仔細傾聽火焰與干柴之間交匯而成的“噼啪”聲。在我看來,這種響聲是非比尋常的,它們其實是兩支軍隊在戰場上廝殺,雙方都拿出頂厲害的武器互相咬牙切齒地爭斗。那“噼啪”的聲音便是雙方武器交鋒時產生的驚心動魄的回蕩。母親見我目光呆滯,總要呵斥我一番,說我巴掌大的孩子想什么破事。于是,我的想象力就在一場猝不及防的暴風雨里消散殆盡。年關的時候,我對母親做的花饅頭著了魔,母親和成面團,再把面團揉成長柱子,拿刀將它切成一塊一塊的,接著用搟面杖將其捻薄,使其成為一個個平面型的圓,然后再用刀在圓圈外圍切一圈占半徑三分之一的線條,之后用手捏成形似花瓣的形狀,等整個圓外圍切割的線條都被均勻地捏造成一個個花瓣的時候,一朵花就呈現出來。母親會在花瓣與花瓣的間隙當中放上一個又一個紅棗,之后繼續累加花朵,不過上層的花朵總要比下層的花朵小一些,呈現出依次遞減的特征。母親通常會累加到五層,有的時候會累加到六層,完成體像是一個金光燦燦的小寶塔。可是,大年三十的晚上,過了十二點才能夠吃,我往往挨不到那么晚,常常咽著口水沉沉地睡去。有一年,我實在抵不住誘惑,就在母親蒸熟花饅頭不久,趁她不注意,捏了左半邊許多大棗吃,那時剛蒸出的花饅頭還很熱,我抑制住滾燙的熱氣硬是沒出聲的吃完了它們。第二天母親從祭神的靈臺上拿下花饅頭的時候,還以為是被老鼠吃了。后來,母親從我口中知道了實情,就想了一個法子,臨近年關,母親做了三個年三十晚上放在靈臺的花饅頭之外,再額外做一個小巧的花饅頭,那是給我解饞的。每次手里捧著香氣撲鼻的花饅頭,我都覺得老屋里點亮起溫柔的燭火,給予我安寧。這種感覺就像夏天停電的夜晚,我們一家四口拿出四張板凳和兩把蒲扇來到老屋的院落,我和姐姐坐在中間,父親和母親一人拿著一把蒲扇為我們扇去悶熱的空氣和煩擾的蚊蟲,我托著腮聚精會神地聽著父親講三國故事。蟋蟀在某處石縫里歌唱,清脆響亮。我聽著聽著,便會睡在母親的懷抱里,父親會把我抱起來,走進老屋的襁褓中,輕輕緩緩地將我放在床鋪上。
村子里的青壯年男性都開始陸陸續續外出打工,父親卻是一個不愿意外出的異類。母親脾氣急,總是大罵父親是頭懶驢,天天只知道守著幾分爛莊稼地過活,一年到頭不知道能掙幾個錢,到頭來連兩個孩子的學費都掙不出。父親悶聲悶氣地坐在屋子里抽旱煙,母親沒好氣地站在院子里一邊喂雞一邊言辭激烈地說著實情。可父親依舊無動于衷,只是眉目緊縮,抽完了旱煙再自個兒卷上一支接著抽,他的目光始終不在母親身上,而是時常看看腳下衍生出的一條有細長裂縫的水泥地,有時還會打量屋子里掛在墻壁上的擺鐘,抑或是瞧一瞧貼在墻上的明星掛歷。每當這個時候,我都能猜到接下來母親破口大罵,甚至動起手腳的情形。是的,我的預感幾乎沒有失算過,我總能聽見母親尖銳暴躁的呼喊和痛罵,甚至把碗筷扔在地上碎裂的聲音。而一向閉口不言的父親最終也會喪失耐性,與母親激烈地爭辯起來。他們最終會扭打在一起,互相撕扯著對方的衣服,全然不顧及模樣的好壞。尚且年幼的我,心中十分恐懼,只能來到院子里,盡可能把身體縮到距離父母最遠的角落中去,毫無目的地撿拾起一塊塊細小的石子把它們壘砌成一座座小山,又從中拿起較為尖細的,在有些濕潤的泥土里劃來劃去。雀鳥常常會停靠在屋檐上歪著腦袋左右打量著我的異常舉動,我很想扔幾塊石子好好教訓一下它們,但怯于父母的爭吵,只能象征性地嚇唬它們幾下。剛開始,它們還會配合地飛去,后來便知道了我的伎倆,依舊如故了。沒有可以繼續玩下去的東西,我的目光會停留在老屋的身上,一左一右兩扇正方形的窗戶像是兩只目光如炬的眼睛,高高的房門又好像一臺電視機,父母正在熱情地盡職地表演著,他們的演技堪稱完美,在我魔幻迷離的眼神中就像是真的一樣。
我畏懼父親和母親,卻是不害怕姐姐的。我上小學的時候,姐姐已經上初中,周一到周五她要留校我是見不到她的。只有周六的一整天和周日的一上午我才能夠在老屋里見到她。姐姐的性格跟父親挺像,是一個文靜的人。再加上她學習刻苦,所以我每次見到她,她都是把自己安置在里屋看書和學習。我總會裝作學習的樣子倒捧著一本語文課本,滔滔不絕地在她身邊背起早在幼兒園就會背誦的《詠鵝》與《靜夜思》。剛開始,姐姐根本不理睬,確切地說,跟我沒來的時候完全一個樣子。我便加大嗓門,加快語速,貼近她的耳朵嘩啦嘩啦地把我的聲音強制性地往她的耳朵里塞。這個時候,姐姐會微微皺起眉頭,回過頭來用冷峻的眼神向我發出警告。每當看到她用這樣的眼神打量我時,我知道自己的擾亂計劃已經開始奏效了,不由得內心竊喜起來。接著,行為越發不可收拾,我會拋棄偽學習的樣子,把語文書本卷起來形成一個擴音器,悄咪咪地放在她的耳朵跟前,在她沉浸在書本的時候,“啊”的一聲大喝。姐姐整個身子會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我會發出陰謀得逞后的大笑。姐姐揉著耳朵站起來,舉起右手直愣愣地指著我,鼻息里噴出十丈高的火焰,說一聲“滾一邊去”。我見她發了火,便打趣地說她頭冒烈火,樣子真是難看,怪不得里屋的遮塵布破了,十有八九是被這火氣給燒沒的。姐姐跺著腳,沒好氣地訓斥我放屁,明明是我小時候拿竹竿捅破的。我便跟姐姐拌嘴,死不承認。姐姐最終辯無可辯,便呼喊母親。對于姐姐來說,這是她最后的殺手锏也是最有效的武器。我會驚慌失措地喊,好姐姐,你別說了,我這就走。可是姐姐不會罷休,直到喊來母親。母親聽完實情,便會理所應當地揍我一頓。姐姐看到我灰頭土臉,怏怏不樂的樣子,便得意揚揚地帶著勝利者的驕傲回到里屋去。可能我的惡劣行為跟姐姐結下了梁子,從四年級開始,姐姐便有意無意地打聽起我的學習成績。有一次,我數學考試不及格,老師要求我把試卷帶回去把錯題改了,并讓家長簽字。我心想,如果被母親看到豈不是又要被痛打,便模仿著母親的字跡簽字,然而字跡寫得確實太難看,根本瞞不過老師,便靈機一動想到姐姐,姐姐問我考了多少分,我說勉強及格,她把試卷拿過去,冷笑一下,問我,五十七分算是勉強及格?我低下了頭,但是她到底替我簽了字,我十分感激她。后來,我跟姐姐又鬧別扭,她喊來母親把我考試不及格的事情揭露出來,結果我還是沒有躲過這份挨打,只是它稍微來遲了一些。這樣,因為學習成績把柄的緣由,我不敢再去惹姐姐的不高興。姐姐升入大學后,我與她見面的次數減少了許多,由于她有半年時間都住在學校,原本屬于她的床鋪歸了我,老屋里的聲響少了許多,我大休回家的一天半大多是悶在床上睡覺或者看手機,整天一副病懨懨的樣子。幸好,老屋的窗是打開的,它時常會帶進一陣清爽的風,吹亂我的發,敞開我的額頭,晾曬我的虛汗。
有一陣,家里因為鼠患嚴重,母親向鄰居家領養了一只黑貓,這只貓通體黑色,我稱它為“黑旋風”。因為我剛剛接觸了《水滸傳》,知道里面有個厲害人物叫作“黑旋風李逵”的。我雖然叫它“黑旋風”,但這只貓卻是一只貨真價實的母貓,行為舉止也十分優雅。它經常臥在院子的陰涼處安靜地打量周圍的角角落落,走起路來輕手輕腳的,好像童話故事里公主模樣的人物。它甚至定時的用舌頭梳理自己的毛發。這樣看來,它實在不像是《水滸傳》里描述的兇神惡煞的“黑旋風”。我也沒見它捉到過老鼠,所以,我走近它的時候,會跟它開玩笑地說:“誰家的貴族小姐陰差陽錯地落入世俗凡塵啊。”它會下意識地把頭甩在一邊,似乎對我的玩笑不甚滿意。后來,這只貓懷孕了,沒過多長時間在放農具的小屋里生下三只小貓,其中有一只也是通體黑色,其余兩只是黑黃兩種顏色雜糅在一起。姐姐經常過來照看它,在吃飯的時候還會特意預留出一點飯菜,親自送給它吃。時間久了,黑貓與姐姐的感情便愈深。姐姐在家的時候,我經常看到她懷抱著黑貓在院子里看書,黑貓卷成一團,舒舒服服地盤在姐姐的腿上,姐姐一只手拿著書,一只手輕輕撫摸著黑貓光亮順滑的毛發,黑貓會從鼻息里發出愜意的“嚕嚕”聲。我不屑地對姐姐說,也不嫌臟。姐姐笑一笑,說我真是一個毫無品位的人。我心里不服氣,就跟她繼續拌嘴。在雞圈里喂食的母親聽見會無奈地說一句:“真是上輩子托生的冤家。”黑貓在姐姐身上伸一個懶腰,睜開睡眼惺忪的眼睛朝姐姐溫柔地喵一聲。然后看向我,冷冷地瞧一眼。我甩一句,真是沆瀣一氣。可惜的是,這只貓后來錯吃了老鼠藥,死去了。對于姐姐而言,不必細說,她哭了許多次,以至于有一段時間,我在她跟前不敢再提有關黑貓的事,就連貓的字眼都不能提。每次歸家,我打量老屋的四周,再也不見黑貓的影子,心里也會升起一股空落落的感覺。我還是會想起那個四月,一只初來乍到的小貓躲在院落的柵欄深處叫個不停,我尋著聲音走近,在柵欄深處看到一只閃著淚光的小黑貓。我揮揮手,說,喂,伙計,你出來啊,我們來玩。它聽到我的聲音往里縮得更緊了些。后來,姐姐從學校回來,我神神道道地告訴她,咱家院子里有只怪物,你小心點。那天晚上吃飯的時候,姐姐竟然把那只怪物抱進了屋子,我有些驚疑,問她,你用什么辦法捉到它的。她指指我的心臟,說,用心。我沒好氣地回復,吹牛。有一時,我聽到老屋外的貓叫聲,會想起自家的黑貓來,它似乎并沒有走遠,依舊在老屋院落的某個角落偷偷望著我,或者愜意地躺在屋脊的某頁瓦片上懶懶的睡覺。或許某一天,它玩累了,睡足了,便從院落嫩綠的草叢里沖出來,撞進我的懷里,親昵地蹭蹭我的額頭,“喵喵”地叫上兩聲,好像在說,好久不見,十分想念。
在高中念書那會兒,村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我們相鄰的土坯老屋都相應地被拆掉建起了嶄新靚麗的水泥房。正趕上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好時候,農村翻新蓋房,政府會有相應補貼,所以那一年村子里有七八成的老屋都被拆除重建了。我回到家看到這樣的情形,便詢問母親為什么咱們還沒有翻蓋。母親沒好氣地說,你不上學,家里就有錢了,有錢早就蓋了。我聽出母親不悅的聲音,便沒有繼續說下去。可能我的話成為導火索,晚上母親同外地打工的父親通電話,聊著聊著便談到翻蓋房子的事情上,也不知什么原因,他們在電話兩端吵起來。周六周天這兩天母親的臉上都寫滿了不快。于是我也很識相地盡量少說話,免得再招來火藥箱的炸裂。周天下午,我便背著書包,不聲不響地離開家回到學校。可翻新老屋的計劃母親天天掛在嘴邊,至少我在她身邊的時候,母親幾乎每天都要念叨一兩遍。后來,母親患上重病,辛苦攢下的一點積蓄很快花光了,家里便再沒有人提及有關翻新老屋的事。所以一直到現在,老屋還是老屋,它一直都在原來的位置安安靜靜地矗立著。老屋的周圍都是又高又俊的新房,美觀氣派。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也被這虛榮的風氣俘虜,極度地厭惡面前可以被稱作“破爛不堪的危房”。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一筆錢,雇幾個拆房專家,毫不姑息地砸垮、砸爛這不堪入目的破房子,以此來擺脫不甚體面的外形。然而,毀掉了它,就等于抹去了幾十年的家族記憶啊,我的母親去世在這間老屋里,我的姐姐出嫁在這間老屋里,我一路求學至今何嘗不是在這間老屋里取暖?母親過世后,父親曾告訴我,他不會再去天南海北打工了,因為他怕老屋院落里生長出野草,擔心老屋內成為成群結隊老鼠的家,他更擔心母親在老屋荒涼的院落里哭泣。母親走了,姐姐嫁了,我也只是偶爾駐足停靠在老屋的旁邊,現在只剩下父親還守衛著老屋。我不知道現在的老屋還能存留多久,我也不知道老屋是否像一個百歲的老人那樣身心俱疲,畢竟它身上的瓦片時有松動,畢竟它外圍的皮膚脫落了一層又一層。我只知道老屋搭建起我與姐姐童年與青春的成長進程,我只知道老屋盤踞著父親與母親幾十年如一日的柴米油鹽。老屋最終把我們一家四口的歡樂、幸福、憂愁、沮喪、哀傷、憤怒、釋懷的情緒統統記錄在自己的文案里。它沒有聲音,卻能夠像一棵樹一樣靜默地觀望著屬于我們這個家庭的一個又一個事件,一個又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