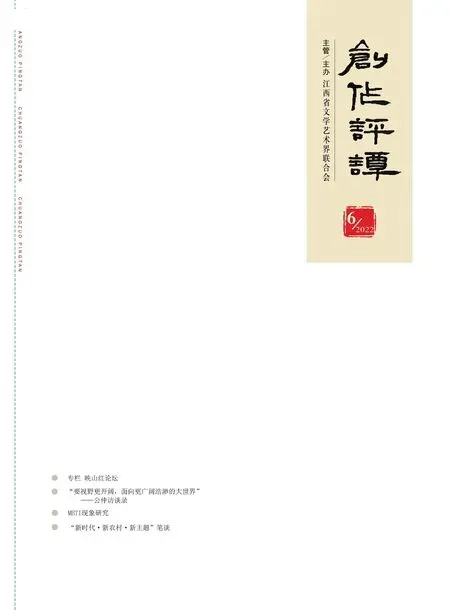“要視野更開闊,面向更廣闊浩渺的大世界”
——公仲訪談錄
◎ 訪談人:李洪華 吳 敏
李洪華(以下簡稱李):陳老師您好!很高興邀請您做這次學術訪談,今年是您的八八米壽,首先祝您身體健康、學術常青!1954年您第一次以“公千里”的筆名在《江西日報》發表文學評論,迄今已68年了,當時您在南昌三中擔任政治課教師,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開始寫文學評論的?能否請您談談當初從事文學評論寫作的經歷和感受。
陳公仲(以下簡稱陳):在訪談前我想先說幾句話:我剛剛過了生日,已是八八老人了。現在做這命題作文,問卷回答,實在難以勝任,勉為其難了。所以,難免會說漏嘴說跑題,甚至答非所問。不過,我一定會說真話,說我想說的、我能說的話。敬請體諒,謝謝大家!
我是1952年參加工作,在江西省教育廳政治輔導員訓練班(現南昌師范學院前身)培訓半年,1953年春即分配到南昌五中教政治,任政治教研組組長兼共青團書記。1953年秋,五中與市立中學合并,定名為南昌三中,我即到了三中,仍教政治和做共青團的工作。由于家庭環境的影響,我從小就喜歡文學,好寫點文章。起初主要寫些教育、語文方面的文章。第一次寫文學評論是在1954年。那時正在上映一部故事片《哈森與加米拉》,青年學生們都很感興趣。《江西日報》社記者來校采訪我,談共青團工作,他談到學生看電影的事,突然興起,約我寫一篇評論《哈森與加米拉》的文章,說可以引導學生們欣賞影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我就欣然答應了。真沒想到,我寫的文章很快就發表出來了,還配有電影照片,在社會上有了些許影響。這讓我產生了一點點的成就感,也鼓勵了我在這方面繼續發展下去。1955年干部政審,由于我海外關系復雜,被認為不宜做政治工作,建議改行從事其他教學工作,我即選擇了語言文學。我的父母都是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在大學工作。我幼年時期家中就有專門的書房,中外各種文學名著十分齊全。從小在這樣的文學氛圍中長大,我產生了對文學的興趣。1955年,我被送入江西教育學院進修語文。1957年“反右”前夕,我又回到三中教語文,1959年后擔任語文教研組組長,一直教高中語文。我對語文寫作抓得比較緊,還主編了一本《中學生習作選》,每篇都有老師的點評。此書流傳很廣,幾年前,三中老校友還在廣西某縣檔案館發現了一本。當時三中名氣超過師大附中,連續八年全省第一名。1963年高考作文題目是《當國際歌唱響的時候》。我們之前在學校復習練筆中,多次以“當……的時候”這樣的題型讓學生練筆,怎樣夾敘夾議。那年三中高考語文成績全省第一名,特別突出。
這說明當時我教語文還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的語文教學特點,一是狠抓語言文字基本功;二是強調時代感,強調結合現實,強調人文關懷。到了大學之后,我選擇了文學理論和當代文學。現如今很多文學理論包括博士論文都與文學創作分割。文學理論從何而來?就是從大量文學作品中總結規律提升而來。可現在,文學理論是從抽象的概念而來,寫出來的東西跟文學創作沒有什么關系,空對空。我曾在《文藝報》上發表過類似的文章,強調文學理論必須與文學創作結合起來才有實際指導意義。但是現在依然是理論還是理論,創作還是創作,兩者分割。現在作家極少看文學理論。我接觸的許多知名作家都說,他們從不看什么文學理論,看了這些都無法創作了。
“文革”前我一直在南昌三中,“文革”中開始下放,大概1968年離開三中。開始是下放在東鄉紅星墾殖場進行勞動改造,后轉到新建縣生米公社。1973年我調到江西大學(現為南昌大學)中文系。當時大學剛剛復辦,就讀的大多是底層推薦的工農兵學員,文化水平參差不齊,不少學員只有小學或初中文化,讀過高中的并不多。當時開門辦學,就是下農村收割插秧,在實踐中學習。直到“四人幫”倒臺,我才開始教寫作,教寫畢業論文,同時帶學生們到報社、出版社、文聯去實習。還帶學生們沿秋收起義的路線做調查,寫了一部《秋收起義史話》。真正的當代文學教學是在1977年正式恢復高考之后。
李:請您談談從中學老師到大學老師這一身份轉變對您當時以及此后學術道路所產生的影響。
陳:中學教學主要是文本教學,大學則主要是宏觀、系統的文學教學,實際上內容沒有改變。中學主要是一些當代文學選出來的經典散文、短篇小說,當然還有不少古文。到了大學內容和視野就更加開闊。
1977年我開始正規地研究當代文學,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個時期一個時期地研究。也接觸全國范圍的文學研究動態。1978年就走出去,到東北、武漢、廣東、上海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另外《文匯報》舉行了一次關于“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討論。我寫了一篇文章,投給《文匯報》,很快就發表了。這是我第一次在省外刊物發表文章。從中學到大學轉變主要是視野開闊了,由文本單篇的分析上升到完整地把握全國以至于全球的當代文學動態分析。
在《文匯報》上我第一次用了“公仲”這個筆名。說起我的名字還有故事呢:我在家五兄妹排行老三,正好在中間,小名叫“中中”。發蒙讀書要個學名,按輩分是“公”字輩,圖簡單,就把我那“中”字加個人字旁就叫“陳公仲”了。可用了一兩年,父親想想不對,古文說伯仲叔,仲是老二,孔子排行老二才叫孔老二,可我是老三呀!不能叫“公仲”,干脆諧音叫“陳公重”。于是,我這名字就用了一輩子了,戶口、身份證都叫“陳公重”。寫文章用筆名,我就把“重”字上下拆開,叫“公千里”。可在“文革”時期,學校校長被打成了“走資派”,我是他手下“四大金剛”的老大,我的名字就成了“牛鬼蛇神”,被批倒批臭。“文革”后期,我來到了江西大學后給《文匯報》投稿,報社在發表文章之前要對作者政審,要單位蓋公章認可才行。我當時心有余悸,不敢用那曾是“牛鬼蛇神”的名字,就又想到我曾用過的“公仲”名字。江西大學就在我文稿作者“公仲”的名字上加蓋了公章。文章發表了,“公仲”這筆名就此一直跟隨著我,以至于許多人把我原名都忘記了,甚至我的有些稿費都因此名與身份證不符而領不到。我這名字的變遷,既反映出了我從事文學道路的里程,也折射出我們國家這半個世紀的歷史印跡。
李:您最初主要是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積極參與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的討論,出版了文學評論集《當代文學縱橫談》,主編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編》。能否請您談談20世紀80年代親歷過的文壇狀況和研究工作。
陳:當時上饒師范學院缺當代文學老師,邀請我去那里教兩個月,讓教務處調課,把當代文學課集中到兩個月內。這期間我發現他們沒有教材,就帶了兩位高才生,一邊聽課一邊做記錄。之后整理出來,編了個小冊子名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綱要》。1981年在廬山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上,將這本書散發了。當時,代表們踴躍排隊,要這本書。不久,這本書受到批評,說這本書“公然與鄧小平文藝政策對抗”。當時,我比較緊張,不少文藝界朋友都不敢跟我說話了。一次偶然的機會,北京朋友來電話問我近況,我就把此事說了。沒想到此事傳到了中宣部。后來中宣部部長王任重的秘書致電省委宣傳部,表示不要搞大批判。省委也開了會,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聯主席俞林代表組織與我談話,要我正確認識此事,讓我自己寫一個檢查,解釋說明此事,把我的檢查也發至全省縣團級。此事就這樣有驚無險過去了。
后來當代文學教材,由十幾個院校聯合編寫,分別作為當代文學史與當代文學輔導教材;又把當代文學優秀作品進行選編成書,供學生們閱讀。我當時分擔的是報告文學與紀實文學部分,而我個人仍覺得不能暢所欲言,就決定獨立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編》一書。這本書是當代文學第一部以個人名義編寫的教材,丁玲為其寫了序。這本書的初稿我給丁玲看了,她覺得有特色,就推薦給了幾家出版社,可那幾家出版社都擔心發行量上不去,怕賠本,不敢接受。我就給了江西教育出版社,他們表示可以出版,但要我保證能發行一萬冊以上,我二話沒說就簽約保證。我找了個書商去操作,第一次印刷就發行了一萬。時值全國專升本考試,急需要教材,書商有全國發行渠道,不斷催著要書,一兩年下來,據說竟銷售了五十萬冊以上。書商不讓我知道銷售情況,怕我要分錢。其實,我根本不在乎錢,書籍能出版,有人讀我就心滿意足了。
1980年代,我參加的學術活動有兩個重要的會議。一是1980年在廬山召開的全國文學理論會議,后來主持人覺得名字太大,容易惹是生非,就改名為全國高等院校文學理論研討會。那是撥亂反正后第一個全國性文學理論會議,有中國社科院、人民日報、中央黨校、中國作協、中國文聯以及不少高等院校校長、專家、教授參加。當時主持會議的主席是陳荒煤(文化部副部長,當時兼任文學研究所所長),省里總管此事的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廳廳長李定坤,會議秘書長是省文聯副主席矢明。我是會議副秘書長,分管接待聯絡和簡報。李定坤對我說,派兩個人給你做助手,一個是文化廳辦公室廖主任,一個是省文聯的劉仁德。我們把廬山當時所有的賓館飯店全包下來了,還不夠住。我把一個賓館的小會議廳改成了寢室,搬來了七八個雙人床,安排一些年輕的代表來住。記得當時余秋雨氣呼呼地來找我,說這里條件太差,要求換個住處。我不認識他,只見報名表上填的是教師,沒有職稱,又較年輕,就安排在這里住。我見他很有些情緒,還是耐心地解釋說:“實在是來的人太多了,臨時加了些床位,請原諒!暫時將就著住下吧。我也和你們住在一起。”說實話,當時廬山條件的確很差。剛剛開放,廬山的接待賓館水電設備尚待更新改造。一個別墅,三五間房,住上三五個老教授專家,一人一間房,有地毯、沙發、會客廳,但只有一個衛生間。吳強說,早上上廁所要排隊,真難等呀!特別是用水沒保證,自來水時有時停,熱水一人一天一瓶。陳白塵說,我一盆水,先洗臉,再洗腳,還要留著沖廁所。丁玲、陳明、公劉先期到達,是以療養名義安排在軍委總后五一療養院,也是兩人共用一廁所。病房還沒有寫字臺,丁玲就用紗布繃帶結成繩子,一頭套在脖子上,一頭在胸前腰間兜著一塊長方形木板,成了寫字臺。丁玲笑著說,這是在北大荒學來的呢。盡管如此,到會代表仍絡繹不絕,人滿為患。
全國正式代表四百多人,其中有丁玲、陳明、王若水、王元化、吳強、徐中玉、錢谷融、侯敏澤、何洛、吳介民、江曉天、繆俊杰、閻綱、王西彥、黃秋耘、公劉、梁信、白樺、陳白塵、葉至誠、顧爾鐔、陸文夫、高曉聲、俞林、李定坤等人。大會會場設在1959年中央廬山會議的會場舊址,討論的分會場就分散在各個賓館。會議提出,不再提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口號,改提為文學為人民服務。丁玲發言,說不提為政治服務,但必須認識到文學是脫離不了政治的。她以自身的文學創作經歷,來說明此事。她還是那樣火氣十足,態度鮮明。而吳強是用《紅日》創作實例,來印證政治干擾過多,會叫作家無所適從。他寫孟良崮大捷后,戰士騎著繳來的高頭大馬,穿著國民黨的將軍服,揮著指揮刀,耀武揚威地在戰場上兜風吆喝。這本來是表現戰士勝利后的驕傲、歡快,蔑視敵人的一種豪情,可后來被批判為“美化國民黨軍隊、丑化解放軍戰士”,只好刪除,再加幾句勝利的口號,小說就干癟乏味了。現在又要改回來,真叫出版印刷單位不勝其煩了。分會場討論得更加有聲有色,豐富多彩。大會上的論述都收入了簡報,再散發給各個會場交流。代表們對這些簡報十分滿意,我也很感寬慰。出簡報是我再三堅持的,我也是從北京學來的。我有幸在北京看到過八屆三中全會的大量簡報,叫我大開眼界,思想大為解放。文學界也應該解放思想、加強思想交流才好。
另一個重大的學術活動是1981年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召開的全國當代文學研討會。我本不愿連年開此種大會,太勞累了,可華中師范學院院長、學會會長王慶生興致盎然,堅持要開,認為這次會議對于“文革”以后全國當代文學研究如何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會址仍選在廬山,這次參會人員仍有三百八十人之多,比上次文學理論會略少,可對當代文學研討來說,也是空前的。全國大專院校教當代文學的教師,幾乎都有代表趕來參加,而全國當代文學研究方面的權威專家,簡直可說是一網打盡了。《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大家有意推選他為學會會長,他也樂意接受,也決定親自到廬山來。于是此事就這么定了。這次會議討論也十分活躍,出了大量簡報。這些簡報,可說是當代文學研究的極可貴的資料。我完好保存了,到時可捐贈給文學資料館。
對于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會議提出了兩個“五七”的觀點。一個“五七”,是指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現在改正了,重新綻放出了絢麗的鮮花,如姚雪垠、鄧友梅、王蒙、張賢亮、從維熙、陸文夫、高曉聲、白樺、邵燕祥、公劉、劉紹棠、流沙河等,非常值得研究;還有一個“五七”,就是根據“五七”指示,上山下鄉的知青里,涌現出了大批年輕作家,如梁曉聲、王安憶、張抗抗、孔捷生、盧新華等,他們寫出了更多大放異彩的作品,然而也有不少的爭議。社會上對這兩個“五七”的作品都十分感興趣。在廬山,游客和廣大群眾對我們的當代文學會也很好奇。于是會后,我們干脆在廬山正街郵電局坡道口擺了個地攤,專賣那些“重放的鮮花”和有爭議的正式出版的文學作品。我和同事盧啟元兩人大大方方吆喝著,這絕不是為了賺錢,只是為了彰顯新時期文學的新成就、新景象。游客觀眾還真不少,成了當時廬山的一個新景觀,被傳為廬山旅游的一段趣聞:教授山上擺攤賣圖書。
李: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您把主要精力轉移到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領域,從《臺灣新文學史初編》到《世界華文文學概要》,從《離散與文學:陳公仲選集》到《八零后文存》,都是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請您談談當初進行學術轉向的主要原因,以及這一轉向對您后來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哪些影響?
陳:1973年我給工農兵教學,帶了一批學生進行黨史研究,到了秋收起義文家市、武漢等地,出了些關于秋收起義、湘南暴動等的小冊子,直到1977年開始教中國當代文學。之所以研究臺灣文學,因為總覺得講中國當代文學,不講臺灣文學似乎少了一些什么,何況,當時臺灣文學在文壇已經十分火熱搶眼了。艾青曾在我編寫的《臺灣新文學史初編》的序言中說:“中國新文學史,沒有臺灣,怎能算完整,怎不覺遺憾?”
當初廣東、福建、北京、上海一些人已經開始研究臺灣文學,幾次臺灣文學的學術會議促使我們開始研究臺灣文學。以前不知道除了中國大陸以外還有這么一個強勢的文學群體,如王鼎鈞、鄭愁予、洛夫、紀弦、痖弦、白先勇、陳映真、聶華苓、於梨華、陳若曦、余光中、黃春明等,他們在海外文壇名聲和影響已經很大了。
1970年代后期我開始接觸臺港文學,覺得臺港文學很有水平,價值觀、藝術表現手法比較新穎。我邀請他們到江西大學來講學,比如陳若曦、於梨華、施淑青、趙淑俠等。他們來校講演,禮堂被擠得水泄不通,講臺地下也坐滿了人,禮堂窗戶都爬滿了人,場面非常壯觀。我從77級開始,就單獨開設了臺港文學及海外華文文學選修課,并在全校開了跨學科的選修課。每次上大課,一個大教室都擠得滿滿的,后面還站了不少旁聽者。我對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關注主要是來自新鮮感。之前一直覺得很陌生,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另一點就是通過文本分析,深知他們的藝術表現能力、文學功底、文化傳統更接近于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他們又多一重海外文化的熏陶。我認為,一個成功的作家必須要有多元文化的融合,靠單一的文化單槍匹馬地闖蕩,是很難走得堅實穩重久遠的。多元文化的融合發展是一個趨勢,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除了有本土傳統文化,還要吸收西方多元文化的營養。1990年代初,我曾寫過一篇長文《走出西部文學小農意識的陰影》,當時是施戰軍從廢紙堆里發掘出來,在《作家報》刊登了一整版。我對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為代表的西部文學有了一些批評,提出要走出小農意識陰影,要有現代意識、多元文化。莫言就有一個特點,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作家,不懂外語,但他的優點是眼界高遠,讀了很多海外翻譯的文學作品和評論書籍,打開了視野。他是個極具個性的作家,觀點獨特,沒有什么清規戒律。我之所以欣賞海外那些優秀的華文作家,就在于他們價值取向多重豐腴,文學修養深厚,語言文學基礎扎實。能出國留學創業的人才,大多有高學歷,術業有專攻,鳳毛麟角。我是特別關注他們的作品,也熱心與海外高校學術交流,在學術研究上一直盡力保持著新銳超前的年輕狀態。
李:長期以來,學界關于華文文學創作及其研究有不同程度的擔憂和質疑,而有些中國現當文學史著述則把“海外現當代華文文學”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整體研究框架。您如何看待上述擔憂和質疑,以及對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處理方式?
陳:國內搞當代文學的一些人,對海外華文文學不讀又不以為然,認為其水平是二流的,瞧不上。另一個是怕觸到政治敏感問題,采取規避態度。如每年中國小說學會的小說評選,很多人認為海外華文文學不應該參加國內排名,我卻盡力爭取。經過幾年的努力,才取得了共識:海外作家作品只要在國內雜志上發表,在國內出版社出版,就可以參評。條件放寬以后,無記名投票,張翎、陳河、陳謙、沙石、施雨、呂紅、曾曉文、張惠雯等都進入過年度全國小說排行榜。
剛剛講到對待海外文學態度,一是歧視、帶有色眼光,二是政治敏感問題。如何克服這些問題,我看,一是研究機構研究部門要將海外華文文學與當代文學放在同等地位加以認識與對待,要平起平坐,要平等;二是評獎方面、科研經費方面、設置學科方面都要給予支持,對待一些敏感問題要寬容一些。值得欣喜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已開始有所動作了。世界華文文學已列為重點項目,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已被定為一級學術單位(序號:318號)。
李:您認為,新移民文學是世界華文文學的新生長點,它為世界華文文學注入一股新鮮血液,并正逐步形成了一支新生的主力軍。能否請您談談這一新的生長點,它的成就超越了當年的留學生文學嗎?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陳:如今新移民文學肯定超過了當年的留學生文學。我們研究海外華文文學,其實一開始就是從留學生文學起步,但經過這四十年的發展,很多研究現在還停留在過去的水平就不行了。當年研究留學生文學的研究者不是走了就是老了,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到今天大量研究者搞來搞去還是研究陳映真、白先勇,很少聽到研究他人的聲音。陳映真、洛夫走了,耶魯大學的鄭愁予退休多年,可現在與過去相比似乎發展變化不大。而如今新移民文學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超越了留學生文學。當年留學生文學主要思想觀念是鄉愁,表現的是憂傷、失望、痛苦的呻吟。而新移民文學所表現的不完全是這樣,既有鄉愁,也有拼搏與奮斗、信心與希望。在國內文壇一些研究者看來,新移民文學較膚淺,表現不夠深刻,認為在異國土地上扎根不夠,文學底蘊不深厚。其實,這是一種偏見。他們對新移民文學閱讀甚少,知之甚微。新移民文學作家大都有高學歷,語言文字功底深厚。他們既有傳統文化的底蘊,又有海外生活的特殊經歷,還有多元文化熏陶,所以,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文學世界,精彩紛呈,所流露出來的思想情感真切生動。他們對文學是寫人情、人性和人道主義的觀念認識會更為執著深刻。
李: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海外華文作家的創作主要依托國內的發表平臺和讀者認可,能否請您談談這些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寫作和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
陳:這個是絕對有影響的。不少華文作家甚至把在國內發表作品當成了個指揮棒,他們往往揣摩著國內報刊、出版社的意圖喜好來選擇自己創作的題材內容、情節結構、人物形象。很大一部分作者以國內發表出版為榮,以國內發表出版來衡量其創作的成就。這樣就改變了海外華文作家創作的初衷。能在國內發表出版,是很好的選項,但是,這不能是唯一的選項。創作的終極目的,是力求不朽,為廣大讀者,為子孫后代,為人類留下不朽的精神財富,也是對自己一生的經歷,思想情感、夢想追求有一個交代,不要枉度此生。現在,海外華文作家作品也有了新的出路,海外出現了不少民間的報刊、出版社,而且很有發展的勢頭。記住,現在面對發表、出版以至于評獎的誘惑,別忘記作家哈金的一句話:“我們應該直面于不朽!”
李:您認為,作為一門學科建設,世界華文文學已經相當成熟、完整,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大多研究未能突出海外華文文學特點。能否請您具體談談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發展面臨的問題,相關研究應如何突出海外華文文學的特點?
陳:先談談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外部情況。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原來掛靠在中國作家協會,屬于國務院僑辦直接領導,現在統歸中央統戰部統一管理。會長、副會長由統戰部委任,在經費上、人員安排上較之以前更收緊了。所以現在學科研究要有突破發展,則更需要民間力量學術支撐。正如近日我在學會成立二十周年寄語中所講,要突出我們學會的民間性、學術性。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科建設發展主要從民間性、學術性出發來發展,不管外面如何,仍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李:您從事學術研究已經超過一個甲子了,至今仍然手不釋卷,樂此不疲。是什么讓您始終保持這樣的學術熱情?能否請您談談在治學之路上對您產生重要影響的學人和著作?回顧過往,您對自己的學術人生有哪些感到欣慰或者遺憾的地方?
陳:保持學術熱情主要是將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要保持自己生命的延續就是要頑強地工作下去。對我來說,就是要不斷地讀書、思考、寫作下去。現如今有種觀點是:年紀大了,需要注重保養,少管閑事。可我以為要有事干反而更能延年益壽。現在老年人一起來就有人攙著,一走路就有人扶著,這樣是不可取的,就應該像訓練小孩一樣,讓他自己走動起來。搞學術也是如此,有學術研究就有了活力,腦子也不至于癡呆。學術寫作已經成為我生命當中的一部分,無法割舍,因此才能時時新鮮,永葆青春。
我在治學道路上受到重要影響的主要有一些傳統的文藝觀念,如恩格斯的論著。恩格斯對文學創作主張“典型環境中典型性格”以及“作品的傾向性越隱蔽越好”,而不是搞什么“三突出”,不是搞“主題先行”。我認為恩格斯的觀點沒有過時。另外當年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妥斯陀耶夫斯基三個“斯基”的文學觀念對我還是有較大影響。在論著上,對我有影響的有觸動的是夏志清。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這部書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這部書實際上是夏志清在耶魯大學的英文博士論文。1987年我到美國,有幸與他交談,他送了這本書給我。這本書對我影響比較大。他的書突出了張愛玲,對張愛玲有些偏愛,也說明張愛玲作品有她自己的特色。其次就是沈從文、錢鍾書以及張天翼。對這些人的研究與評價與國內非常不同,他的價值觀以及評價手法對我影響比較大。我后來創作的幾本文學史書是受了他的一些影響的。
令人欣慰的地方,首先是我覺得當代文學的幾個“史”差不多都搞全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編》《臺灣新文學史初編》《世界華文文學概要》,這三本書基本上囊括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反響較好。《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編》銷量突出。馮牧在《文藝報》上撰文認為《臺灣新文學史初編》“在同類書中,屬上乘之作”。《世界華文文學概要》已有了國際影響,我在韓國開會,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說,我們還在用這本書作教材呢。第二個值得欣慰的是在國內對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以及新移民文學的研究做了一份應有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先后開了三個大型的國際會議,把歐美澳及東南亞的主要華文作家都聚集一堂,共商發展華文文學之大事,結集出版了三本文集,在全球有著一定的影響。第三個成就感就是參與主持了六個重要的文學會議:一是1980年的全國文學理論研討會;二是1981年的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三是1993年的第六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正式將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定名為世界華文文學,是華文文學研究公認的一個轉折點、里程碑;四是1997年中國小說學會全國年會(會上我被選為小說學會副會長);五是2010年在南昌舉行的首屆中國小說節;六是2014年首屆新移民文學研討會。
遺憾的是后繼乏人。20世紀80年代,華文文學研究盛況空前,華文文學研究成為我們學生畢業論文的熱門選題,但近些年來研究者日漸減少。研究不是追求熱鬧,而應該追求不朽。有些學者認為華文文學必死無疑.一些海外二代、三代移民慢慢失去了母語,華文文學創作和研究只能依靠老人,目前可以說是日漸式微,但還不能認為必死無疑。因為移民是一代一代前赴后繼,不會中斷的。有新生代移民,就必然有新移民文學。以新移民文學為主體的華文文學,前途是光明的,不必悲觀。世界華文文學必定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但需要有更多人的堅持不懈。眼下困難還是蠻多的。但有億萬華人為后盾的華文文學絕不會死,只是有些時候可能會寂寥,有起有伏,有高潮期也有落潮期,這是正常的現象。
李:長期以來,您一直呼吁學界以更多的熱情關注海外華文文學,鼓勵年輕學者從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作為前輩學人,您對將要或正在從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年輕學者有些什么建議?
陳:研究者要耐得住寂寞,要堅守不移。賺錢是不可能的,搞文學事業本來就是孤獨、寂寞、清貧的,要有堅守的犧牲精神,要追求不朽。
李:作為一名扎根于贛鄱大地的著名文學評論家,您在從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同時,也長期關注江西本土文學創作狀況,撰寫了大量關于江西作家創作的評論文章。能否談談您對近年來江西文學創作的印象及其未來發展的期待?
陳:江西文學事業自古以來是非常發達的。民國時期梁啟超曾說,中國文學最突出的兩個省是江西與四川。新中國成立后,江西有突出影響的作家不多。有位江西大學的前輩胡曠,代鄧洪寫了個《潘虎》,全國影響不小,號稱是“中國的《夏伯陽》”。戲劇創作上有石凌鶴,小說創作有陳世旭《小鎮上的將軍》。改革開放以來,江西大學有“三胡一相”(胡平、胡辛、胡金岱與相南翔),我在《光明日報》上戲稱為“三只老虎、一頭大象”。現在年輕一代有位阿袁,是全國難得的一顆文壇新星。
江西創作要發展,就要走出二三流城市的局限,正如我寫的電視劇《井岡之子》中的人物獨白:“該下山了,外面還有更廣闊的天地與巨大的海洋。”江西應該要有個“下山意識”,要視野更開闊,看看外面的風景,面向更廣闊浩渺的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