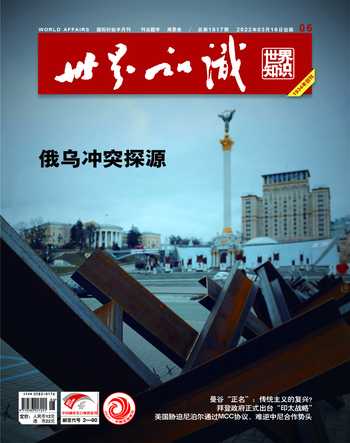烏克蘭危機是能源權力轉移的實驗室

牛新春
隨著全球能源轉型的不斷推進,能源權力的轉移不可避免。但是能源轉型是個長期、緩慢甚至反復的過程,難以確定一個清晰的起點和終點,與之相伴的權力轉移亦是如此。實際上,石油權力的轉移早就開始了,但是人們的認識似乎還停留在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運時期。
1960年代,隨著石油國有化運動的開展,石油權力從西方大石油公司轉移到產(chǎn)油國政府手中。1973年阿拉伯產(chǎn)油國對一些美歐國家實施石油禁運,收到了政治、經(jīng)濟效益雙豐收的效果,既迫使美國做出政治讓步,又讓油價長期處于高位。這次石油危機產(chǎn)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以至于今天國際社會仍然普遍相信石油權力還掌握在產(chǎn)油國手中。
而事實上,隨著石油消費峰值的來臨,現(xiàn)實中的石油權力正從產(chǎn)油國轉移到消費國,這是石油權力的范式轉變。1973年以后的“石油制裁”大都是消費國對生產(chǎn)國的制裁,從未發(fā)生過生產(chǎn)國對消費國的制裁。特別是2017年以來,美國對伊朗、委內瑞拉、俄羅斯三國實施了程度不同的石油制裁,而這三國的石油產(chǎn)量占到全球的六分之一。對比1973年阿拉伯產(chǎn)油國對美國的制裁,這真是天翻地覆的變化。過去,能源安全是指消費國獲取石油的可靠性;未來,能源安全可能指產(chǎn)油國獲得市場的穩(wěn)定性。然而,這些案例似乎并不足以改變國際社會的傳統(tǒng)看法。原因是,這些案例的說服力不夠,因為制裁者與被制裁者的地位不相稱,不是消費者與生產(chǎn)者之間旗鼓相當?shù)妮^量。而這一次烏克蘭危機引發(fā)的能源權力博弈則完全不同。
俄羅斯是全球數(shù)一數(shù)二的油氣生產(chǎn)大國,2021年俄羅斯原油產(chǎn)量排名全球第三,天然氣產(chǎn)量排名第二;俄羅斯也是油氣出口大國,2021年俄羅斯石油出口量全球第二(居沙特之后),天然氣出口量全球第一。歐盟則是全球最大天然氣消費區(qū),第二大石油消費區(qū)(僅次于美國);歐盟也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氣進口區(qū),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僅次于中國)。更重要的是,歐盟與俄羅斯在能源上高度相互依賴,歐盟是俄羅斯能源最大的市場,俄羅斯是歐盟能源進口最主要的來源。2020年歐洲25%的進口石油來自俄羅斯,38%的進口天然氣依賴俄羅斯。2019年歐盟市場占俄羅斯天然氣出口的81%,2020年占48%,歐盟市場占俄羅斯石油出口約的50%。
顯然,同美西方對蘇丹、伊朗、委內瑞拉等國家的制裁不同,這是全球最大體量的能源生產(chǎn)者與消費者的博弈,是驗證能源權力轉移難逢的自然案例。
迄今為止(3月2日),歐俄雙方對動用能源制裁都非常謹慎,但種種跡象顯示,如果從零和博弈角度看,歐洲處于優(yōu)勢地位,騰挪空間較大。俄羅斯官方只字未提能源制裁,相反普京一再強調,俄羅斯不會切斷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事實上,盡管烏克蘭戰(zhàn)火紛飛,天然氣費用支付困難重重,但途經(jīng)烏克蘭的天然氣管道仍然正常供氣。歐盟也明確把能源交易排除在金融制裁之外,以確保當前的供應不中斷。但是,歐盟已經(jīng)禁止投資俄羅斯能源產(chǎn)業(yè),英國石油公司等美歐大公司宣布從俄羅斯撤資,德國宣布暫停北溪2號項目,未來將把俄羅斯天然氣進口量降低一半。美國則強調,對俄羅斯能源制裁的選項一直在桌子上。可以說,美歐已經(jīng)動用除切斷現(xiàn)貨供應外的其他一切制裁措施。
俄歐之間不論誰制裁誰,經(jīng)濟上都是雙輸。短期內,俄羅斯找不到新買家,歐盟找不到新貨源。正如國際能源戰(zhàn)略專家陸如泉所言,跨境天然氣交易是一種集“氣源—渠道—消費市場”為一體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五到十年的時間構建,一旦建成則很難輕易放棄,因為替代成本較高。同1973年的情形不同,目前國際能源市場供應寬松,若假以時日,歐洲可以適應沒有俄羅斯天然氣的狀況。如果真有能源制裁發(fā)生,短期內雙方都有困難,長期看俄羅斯困難更大。
2021年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為72%,其中50%來自中東。石油依賴到底是中國中東政策的資產(chǎn)還是負債,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中國中東政策中最重要的問題。這次烏克蘭危機可能會提供一些理解問題的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