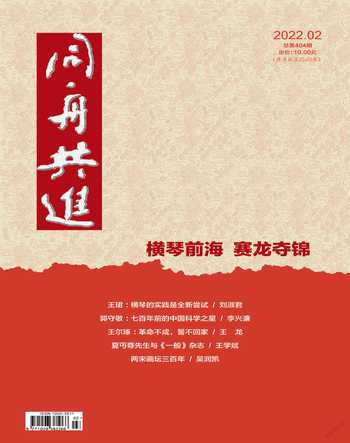夏丏尊先生與《一般》雜志
王學斌
1925年至1927年,被著名出版家張靜廬先生稱之為“新書業的黃金時代”。這期間,有一位生性謙遜的浙江讀書人默默耕耘,成為影響了萬千青年讀者的教育家、出版家。這位學人是夏丏尊先生。
“五四”前后,夏丏尊執教于浙江第一師范,與陳望道、劉大白一道聲氣相求,共同促使新文化之風揚播于江浙教育界;其后,夏追隨經亨頤,在白馬湖畔共建春暉中學,推行男女同校新式教育,并與豐子愷、朱自清、朱光潛等人形成了頗有影響的“白馬湖文學”;上世紀20年代中后期,夏輾轉到上海,與匡互生在上海江灣創建立達學園,并初涉出版界,將《一般》雜志辦得有聲有色,可謂在教育和期刊方面的雙重試驗。
1925年,春暉中學風波后,夏丏尊離開白馬湖去了上海。這時,先前抵滬的匡互生遂出面邀請夏及胡愈之、周予同、劉大白、夏衍、章錫琛、朱光潛、豐子愷等組織“立達學會”,并提議創辦“立達學園”,經過學會協商同意,立達學園遂從此誕生。
在立達學園期間,除去日常教學,夏丏尊與同仁們一道承擔起編輯學會刊物《一般》的重任,這也成為其出版家生涯中頗為重要的一段經歷。
作為《一般》的創辦者,立達學人是一群志趣相投的同志,他們兼有教育家、文學家、出版家的多重身份,也接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立人”的思想貫穿于他們的教育、創作及出版等文化活動中。在教育上他們主張“人格教育”;在文學上,相比“以破為立”的主張,他們持相對溫和穩健的文化立場,反對“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堅持平民的寫作立場。當時貌似刊物品種繁多,思想界各種主義盛行,實際上卻讓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學生有些無所適從。《一般》雜志同人也批評出版物雖各有門類,卻與一般人不十分相關。“雖洋洋大文,但是比學校里的課本還難懂,并且與一般人的生活上無直接關系,因而總不十分發生興趣”,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般》雜志創刊,展現了他們的時代擔當。
《一般》的刊物定位十分明確,就是一本針對青年的雜志。創刊號由夏丏尊親手題字設計,封面插畫則由豐子愷繪制完成。在夏丏尊擔任主編的時期,豐子愷負責裝幀設計,同時方光燾、胡愈之、葉圣陶、劉薰宇、劉叔琴、鄭振鐸等擔任責任編輯。
之所以取名為“一般”,是含有“平常、普通、平凡、大眾”之意,“一般的人,寫一般的文章,面向一般的讀者”。并且《一般》雜志的第一期,沒有沿用其他刊物慣用的“創刊號”一詞,而是別出心裁地取名“誕生號”。“誕生”一詞有特殊含義,實則與《一般》同人的教育理念相似,他們認為教育需具備連貫性,正如匡互生所言:“一個人如果能從進幼稚園起至入大學為止,在一個學校中,只要學校辦的好,他所受的影響一定會比進四五個學校好些。”葉圣陶也認為:“改革教育的意識不能不從早喚起,改革教育的工具不能不從早準備。”《一般》同人希望《一般》就如一個在他們手中呱呱墜地的嬰兒,通過對其精心呵護、認真培養,最終能夠茁壯成長、大樹參天。
同樣值得注意也頗耐人尋味的是,《一般》的發刊詞,由夏丏尊擔綱撰寫,發刊詞寫得不落俗套,通過隨性的對話形式展開,向讀者展現了《一般》創辦的目的、宗旨、趣味化及特色:
“好久不見了,你好!”
“你好!”
“聽說你們要出雜志了。真的嗎?”
“真的。正在進行中。”……“你喜歡看雜志嗎?”
“看呢……我雖也入過學校,但并無專門知識,雜志中的洋洋大文,覺得比學校里的課本還難懂,并且似乎與我們一般人的生活上,也無直接關系,所以總不十分發生興味。”……“那你們的雜志,將來屬哪門類呢?”
“想并不拘于哪一門類,只做成一種一般的東西。”
“那么,你們的主張怎樣……你們預備取哪一條路?”
“我們也并不想限定取哪一條路,是給一般人作指導,救濟思想界混沌的現狀。”
“注重研究學術嗎?”
“當然,不過我們想和人家方法不同一些。要以一般人的寫實生活為出發點,介紹學術,努力于學術的生活化。”……“我們將來想注重趣味文學作品不必說,一切都用清新的問題。力避平板的陳套,替雜志界開個新生面。”
“很好,那將來這份雜志取什么名稱?”
“就叫做一般……我們無甚特別,只是一般的人,這雜志又是預備給一般人看的,所說的也只是一般的話罷了。”
正如夏丏尊所言:“《一般》的目的原想以一般人為對象,以實際生活出發來介紹些學科思想”,“用清新的問題,致力于學術的生活化”。《一般》的讀者針對性很強,是給那些上過學校但并無專門知識的,或接受中低等教育的學生傳播新知,普及文化,提高修養的社會讀物。這樣的辦刊定位與《一般》同人的文化理念是一脈相承的,正像夏丏尊所說的“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東西都有大的涵義”,“人生不單因了少數的英雄圣賢而表現,實因了蚩蚩平凡的民眾而表現的”。
當然,《一般》的從無到有,并非夏丏尊一人之功。以夏為首的《一般》同人乃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們在教育、出版、作家等職業中自由穿梭,在每個崗位上肩負文化啟蒙、社會批評的重責。在出版崗位上,夏丏尊等同人所秉持的是精英趨向的理念。首先,《一般》雜志不看重出版的商業性,顯示其重在強調“開啟民智”的姿態,夏丏尊就認為出版事業應是“傳達文化,供給精神食糧為職志”。以此之故,夏丏尊等人就看不上當時上海另一份以通俗文學為特色的刊物《禮拜六》。夏氏用“閑暇”“消遣”來形容《禮拜六》,用叉麻雀、逛游戲場來類比之,這正是對商業性運營的《禮拜六》等雜志的否定。
其次,夏丏尊等同人自身皆是義務寫稿,義務編輯。章克標曾回憶道,為《一般》寫稿的大都是立達學會會員,不取稿酬,當編輯也是義務的。沒有稿費自然受限于雜志的經濟條件,同時也彰顯了夏丏尊等人將文化信念置于經濟利益之上的態度。
《一般》雜志的欄目設置,經過眾位學者的精心設計與策劃,體現出濃厚的“一般”風格或“夏氏”風格。
作為《一般》的招牌欄目,“論文”欄目刊登的文章內容豐富,涉及面頗廣,包括社會問題、科學知識普及、青年教育、學術研究性論文等內容。青年教育的文章在論文中占有較大的比重,這與《一般》同人重視青年學生的教育是分不開的。內容涉及青年的生活教育、審美教育等諸多方面,包括朱光潛的《寫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這十二封信在雜志上連載,對青年讀者的影響很大,就連夏丏尊也大力稱贊,創刊以來“這十二封信是最好的收獲”。豐子愷對青年審美教育更是不遺余力,在雜志上發表了30余篇的審美文章,對中西方的美術、音樂等內容作了詳細的介紹。
夏丏尊在雜志編排上有意呈現出對讀者進行思想啟蒙、知識普及及創作互動的特點。就創刊號來說,編排的文章既有貼近讀者實際生活,對其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的《青年底生活問題》,亦有補充讀者課外閱讀知識,供給科學養分的《趣味豐富的秋的天象》,還有增長讀者見識,拓寬視野的《旅英雜談》,更有供給文學知識與趣味的小說,這種短文雜排的方式有利于讀者對文化知識進行綜合、全面的吸收。
創設的“書報評林”與“介紹批評”欄目,加強讀者在選擇書目時的針對性與有效性,讀者與作者欄的編排,有利于讀者與作者有效的溝通互動。總之在編排的量上以及質上,夏丏尊曾多次坦言自信“無愧于讀者”。
此外,文畫結合的編排設計更能充實雜志的面向,豐富與詳實內容,吸引讀者的眼球,增加閱讀的趣味性。夏丏尊等人極其重視插圖的效果,增加插圖在內容上增加豐富性,在形式上增加藝術性,這當然也是忠于讀者意識的一種體現。
同時在雜志內容設置上,夏丏尊準確把握了讀者的閱讀心理。鑒于雜志界“洋洋幾千大文,卻與一般人不相干”的現象,夏丏尊在內容選擇上特別強調了“注重趣味文學作品”和“力避平板的陳套”。具體來說,針對科學、學術性文章,夏丏尊等人力求將其生活化、普及化,在這一方面《一般》同人撰寫的文章居多,如匡互生《趣味豐富的秋的天象》、豐子愷的《秋的星座及其傳說》、夏承法的《關于真空》等文,皆是用樸實的筆調,深入淺出地介紹科普知識。
如豐子愷在介紹《秋的星座及其傳說》中,從自己與小女兒阿寶關于星星、地球是什么的對話切入,用故事敘述性的語調解釋各個星座。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言,他只是“一般的人”,只愿講“一般的話”。在與讀者的溝通中,夏丏尊等以親切的稱呼與讀者產生共鳴,如在誕生號介紹以及《寫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諸多同人文中,皆以“朋友”稱呼讀者,專門于文末署“你的朋友”,這顯然是一種平易近人的談話風格,如春風化雨般滋潤青年——用讀者熟悉的口吻、習慣的方式、親切的稱謂,傳播最急需的知識與思想,這就是夏丏尊推廣新知的獨特方法。
人格教育、平民意識是《一般》貫徹其中的兩條思想主線。雜志同人中夏丏尊、豐子愷、劉叔琴等大部分都有海外的留學經歷,在對待師生關系上,并沒有遵從傳統的“師徒如父子”的森嚴等級界限,他們拆解了二者間的藩籬,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師生交往。在《一般》同人的創作中,隨處可見他們和青年學生的平等關系,如葉圣陶所言:“這個‘朋友’不是一種浮泛的稱謂,欲表示我們真心誠意的把諸君認作朋友。”同樣的話夏丏尊也表達過,他在評價朱光潛寫給學生的十二封信中說:“信中首稱‘朋友’,末署‘你的朋友’,在深知作者的性行的我看來,這稱呼是籠有真實的感情的,決不只是通常的習用套語。”
《一般》中另外一個平民意識的思想特征,是以夏丏尊為代表的學人們長期堅持的創作與編輯理念與立場。《一般》同人不僅自己構筑平民的社會角色,同時他們還號召社會去關注平民,過平民的生活。朱自清呼吁:“文人得做為平民而生活著,然后將那生活的經驗表現出來,傳達出來。”朱光潛在給青年學生的信中,也號召青年學生不要顯擺知識分子的臭架子,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到民間去。俞平伯更是指出要成為平民詩人就必須實現平民的生活,做平民的詩。
具體到文學寫作層面,他們的平民化體現在情感上與平民達成的共鳴,他們的作品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設計,也沒有義憤填膺的激烈言辭,而大多取材于生活瑣事,用真摯的情感、質樸的語言書寫生活中的不平、悲憤。他們主張“文學應當反映社會的現象,并且討論人生的一般問題”,從這一點上來說,是非常容易與平民階層產生共鳴,實現心靈真誠溝通的。
然而,《一般》雜志在發行的過程中,已隱伏了由盛及衰的因素,1929年底,在刊行第36期后戛然而止。細究起來,停辦的原因第一是人力、財力不足。創辦之初,夏丏尊等人干勁十足,并為《一般》勾勒了理想的藍圖,而就在雜志出版三期后,同人之間已漸生力不能支的感覺。夏丏尊也“自認不是辦雜志的人,姑且拼了命做去再說吧”。
人力不足,財力有限,于是乎稿源也不可能源源不斷。魯迅也認為《一般》的主編“對于稿件的錄用并不輕松”,因而“它發表的作品都在水準之上”。如夏丏尊原準備將第二卷第一號即新年號出成擴大版,但因“征到的新年稿件不多,把別的普通稿件充積進去呢,也覺得無甚意味,結果只仍出了這樣的一冊”。這里固然體現“寧缺毋濫”的態度,同時也緣于他們對稿件質量的把控相當嚴格之故,稿源自然捉襟見肘。
不過以上原因似乎不是《一般》雜志最終消失的主因。作為知曉內情之人,章克標似乎道出了其中主要的緣由:
開頭,開明書店的出版方針不明確,直到1930年才決定以中學生為對象的青年讀物為主再加中學教課書,因之決定了出版《中學生》雜志……同時,又將《新女性》及《一般》兩雜志停刊,以集中力量,這都是出于章老板的決策。那是因為開明資力有限不能兼顧之故。
這中間,開明書店在出版方面逐漸摸索出了一條路子,想要除文藝一般之外,采取以中等學生的課外讀物為重點,更進一步出銷行數量大的教科書,因而要先辦一份給中學生看的雜志來開辟道路。就直截了當取名叫《中學生》雜志了。這樣就把《一般》停了,因之,也可以說《中學生》是《一般》投胎轉化而來。
因而,《一般》驟然停刊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中學生》雜志的替代。其實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生雜志旋起旋滅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大概因為資金難以支撐事業,或是內部人員辦刊理念不合,也有如《一般》這樣,被其他的雜志所取代。
《一般》同人作為一群極具教育理想及文學關懷的知識分子,他們依托雜志,在文學教育上提倡人格教育,注重人格感化,普及知識,啟蒙大眾,立足民間,關懷青年,與平民腳踏實地,共同致力于培養具有“立人達人”的健全人格的人,實是一群不“一般”的人,這份雜志在那個時代也實在不一般。
在20世紀20年代,《一般》同人為當時的文化界注入了一股別樣的清流,只有充分體會以夏丏尊為代表的《一般》同人的堅持與信念,才能理解他們將文學教育作為終身的事業,真正懂得他們為新文學新教育所做的努力與貢獻。
濫觴于白馬湖畔,發展于立達學園,成熟于上海開明書店,正是基于對出版事業的熱衷與身體力行,才使夏丏尊成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