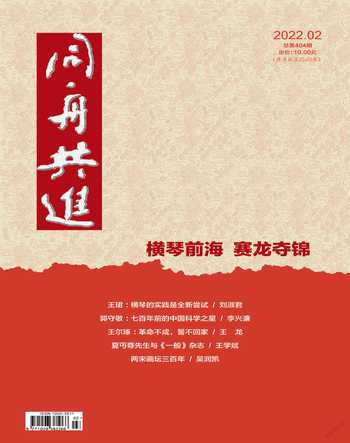郭守敬:七百年前的中國科學之星
李興濂
郭守敬,字若思,邢州邢臺縣(今河北省邢臺市)人,元朝天文學家、水利學家。1970年,國際天文學會將月球背面的一座環形山以“郭守敬”命名。1977年7月,經國際小行星組織批準,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把1964年發現的太陽系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郭守敬”。
郭守敬少有奇志,不喜玩樂,對數學、天文、水利有著濃厚興趣。少年時代的他,曾根據書上的一幅插圖,用竹篾扎出一架渾儀,還做了一個土臺階,把竹制渾儀放在上面,進行天文觀測。他還根據北宋科學家燕肅拓印的石刻蓮花漏圖,弄清了這種在當時最先進的計時儀器的工作原理。
郭守敬十多歲時,祖父郭榮聽聞好友、大學問家劉秉忠因守父喪,正在邢臺西南的紫金山中結廬讀書,便把郭守敬送到劉秉忠的門下。劉秉忠也是邢臺人,郭守敬在他的指導下,專心地學習了三年,還結識了學者張文謙、張易、王恂等人,他們聚在一起研究探討天文歷法等,時人稱之為“邢州五杰”。后來,劉秉忠、張文謙和張易都成為元朝的開國重臣,對郭守敬的事業多有提攜,王恂則成為郭守敬終身摯友和同事,在《授時歷》的編制工作中,王恂的貢獻與郭守敬齊名。
中統三年(1262年),張文謙向忽必烈推薦了郭守敬。郭北上應召時,把剛鑄好的一套蓮花漏運到燕京,取名為“寶山漏”。這套計時器構造精巧,水流均勻,計量時間很準確,后來成為元代司天臺(即國立天文臺)的計時工具。
在邢臺縣的北郊,有一座石橋。金元戰爭時,這座橋被毀壞了,橋身陷在泥淖里。日子一久,竟沒有人說得清它的所在。郭守敬勘察了河道上下游的地形,對舊橋基有了判斷,根據他的指點,一下就挖出了被埋沒已久的橋基,此事在當地引起了不小轟動。石橋修復后,四方游民紛紛歸附,邢臺戶口增加了十倍。當時的文學家元好向還特意為此寫過一篇碑文——那一年,郭守敬剛剛20歲。
元朝初年的歷法是遼金以來的歷法,已經使用了200多年,誤差很大。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決定設立“太史局”,重新修訂歷法,并任命郭守敬和王恂率領南北觀測天象的官員進行觀測和推算工作。
在觀測天象中,首先需要解決儀表問題,郭守敬創制了簡儀、高表、候極儀、立運儀、仰儀、景符、窺幾等16種儀表,數量之多、質量之精巧準確都超過前人。簡儀中使用了滾柱軸承,西方的類似裝置,是在200年后才由達芬奇發明出來。
郭守敬在景苻、仰儀等儀器中運用了“針孔成象”的原理,這在中國光學史上是罕見的成就。300年后,利瑪竇在南京看到這幾件明初時從北京運到南京的天文儀器,贊嘆說:“其規模和設計的精美遠遠超過曾在歐洲看到和知道的任何這類東西。這些儀器雖經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氣變化的考驗,卻絲毫無損于它原有的光榮。”
郭守敬、王恂與尼泊爾建筑師阿尼哥合作,在大都興建了一座新的天文臺,這是當時世界上設備最完善的天文臺之一。郭守敬用創制的天文儀器進行了許多精密的天文觀測,從而使《授時歷》的編制有了可靠的觀測基礎。他測出一個回歸年數值為365.2425日,并派出14個觀測隊,到全國27處地點進行了天文觀測,史稱“四海測驗”。
郭守敬從上都、大都開始經河南轉抵南海,跋涉數千里,親自參與其中。他根據“四海測驗”的結果,參考了一千多年的天文資料,七十多種歷法,按照日月五星在太空運行的自然規律,終于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編制成新歷法。
忽必烈對新歷法極為滿意,他按照《尚書·堯典》中“敬授民時”一語,將新歷法定名為《授時歷》,此后通用了360年。《授時歷》推算出一個回歸年為365.2425日,即365天5時49分12秒,與地球公轉的實際時間只差26秒鐘,和現在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歷》(比《授時歷》晚了三百多年)的周期一樣。
從20歲開始邢臺治水,郭守敬的宦海生涯中2/3的時間都奔波在水利工地上。元世祖中統三年(1262年)春,張文謙向忽必烈推薦郭守敬,郭一連提出六項水利工程計劃。忽必烈當即任命郭守敬為“提舉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次年,他又被升任為副河渠使。元朝北部地區的水利建設和南北大運河的貫通,基本上都是郭守敬的功勞。其中,最能體現郭守敬非凡才能的工程,是修復西夏水利和開鑿通惠河。
西夏水利是指原西夏興慶府(今寧夏銀川)一帶黃河兩岸的水利設施。早在秦漢時,這一帶就開鑿了許多河渠系統,引入黃河水灌溉,成為西北地區的重要糧倉。但在蒙古滅西夏戰爭中,水利設施損壞殆盡,致使九萬多頃良田荒蕪。
1264年,郭守敬在西夏深入考察實地資料,親率民工開挖疏浚,對原有的正渠、大小支渠“因舊謀新,更立閘堰”,使之煥然一新。整個工程在地方官民的支持下,不到一個季度就完成了。數萬項農田得到了及時灌溉,渠水四達,稻菽豐收,使西夏再現了“塞北江南”的景象。當地人為此建立了“郭氏生祠”,并立碑以紀其事。
1265年,郭守敬自西夏返京途中,乘舟順黃河而下,行至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發現此段河可通漕運。他還考察了査泊、兀剌海一帶,認為這里的許多古渠修復后可再用。兩年后,忽必烈采納了郭守敬的建議,下令在此段黃河中開辟漕運,設置水上驛站,方便了西夏糧食外運,加強了西夏與元朝中央的聯系。這一年,郭守敬被任命為都水少監,協助都水監掌管水利工程。
從西夏回來后,郭守敬開始著手解決大都漕運的問題。由于設計周密科學,開挖的河道經受了多次洪水的考驗,成功地使用了近三十年,特別是通過這些河道將西山大量的石料、木材運抵城內,有力支持了元大都的建設。但因通州地勢較低,大都附近水源有限,不能負擔起運河水量,郭守敬經過反復實踐,設計出一套復雜而又精巧的水利系統。1293年,總長160多里的京通運河終于開通,實現了從杭州至大都的全線通航,漕運的糧食由每年幾萬石猛增到一百幾十萬石。忽必烈欣然將其命名為“通恵河”——郭守敬治水成功,才有了北京城700多年的定都史。
此外,郭守敬還開建了甕山泊、積水潭兩座水庫,使運河中的水位保持相對穩定的高度。為使引水平緩東流,保證漕運水量,郭守敬在運河上每十里設一閘,這些閘壩解決了因地勢落差大,水流容易一泄而過的難題,使運河保持了足以行舟的水量。這一創舉是郭守敬在水利史上的奇跡,如今的巴拿馬運河、長江三峽、葛洲壩等水利工程,仍采用這種方法解決行船的航運問題。郭守敬還提出以海平面作為基準,比較大都和汴梁兩地地勢高低的差別,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海拔”的概念;他還曾溯黃河而上探尋黃河發源地,由此成為科學考察黃河源頭的先驅者。
1298年,元成宗要在上都西北鐵幡竿嶺下開渠,郭守敬經過實地勘查,了解到該地雨量集中,易發山洪,建議修建50至70步寬的大渠,然而,主管此事的官員認為沒有必要,施工中把寬度縮小了1/3。次年,大雨驟至,山洪溢出河渠泛濫成災,淹沒人畜、田地無數,差點沖毀了皇帝行宮。元成宗不得不避水而走,他對大臣感嘆:“郭太史真神人也!”后來元成宗下詔,官員年滿70才可以退休,但郭守敬不能退休,此后元朝形成了天文官員不退休的制度。
郭守敬的一生,歷經四朝皇帝,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為我國的水利和天文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