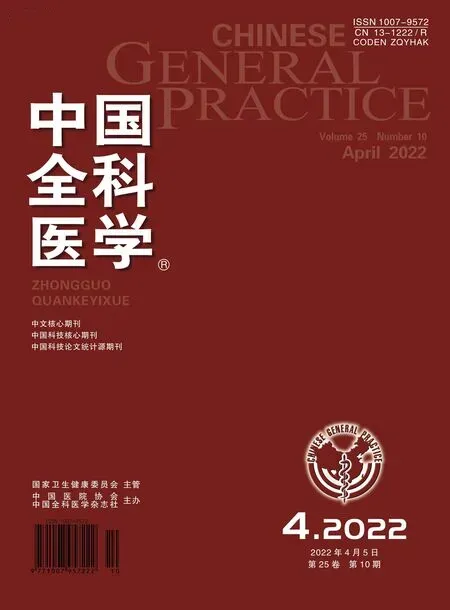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的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影響因素及其組合路徑分析
張敏,張淑娥,時宇,王鴻妮,紀科宇,程偲雨,趙鑫,孫濤*
地方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建設是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徑,地方政府創新則是國家治理體系演進與躍遷的原始動能。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創新研究一直是政治學界與公共行政管理學界頗為關注的議題。近年來,衛生改革與政策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地位與價值日益提升。其中,縣域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改革與建設是我國深化醫改的重要舉措,亦被地方政府納入重要民生工程。2019年5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印發《關于推進緊密型縣域醫療衛生共同體建設的通知》,明確了縣域醫共體建設的工作目標[1]。近年來,隨著醫改的不斷深入,縣域醫共體建設已經步入了“加速期”[2]。多地圍繞醫共體改革進行了積極探索與實踐,例如安徽、浙江、內蒙古、山西等地涌現出了多樣化的、地方政府主導的縣域醫共體建設創新舉措,尤其是政府創新過程中多因素的交錯互動[3]衍生了天然的“政策實驗田”[4]。地方政府作為推進地方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關鍵行動者,如何實現治理過程的創新成為檢驗其治理成效的關鍵。
地方政府創新的動因和影響因素具有復雜性和動態性[5]。我國地方政府創新的基本動因可分為直接動因和間接動因兩個方面,既存在于客觀的制度環境(生態視角)之內,又存在于主觀的內在需求(組織困境視角和利益視角)之中[5],如基層社會的壓力[6]、地方政府間競爭的需要[7]、民眾認同的需要、官員政績的需要[7]、地方官員的個性[6]等。不同地區的地方政府囿于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社會環境、民族文化等因素,其創新動力亦存在差異[8]。陳朋[9]通過對影響地方政府創新的因素進行全面探索,發現影響地方政府創新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結構化因素”(如區域發展水平、府際競爭)、“個體化因素”(如地方官員的主動作為)及“事件性因素”(如危機的現實“倒逼”和宏觀政策的潛在引導)等層面。
認真梳理后,發現學術界雖然承認地方政府創新受多種因素影響,但鮮有學者從整體視角研究各因素與地方政府創新實踐之間的因果關系,并探討地方政府創新影響因素的組態效應。為豐富衛生政策研究中地方政府創新研究的話語譜系,提高地方政府創新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本文以中國醫院協會醫共體分會于2020年舉辦的第二季“尋找縣域醫共體實踐價值案例”評選活動的初選結果(14個案例樣本)[10]為基礎,基于組態視角,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csQCA)法,對縣域醫共體政策創新的類型及影響因素的交互作用進行探索性解析,分析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生成原因和機制,旨在為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中的因果關系提供參考性解釋框架,并推進地方政府創新研究的本土化理論構建。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方法的選取 本研究是將定性比較分析(QCA)引入醫共體創新實踐領域來分析地方政府政策創新影響因素的一次探索性嘗試。QCA以案例為導向,被廣泛運用于跨案例比較分析中,不同于傳統研究方法只關注單一的因果模式,其更關注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即多重并發因果關系[11]。QCA將來源于真實案例的證據與理論上可能產生結果的因果組合進行系統的比較[12-13],旨在實現將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優勢進行整合。考慮醫共體創新實踐具有“多因素復雜并發”的特征,故本研究選擇QCA作為研究方法。QCA共有9個關鍵步驟,在具體運用過程中形成了csQCA、模糊集分析(fsQCA)、多值集分析(mvQCA)3項分析技術[14]。基于文獻回顧和研究主題特點,本研究采用csQCA法對數據進行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從研究對象特點來看,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是多因素參與的復雜過程,通過csQCA可挖掘出多種前因條件組合與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之間的聯系,有助于解釋區域間地方政府創新差異的形成機制,可為各地提升醫共體創新績效提供可行性建議;第二,從研究樣本特點來看,本研究以14個案例樣本為研究對象,樣本數量較少,故不宜進行大規模的統計推斷,而csQCA作為一種案例導向的研究方法,在中、小規模樣本處理中更具優勢;第三,從研究變量特點來看,本研究探索的是可能的影響因素對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是否起到了推動作用,結果變量、條件變量均屬于二分類變量(非連續型變量),而csQCA主要用于二分類變量資料的分析[11]。
1.2 案例樣本的選取 在使用QCA法時,案例的選擇需要考慮研究的實際需要、案例結構的清晰性、案例背景特征的相似性及案例的可得性等因素。QCA結果的穩健性主要取決于樣本是否具有代表性[15]。本研究以中國醫院協會醫共體分會于2020年8月舉辦的第二屆“尋找縣域醫共體實踐價值案例”評選活動的初選結果為案例源,案例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案例庫包含14個不同地域、不同創新主題的樣本,滿足了多案例比較分析時樣本需多樣化的要求。14個案例分別來自黑龍江、山西、浙江、內蒙古自治區等9省份下轄的5個縣級市、1個區、8個縣,樣本覆蓋了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部地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創新成果涵蓋黨建、醫保改革、管理、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等方面,可體現不同區域、城市縣域醫共體探索與實踐的差異性,見表1。

表1 本研究納入的14個縣域醫共體實踐價值案例Table 1 The 14 value cases of practice of county medical community included in our study
1.3 變量的選取與編碼 于2021年3月,通過瀏覽政府網站上的公開信息、電話問詢、利用各搜索引擎查閱官方新聞與官方媒體報道等方法,準確獲取編碼所需數據。根據文獻和案例背景建構編碼的標準和結構。編碼結果由課題組的2名研究者共同認定,當出現分歧時,回溯材料和文獻,直至達成一致意見。
1.3.1 結果變量 以“政策創新類型”為結果變量,依據王猛[16]基于類型學視角梳理出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類型及分類標準,將地方政府的創新類型分為“中央主導型創新”“地方回應型創新”“地方自發型創新”三類。根據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是否具有自發性,將“中央主導型創新”和“地方回應型創新”編碼為0(非地方自發型創新),將“地方自發型創新”編碼為1。
1.3.2 條件變量 條件變量的確定是QCA研究中的關鍵環節,變量的確定要遵循一定的理論和方法。根據案例數與前因條件數間的可通約性,“對于中等大小(10~40)的樣本,解釋條件的數量最好是4~7個”[11]。本研究基于文獻歸納法[17],立足于地方政府創新影響因素或創新動因有關的文獻資料,通過綜合考慮文獻的代表性、研究結論的科學性、數據可獲取性、案例情景及我國縣域醫共體實踐特點等,共篩選出5個影響地方政府創新水平的因素。(1)經濟發展水平。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對地方政府創新具有非常明顯的促進作用[9]。研究表明,當一個地方擁有充裕的財政資源,那么該地政府的創新更易成功[18]。楊雪冬[19]通過對“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的評選結果進行分析也提出,“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創新越多”這一判斷是有統計學上的依據的。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也有可能給地方政府造成無形的壓力,進而促使其采取創新舉措來改變醫共體實踐的現實困境 。因為較低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可能引發潛在的政治危機,進而影響地方政府決策者的職業發展[9]。(2)行政層級。地方政府創新的行動主體具有多樣性,其中區(縣)級政府和地級市政府是地方政府創新的主體[19]。在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下,縣域醫共體政策執行并非是單一機構貫徹政策目標的行動結果,執行活動多嵌在混沌行政環境中,呈現多元復合型的執行樣態。同時,地方政府層級不同,其圍繞各種有形或無形資源而展開的府際間競爭的激烈程度也不同,故行政層級是影響地方政府積極響應創新政策、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重要因素。陳朋[9]也指出,在當前資源分配體制下,省級及以上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占據優勢地位,所以其創新動力更強。(3)地理區位。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呈現明顯的區域性差異,具體表現為東部、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創新動力更強[20]。此外,一項針對“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獲獎項目的研究也表明,相較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地方政府的創新實踐受到更多贊譽[20]。所以,激烈的區域間競爭是我國地方政府創新的主要影響因素[21]。(4)問題屬性。問題屬性指的是影響地方政府創新的事件性因素,是地方政府創新實踐的“催化劑”。從某種角度來看,地方政府創新也是被各種現實問題“逼”出來的“不得已”的選擇[9]。問題屬性包括兩層內涵:一是,因現實情景中的難題“倒逼”而選擇創新;二是,因宏觀環境引導和刺激而催生的創新。總體而言,創新動機不同,地方政府在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進而導致醫共體創新實踐結果不同。(5)平臺。本研究中的平臺指的是樣本來源地區在開展縣域醫共體建設前是否被國家設立為試驗區或觀察點等。地方政府的創新實踐有無“平臺依托”,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上級政府對地方政府創新的重視程度和態度取向。平臺可起到降低創新的不確定性/風險和保護創新實踐成果的作用[19]。概而言之,“平臺”因素為調節變量,地方獲得的平臺支持情況不同,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效果和效益也存在差異。條件變量的賦值標準見表2。基于此,構建csQCA真值表,見表3。

表2 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條件變量的代碼、定義與賦值標準Table 2 The code,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standard of condition variables for the county medical community innov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表3 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條件變量和結果變量的csQCA真值表Table 3 The csQCA truth table for the condition variables and outcome variable of county medical community innov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1.4 統計學方法 利用FsQCA 3.0軟件對數據進行基于清晰集的QCA。按照csQCA的步驟,首先對5個條件變量進行必要條件分析。單一條件的必要性分析目的是判斷單一變量是否為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必要條件。通過一致性和覆蓋率確定條件變量和結果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必要關系。一致性指標的取值若>0.8,意味著有80%以上的案例符合一致性條件,表明前因條件是結果變量的充分條件。一致性指標的取值若>0.9,則表示前因條件是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即結果變量可以被前因條件獨立解釋[22]。反之,則說明不能將前因條件看成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即結果變量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23]。覆蓋率指的是條件變量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了結果變量。覆蓋率數值越大,則表示條件變量對結果變量的解釋力度越大[24]。在單個條件變量不足以構成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必要條件時,通過充分條件組合分析,探究前因條件組合如何導致被解釋結果的出現。利用FsQCA 3.0軟件,對真值表進行布爾最小化運算(設置一致性閾值為0.8),在標準化分析后,得到QCA的3種解,即復雜解、中間解、優化解。以覆蓋率作為主要觀察指標,覆蓋率數值越大,說明前因條件組合對因果路徑的解釋能力越好[25]。
2 結果
2.1 必要條件分析結果 5個條件變量的一致性均<0.9,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行政層級、地理區位、問題屬性及平臺均不是地方自發型創新的必要條件(表4)。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發生并不是由單一因素所致,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5個條件中,“平臺”的一致性最高,達0.86,雖然符合充分條件的標準(>0.8),但沒有通過必要條件的一致性檢驗,仍需要與其他變量組合進行多重復雜關系因果分析。

表4 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單個條件的必要性檢驗Table 4 Necessity test of individual conditions for county medical community innov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2.2 充分條件組合分析 參照當前QCA主流研究,大多數社會學家都認為合理有據、復雜度適中、不允許消除必要條件的中間解是QCA研究中匯報和詮釋的首選[26],故本研究將重點匯報中間解。限于篇幅,本研究僅列出基于中間解的條件組合分析過程(表5)。所有前因條件構型的一致性指標都為1(>理論值0.8),說明5個前因條件組合中的所有案例都滿足一致性條件,即5個前因條件組合都是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充分條件。原始覆蓋率為0.14~0.43,說明前因條件組合能夠解釋的個案占個案總量的比例為14%~43%。凈覆蓋率為0.14~0.43,解釋本組合最高達到43%。5個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充分條件組合,總體覆蓋率為1,表示所有影響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因素100%都包含在以上5個前因條件組合中,總體一致性為1。因此,該5個前因條件組合能夠有效解釋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影響因素。5條組合路徑分別為:(1)經濟發展水平*~地理區位*平臺;(2)行政層級*~地理區位*平臺;(3)經濟發展水平*問題屬性*平臺;(4)~經濟發展水平*地理區位*~問題屬性*平臺;(5)經濟發展水平*行政層級*地理區位*問題屬性(圖1)。符號*表示變量鏈接,表達“且”的交集關系;符號~表示“非”,意味著該變量在組合中一定不存在。“經濟發展水平”出現在3條組合路徑之中,“平臺”出現在4條組合路徑中,這與必要條件分析中“經濟發展水平”和“平臺”兩因素具有較高的一致性這一結果相吻合。

表5 基于中間解的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充分條件組合分析Table 5 The conditional combination analysis of county medical community innov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based on intermediate solution)

圖1 我國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影響路徑模型Figure 1 The path models of innovation practice incounty medical community innov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2.3 構建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實踐的影響路徑模型通過深度分析以上5種條件組合,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兩種解釋模型:平臺型創新模式和動機型創新模式。(1)平臺型創新模式。平臺型創新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這種模式驅動下開展的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更加體現了地方政府創新的自發性。符合該模式特點的條件組合包括組合1、2、3。組合1表明,若位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中部/西部/東北部地區,且有平臺支持,那么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開展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組合2表明,若為位于中部/西部/東北部地區的縣級市/區,加之有平臺支持,那么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開展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組合3表明,若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且自身有主動發展和改革的意愿,加之有平臺支持,那么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開展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2)動機型創新模式。符合該模式特點的條件組合包括組合4、5。組合4表明,若位于東部經濟發展狀況欠佳的地區,受迫于現實發展危機,那么地方政府會傾向于進行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以福建省將樂縣為例,將樂縣位于福建省西北部,201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57.96億元,由于受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醫療資源流動不順暢等因素的制約,基層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就醫秩序不合理等問題日益突出,在現實困境的“倒逼”下,將樂縣開展了醫共體探索,通過“三醫聯動”改革、構建整合型醫療服務體系及轉變服務模式等系列改革舉措,提升了基層就診率。組合5表明,若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好,且為東部地區的縣級市,加之自身有主動創新的動機,那么地方政府會傾向于進行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以廣東省高州市為例,高州市位于廣東省西南部,2019年的GDP為631.89億元,在經濟優勢的助推下,為進一步優化醫療資源配置,讓鄉鎮村民就近享有較高水平的醫療保障,高州市以“創高地、強基層、補短板”為原則,探索出了獨特的醫改“高州模式”,先后被確定為省和國家的醫改示范縣。
3 討論
在中國公共政策的執行語境下,平臺支持成為提升地方政府履職水平、推進公共政策改革和議程的核心動力之一[27]。平臺支持有助于促進“上層政治注意力”與“地方政府實踐”“互見”,激發地方政府創新勢能,賦能地方治理中的行動者,激活各層級行動者的能動性,統一共識并打破執行“屏障”,推動地方政府的創新實踐(典型案例為安徽省阜南縣和山西省高平市)。此外,在資源不足的現實情境下,“有為政府”的積極政策創新將有助于地方政府履行責任、緩解地方政府困境。在經濟勢能良好的情況下,若有“主動有為”、動機的加持,地方政府在創新實踐上更偏好于“政策創高”與“自主補短”(典型案例為福建省將樂縣和廣東省高州市)。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議:(1)地方政府若要實現高水平的醫共體創新實踐,應該關注政策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強相關性。地方政府是一個由輸入、轉換和輸出三部分構成的開放系統[28],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實現高水平的醫共體創新實踐的前提和動力。所以,為了真正促進二者的互融共生,各地方政府務必加強制度供給,構建基于不同階段的政策工具矩陣,避免單一政策工具使用所引起的單向性偏差。此外,政府需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創造良好的經濟運行環境,進而在助推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加速推進縣域醫共體的創新實踐。(2)激活地方政府主動創新的意愿是促進縣域醫共體創新發展的關鍵。在當前我國公共治理實踐中,基層公共部門更具創新潛能,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本質上是“委托-代理”關系下尋求在中央制度建構之下的地方自主發展空間。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正面臨著雙重壓力,即不同地域之間的張力[28]、上級政策要求與本地現實利益之間的沖突。所以,平穩推進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需要建立起“中央頂層設計”與“基層區域化探索”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重視地方政府所扮演的“先行官”角色,允許地方政府“摸著石頭過河”。建議不斷完善政策激勵機制,進而實現政策企業家精神理論內涵與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真實情境的“雙向貫通”;重視塑造不同行動主體在醫共體創新實踐上的共同價值觀。同時,還須賦能醫共體建設的行動主體,并將權力“下放”,使其擁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權來突破醫共體創新實踐中遇到的“瓶頸”,探索營造醫共體創新實踐的政策和制度環境。(3)強化對縣域醫共體的平臺支持是促進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的保證。地方政府內部政策企業家的創新行為是由區域發展情境、行動者的創新意向及其所處的社會網絡共同決定的[29]。平臺支持作為有利于地方政府開展醫共體創新實踐的政治資本,具有強大的政治勢能,是醫共體實現持續創新所需要具備的(社會網絡)資源。地方政府借助平臺資源,“向上”可以為自身爭取到更多的行政資源,“向下”可以克服面臨的重大阻力。此外,被列為試點平臺,也可視作政府從宏觀層面上為其背書和對創新的回應,尤其是對于地方政府自發型創新而言,創新模式的推廣和發展需要中央政府的積極回應、為其背書。
綜上,本研究以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為觀察對象,驗證了地方政府創新的因果關系是非線性的這一觀點;以縣域醫共體實踐價值案例為數據源,運用csQCA法,探尋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影響因素及其組合路徑,揭示了該類地方政府創新實踐的共有屬性及呈現“同花異果”局面的原因。分析發現: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影響因素的組合構型是非唯一的,不同地方政府主導的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需要通過不同的路徑實現。因此,不同地方政府應根據自身特征選擇最為適宜的創新路徑。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本研究雖然對于理解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的機理乃至地方政府創新都具有一定價值,但仍具有一定情境性,結論能否適用于其他的政策創新實踐場景,仍有待進一步論證。其一,本研究所選取的案例均來自“縣域醫共體實踐價值案例庫”,案例庫中的案例雖然整體質量較高,但數量不多、難以全面/系統反映當前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情況,故本研究納入案例的代表性可能不足,結論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風險。未來,仍然需要納入更多有代表性的案例,與時俱進,更新或修正研究結論。其二,案例呈現的信息不夠完整,尤其是微觀層面的信息,且采集到的變量信息是否經過了“修飾”或“加工處理”難以確定。其三,在微觀層面上,本文忽視了政策企業家在推動政策創新中發揮的關鍵作用,所以可能存在一定偏倚。未來仍須輔以其他視角和方法,來對地方政府縣域醫共體創新實踐進行多視角、全方位及全要素的透視。
作者貢獻:張敏、張淑娥、孫濤提出研究選題方向和總體研究目標,負責設計研究方案及確定研究方法,并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張敏、時宇、孫濤對研究進行可行性分析;王鴻妮、趙鑫負責文獻/資料收集;張敏、王鴻妮、紀科宇、程偲雨、趙鑫負責文獻/資料整理;張敏負責論文撰寫;張敏、張淑娥負責論文修訂、質量控制及審校;張淑娥、時宇負責英文的修訂;所有作者確認了論文的最終稿。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