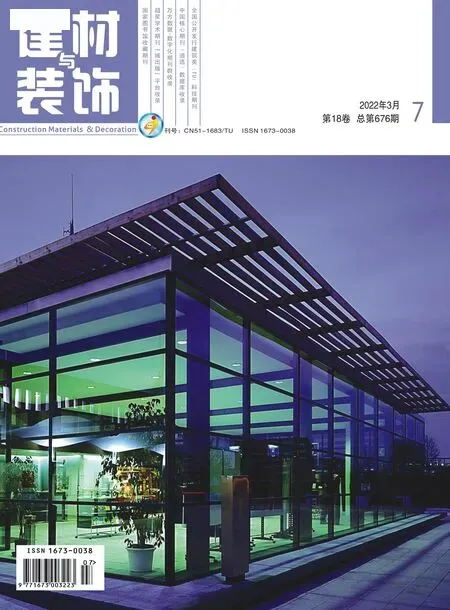國子監建筑的發展與其在城市中的空間位置變化
葉晟
(南京工業大學建筑學院,江蘇 南京 211816)
0 引言
國子監直達天聽,送輔國之棟梁。其前身為三雍、太學,成熟的國子監形制于隋唐成型。國子監授孔孟之道、傳先賢之經,也作帝王視學、釋禮之用。經歷了三雍、太學、國子學等發展演變,最后形成了機構完善、功能齊全、建筑形制成熟的國子監形式。
國子監制度本身與其建筑形制都對中國教育史有著巨大貢獻,既是中國教育史的重要內容,也是明代國家官員培訓制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對其建筑形制的研究,也是明代皇家建筑的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國子監是天下教化之圣地,名儒咸集,學子莘莘,自隋唐時期定制以來,傳承一千四百余年,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本文將從中央官學的發展、官學地位的提高所帶來的國子監在城市位置的變化、建筑形制的發展,梳理各主要朝代中,國子監建筑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
1 國家官學的萌芽——有史以來至先秦
“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有史可查的教育傳承之始,見于《尚書》。《禮記》載“瞽宗,殷學也”“天子命之教,然后為學......天子曰辟雍”,是商和西周官學的教學位置。《左傳》云,“學在四夷”,春秋戰國,諸侯建立了自己的教育系統,但不能說教育已經普及到了民間。先秦,演變出“三雍”,集祭祀、教學、布政等功能集合的建筑群。“靈臺、辟雍......周公因之,而定三雍之制”[1],三雍建筑是一組包括了學校在內的綜合性禮、樂、祭、政建筑群,其建筑形制也是當時最高規格之一。
《白虎通義·辟雍》曰“天子立辟雍......行禮樂、宣德化也”;《白虎通義·靈臺明堂》曰“天子立明堂者......出教化”;《詩經·大雅·靈臺》載,“民經始靈臺......不日成之”。三代至戰國時期,教育建筑圖樣已難以考證,漢武帝封禪泰山,欲做明堂,已不能知其形制。《白虎通義·辟雍》曰“辟者,璧也,象璧圓......雍者,雍之以水”,推測辟雍是環形建筑,以流水環繞。《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五室,凡室二筵”。關于靈臺的記載鳳毛麟角,“靈臺高三丈,十二門”[2],后來靈臺逐漸被“司天臺”等取代,筆者推測“靈臺”為高層樓閣建筑,其象征帝王威儀的意義與其高聳的視覺效果是大于使用價值的。
2 國子監的前世身——漢魏晉南北朝
漢武帝時期,“為博士官......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得受業弟子”[3]元朔五年,太學正式設立。“莾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筑舍萬區”[4],西漢末,太學的學舍有了很大的規模。兩漢長安的禮制建筑主要集中在南郊[5]。
兩漢時期,禮制建筑只有宗廟和社稷壇位于城內。城市南郊便是太學所在的以“三雍”為主的祭祀建筑群。“王莽......起國學于郭內之西,南為博士之宮官,寺北出......其中央為射宮,門西出......選士肆射于此中。此之外,為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此之東,為常滿倉。倉此之北,為會市......其東為太學宮官。寺門南出......學士司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6]。根據典籍可以推斷,西漢太學以博士宮為主體,有“射宮”也就是后世射圃的雛形用于行射禮,有“市”供學子易物、議論、行禮樂等活動。東漢之都為洛陽,其城市規劃多依長安而建,太學亦然。此時,隨著教學位置的轉移,“三雍禮”中的學禮也逐漸向太學轉移。
曹魏時期,《三國志》記載,正始二年祀孔子于辟雍,正始五年,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文獻中的“辟雍”應是指太學[7]。《晉書》記載,公元二七六年國子學首次創立。“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太學之與國學......異其貴賤耳”[8]西晉初年,太學仕庶皆可入學,故創立了國子學,出現了兩學并行的模式,用于維護貴族階級。魏晉南北朝期間,由于政治現象的紛擾,學校的發展緩慢,此時仍有三雍建筑,國子學也在其中。南朝時期,僅有宋朝、梁朝的教育有所創建。元嘉二十年,建立國子學,七年后又停辦。《述征記》載“太學在國子學東二百步”,西南為國子學,東南為太學,皆是在漢魏官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東晉時期,繼承了二學并立的方式,位置在建康城南郊。六朝時期,太學一度移入宣陽城內,其建筑“儀賢堂......在宣陽口內路西,七間”[9]。
這段時間里,漢代創立了“太學”;晉首創“國子學”,皇帝視學、行學禮漸漸頻繁,太學、國子學兩學并立是官學逐漸脫離太常的雛形。漢朝行郊祭,太學在南郊。以建康為例,官學起初在淮水南,后移入宣陽門內,又重修太學于太廟之南。
自先秦“三雍禮”形成以來,學禮便屬其中。直到到漢明帝時,“學禮”才基本獨立在外進行;東漢,帝頻視學于太學,學禮進一步向官學轉移;至于魏晉,三雍禮逐漸廢止。此后,“三雍”消失,這與當朝未建“三雍”建筑也不無關系。但從結果上來看,此時“三雍禮”與“三雍建筑”可以說是徹底退出了國家官學教育的歷史舞臺了。官學授學與行學禮的功能脫離了“三雍”,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機構,國子監制度的創設也正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而來。
3 國子監的創設期——隋唐
隋朝前,三雍建筑已經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國家教育的功能開始由當時的國子寺承擔;隋文帝時期,國子寺脫離太常管理,獨立行使教育、管理職能;隋揚帝時期形成了國子監制度的雛形[10]。唐高祖武德元年設國子學;唐太宗貞觀二年改為國子監,洛陽亦設國子監。成型于隋唐時期的國子監模式,成為后世歷朝歷代培養人才、選拔官員的重要途徑,堪稱中國教育史上最重大的變革。
長安地處平原,當時的城市設計為里坊制,是典型的對稱式布局,三套城墻分別界定宮城、皇城和外城。出朱雀門正對御道為城市縱向軸線,東西對稱,朱雀門所對大街為長安城橫向主要街道。國子監位于城市中軸線附近,地處中心建筑群,與太廟一墻之隔。長安國子監東部為孔廟,以供奉孔子的祭殿為核心。南有門,面闊三間。國子監有講堂,其北為國子館,再北為廣文館、太學、四門館。洛陽的國子監,其形制依長安而筑,地處正平坊,孔廟也設于其中。
隋唐創建的國子監,在屬性上,為唐朝五監之一,是名副其實的管理部門而非簡單的一所學校,還兼具天下學規制定、教材出版等功能;在形制上,開創性的將孔廟與國子學合并設置,形成了后世廟學合一的建筑形制,并逐漸演化出了左廟右學、前廟后學等多種制式。國子監的制度在此時已經正式確立下來,包括其建筑形制、教育模式、學規學訓等,為天下學校和后世的各類書院定下了準繩。
4 國子監的波折——宋元
北宋初年,改后周之國子監,修繕增建;時至真宗,國子監已經成為當朝官員嫡親附學充貢之地;仁宗時,“殊無肆習之法,居常聽講者,一二十人爾”[10]。此情此景,一場以振興教育的改革掀起,太學因勢而創,但仍隸屬于國子監。元代國家教育體制與過去以國子監為最高學府不同,有國子監、蒙古國子監和回回國子監三處,下各轄國子學。元代的官學體系,是各方政治斗爭下的產物。建國之始,為籠絡天下漢人、國家穩定而建廟設學,建立了國子監。在國內漢蒙政治斗爭下又產生了蒙古國子學。后回回部族崛起,攫取政治權利,又誕生了回回國子學。從名義上說,三方國子監高于國子學,然二者實各行其事。
《東京夢華錄》載,“出朱雀門......過龍津橋南去......東劉廉訪宅,以南太學、國子監”。宋開封,以出朱雀門的御道為城市中軸線而設計,國子監位于其側。元朝國子監是以金宣圣廟而建,在都城的東南隅。宋朝的國子監,學監有三禮堂,先師廟有大成門、蓮池、大成殿,后有稽古閣藏書。慶歷四年,詔以錫慶院為太學,太學自此擁有了自己獨立的學舍。太學以明善堂為教學核心建筑,有射圃行“射禮”。大蒙古國國子學以國子監為建筑核心,國子監有兩掖。前有博士廳及六堂供考課授業。學區后為生活區,有學舍、餐廚供師生日常起居。大成殿是孔廟的核心建筑,其兩側有廊廡。大成殿與廊廡分別祭祀先師與諸賢。廟有大成門,配套有神庫、神廚等。總占地接近40 畝,規模極大。
5 國子監的鼎盛——明清
明代國子監的初設,則可追溯到元末至正二十四年,既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未得天下而先立官學。明洪武十五年,在雞鳴山南,國子監落成;永樂十八年,由于戰時需要,遷都北京,北京國子監落成,并以此為國子監。洪武八年,鳳陽國子監落成。鳳陽的營造由于多方原因中斷,洪武二十六年,鳳陽國子監被取消,并入北監。由于地勢,南京難以營建北京那般縱橫軸線規整的都城。“國子監在南京城內西北七里...... 右為欽天之山”[11],左學右廟。國子監建筑群(圖1),學宮以彝倫堂為中心,分列六堂,東西有師生居住的會館,并配有餐食、藏書、沐浴等設施。

圖1 明南京國子監位置(圖片來源:《中國歷史地圖》)
孔廟以大成殿為核心,連接兩廡。鳳陽國子監位于位于云霽街明倫坊內。云霽街為皇城南側的東西橫街,與洪武大道垂直交匯。其建筑形制依照南監而筑。北京國子監,在元朝舊址而設。明初改元崇文閣為彝倫堂,東率性、崇志、誠心堂,西正意、修道、廣業堂。監西有射圃,監東為孔廟。清時,繼承了明代的國子監形制,有修繕和增置。雍正九年,于方家胡同建“南學”供師生教學于起居。辟雍之制已消失許久,乾隆皇帝下令在國子監營建辟雍,在登基50 年之時臨雍講學。建筑位于彝倫堂前,其形制中為辟雍殿,外環水(圖2)。其制如古,辟如璧,整個場地呈現圓形,雍為雍之以水,以流水環繞辟雍殿。

圖2 皇受育民
南監由于南京城地形的原因未能在城市設計的軸線附近,然而其體量與形制,都是南京十廟中其他九廟遠不能及的。鳳陽國子監,國子監建筑與歷代帝王廟、開國功臣廟等國家最高禮制建筑同級而設,地位崇高。北京國子監,據《詔建辟維工程估計錢根數日奏》,整個工程鑿井四口取環雍之水,辟雍殿更是氣勢恢宏,其經費約等于國子監數十年的教育經費,花費白銀總計二十萬兩,國子監的建筑規格更上一層。
6 結語
國子監的誕生并非一蹴而就,國子監由“三雍”“太學”“國子學”逐步演化成為獨立的“國子寺”,最后在唐朝形成了成熟的“國子監”制度。由一個單純的教學機構,成為一個兼具國家最高學府與教育管理的機構,制定各項教學規定。后世的中央官學都沿用了這一制度,兩宋期間興起的地方書院亦是如此。
建筑位置由漢代的郊外逐漸發展至南北朝進入城內;繼而至唐朝與文武廟并列;最后到明清時期地位與太廟等國家大祭建筑并行。
建筑形制從秦漢時期與祭祀、布政的“三雍建筑”,到魏晉時期形成獨立的學宮;唐朝,形成了“廟學合一”的建筑形制,并在后世衍生出左廟右學、前廟后學等多種形式。其規模逐步增大、形制日益隆重。明清時期是國子監建筑的鼎盛期,其選址位于都城營建核心,建筑形制等級高,學禮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