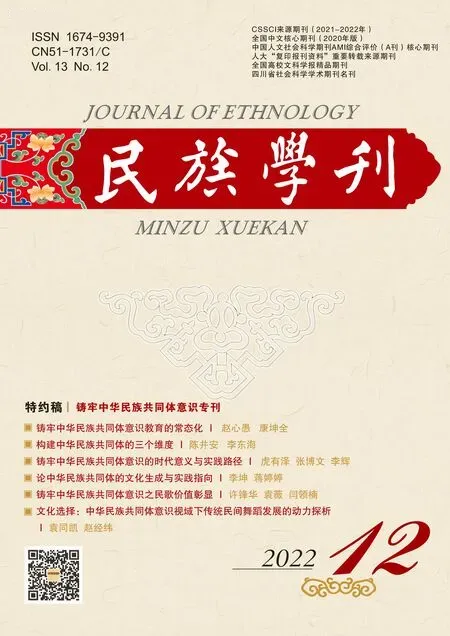元明清時期中國多民族飲食文化交流交融及其作用
杜 莉 王勝鵬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歷史上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互鑒發展,形成了唇齒相連、難以分離的多元一體格局,共同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共同創造了歷史悠久、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飲食文化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飲食文化,廣義上是指人們在長期的飲食生產和生活中創造并積累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它作為人們飲食生產與生活方式、過程等構成的全部食事活動總和,從結構和存在形式上可劃分為兩大類別的層次:一是物態文化層次,包括食材、菜點品種、茶酒飲料、烹飪器具設備等。二是精神文化即非物質文化層次,又包括飲食制度、飲食禮儀、飲食民俗和飲食思想、飲食科學、飲食藝術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1]飲食文化是了解和探究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一部中國飲食文化史,就是從古至今中國各民族飲食文化交流交融、共同創造發展并匯聚而成,多元一體,輝煌燦爛。從先秦到元明清的數千年歲月里,中國歷經了多次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由于人口遷移、族際通婚、經貿往來甚至戰爭等多重因素促使各民族飲食文化不斷交流交融,各民族從相互知曉了解到相互學習借鑒,相互補充、融合創新,共同鑄就了各民族飲食文化和中華民族飲食文化的豐富、獨特與繁榮,也從飲食文化這一獨特領域有力地助推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而元明清時期,是中國多民族大交流、大交融的極其重要時期,多民族飲食文化交流交融內涵豐富,對發展中國飲食文化和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元明清時期多民族飲食文化交流交融狀況
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是,歷史上統治者曾是蒙古族、漢族和滿族等。他們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采取不同政策措施,一方面強調民族差異性,另一方面推動民族交流交融。元朝蒙古族統治者將全國人分成四等,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色目人包括畏兀兒、回回、乃蠻等,漢人包括北方漢人和漢化契丹人、女真人,南人主要包括江浙等南方各地之人。四個等級的民族有著不同政治、法律等地位,擔任要職的絕大多數是蒙古人和色目人。清朝滿族統治者在較長時間內強調“滿漢畛域”,禁止滿漢通婚,官職分滿漢,滿族人享受生活特權,滿族與漢族在法律上有一定區別等。蒙古族和滿族統治者也在文化、經濟等方面重視民族交流交融,尤其是清代中期及以后注重“滿漢一體”。其中,漢族與少數民族飲食文化的交流交融成為一個亮點,并且呈現出雙向互動、雙層齊備、互鑒創新的特點。漢族將其飲食文化傳給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將其飲食文化傳給漢族,各民族相向而行、互動交流,既涉及食材、菜點品種、茶酒等物態文化層次,也涉及飲食品制作技藝和飲食禮儀、習俗、制度以及飲食思想等非物質文化層次,雙層兼備、內容豐富,并且相互吸收、借鑒與創新。
(一)少數民族飲食文化向漢族的傳播與吸收
元明清時期,隨著蒙古族、回族、滿族等民族先后大量進入中原和江南等漢族地區,各民族商貿往來頻繁,以飲食品及其制作技藝為代表的少數民族飲食文化等大量傳入漢族地區,其飲食品成為部分地區常見品種。
元代時,回族、女真、蒙古等民族飲食品及制作技藝不斷傳入漢族地區,受到漢族高度重視,與漢族飲食品一起成為人們的日常飲食品,并且系統收錄于書中。元代無名氏《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是一部家庭日用大全式的生活小百科全書,內容豐富多彩,“信居家必用者也”。該書共十集,記載飲食的有兩集、30余類,主要是漢族飲食,但也專列“回回食品”“女直(即女真)食品”兩類。其中,“回回食品”有設克兒疋刺、卷煎餅、糕糜、酸湯、禿禿麻失、八耳塔、哈爾尾、古刺赤、海螺廝、即你疋牙、哈里撒、河西肺;“女直食品”有廝刺葵菜冷羹、蒸羊眉突、塔不刺鴨子、野雞撒孫、柿糕、高麗栗糕等。[2]這是較早系統收錄回族、女真食品的書籍,在家庭日用之書中將其與漢族食品并列,說明元代時這些少數民族食品已十分流行、與漢族食品一起成為人們居家常用食品。
明清時期,北京作為首都,以漢族聚居為主,但蒙古族、回族、滿族等民族先后大量進入,將各自飲食品及其制作技藝帶入北京,使其成為北京飲食的組成部分。明代宋詡《宋氏養生部》之序言:余家世居松江,家母“幼隨外祖,長隨家君,久處京師”,“鄉俗烹飪所尚,于問遺飲食,審其酌量調和,遍識方土味之所宜”,“余故得口授心傳者,恐久而遺忘,因備錄成帙,而后知天下之正味也”。[3]2-3宋詡是江南華亭人,其母親“久處京師”、學到許多北京菜點制法,又傳授給他,他編成《宋氏養生部》。由此,該書收錄的菜點應以北京風味為主、兼及江南風味,所載的回回煎餅、香露餅等回族面點及制法表明已進入北京。其“香露餅”(之二)言:“用水、小粉再湛潔二斤,同白砂糖、熟蜜各四兩,入鍋,慢火調煎至濃,加香熟油四兩,再調煎極稠,碾去皮胡桃、松仁和之,為厚餅,冷定,切小塊,摻以餹香少許。即回回曰哈哩哇。”[3]51“香露餅”被回族稱為“哈哩哇”,極具回族特色。進入清代,北京飲食市場上則聚集了更多民族食品。邱龐同《中國面點史》引乾隆時楊米人《都門竹枝詞》言:“涼果馇糕聒耳多,吊爐燒餅艾窩窩。叉子火燒剛買得,又聽硬面叫餑餑”,“果餡餑餑要澄沙”,“哈爾巴同打辣酥”[4]叉子火燒、硬面餑餑、果餡餑餑、哈爾巴等是滿族面點和菜肴。此外,傳入北京并流行的還有滿族著名面點薩其瑪。它又稱薩奇瑪、沙其瑪、賽利馬等,對應漢語為“糖纏”,是一種將面條炸熟、加糖拌勻后再切成小塊的面食品,色澤米黃、質地酥松綿軟、香甜可口。清代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載:“薩齊瑪乃滿洲餑餑,以冰糖、奶油合白面為之,形如糯米,用不灰木烘爐烤熟,遂成方塊,甜膩可食。”[5]如今,薩其瑪不僅是北京名食,也傳遍全國,已成為中國著名面食品之一。明清時期,除了北京,少數民族飲食也進入了江南、西南等漢族地區。江蘇人李斗《揚州畫舫錄》載有滿族“硬面餑餑”。四川人李化楠撰《醒園錄》記載了“做滿洲餑餑法”:“外皮,每白面所,配豬油四兩,滾水四兩攪勻,用手揉至越多越好。內面,每白面一斤,配豬油半斤(如覺干些,當再加油),揉極熟,總以不硬不軟為度。才將前后二面合成一大塊,揉勻攤開,打卷切作小塊,攤開包餡(即核桃肉等類),下爐熨熟。”[6]
(二)漢族飲食文化向少數民族的傳播與吸收
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在每一個時代通常都是雙向互動的。元明清時期,漢族在與蒙古族、滿族、回族、藏族等民族的交往過程中,將自己的飲食文化傳給其他民族,主要包括食材、飲食品種及制作技藝及飲食習俗、飲食制度等。
元代時,蒙古人、色目人等級較高,漢人、南人雖然等級低、但文化較先進,因此,漢族的飲食文化以及回族、維吾爾族等民族的飲食品制作技藝和飲食思想、飲食制度被蒙古族吸收。如漢族的茶及飲茶習俗和糖霜、橙橘等已進入元代蒙古族的飲食生活。元代初年耶律楚材《贈蒲察元帥七首》其三言:“主人知我怯金觴,特為先生一改堂。細切黃橙調蜜煎,重羅白餅糝糖霜。幾盤綠橘分金縷,一碗清茶點玉香。”[7]元代宮廷采用周代宮廷“醫食相通”的制度和漢族“飲食養生”思想,在宮廷設置飲膳太醫之職。宮廷飲膳太醫忽思慧編撰的《飲膳正要》實質上是一部用于宮廷飲食的飲食養生學著作,其卷一“聚珍異饌”主要記載的是蒙古族飲食品,但也記載了漢族和維吾爾族、黨項羌人、回族等的飲食品及其制作技藝,包括漢族的包子、饅頭、角子等面食,“畏兀兒茶飯”如“搠羅脫因”,黨項羌人的“河西飲食”如“河西米湯粥”“河西肺”,數量較多的“回回飲食”如“禿禿麻食”等。可以說,《飲膳正要》是一部中國多民族飲食文化長期交流交融的結果和見證。[8]
明清時期,尤其是明代末年至清代,隨著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的道路,美洲作物沿絲綢之路不斷進入中國,加之滿族入關、統治全國,原產于美洲的食材如玉米、土豆、番薯、辣椒等從漢族地區逐漸傳播至少數民族地區,漢族的菜點制作技藝、飲食習俗、飲食制度等也更多地被滿族吸收借鑒。玉米,原產于中南美洲墨西哥和秘魯一帶,又稱玉蜀黍、御麥、包谷、苞米、番麥等;土豆,原產于南美洲秘魯,又稱洋芋、羊芋、馬鈴薯等。玉米、土豆及其種植技術在清代時已由漢族地區傳入中國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如在彝族、藏族等聚居區不僅成為其食材,也成為貿易品。清代王培荀《聽雨樓隨筆》卷三輯清代楊國棟《峨邊竹枝詞》言:“今年玉蜀滿山頭,才得開荒便大收。共約鄰家賽神去,瓜蘆池上水初秋”。[9]周斯才《馬邊廳志略》卷六“夷俗”載:“夷地出產藥材,如貝母、黃連、附子、厚樸、麝香并包谷、雜糧之類入漢地,俱換布匹、煙鹽、針線并綢綾緞等件”。[10]峨邊、馬邊是彝族聚居地之一,玉米在當地大量種植,不僅是彝族糧食,還作為貿易物品與漢族交換。此外,清代時,土豆傳入彝族地區后也被種植、食用和售賣。清代同治《會理州志》載有“洋芋”并注:“或作羊芋,燒、煮皆可食,又可為粉。”乾隆年間,玉米隨移民帶入,在甘孜藏區打箭爐(今康定)等地種植。[11]清代道光年間李涵元、潘時彤編纂的《綏靖屯志》卷四已載有“玉蜀黍”即玉米。綏靖,今阿壩州金川。藏族地區的土豆種植稍晚于玉米,主要在清代光緒、宣統年間。光緒《定瞻廳志略》及《爐霍屯紀略》在物產中皆載有“羊芋”即土豆。《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載,清末德格同普(今屬西藏江達)知事創辦農業試驗場,鑒于土豆“耐寒,宜于高原沙地,三月下種,七月成熟,不懼風霜”,優勢明顯,從內地引入種苗,試驗選擇,用高產實效而向民間推廣。[12]此外,漢族節日食俗及飲食品和地方菜也系統地傳入清代宮廷。據《欽定大清會典》載,內務府之下的“掌關防管理內管事務處”設有餑餑房,承辦每年上元節、端午節和中秋節宮中所需要的元宵、粽子和月餅。康熙、乾隆多次東巡、南巡,品嘗到山東和江南菜點,使得山東菜、江南菜等逐漸進入宮廷飲食。邱龐同《中國面點史》引用了乾隆南巡時揚州、蘇州、杭州的御膳食單,僅以《乾隆三十年江南節次膳底檔》為例,記載了乾隆品嘗的江南面點有30余種,包括果子糕、爛鴨面、雞肉餡包子、鴨子火熏煎粘團、蘇造雞爛肉面、酥火燒、素包子等,許多品種后來成為宮廷面點。[13]蘇州廚師張東官在乾隆南巡時為其做菜、受到好評,后來又兩次被借入御膳房制作江南菜,促進著清宮吸收江南菜。
(三)漢族與少數民族飲食文化互鑒交融
元明清時期,中國進入又一個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時期,漢族與蒙古族、滿族等民族在飲食文化的多個方面互動交流,相互不斷學習、借鑒交融,產生出具有融合特征的、新的復合型飲食文化。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元代的許多面食品及其制作技藝和清代滿漢全席。
元代時,草原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在飲食上除了繼續保持肉食和奶制品為主,還吸收借鑒漢族的饅頭、包子、角子等面食品及其制作技藝,并與自身的食材相結合,創制出許多具有蒙古風味的新品種。如饅頭,相傳由三國時期的諸葛亮發明,分為有餡和無餡兩種,經過魏晉南北朝和唐宋的發展,到元代時已經具有成熟的制作技術和多樣品種,這體現了漢蒙交融。元代無名氏《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飲食類”之“干面食品”載“平坐大饅頭”的制法,將面粉加入酵汁后揉成團,待發酵后下劑,“搟作皮,包餡子。排在無風處,以袱蓋。伺面性來,然后入籠床上,蒸熟為度”[2]118。在元代宮廷飲食中,有倉饅頭、鹿奶肪饅頭、茄子饅頭、剪花饅頭等饅頭品種,并且以羊肉、羊脂、鹿乳等食材創制而成,蒙古風味濃郁。忽思慧《飲膳正要》卷一《聚珍異饌》載,“倉饅頭”是以“羊肉、羊脂、蔥、生姜、陳皮,各切細”,加入“料物、鹽、醬,拌和為餡”,“茄子饅頭”是以茄子與羊肉、羊脂等為餡:“羊肉、羊脂、羊尾子、蔥、陳皮,各切細,嫩茄子去穣”,“同肉作餡,卻入茄子內蒸,下蒜酪、香菜末,食之”。[14]
清代時,雖然滿族貴族居于統治地位,但是漢族文化具有一定先進性,使得滿族統治者不得不從強調“滿漢畛域”逐漸轉變為注重“滿漢一體”,滿族與漢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加深。由此,清代宮廷出現滿漢飲食文化并存、滿席與漢席并列,進而在官府、民間出現新的宴席品類,即滿漢席、滿漢全席。清代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四首次記載乾隆南巡揚州時揚州官府舉辦的“滿漢席”情況:“上買賣街前后寺觀皆為大廚房,以各六司百官食次,包括第一分頭號五簋碗十件有燕窩雞絲湯、海參匯豬筋等13個品種,第二分二號五簋碗十件共12個品種,第三分細白羹碗十件共11個品種,第四分毛血盤二十件共14個品種,第五分洋碟二十件,熱吃勸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徹桌,鮮果十徹桌,所謂‘滿漢席’也”。[15]這是一份最早且最完整的滿漢席食單,共有130個飲食品種,以江浙菜為主,滿族燒烤為輔,集山珍海味、滿漢烹飪技法于一體,是滿族與漢族飲食精粹合璧。不久,蘇州等地飲食市場上出現了不同的滿漢席及菜品。清代顧祿《桐橋倚棹錄》卷十“市廛”之“酒樓”載:蘇州三山館等酒樓賣滿漢大菜、舉辦滿漢席,“所賣滿漢大菜及湯炒小吃則有燒小豬、哈兒巴肉、燒鴨、燒雞、燒肝……”;其宴席之菜“有八簋四菜、四大四小、五菜、四葷八拆、以及五簋、六菜、八菜、十大碗之別”。[16]清代袁枚《隨園食單》從側面說明了滿漢席產生的原因及目的。該書“本分須知”言:“滿洲菜多燒煮,漢人菜多羹湯。童而習之,故擅長也。……今人忘其本分,而要格外討好。漢請滿人用滿菜,滿請漢人用漢菜。”[17]21其“戒落套”言:“今官場之菜名號有十六碟、八簋、四點心之稱;有滿漢席之稱……只可用于新親上門、上司入境,以此敷衍”。[17]35《隨園食單》初刻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說明“滿漢席”已在乾隆時的官場通行,滿族與漢族相互交往交流時以對方飲食宴客來示好,主要目的是迎送、酬酢等。此后,隨著清代官員在各地的調動,滿漢席流傳到全國許多地方,但沒有統一通行的席單,只有相同的基本格局,其菜點品種及數量則根據傳入地飲食習俗、食材及菜點狀況而不斷調整融合,形成了既有相同之處又各具地域特色的多種“滿漢全席”,相同的核心在于滿漢烹飪技法與菜點的集合。清末徐珂《清稗類鈔》“飲食類”載:“燒烤席,俗稱‘滿漢大席’,筵席中之無無上品也。烤,以火干之也。于燕窩、魚翅諸珍錯外,必用燒豬、燒方,皆以全體燒之。”[18]6266張白居編《四川滿漢席》收錄了李劼人《舊賬》之“送點主官滿漢席單”,有正菜八個、熱菜八個、圍碟十六個,以及燒小豬一頭、哈耳巴、大肉包一盤、朝子糕一盤等。席單下原注言:“此席單并非滿漢全席,以海味不全、八珍未備故也。”[19]它是清道光十八年(1836年)成都舉辦的滿漢席,是在特定時間、特定場合的特色滿漢席,小巧而不失莊重,雖珍味不全卻滿漢合璧。
二、元明清時期多民族飲食文化交流交融的意義與作用
元明清時期,漢族與少數民族在飲食文化上的交流交融不僅雙向互動、雙層齊備,而且相互學習吸收、互鑒創新,既豐富了漢族和少數民族各自的食材、飲食品及制作技藝飲食思想、飲食制度、飲食習俗等,改善了各自飲食結構,也創造了許多新的融合式飲食文化內涵,在中華民族飲食文化“多元一體”格局不斷發展上起到了互補共進、共促創新繁榮的重要作用,也從多民族飲食文化的交流交融這一獨特領域有力地助推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不斷牢固與壯大。
(一)多民族飲食文化交流交融是各自飲食文化創新發展的動力源
元明清時期,各民族之間的飲食文化交流交融,不是簡單照搬,不是“1+1=2”,而是“1+1﹥2”。各民族在面對傳入的其他民族飲食文化時不僅采取“拿來主義”、直接為我所用,還以此為基礎吸收借鑒,并與本民族飲食文化相結合、融會貫通后進行創新發展。正是由于各民族在食材、飲食品及其制作技藝等方面不斷交流交融,才使得各民族飲食文化獲得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動力源泉,既豐富了本民族的飲食文化內涵,也極大地促進了蘊含多民族飲食特點的中華民族飲食文化共同體不斷發展。
以漢族飲食文化傳入少數民族地區而言,如前所述,元代時蒙古族面對傳入的漢族面食品及其制作技藝,在吸收借鑒的基礎上結合特產食材而創制出眾多蒙古風味的面食品,如饅頭、包子、角子等。明末清初時原產于美洲的食材及其種植技術、烹飪技藝從漢族地區逐漸傳播至少數民族地區,不僅豐富了少數民族地區的食材品種,也成為當地的日常飲食品。最典型的是土豆、玉米、番茄、辣椒、番薯等,不僅在四川、重慶、貴州等地的少數民族地區廣泛種植,也在當地創制出許多新菜點,如四川甘孜、阿壩藏族的洋芋擦擦、洋芋糍粑、攪團,重慶土家族金裹銀(即玉米粉與大米混合制作的金銀飯)、貴州苗族酸湯魚,等等。清代中期以后,漢族節日食品、日常飲食和宴席制度進入滿族宮廷,豐富了滿族飲食文化。此外,漢族地區的茶葉傳入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地區,又融合創制出新的品種,成為其不可缺少的日常飲食。如藏族將茶葉與土產酥油結合創制的酥油茶,成為藏族日常飲品;蒙古族將茶葉與土產牛奶結合創制的奶茶,也成為蒙古族日常飲品。清代徐珂《清稗類鈔》“飲食類”的“藏人之飲食”載:“藏人飲食,以糌粑、酥油茶為大宗,雖各地所產不同,然舍此不足以云飽”,進餐時“司廚者以酥油茶輪給之,先飲數碗,然后取糌粑置其中,用手調勻,捏而食之。食畢,再飲酥油茶數碗乃罷”[18]6249-6250;其“蒙人之飲食”條言:“蒙人一日三餐。兩乳茶,一燔肉。”[18]6248
以少數民族飲食文化傳入漢族地區而言,最突出的是食材和菜點品種及其制作技藝傳入漢族地區,由漢族吸收借鑒后融合創新而成為日常飲食品。元代時,羊肉、乳酪等蒙古族常用食材進入漢族地區,漢族用自己擅長的烹飪方法制作出許多菜肴,同時,回族、女真族的菜點也直接進入漢族日常飲食,并收錄于元代無名氏《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清代時,滿族和漢族飲食文化交流交融,除創制滿漢全席外,還創制了許多著名菜點。如滿族傳統菜肴白片肉傳入四川,四川人用川味調和創制出川味白肉系列名品。袁枚《隨園食單》“特牲單”載白片肉制法:“須自養之豬,宰后入鍋煮到八分熟,泡在湯中一個時辰取起。將豬身上行動之處薄片上桌,不冷不熱,以溫為度,此是北人擅長之菜。南人效之。”[17]52白片肉傳入江南后,經四川人李化楠、李調元父子傳入四川,其《醒園錄》載“白煮肉法”:“凡要煮肉,先將皮上用利刀橫立刮洗三四次,然后下鍋煮之。隨時翻轉,不可蓋鍋,以聞得肉香為度。香氣出時,即抽去灶內火,蓋鍋悶刻撈起,片吃,食之有味。”[6]這里的白煮肉是“片吃”,即白片肉。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覽》之“成都家常便菜”不僅有“白肉”,還出現了融合創新品種“椿芽白肉”。[20]此后,在白肉中加大蒜泥用量,則創制出蒜泥白肉。類似的融合創新品種還有奶皮元宵、奶子棕、奶子月餅、東坡羊肉等。
(二)多民族飲食文化交流交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蓬勃發展的助推劑
民以食為天,食為八政之首。中國古代先賢認為飲食不僅僅是滿足人的生理需求,更是治國理政的首要之事。《尚書·洪范》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21]解決多民族國家人民的飲食問題、豐富和完善其飲食生活,對促進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元明清時期,多民族飲食文化交流交融,不僅豐富了各民族的食材、飲食品種等物質文化內涵,也改善了各民族的飲食結構,融入了各民族的飲食制度、飲食思想、飲食習俗與禮儀等非物質文化內涵,使各民族在飲食文化上既有各自特色、又水乳交融于一身,成為促進中國飲食文化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蓬勃發展的助推劑。
以食材、飲食品種與飲食結構為例,《黃帝內經·素問》“藏氣法時論”:“五谷為養、五畜為益、五果為助、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益精氣。”[22]這是中國人飲食養生之道和最早提出的飲食結構理論。但是,在古代長期的生活實踐中,漢族以農耕文化見長,種植的谷物、蔬果等食材品種及數量較為豐富,農業發達,畜牧業發展卻遲緩,養殖的禽畜數量不足,在“六畜”中豬、狗、雞較多而馬、牛、羊較少,其飲食結構以素食為主、肉食為輔,皇帝及達官顯貴的肉食較多而平民百姓食肉極少。《孟子·梁惠王》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23]可以說,古代漢族人大多缺乏優質肉類蛋白質、B族維生素等,飲食結構不平衡、不合理,身體健康受到影響。而藏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常以游牧為主,馬、牛、羊較多,較少出產蔬菜、水果,其飲食結構以肉食為主、素食為輔,缺乏蔬果。《宋史·吐蕃傳》載,當時的吐蕃人“喜啖生物,無蔬茹醯醬,獨知用鹽為滋味,而嗜酒及茶”。[24]這導致古代許多少數民族十分缺乏維生素C、膳食纖維等,飲食結構也不平衡、不合理,影響身體健康。元明清時期,通過漢族與少數民族交流交融,漢族人獲得了數量較多的馬、牛、羊,畜牧業得到發展,牛羊肉菜點增多,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肉食不足,補充了肉類蛋白質、B族維生素等,改善了飲食結構,促進了漢族人體健康發展;而藏族、蒙古族則獲得了一些蔬菜、水果和茶葉,農業得到發展、植物食材增加,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蔬果的不足,補充了維生素C、膳食纖維等,也改善了飲食結構,促進了藏族、蒙古族等群體健康發展。清代張繼《定瞻廳志略》載,瞻對(今甘孜州新龍縣)等地,“菜蔬則羊芋、萊菔、圓根。圓根,用處最多,人畜皆食,種者甚多。蔥、蒜苗、白菜、蓮花白,則漢民種而食者也。”[25]可以說,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食材交流交融是不可或缺的要事,進而成為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蓬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以飲食制度、飲食思想和飲食習俗而言,漢族在先秦時期提出“醫食相通”的飲食制度和“藥食同源”飲食思想,唐代時提出系統的食療養生思想,到元代時則由蒙古族、回族吸收借鑒并進一步發展。《周禮·天官》“冢宰”載,周代宮廷設有四種不同職責的醫官,“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麥,魚宜蓏。”[26]食醫負責調配王室貴族飲食的寒溫、滋味、營養等,類似于當今營養師,并且常根據四季不同搭配不同食材。《黃帝內經》論述了“藥食同源”思想,不僅提出“養助益充”的飲食養生思想和飲食結構,還在《素問》《靈樞》中專門論述飲食五味與人體臟腑的關系,強調飲食五味對五臟有補益作用、但過量則損傷臟腑。唐代時,孫思邈在《千金要方·食治》首次提出系統的食療養生思想,強調飲食配膳的宜忌等。其《千金翼方》收載研制了“豬肚補虛贏乏氣力方”等許多食療方,注重葷素配搭和調味。到元代時,以蒙古族為主的宮廷采用了“醫食相通”的飲食制度和“藥食同源”等飲食思想。回族人忽思慧作為宮廷飲膳太醫,負責宮中飲食調理、養生療病等事,非常重視食療與食補實踐,通過整理、總結歷代宮廷食療經驗,并集元代以前飲食養生學之大成,編撰出《飲膳正要》。該書共三卷,卷一載“養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飲酒避忌”“聚珍異饌”等六部分九十五方,卷二載“諸般湯煎”五十六方、“神仙服餌”二十六方、“食療諸病”六十一方以及“四時所宜”等內容,卷三載有谷物、禽品、魚品、果品、菜品、料物等原料200余種,始終貫穿“食療養生”“藥食同源”思想,又有所發揚光大。該書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飲食養生學專著,對“藥食同源”飲食思想的繼承和創新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促進了中國飲食文化發展和各民族人民身體健康。
三、結語
綜上所述,元明清時期,漢族與少數民族飲食文化的交流交融,具有雙向互動、雙層兼備、互鑒創新的特點,相互之間傳播、吸收與借鑒,既涉及食材、飲食品種等物質文化層次,也涉及飲食習俗、禮儀與飲食思想等非物質文化層次。元明清時期的多民族飲食文化交流交融具有十分重要的雙重作用,既是各民族飲食文化創新發展的動力源,又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蓬勃發展的助推劑,漢族廣泛地吸取借鑒少數民族飲食文化的精華并加以融合創新,也將自身的飲食文化傳播到其他民族地區,兩者相互吸收借鑒與融合創新,不僅豐富和發展了各民族的飲食文化,共同創造了傲然于世、聞名遐邇的中華飲食文化,而且使各民族人民更加相互依存、水乳交融,如一顆顆石榴籽一樣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緊緊相擁、共同奮斗、共同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斷牢固壯大、走向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