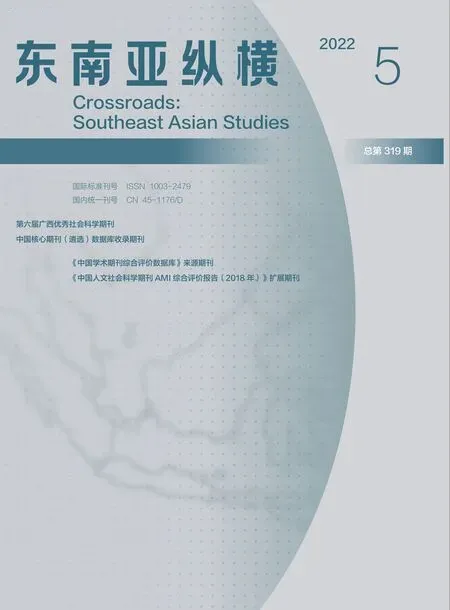中國—東盟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產權惠益共享問題研究
黃 捷
中國—東盟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資源豐富,很多非遺存在同源的關系,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逐漸成為中國與東盟合作的一個重要領域。加強中國—東盟非遺交流與共享,強化非遺知識產權保護,有助于推進雙邊關系全面發展。《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拓寬了中國—東盟非遺合作的空間,更有利于實現雙方互利共贏①見《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第35條、第37條、第39條。。建設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需要不斷推進中國—東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區域一體化。
一、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的發展前景和現實基礎
(一)中國—東盟知識產權區域一體化發展是惠益共享的基礎
推動中國—東盟建立區域一體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中國—東盟共建共治共享惠益的現實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開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則,深度參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框架下的全球知識產權治理”,“要深化同共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知識產權合作,倡導知識共享”①習近平.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激發創新活力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J].求是,2021(3):4-8.。隨著中國與東盟各國在非遺方面的合作與交流不斷加強,僅在中國或者東盟某一國家對非遺進行知識產權保護,無法實現資源的利益最大化,不利于非遺知識產權的惠益共享。目前,中國—東盟的合作已經從經濟領域伸延到文化領域,區域一體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是開展非遺傳承、活化利用等合作與交流的保障,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成為發展對外文化貿易的重要途徑。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構建了中國—東盟非遺資源跨境保護的框架,中國與東盟各國可以在中國—東盟區域一體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中實現互惠互利、合作共贏。以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的跨國流動保護為基礎,推動知識產權區域一體化建設,是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共建共治共享惠益的有利條件。
中國—東盟各項知識產權合作協議的簽訂是中國—東盟區域一體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立的法律基礎。1995年東盟成員國簽署的《東盟知識產權合作框架協議》,對東盟知識產權合作的目標、原則、范圍以及活動的審查等內容作了相關規定,是東盟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法律基礎和制度框架,強化了知識產權區域保護。盡管該協議沒有限定知識產權保護的具體范圍,但將非遺納入知識產權制度保護的范圍,是東盟國家之間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的具體內容和治理路徑。中國—東盟文化區域一體化發展趨勢推動了中國—東盟知識產權區域一體化發展的進程,拓寬了中國—東盟知識產權合作的領域。在《東盟知識產權合作行動計劃(2016—2025)》中,通過實行東盟知識產權規劃,加強東盟區域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推動了中國—東盟對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的進程。《落實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聯合宣言的行動計劃(2021—2025)》提出,共享物質和非遺管理知識,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專門知識交流;落實《中國—東盟知識產權合作諒解備忘錄》,加強知識產權領域合作;鼓勵東盟成員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積極推進中國—東盟在國際知識產權體系建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等。“一帶一路”建設強調把中國的發展同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聯系起來,通過各國之間的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推動沿線國家不斷朝著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邁進②宋才發.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解析及全球化治理探討[J].黨政研究,2019(3):54-64.。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與東盟水陸相通,東盟各國之間利益高度融合,非遺交流合作成為引領中國—東盟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力量。推動區域一體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發揮了橋梁紐帶作用,構建互利共贏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為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惠益共享創造條件,也為中國—東盟非遺保護提供了現實的法律合作基礎。
(二)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是中國—東盟關系發展的重要紐帶
區域一體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建立的有效保障,促進了中國—東盟的文化交流深入發展。中國—東盟重視多邊文化交流,積極參與區域合作,通過中國與東盟(10+1)、東盟與中日韓(10+3)和國際文化公約等層面的合作不斷深化多邊文化交流③李紅,彭慧麗.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與東盟文化合作:發展、特點及前瞻[J].東南亞研究,2013(1):101-110.。中國—東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體現出共享的統一發展與協調發展,非遺獲得知識產權保護是雙邊惠益共享的基礎,建立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可以有效促進中國—東盟非遺最大化利用。
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建立的制度基礎,為中國—東盟雙邊關系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環境。新時代背景下,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規則、保護方式等要有新的發展定位和目標,需要不斷提升知識產權區域和國際合作水平①管榮齊.新時代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化對策[J].學術論壇,2019(4):36-44.。中國—東盟文化交流日益加強,若非遺無法獲得知識產權的全面保護,對非遺進行傳承和活化利用的知識產權人無法獲得相應保護,市場就無法通過資源配置補償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將會打擊知識產權人的創造積極性,進而影響中國與東盟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發展。
中國—東盟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下的非遺惠益共享、非遺保護多元共治、非遺發展環境共建,能夠最大化實現合作共贏。當前,中國正致力與東盟國家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通過加強文化交流為紐帶實現非遺知識產權的惠益共享,對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非遺資源豐富,具有極大的產業潛能,對非遺資源進行知識產權保護迫在眉睫。為此,中國與東盟國家都采取了相關措施,通過立法保護非遺,共同維護非遺資源的利益取向,尋求雙邊在非遺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共同利益。
(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促進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實現的有效途徑
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拓寬了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的途徑。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促進了文化交流、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通過明確知識產權人的專有權,為中國—東盟非遺交流提供了有效途徑,以激勵機制激發知識產權人創造更多的知識財產,為中國與東盟各國獲取和共享非遺信息提供有利的資源基礎。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重要內容,通過激勵機制充分地激發知識產權人為社會創造更多的知識財產,不斷滿足社會對知識財產的需求,促進知識財產在社會上的傳播,推進文化的交流和社會的進步。《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簡稱TRIPS)以發達國家現代知識的發展水平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標準,是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利益訴求的重要體現。TRIPS保護的范圍主要是現代知識產權,而非遺并未納入其保護范圍,只有非遺的表現形式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標準,才能納入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基于非遺的傳承性和特殊性,中國與東盟各國可以通過推進區域一體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來發揮資源優勢和發展優勢,以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基礎,不斷深化中國—東盟非遺的交流與合作,通過建立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實現雙邊互利共贏。非遺獲得知識產權保護,是對其傳承和活化利用的保障,也是實現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的重要內容。知識產權是非遺權利人獲得保護的基礎,區域一體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的建立提供了制度基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非遺共享與專有之間尋求平衡,強調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平衡與協調。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授予了知識產權人對知識財產的專有權,這種專有權與非遺的特殊性具有社會價值和目標的一致性。合理限制知識產權人的專有權有利于實現知識產權人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平衡。
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逐步向區域一體化趨勢發展,成為中國與東盟各國互利共贏的重要保障。隨著文化全球化發展,中國—東盟之間的文化合作與交流日益加強,非遺的輸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東盟文化交流的進程,成為文化資源互補的保障。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中國—東盟非遺交流提供了制度基礎,有效保障了知識產權人的權益,促進了非遺的傳承與活化利用。中國—東盟對非遺進行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日益增強,它的跨國保護有效推動了中國—東盟知識產權的區域一體化發展。實現中國—東盟非遺跨國保護,強化中國—東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協調發展,規范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和標準,是推動中國—東盟知識產權區域一體化建設的重要手段。非遺知識產權的惠益共享由區域內國內合作向區域內國際合作擴大,推動知識產權保護區域一體化,協調非遺知識產權保護在區域內的矛盾和沖突,是區域一體化發展的需要和制度發展的趨勢。加強中國—東盟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合作,有助于協調發展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和提高中國—東盟知識產權的一體化程度①高蘭英,宋志國.《2004—2010年東盟知識產權行動計劃》及實施述評:兼論其對構建中國—東盟知識產權合作機制的啟示[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79-85.。
惠益共享打破地域的局限,以中國—東盟區域一體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構建為基礎,通過共享非遺知識產權實現文化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保護。共享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能夠傳播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非遺,鼓勵知識產權人通過非遺的傳承與活化利用推動創新發展。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的目標是促進非遺保護、傳承、發展,若非遺無法獲得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社會其他成員可以任意使用非遺,非遺傳承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其積極性和創新性將會受到影響,最終會阻礙中國—東盟非遺的傳承和發展。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如何在中國—東盟非遺惠益共享中維持知識產權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利益平衡及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的利益平衡,需要進一步探討。
二、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建立存在的問題及其根源
(一)非遺傳承的共享性與知識產權保護的專有性相沖突
非遺獲得知識產權保護在一定程度上會制約非遺的共享,進而影響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的實現。實現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需要有豐富的非遺資源作為基礎,然而中國與東盟各國對非遺的保護制度各不相同,部分非遺無法在彼此之間自由流動,部分經認定的非遺是知識產權保護的智力勞動成果,未經知識產權人的許可,不可以隨意使用。經世代相傳的非遺大部分處于共享狀態,一定程度上與非遺知識產權專有性保護的目的相背離。
非遺傳承的共享性在中國—東盟文化交流中日益發揮重要作用,但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的專有性使其傳承的共享性難以得到全面實現。非遺是文化交流、文化合作與文化利用的重要資源,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有利于實現非遺資源的優化配置,為中國—東盟的非遺保護、傳承、發展提供了有利的交流平臺和實踐基礎,是中國—東盟之間文化交流合作日益增強的重要標志。中國與東盟在長期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了相似的文化,使得中國與東盟不少國家的非遺具有相似性。但是,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的專有性制約了非遺在中國—東盟傳承的共享性,使得這些具有相似性的非遺難以獲得有效傳承。
知識產權保護的專有性和獨占性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的空間。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建立在資源自由共享、資源自由流通、資源自由獲取等基礎之上,在一定前提條件下可以獲得使用資格。非遺的跨國傳播體現了文化多樣性發展的目標和需求,促進了文化資源共享的發展。地域性是非遺獲得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屬性,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遺獲得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范圍。中國—東盟構建區域一體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有利于實現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由于中國與東盟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水平不同,對非遺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措施存在差異,這些因素制約了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的發展進程,而跨境的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又使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的專有性和獨占性的實現受到影響。此外,由于中國與東盟各國對本國非遺的知識產權保護訴求各異,使得在非遺合作與交流中產生博弈和沖突,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非遺應有價值的利用,影響了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的實現。
(二)中國—東盟非遺活化利用缺乏利益保障機制
非遺保護已經成為中國—東盟國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但由于缺乏利益保障機制,中國—東盟非遺的活化利用難以得到合理的補償和回報。目前,中國—東盟非遺的價值沒有得到充分認識,而且非遺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足,部分使用者沒有給予非遺傳承人、來源性群體、族群、傳統社區等主體相應的報酬,并通過申請知識產權保護的方式來獲得利益,損害了相關利益群體利益分享權。根據現行的法律制度,難以向非遺資源的利用者追償利益,導致非遺資源的價值得不到合理的利益回報①楊巧.知識產權國際保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25.。
中國與東盟國家擁有豐富的非遺資源,部分非遺資源的利用者對非遺進行加工利用并獲得知識產權,在文化市場中獲取經濟利益。但部分非遺資源的利用者并沒有給予中國—東盟非遺資源的來源地或者來源國利益分享,損害了非遺來源地或者來源國的利益。因此,對非遺進行知識產權保護能更好地實現非遺的利用價值,通過建立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保障非遺的利用價值得到合理的回報,能更好地保護中國—東盟非遺資源,促進文化多樣性與可持續發展。
(三)中國—東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差異限制惠益共享的范圍
中國與東盟各國對非遺知識產權保護模式的差異,增加了非遺資源提供者或者提供國獲得惠益分享的難度,使得非遺持續利用與發展的范圍受到影響,也給知識產權保護區域一體化建設帶來挑戰。中國與東盟各國對本國非遺保護的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中國—東盟非遺的知識產權保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遺的創新發展和進一步挖掘,阻礙了知識產權保護的一體化建設的進程。中國與東盟各國在制定本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方向和模式上都存在較大的差異。譬如,在商標權保護方面,在商標權的保護范圍、馳名商標的認定和地位等存在差異;在專利權保護方面,在專利權的保護期限、專利權的客體等的規定各異;在著作權保護方面,中國與東盟在對合理使用的界定范圍上存在一定的差異。由于中國與東盟區域內沒有規定最低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中國和東盟各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增加了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的難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非遺在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有效的利用和流動,導致制定區域一體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相對困難,使得非遺缺乏惠益共享的機制框架和合作基礎。因此,通過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建立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平衡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利益追求,才能從制度上協調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差異。
三、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的設計
(一)確立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的原則
1.利益平衡原則
利益平衡是知識產權法價值構造的內核②馮曉青.知識產權法的價值構造: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機制研究[J].中國法學,2007(1):67-77.,平衡中國—東盟非遺的利益成為構建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的基礎。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各異,使得中國與東盟各國對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的利益訴求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非遺獲得知識產權跨境保護的難度,凸顯了中國—東盟在非遺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利益失衡。中國—東盟的不同主體出于不同目的和需求,對非遺進行營利性與非營利性使用,通過平衡中國—東盟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強化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更有利于非遺的跨國流動。從利益均衡角度上來看,非遺傳承群體若沒有獲得利益或者獲得較少利益將會違反分配正義,因此在利益分配中應當考慮給予其適當的利益。堅持在充分尊重各國國情的基礎上開展知識產權的交流與合作,充分帶動知識產權保護相對滯后的國家①李曉鳴,翟全軍.“一帶一路”建設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J].云南社會科學,2019(5):45-51.,適當給予支持和幫助,使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保護得到協調發展。
2.國民待遇原則
國民待遇原則可以協調中國—東盟對非遺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差異。目前,《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及其他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均確立了國民待遇原則。在非遺知識產權保護中,遵循國民待遇原則可以有效協調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和局限性,締約國的外國國民和本國國民享有同等的權利,負擔著同等的義務。中國—東盟遵循國民待遇原則,有利于建立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中國—東盟依據國民待遇原則保護各國的非遺,平衡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使非遺在中國—東盟實現知識產權的跨國保護。部分東盟國家制定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協調其他東盟國家享受成員國國民待遇,其他成員國將不斷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這為建設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提供了有利的基礎。
3.國家主權原則
國家主權原則是非遺國際保護的重要原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16條規定:“為了擴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響,提高對其重要意義的認識和從尊重文化多樣性的角度促進對話,委員會應該根據有關締約國的提名編輯、更新和公布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充分體現了國家主權的地位和意義,強調了國家對其領土內的非遺負有保護的義務和享有管轄的權利,其他國家、國際組織不得干涉其中。當某一國未能履行義務保護其非遺時,國際社會有權采取措施保護該國的非遺。某些進入公有領域的非遺,由于傳承人的相關權利空缺,國家可以作為權利主體,行使傳承人的相關權利。在中國—東盟進行非遺交流時,為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應當遵循國家主權原則,國家在特定情況下作為非遺的權利人有利于非遺的保護,也更有利于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的構建。
4.文化多樣性原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2001年)、《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2005年),為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指出了文化對于社會群體的重要價值,文化多樣性的構成形式、表現形式及重要價值。中國—東盟在長期的文化交往中即形成了文化特征的相似性,也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差異性,這凸顯了中國—東盟文化多樣性的發展狀態與趨勢②韋永貴,李紅,牛曉彤.中國—東盟文化多樣性與相似性測度及其投資效應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9(2):45-57.。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非遺交流是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的具體方式,從整體上促進了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文化多樣性發展是中國—東盟文化交流的目的之一,為非遺的傳承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東盟非遺的合作交流與文化多樣性共生發展,可促進中國—東盟非遺交流、傳播、創新,進而從整體上實現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同時,豐富中國—東盟文化交流的內容和形式,可為非遺的惠益共享提供文化多樣性發展的有利基礎,進而促進中國—東盟文化多樣性與可持續發展。
(二)探索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機制的程序規則
1.惠益共享的基礎:合理界定惠益共享的規則
合理界定中國—東盟非遺惠益共享規則是中國與東盟各國獲得非遺共享利益的重要前提。惠益共享的規則構建具體為,以授權許可作為共享惠益的界定。非遺的國際交流與商業發展需要惠益共享機制調節惠益的獲得,通過制定中國—東盟授權許可規則,明確授權的條件與范圍。中國—東盟非遺利用授權許可規則的確立主要體現在:一是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商業化利用非遺的重要保障;二是平衡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利益;三是實現中國與東盟之間非遺的惠益共享。在中國—東盟授權許可規則構建中,通過體系化的管理制度實現東盟非遺資源共享。中國—東盟可以積極協商并進行雙邊協調,在雙邊授權許可的前提下建立雙邊非遺知識產權共享機制,并將雙邊認可且受知識產權保護的非遺納入非遺資源共享機制。為促進惠益共享機制的創建,可以設立管理組織對中國—東盟的非遺授權許可進行統一管理,建立中國—東盟非遺資源共享數據庫,促進中國—東盟在非遺資源共享方面的項目合作,集中對中國—東盟授權許可共享的非遺進行管理,以集中管理作為各國雙邊惠益共享機制的有效保障。
2.惠益共享的保障:設立特別登記程序
進入公有領域的非遺可以通過設立特別登記制度獲得惠益共享。知識產權保護具有期限性,當非遺獲得知識產權保護的期限屆滿就會進入公有領域。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利用中國—東盟非遺資源,使非遺的來源性群體獲得共享利益,可以通過設立特別登記機制延續來源性群體的專有權。依據利用目的,具體分為兩種備案登記情況。一是對中國或者東盟某國非遺的使用以傳承和保護為目的的,向非遺來源地登記備案即可,無需付費。在中國—東盟文化交流中,往往因新聞報道、文化交流、學習知識等以傳承和保護為目的使用中國或者東盟成員國進入公有領域的非遺,為實現中國—東盟雙邊惠益共享的目的可設立特別登記程序,即使用者向非遺來源地備案登記并說明使用目的、使用范圍、使用方式。二是以商業利用為目的使用中國或者東盟成員國進入公有領域的非遺,為保障來源地群體的利益,需向非遺來源地登記備案并支付相應的費用。譬如,為保障原住民和當地文化社區的利益,菲律賓制定了《土著人權利法案》,對當地文化社區享有利益分享權作了明確規定。特定社區的傳統知識在商業利用中所獲得利益的,該特定社區基于其地位有權在10年的期限內按照適當的比例分配獲得利益。特定社區所獲得的收益由特定的組織管理,如無特定組織管理的,則由國家管理①黃玉燁.民間文學藝術的法律保護[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112-118.。探索中國—東盟非遺惠益共享特別登記機制,可以借鑒菲律賓對當地文化社區權益的保護模式,對中國與東盟各國領域內進入公有領域的非遺進行登記保護,細化惠益共享機制的規則。對來源地進入公有領域非遺進行商業化利用的,在一定的年限范圍內按照適當的比例分享因利用非遺所獲得的商業利益,特定的來源性群里所獲得的收益由該來源性群體所在國管理。
(三)構建多元一體與協調的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保護機制
1.建立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保護協調機制
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保護協調機制的建立應從協調中國—東盟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尋求突破,探索建立中國—東盟區域內統一的知識產權登記機構,通過構建協調機制實現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惠益共享。一是制定優先注冊權機制。中國或東盟某國的權利人基于該國某項非遺向該國申請知識產權保護并獲得登記或者注冊的,該知識產權人享有優先在中國—東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登記或者注冊的權利;中國或東盟某國的權利人基于該國某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申請中國—東盟知識產權保護并獲得登記或者注冊的,該知識產權人享有優先在該國登記或者注冊的權利。優先注冊權的享有以獲得在先知識產權為前提,在先知識產權包括中國—東盟區域知識產權和中國—東盟成員國國內知識產權。二是設立轉換申請機制。中國—東盟區域知識產權和中國—東盟成員國國內知識產權基于不同的法律制度取得知識產權保護,所取得知識產權的法律效力各不相同。轉換申請制度是以單向轉換的形式保護中國和東盟各國非遺的知識產權,以非遺為基礎申請中國—東盟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失敗的情況下,不影響其再申請其國內知識產權保護。
2.制定多元一體化的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保護機制
通過制定有別于傳統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的中國—東盟特殊的非遺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實現區域內非遺知識產權的惠益共享。中國—東盟以制定區域一體化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為共享惠益的有效保障,防止非遺資源的濫用和盜用,最大限度保護中國—東盟區域內非遺。譬如,歐盟建立了區域一體化的知識產權體系,但歐盟區域內并沒有建立統一的著作權制度,它主要根據具體的問題確立相應的著作權保護標準,以指令的方式解決歐盟各成員國著作權制度的差異,要求成員國通過轉化的方式將指令融入國內法中。歐盟對著作權一體化的建設采取精神權和財產權分開保護的模式,精神權主要以各成員國國內法的規定保護,財產權主要采取一體化立法強化著作權一體化建設。在商標權領域,歐盟各成員國國內商標法律制度和歐盟跨國商標法律制度并行,并通過設置優先注冊權制度、轉換申請制度、共同體商標特有的訴訟管轄和法律適用制度等機制協調這兩種法律制度運行①朱雪忠,柳福東.歐盟商標法律制度的協調機制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中國法學,2001(4):152-161.。中國—東盟可以借鑒歐盟的立法模式,在區域范圍內制定非遺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中國—東盟通過促進中國與東盟成員國多元化的國內立法融合實現區域知識產權制度的統一。1995年,東盟各國在泰國簽訂《東盟知識產權合作框架協議》,合作的范圍主要包括現代知識產權②《東盟知識產權合作框架協議》第3條第1款規定:東盟知識產權合作的重點領域包括著作權及其相關領域、專利權、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地理標志、未被披露的商業秘密及集成電路外觀設計等方面的內容。,為構建多元一體化的中國—東盟非遺知識產權保護機制提供了制度框架。《東盟知識產權合作框架協議》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知識產權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是中國與東盟知識產權一體化建設的基礎,中國與東盟各國國內法的多元化是中國與東盟各國非遺獲得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保障。由于知識產權的屬地性,中國和東盟各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利益訴求各異,以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國內立法作為相互借鑒的參考,通過多樣性與統一性融合建設區域知識產權一體化,有效化解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知識產權制度的沖突,有利于形成統一的知識產權制度;以保護和傳承中國—東盟的非遺為基礎,可以通過在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等知識產權領域采取分別立法的模式,對于不同領域的知識產權進行區別化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