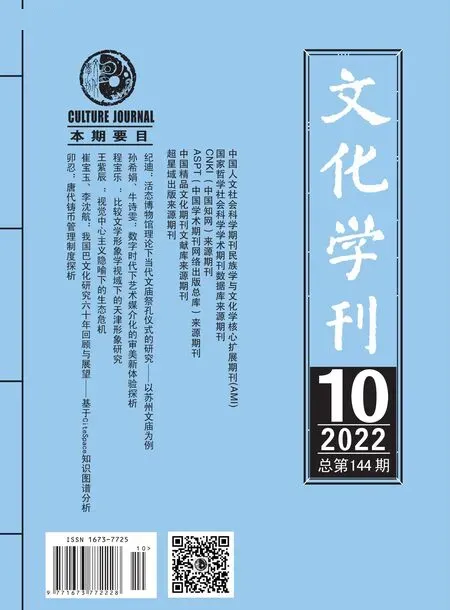淺議洛陽橋的歷史格局與價值
梁少金 吳 安
洛陽橋,又名“萬安橋”,始建于北宋年間(1053—1059),位于福建省閩南金三角之泉州市東郊約10公里處,橫跨晉惠二邑,雄峙于洛陽江萬頃碧波之上。洛陽橋是中國宋代第一座梁式海港大石橋,其中的“筏型基礎”“種蠣固基”等在全國均屬于具有高度價值的建筑發明;該橋被列為我國“四大名橋”之一,在我國橋梁歷史發展中一直占據著重要位置,深受人們的歡迎和喜愛。
一、洛陽橋的歷史格局演變
洛陽橋又稱萬安渡橋,該橋建成前只能以船只擺渡交通兩岸。北宋慶歷年間在此架設浮橋通行,蔡襄于北宋嘉祐元年—四年(1056—1059)督造萬安橋,自此揭開一段洛陽橋與洛陽港的盛衰史,洛陽橋的歷史演變可劃分為始建、擴建、破壞和保護四個時期。
(一)始建時期:北宋至南宋
北宋皇祐五年(1053)至嘉祐四年(1059)洛陽橋建成,包含洛陽橋橋體360丈(宋尺折算約936~1116米)、石像4座、塔8座、中亭(泗洲亭)和義波真身庵。據史料記載,自洛陽橋建成至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共193年間,洛陽橋共重修五次,均由郡守主持,但無碑刻紀文留存。自始建至南宋末年,洛陽橋格局有以下變化:在洛陽橋橋體中部建濟亨亭;遷建與興建數座洛陽橋相關紀念和祭祀建筑,將橋北萬安橋院遷建于洛陽橋南,移泉州府放生池于洛陽橋畔[1]宣和年間(1120—1125)始建蔡忠惠公祠;淳祐元年(1241)賜額“昭惠”,將鎮海庵改稱昭惠廟;距昭惠廟數百米處后人建義波真身庵紀念筑橋有功的義波和尚;在洛陽古街東北段北側建古井禪寺奉祀觀世音菩薩,以祀觀音大士顯靈相助施茶藥保造橋工役民夫安寧。至此,洛陽橋與紀念、祭祀建筑形成的核心主體格局基本形成,其中洛陽橋與蔡忠惠公祠、昭惠廟、義波真身庵的格局一直延續至今。
元代可供查閱的文獻較少、記載也較少,零星記載橋中始建泉南佛國亭、橋南建契監郡祠,其余未得其詳。
(二)擴建時期:明至清末期
自洪武初年至崇禎末年共276年間,洛陽橋共重修七次,主要由知府主持,亦有郡人資助參與。明代洛陽橋格局有以下變化:洛陽橋橋體增高三尺,并于橋南修建徐公閘,于蔡忠惠公祠西側建蔡善繼祠;于中洲修建西川甘雨亭、洛橋新城、鄭虎臣廟、萬公祠、建祠(姜生祠)豎華表、牌坊;于洛陽橋南北兩端增筑鎮風塔兩座;于橋北側昭惠廟前建蔡錫祠;于昭惠廟北側建寧公生祠;洛陽橋紀念性建筑蔡襄祠重修五次,昭惠廟重修三次。
《洛橋新城記》碑記中記載了洛橋新城的形制與規模:“兵憲育吾萬公,為行營時所筑也,人謂之‘防倭第一城’,輸運廢橋各處石,又砍近山諸石以輔之,而間市所得木為樓屋,不旬曰城成,咸稱洛橋新城,城南門曰萬全,以通晉江也;城北門曰萬勝,以通惠安也。蓋因萬安橋美名,又用萬公姓以志不忘云”[2]。
清代共296年,據文獻可知,洛陽橋共重修了九次,主要由知府、縣令、總督、大學士等主持,清代洛陽橋格局有以下變化:于洛陽橋橋北昭惠廟前建夏將軍廟(后毀),沈汝瀚題“海內第一橋”石匾[2],重修蔡忠惠公祠三次,重修昭惠廟兩次。
(三)破壞時期:民國時期
民國是洛陽橋破壞時期,千年古橋屢遭厄運,有過十九路軍之改建以及地方政府之破壞。一是蔡廷鍇改建橋面,改洛陽橋為鋼筋混凝土路面,并向兩側拓寬橋面至7米,以利通汽車;二是全國抗戰開始,地方官吏竟下令將各地公路及橋梁加以破壞。郡人為便行旅,乃募資購置木板,覆蓋于人工破壞之橋面洞孔處,保護洛陽橋。
(四)保護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共73年,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政府即著手維修保護。依次將洛陽橋確立為福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7月25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貿易中心”的文化遺產點,前后進行了三次修繕,整治周邊環境,并在洛陽橋西側修建公路橋,以減輕洛陽橋負擔;重修蔡忠惠公祠三次,重修昭惠廟三次,重修義波真身庵四次。
洛陽橋自北宋始建至今,完整保存了洛陽橋橋體、塔、亭與紀念建筑為一體的歷史格局,現存橋體長731.29米,寬4.5米,橋墩45座,欄桿石柱500根;保存有中亭、甘雨碑亭(中有“西川甘雨”石刻)2座橋亭;現存橋南端東側石塔、橋南端西側石塔、橋北端東側石塔、橋北端西側石塔、洛陽橋中段西側石塔、中洲西北側石塔、中洲東南側鎮風塔(上有“鎮風塔”石刻)共7座橋塔;護橋石雕神像4座;完整保存蔡忠惠公祠、昭惠廟、義波真身庵、古井禪寺等四座紀念建筑,古井5口,以及大量碑刻[3]。
二、洛陽橋的價值
(一)洛陽橋的建造是北宋泉州對外貿易繁榮、泉州港擴建的產物,是宋代泉州的商貿活動與海外交通發展的重要歷史見證
在北宋時期,泉州的經濟貿易發展就呈現出了海洋化趨勢,泉州也成為了重要交易港口之一,洛陽橋的建造與當時社會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聯系。洛陽江下游是宋代泉州港的一個內港,這一帶的烏嶼是孤立于江中的一個島嶼,港道深邃,為從海上到洛陽橋的海舶必停之處,船停后再由駁船轉運貨物。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宋代先后建造了洛陽橋、盤光橋,兩座橋之間的距離較近,整體呈現出了比較壯闊的景象,充分說明了當時以烏嶼為中心的洛陽小海經濟的繁榮。洛陽橋是在泉州海洋貿易繁盛的時代背景下,泉州地區開始普遍性地造橋活動的典型代表。洛陽橋建成之后為當地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提供了蓬勃生機,是海外交通技術發展的有力保障。
(二)洛陽橋是我國宋代第一座海港梁式大石橋,首創“筏型基礎”“種蠣固基”“浮運架橋”造橋技術,在中國橋梁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揭開了隨后而來的南宋建橋高潮,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在中國橋梁史上,洛陽橋與趙州橋并駕齊驅;洛陽橋在我國甚至世界橋梁歷史發展進程中都發揮著重要價值,占據著重要位置。對外貿易的擴大和經濟水平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洛陽橋,為洛陽橋的發展建設提供了切實保障,也讓洛陽橋的歷史格局和價值涵蓋了更深層次的底蘊。歷代泉州地區有記載的建橋有149座,注明為南宋時建或南宋時修的有117座[4],“總長度達萬丈以上(五六十里)”,其中高峰期為“紹興年間”。這一時期建設的橋梁在歷史上都留下了重要影響,絕大多數橋梁都建在海灣或濱海之上,貫串福州、閩南等多個城市,對這些城市的交通規劃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滿足了當時我國對外海洋貿易的切實需求。
(三)伴隨洛陽橋的建造和歷代的修葺而涌現出眾多祠廟,大多祭祀歷代修建洛陽橋有功者,每座祠堂廟宇的由來就是一個歷史人物被神化的過程,反映出中國傳統社會多神崇拜以及儒、釋、道雜糅的宗教文化特征
歷代以來在洛陽橋橋北有昭惠廟、義波真身庵、古井禪寺、蔡錫祠、夏將軍廟、寧公生祠、陳公祠,在中亭附近有鄭虎臣廟、萬公祠、姜公生祠、觀音廟,在橋南有蔡忠惠公祠、萬安橋院、蔡繼善祠、輿慶堂、契監郡祠。今存昭惠廟、義波真身庵、古井禪寺、蔡忠惠公祠,為當代重修。這些祠廟大多祭祀歷代修建洛陽橋有功者,有著濃厚的宗教神秘色彩。此外,每座祠廟的由來幾乎就是一個歷史人物被神化的過程,現今這些祠廟還兼有儒、釋、道各家色彩,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多神崇拜以及儒、釋、道雜糅的宗教等文化習俗特征[5]。
(四)通遠王在我國歷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被稱為第一代海神,前后有400多年的時間被高度關注和重視,其中昭惠廟是歷史重要見證之一
眾多歷史資料中都記載了“通遠王”的來源和發展,認為其是從洛陽橋頭的昭惠廟開始發展的。據載,萬安橋未建時,《泊宅篇》中說古萬安渡“水闊五里”,《閩書》中說“深不可址”,一遇狂風,則“沉舟被溺死者無算”[6],泉州人李寵首先在江中建造了幾個石墩,加上木板,作為浮橋。北宋皇祐五年(1053)正式開始建設洛陽橋,在剛開始建設洛陽橋時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工程比較浩大,加上自然環境的影響,再加上當時比較信奉神明,于是將通遠王作為精神支柱。乾隆《泉州府志·卷16》說:“昭惠廟在萬安橋,北宋郡守蔡襄建。……”《隆慶府志》中清楚記載了通遠王的形態、衣著等顯著特征,尊稱其為海神,顯赫達400多年,被譽為“其靈之著,為泉第一”。這也是通遠王從山神進化為雨神再進化為海神的重要史料。所以,洛陽橋的歷史格局和價值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和對外海洋貿易方面,在其中也延伸出了很多民間文化信仰。
(五)洛陽江為泉郡北面天然屏障,萬安渡乃南北交通孔道,形勝天成,洛陽橋的建成則打通了此處的南北交通,跨洛陽橋、循洛陽江均可直取泉州,是泉州海防軍事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具有極其重要的軍事地位
洛陽江集晉、惠兩邑諸山眾多溪流之水,匯成滔滔洪流而成“洛江天塹”,實乃泉郡北面天然屏障;而萬安渡為南北交通孔道,形勝天成,具有極其重要的軍事地位。倭寇循江而入,沿橋以進,數犯郡畿。明嘉靖年間,萬僉憲民英將軍于洛陽橋中洲興筑“洛橋新城”以御倭寇,并大敗倭寇于洛陽橋,使倭寇不敢再循橋而東以掠泉州;明代鄭成功與清兵爭戰,亦嘗斷洛陽江萬安橋以相抗衡;至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也曾斷橋數次,以防日寇長驅直入。
(六)洛陽橋是中國宋代第一座海港梁式大石橋,其中很多先進的建橋技術在今日依舊廣為流傳,被很多建筑人所借鑒,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傳承意義
1.洛陽橋建于“水闊五里,深不可址”的江海交匯處,是中國宋代第一座跨海梁式大石橋。筏型基礎就是沿橋基的直線,在江心深水處首先應用壘石、匝石、疊石,形成一條橫跨江底的矮石堤,作為建橋立墩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造形似小船的橋墩,以分流大水的沖擊力度。這就是現代稱之為“筏形基礎”的橋基,也是洛陽橋重要的基礎。
2.《宋史·蔡襄傳》載:洛陽橋“種蠣于礎以為固,至今賴焉”。即將繁殖于江邊石上的牡蠣引附于江底基石和橋墩上,讓其繁殖,對于整個橋身有著穩固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關鍵部分,逐漸成為歷史上橋梁建筑中的首個創舉。
3.“浮運架梁”在900多年前造洛陽橋就得以應用。明人王慎中《泉州府萬安橋記》載:“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牽”;姜志禮所記:“舟至泊于橋”“乘潮長而上”“懸羅拿石,一繩千鈞”。“浮運架橋”法的具體施工辦法“石由陸路拉到海邊,乘漲潮時船駛到灘地,潮退船擱淺,用跳板拖石梁上船待潮漲船浮,運到橋址梁孔之間……墩上扎了獨角把桿豐碑或人力把桿釣桿。掛穿滑車懸機從船上吊起石料,抽走船只,慢慢吊放石梁弦牌”[7]。
三、結語
洛陽橋與留存至今的大量碑刻真實記錄了洛陽橋自身的發展與演變過程,也真實記錄了歷代郡守、僧人、名人在各個歷史時期對洛陽橋陸續修建、修繕及在此修行的歷史事件及其歷史環境。洛陽橋歷代以來為文人騷客揮題吟詠,與周邊的歷史環境形成八景之勝即:“海內第一橋、洛江雙虹、清源倒影、中亭映月、洛陽潮聲、龜蛇鎮江、西川甘雨、松不過墻”,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洛陽橋造橋的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有的搬上戲曲舞臺、熒屏、畫壇,成為傳統題材,創作出許多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對當地文學藝術領域產生了比較深刻的影響。
洛陽橋上的月光菩薩與洛陽橋相守千年,相約看盡這人世煙火繁華,潮起潮落間已歲歲年年,月光遍照千年情,洛陽相守孤月輪!慶幸歷史留給了我們洛陽橋,歷史的每一步進程都是鮮活生命的展開和飽滿感情的抒寫,在新時代、新形勢下我們正在努力保護這座千年古橋,讓其繼續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為共和國的精神文明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