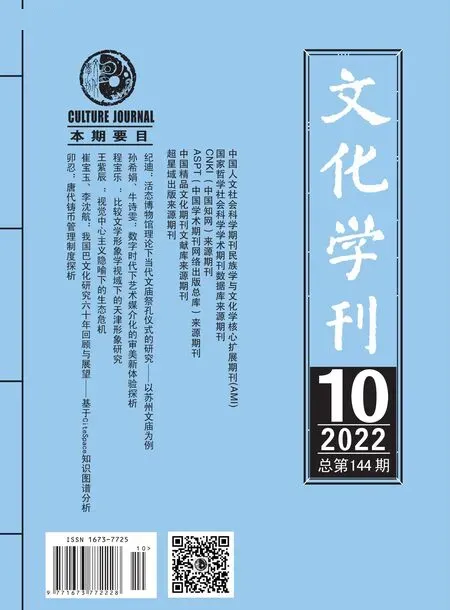基于儀式理論的杭州傳統節日休閑開發
——以中秋節為例
何王芳 田 豐
一、引言
民俗學家蕭放認為:“傳統是動態的,它本身也在不停地發展變化,優良的節俗傳統與現代社會并不沖突,相反它對現實生活有著積極的提示和輔助作用。”[1]對于今天的人們而言,傳統正在逐漸淡出日常生活。傳統節日往往只是抽象的時間,而非具體的生活,這不僅不利于保護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也無法發揮出節日對人們現實生活的重要作用。
本文試圖從人類學儀式理論出發,以杭州中秋節傳統節日民俗休閑生活為研究對象,借助儀式理論和史料梳理,對古代杭州中秋節生活進行審視,借助儀式理論“分離-閾限-融合”三階段,分析古代杭州中秋節休閑活動及其特點,并在此基礎上思考傳統節日文化的復興和節日休閑的發展問題。
二、從儀式到休閑
(一)理論回顧
人類學儀式理論經歷了20世紀的發展,從宗教領域進入到世俗領域。維克多·特納在前人范·蓋內普的基礎上,提出了“閾限前-閾限-閾限后”的儀式劃分階段。而后,納爾遜·格雷本從儀式性質、儀式結構與閾限體驗等各方面對儀式與旅游做出比對,進而得出“旅游是一種特殊儀式”的論斷。[2]由此,人類學儀式理論在旅游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近年來,國內不少學者也逐漸對儀式理論的應用開展了相應的研究,王榮、滕星(2016)研究了儀式理論對民族教育的啟示[3];李慧(2020)側重于考察儀式理論在旅游營銷中的應用[4];馮一鳴、張立波、周玲強等(2021)則在旅游儀式的基礎上,將其運用于文化產業體驗模式的研究[5]。這些研究一方面說明了儀式理論在旅游及相關產業當中有著極強的應用性;另一方面相關的研究仍屬于少數,因此,關于儀式理論的應用還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具體應用
休閑學者潘立勇先生認為,休閑產業是以“人的發展與實現”為明確目的的。[6]與休閑產業的目的類似,人類學所關注的主題也正與休閑產業相契合。在中國傳統節日休閑的研究中引入人類學儀式理論,正是因為人類學儀式理論對于休閑研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美國休閑學者杰弗瑞·戈比曾言:“在休閑和宗教之間存在的種種聯系之中,最重要的一個是二者都源于慶典。宗教信仰對宇宙萬物和人在其中的存在產生一種贊美的情感,而慶典也正是源于更為正規的宗教儀式。”[7]178-179而多數中國傳統節日的起源和相關的慶祝儀式都與早期社會的原始宗教崇拜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如上巳節的吞卵習俗、中秋節的拜月習俗等。因此,將中國傳統節日休閑發展置于儀式理論視角下,能夠讓休閑回歸到最原始的情感產生場域內,明晰傳統節日休閑在不同社會發生的內在邏輯,從而把握深埋在休閑活動之下的人們真實的休閑感。“當且只有當我們心懷感贊之時,休閑感才會出現。”(杰弗瑞·戈比語)而借助儀式理論,能夠幫助我們找到傳統節日中那些使人們心懷感贊的儀式,并在此基礎上將這些儀式通過休閑的方式融入現代社會,并借此保護傳統節日。
三、古代杭州中秋節休閑發展狀況
(一)發展歷史
古代杭州的中秋習俗主要在南宋時確立,而從南宋杭州百姓的市民生活中也能一窺古代中秋休閑發展的狀況。宋時中秋節已經成為民俗節日,中秋放假一天。因而在時間上,給休閑活動的形成提供了閑暇時間。從文獻記載來看,當時的主要活動有以下幾項:賞月、拜月、觀潮、放燈、歇眼。
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時,又謂之“夕”。此際金風薦爽,玉露生涼,丹桂香飄,銀蟾光滿,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臨軒玩月,或開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歡。至如鋪席之家,亦登小小月臺,安排家宴,團子女,以酬佳節。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強迎歡,不肯虛度。此夜天街賣買,直到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晚不絕。蓋金吾不禁故也。[8]
從吳自牧的描寫中,能夠很明顯地看出賞月、拜月習俗的休閑意味。拜月習俗體現出原始社會中人們對于月亮崇拜的延續,不論貧富家庭,都通過拜月、賞月表達對親人的思念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因南宋時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市民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賞月、拜月儀式中蘊含的休閑因素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步顯示出來。
觀潮與放燈兩項習俗同樣是南宋臨安中秋節的重要習俗,盡管錢塘江大潮在農歷八月十八時最為壯觀,但其時間與中秋臨近,且中秋之際潮水已蔚為大觀,因而觀潮也成為杭州人中秋節的重要習俗之一。而觀潮活動中出現的“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景象,說明南宋觀潮習俗的休閑意味已經萌芽。放燈習俗與觀潮習俗同屬祭祀習俗,周密《武林舊事·中秋》中記載:“此夕浙江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滿水面,爛如繁星,有足觀者。或謂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觀美也。[9]”周密在此處提到“江神所喜”,表明放燈習俗本是為祭祀江神,人們通過點亮羊皮小水燈,迎接潮神的生日并祈求來年風調雨順。爛如繁星的江燈引來無數行人駐足觀賞,儀式本身所具有的美感和絢爛也成為其所具有的休閑意味。
元代杭州中秋習俗基本承襲南宋,沒有巨大的變化。明代杭州中秋節的主要習俗也大都承自南宋,而贈送月餅的習俗雖然在宋代史料中未出現直接記錄,但《夢粱錄》和《武林舊事》中均已提及月餅,結合宋時賞月、拜月的習俗,明代贈送月餅的習俗也應承自南宋。明代中秋習俗最大的變化是出現了明顯的休閑傾向,借看潮為名隨意酣樂,不僅反映出明代中期杭州市民生活的繁榮,更說明時人對傳統中秋節習俗的態度從宗教祭祀向世俗休閑的需求轉變。
清代杭州中秋節習俗的演變主要是由于清軍入關后帶來的滿漢文化交融,據成書于同治年間的《杭俗遺風》記載,清代杭州中秋習俗主要有湖山賞桂、中秋斗香及江干觀潮。賞桂盡管未在前代史料中明確指出,但《夢粱錄》《武林舊事》等書中描繪中秋風情時,都有提及桂花。中秋斗香則是明清時期衍生出的新習俗,中秋燒斗香的習俗約形成于明清時期,是舊時祭祀習俗,又以清代為盛。斗香的制作方法是:將許多細香扎成圓柱形作為底盤,在扎幾個較小的圓柱一層層摞上去,整體上呈塔形,所以又叫塔香。[10]伴隨燒斗香活動一起開展的唱南詞等,則反映出了清代杭州祭月、拜月習俗中衍生出的新的休閑方式。
(二)中秋節休閑活動的儀式分析
通過梳理南宋至明清杭州中秋節習俗的歷史流變,筆者發現猶以明清之后,世俗生活相比于前代更加豐富,功利性的祭拜、祈求與世俗的情感、愿望構成普通民眾中秋節習俗的主要形態,中秋節成為民眾時間生活的重要節點。也正是因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市民生活逐漸興起,傳統節日中的休閑傾向也越來越明顯。如果說南宋時期中秋節習俗中祭祀目的與休閑目的并存,那么明清兩代杭州中秋節習俗則主要以休閑目的為主。依據人類學儀式理論的模式,即“分離-閾限-融合”三個階段,對應到傳統節日活動中則分別指節日準備、節日活動、回歸日常三個階段。
1.分離:脫離日常生活,進行節日準備。從南宋到明清時期,古代杭州中秋節的民俗休閑活動都與儀式有著緊密的聯系。而進入儀式的第一個環節就是脫離日常生活。傳統農耕社會生活不斷重復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節奏,即使是城市中的人們也需要為生計忙碌。因此,人們需要從日常生活中脫離出來,進入儀式過程才能使休閑成為可能。由于南宋臨安中秋節準備活動的文獻較少,而南宋習俗大都承自北宋,故此處借鑒北宋開封中秋節的描述作為參考。《東京夢華錄》中記載:“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彩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11]“望子”即酒家的酒簾,說明在中秋節前人們已經開始進入到儀式的閾限當中,通過這些準備活動,人們開始從日常的勞動生活中抽離出來,同時也感受著周圍生活環境的改變,逐漸進入節日的閾限中。
2.閾限:反結構的互動儀式。閾限是通過儀式的核心,是人們脫離舊境地、進入新境地之間的模糊過渡階段。該階段發生大量反結構互動儀式。[12]以賞月、拜月為例,依據《夢粱錄》的記載,不難發現,不論是王孫公子、富家巨室,還是鋪席之家、貧窶之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以酬佳節,不肯虛度”。而由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所產生的原有社會結構,也在這一儀式過程中得到了反轉:王孫公子與鋪席之家本屬于對立的社會階級,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而共同的儀式過程使得崇拜情感進入社會的中心,短暫地模糊了原有的社會階級,在儀式面前體現出了一致性、平等性的特征,從而使得儀式中的所有人進入到交融的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下,人們能夠最大限度排除外在壓力,獲得放松的心情,進而達到和世界處在最和諧狀態的方式,接近閑暇真正的核心。[13]
3.融合:回歸日常生活。儀式的融合階段是指人們離開儀式閾限,融入新的自我并回歸日常生活的階段。傳統節日的時間設置所依據的正是傳統社會的計時系統,而這套計時系統在根本上是契合傳統農業生產的,伴隨著農業等生產活動周期性間歇的到來,休閑娛樂的時間也就穿插其中。農業生產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單調和乏味的,而城市中的商人、市民等也在為了各自的生計所奔忙,同時需要面對政府各類捐稅帶來的生活壓力。傳統節日活動使得人們獲得了一段時間的休閑,是平日單調生活、辛苦勞作的調節器,也是平日傳統禮教束縛下人們被壓抑心理的調節器。[14]135-139人們從節日的歡愉中獲得了極大的放松,轉而重新投入到日常生活中,開始新的生產周期。
通過儀式分析,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南宋時期杭州中秋節活動所帶來的休閑意味。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繁榮,市民生活的富裕也導致了社會消費主義的傾向,造成休閑失范,這在中秋斗香習俗中有具體表現。《杭俗遺風》中提及:“斗香近亦通行,然不如前之鋪張揚厲,無非循名而已。究其實,亦無謂之舉動。然在承平之世,富家大戶,當然有此景象也。”《杭俗遺風》成書于同治年間,可見在同治以前,燒斗香曾成為富家大戶攀比的手段。斗富攀比強化了他們作為上層階級的經濟實力,使得社會分層的便捷進一步明晰,不利于儀式閾限的形成,更無法達到交融的狀態。
四、啟示與建議
中國傳統節日是一座文化寶庫,在今天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挖掘傳統節日,開發傳統節日文化資源對未來休閑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通過儀式理論透視古代杭州中秋節的休閑狀況,也給未來開發傳統節日資源以啟示。
(一)提升民眾的自發性和參與度
在古代社會中,傳統節日都與原始的信仰崇拜有關。信仰與崇拜的產生并不是來自對象對人們的強迫,而是來自人們內心最真實的情感流露。同時,作為傳統社會中少有的全民性活動,不同階級、階層和等級的人,不同職業、性別、民族、地域的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參加這類活動。[14]123-129因此,這些節日在本質上都是自發性的,也正是由于這種自發性的存在,節日的儀式才能夠形成和進行,人們才能夠真正參與到節日儀式中。
針對現代社會人們物質生活逐漸富足,而無法體會傳統節日中的原始情感。首先,應當加強宣傳教育工作,從認知層面入手,普及傳統節日及相關知識,做好宣傳工作,讓民眾了解節日文化,激發他們的文化認同。其次,可嘗試以社區或鄉村為單位組織傳統節日民俗活動,依靠當地的鄉賢、文化工作者以及社區工作者,調動人們的自發性,讓節日回歸老百姓的生活。
(二)避免過度市場化和消費化
從杭州清代斗香的案例中能夠看出,斗富攀比不利于儀式閾限的形成。究其根本,儀式需要體現一致性、平等性的特征,而斗富行為只能夠強化原有的社會結構,進一步突出社會矛盾,這在本質上與儀式是對立的。而過度市場化、消費化及市場失靈等情況,會加劇社會中的階層分化,同樣無法形成儀式的閾限。
因此,在開發傳統節日資源時,需要政府及有關部門介入監管,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管理和規范。過度的消費化會使休閑活動偏離休閑的中心,反而加劇了人們的心理壓力。而對于一些地方性節日儀式性活動的參與,盡量采取免費或象征性征收門票的方式,讓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和體驗儀式過程,在其中獲得休閑感,而不是讓這些活動成為上層社會或是富家子弟的專利,這在本質上也不符合儀式所提倡的價值觀。除此之外,對于現代社會中的一些網紅消費模式也要采取謹慎的態度,傳統節日是周期性的活動,只有注重提升節日活動的品質才能從根本上吸引民眾參加,使儀式的周期性得以延續。
(三)對傳統節日休閑活動進行創新
文化在本質上是變遷的,儀式作為一種文化符號,隨著人類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其作為符號的象征性意義與內涵也應當被賦予新意。而文化也只有在與新時代磨合的過程中不斷進行創新,才能真正獲得強大的生命力。從杭州中秋節的發展歷史中也能夠看到,在不同的時代會融入不同的時代內涵。
要實現對儀式的創新,以儀式作為參考標準是合適的:清代的“中秋斗香”不利于儀式閾限的形成而逐漸消失;明代雖無水軍閱兵,但觀潮之風更盛于南宋。因此,在傳統節日創新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對傳統節日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明晰傳統節日中儀式產生的機制和時代條件,主動傳承傳統節日中符合當代社會生活的休閑活動;另一方面要充分把握現代文化特點,立足人們的文化需求,對儀式的過程、禮儀等進行合適的調整,讓這些儀式更貼近現代人們的生活。
五、結語
杭州作為中國七大古都之一,也被譽為“東方休閑之都”,這是杭州發展文化休閑的現實基礎。將杭州地方傳統文化融入休閑當中,不僅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更能夠提升杭州休閑活動的文化內涵。而借助人類學的儀式理論對杭州傳統中秋節休閑活動進行分析,能夠厘清傳統節日休閑運作的邏輯,對于今天重新挖掘傳統節日文化,開展傳統節日休閑開發具有重要意義。
杰弗瑞·戈比曾提及“暢”的概念,在達到“暢”的體驗時,人們注意力高度集中,沒有心思注意與此無關的事,也不考慮別的問題。自我意識消失,甚至意識不到時間的存在。[7]178-179通過儀式理論的考察,我們就更能理解人們在休閑過程中如何達到“暢”的體驗。在今天這個新的發展起點上,作為“東方休閑之都”的杭州在未來發展休閑產業的過程中,也應該將“暢”作為核心目標。